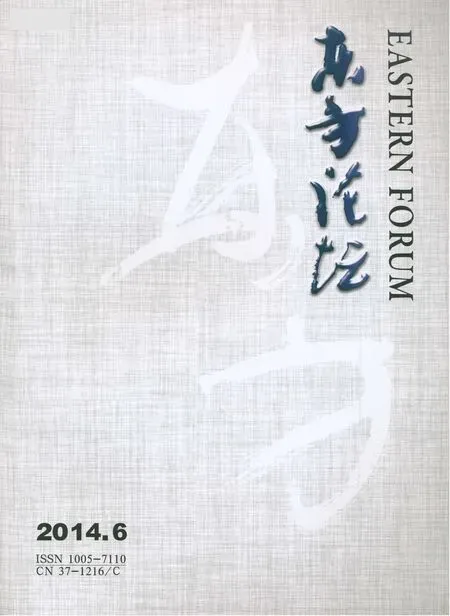論莊子“逍遙游”的自然美學觀
王 凱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論莊子“逍遙游”的自然美學觀
王 凱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天地有大美,因為它含著道的樸素;自然有大情,因為它涌動著永恒的生命之流。“物我為一”肯定了人與大自然的同質同源,“以物觀物”主張以審美的目光觀看萬物。只有齊物,才能逍遙,“物化”之際,人與物交感互動,渾然一體。體現在心物關系上,是物的自然作用于心靈的自然,碰撞的結晶則是樸素、純粹的美的情感的生成。莊子的心物觀、物化觀及其“逍遙游”的自然美學思想,深刻啟迪和直接催發了中國古典美學許多重要的范疇。
以物觀物;順物自然;心與物游
一、“以物觀物”與“物感”
“以物觀物”是莊子的觀物態度,也是審美的境界,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中國美學的審美方式和創作方式。如: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贈秀才入軍十四》)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1](P101)
在此,作者完全溶入自然之中,達到一種物我兩忘的高度自由的創作狀態。這種創作和情感表現方式是以自然本身生成的方式創作作品,此作品必須是帶有自然性,以自然本身顯現的方式顯現自然,而不是按作者的主觀意愿去表現自然。這種方法為中國歷代文人所推崇。自然是生命的律動和涌現,藝術家的使命就是把這生命律動的氣韻復制下來,以作品的形式表達出來。
自然山水的律動和涌現本身便是天機的泄露,詩人不必苦思冥想,應順著自然山水的自身顯現,摘取其中的精彩片斷。自然的生成本身自成其道,自成其理。“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大自然本來就是如此,眼前的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謝靈運下面的這首詩涉及到了這一問題: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俯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豐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嘆,賞廢理誰通?(《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2](P198)
在這首詩中,初篁的“苞”,新蒲的“含”,海歐的“戲”,天雞的“弄”,都形象而鮮活地再現了大自然的盎然生機。當問到“解作竟何感”,回答是“生長皆豐容”。大自然的活力在于自身的生命運動,沒有生命的生長,就沒有宇宙的美麗與和諧。以此態度觀物,會使人“撫化心無厭”,因為在此情境下,心靈的律動與物的律動已處于生命節奏的共振之中。
這里我們不禁聯想到公案的禪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春來草自青。”這同樣是道出了物各依自性生成生長,萬物都以不同的外在方式演繹著相同的、內在的自然生命的主題。冬去春來,潮起潮落,這是自然的本性,即是天機亦是道。有了這樣的體悟,我們便可在眼前的“綠籜”“紫茸”里,感受到自然涌現的生命氣韻,領略到宇宙間生生不息的力量與循環。
鐘嶸認為,詩貴在“直尋”(《詩品》)。所謂“直尋”就是講究觸景生情的直接性和連續性,不要分開和中斷,要把“即目”“所見”的景色直接地呈現出來。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凈化心靈,虛以待物,溶入自然的律動之中。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到的“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方”,“圣賢映于絕對,萬趣融其神思”,正是藝術創作時的自然心態。唐代司空圖的《詩品》中有“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為期”的說法,表達了同樣的觀物態度及創作方法。在中國古典藝術實踐中,有許多優秀的作品體現了這一創作原則,如王維的詩: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這是一幅寧靜而和諧的春景畫面。當朦朧的夜幕緩緩降臨,桂花輕輕地飄落,月亮悄悄地鉆出,清脆的鳥嗚伴隨著花影月光,向四周蕩溢漫延開來。大自然散發著最原始的生命氣息,不忍心對它有一點點的驚動。詩人仿佛是在同大自然一同呼吸。春山一片寧靜和諧,神秘動人,哪里還需要詩人來議論發揮;春景如此含情脈脈,溫柔似水,哪里還需要詩人去投射移情。在生命如此充盈的環境中,詩人的使命就是原樣地摘取其中的一幅畫面,凝固一個永恒的瞬間,神韻自然孕藏于其中。韋應物的詩《池上》就是這樣一個絕妙的定格:
郡中臥病久,池上一來賒。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流。
人與自然天地以氣相通,人的生命是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個部分,因而人可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也能夠讓人的生命情感產生波動。中國古典美學的“物感”說,所強調的正是物對人的自然情感的觸動。陸機云:
貯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澡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3](P66)
這段文字是講創作的準備及創作動機的產生。創作動機的萌發,主要是來自于“物感”。四時歲月的更替引發人的傷感,春夏秋冬的景色激起人的不同情緒。“嘆”,是情感的波動;“思”,是思想的萌發,悲喜之中,感物生情,由此產生創作的欲望和沖動。這就說明,創作動機的產生過程應該是隨意而自然的。劉勰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蕙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物色”“物容”都是指自然物的聲色。自然物色的變化就是物的自然顯現,一葉一蟲都含著生命的情感,不可能不感動人的心靈。而人的心靈感動又不可能不反映到詩文中來。因此,心情是隨物而變化,言辭是依情而觸發,這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對于“物感”,鐘榮是這樣描述的: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3](P106-107)
與鐘嶸同時代的蕭子顯對“物感”也有精彩議論:
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5](P512)
春風春鳥,秋月秋蟬,早雁初鶯,開花落葉……大自然總是充滿著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在生命的萌動中,不可能不鼓動人的情思,搖蕩人的性情。人應該以自然的心態去迎接萬物。心靈一旦排除了各種束縛,進入到虛靜的狀態,情感之河就會自由地流淌,并且隨著物動而起伏。“有斯來應”非常貼切地說明了情感發生的自然性,這在《淮南子》中被稱作“與物接”。
中國美學的“物感”說,強調的是物對人的情感的觸發,這同西方那種主張以人的情感投射于物的“移情”說有著明顯的不同。“物感”說是體驗論而非認識論,它不同于西方那種建立在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基礎上的機械激反映論,把人完全視為受動的一方。“物感”本質上是“交感”,它不只是審美主體單方面的感覺活動,還包括審美對象方面的反應,是人與物的相互融合、交感互動的過程。片面強調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就不可能產生交感互動。在交感互動的過程中,并無主客之分,也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區別,而是同步進行的相互感應。正基于此,中國古典美學更多的是使用“會”“應”“交”“觸”“契”“遇”“合”等概念,來表達交感和諧的思想。如“會心處不必在遠”。[1](P101)
總之,“物感”說強調物的“有情有信”,主張人要“虛以待物”,目的是排除人的主宰地位,反對人強制于物,并不是否定人的心理作用。相反,人的心靈的凈化,各種非自然情感的排除,恰恰是人與物相互感應得以發生的前提。心靈是水,靜則明,明則虛,虛才能“勝物而不傷”。在這點上儒家也有相同的體認,如朱熹認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詩集傳序》);孔穎達認為“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物感情遷”(《毛詩正義》)。這都是強調清靜自然的心靈狀態在審美過程中的重要性。
二、“順物自然”與“感興”
如果說“物感”強調的是審美感受的一般性原則,那么“感興”則是這一原則在藝術創作中的具體運用。“感興”與“物感”一樣,也是中國古典美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的含義比較復雜,既有莊子“順物自然”思想的直接影響,也帶有儒家思想的某些烙印。
如果說審美發生的心理前提是“虛靜”,那么審美發端的心理活動就是“感興”。“感興”中的“感”一般指感覺、感受的意思,但不只是人的單方面的感覺活動,也包括物的方面的反應,是相互的交感互動,有時也稱為“應感”“感會”。陸機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3](P70)劉勰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4](P184)遍照金剛認為:“感興勢者,人心至感,必有應說,物色萬象,爽然有如感會。”[6](P126)強調物我雙方的“交感”“應感”“感會”,是中國古典美學審美感知論的重要特點。也正是因為它是物我雙方的交感互動,所以它不是認知活動,而是體驗活動,屬于審美體驗論。
“興”在中國古典美學中含義很多。從美感論的角度講,“興”指的是人的情感被激發的狀態。唐李善說:“興會,情所會也。”(《文選注》)“興”的意思是“起”。《說文》《爾雅》均以“起”訓“興”。孔穎達云:“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毛詩正義》)劉勰云:“興者,起也。”(《文心雕龍·比興》)這里的“興”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特定的感物情態、情趣。“興”強調的是情之“起”,而情之“起”又與“物動”相關,只有“物動”才能“起情”。
“興”有時也與“比興”連用,有隱喻和寄托之意。劉勰云:“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4](P208)比是就心積的憤怨而斥以言詞,興則是圍繞譬喻來寄托告語。
從以上可看出,“興”與“物感”聯系甚密,從審美心理發生上講,兩者都是突出由物到情,由外而內。鐘嶸所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3](P106)其中的“搖蕩性情”就是“興”。唐賈島說:“興者,情也。謂外感于物,內動于情,情不可遏,故曰興。”[7](P36)宋楊萬里認為:“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庚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于作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感隨焉,我何與哉!天也,斯謂之興。”[8](P2841)此處講的“天”特指自然無為,而非人為之意。“興”之所以是“天”,是因為消除了詩人的先入之見,是詩來尋找我而不是我去尋詩。“興”并非一開始就存在,詩人一開始無意于作詩。處在虛以待物的虛靜狀態。“興”是先有外物的觸動,然后起情,這才作詩,這說明審美情感是后發生的,是一個順物自然的過程。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物感”與“興”的相通性。
由于“物感”與“興”的相通,中國古典美學常常把“感”與“興”合成為一個詞,稱之為“感興”。與此相關聯,又創造出了“興會”的概念。“興會”更直接的表達出審美發生時的心理狀態,鮮明的展示出中國美學的特色,而西方美學則很難找到如此貼近的詞語來表達相同的意思。儒家以及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文論家,往往把“興”與一定的道德和倫理內容相關聯,即比德。“比德”是強調把自然山水與人的道德倫理情景作類比。而本文所探討的“興”主要突出的是人由物所引發的自然情感,是純粹的自然之情的運動過程。莊子的美學思想是以“物感”為基礎的自然美學觀念,而不同于儒家政治化、倫理化的美學思想。具體的說,受莊子自然美學思想影響的“興”具有如下突出的特點:
第一,“興”體現了藝術創作的自然性。“興”的自然性來自于人和物的自然本性,而且人和物的自然性決定了雙方可以直達暢通,相互交融,渾為一體。因此,只有順物自然才能物動起情,才能出現“感興”。清葉燮云:“當其有所觸而興趣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9](P567)王夫之云:“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勃然興矣”[10](P383-384);“興在有意無意之間……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為珀芥也”(《詩繹》)。這些都非常形象的說出了“興”的自然性。
第二,“興”體現了藝術創作的直覺性。“興”以及相關聯的“感興”“興會”,含有直覺和靈感的意味,具有非理性的特征,經常是在瞬間閃現出來的。直覺和靈感是突發性的,是一種偶然性的自然狀態。用日本今道友信的話說,“興”是一種情感的“興騰”,這個“興騰”是垂直的,是“垂直地興騰起來”“垂直地面向超越者”,因而可以直觀事物的本性。這正是“感興”的直覺靈感狀態,這在藝術創作中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登高遠眺,物感情發,對天地萬物的永恒和個體的渺小產生強烈的感觸,在此超越中,靈感突然到來,詩句油然而生,如從天降,由此創作出了動人心弦的千古絕唱。
第三,“興”體現了藝術創作的隱喻性。“興”是一種隱喻的形象。劉勰說“比顯而興隱”(《文心雕龍·比興》),“隱”即“復義”“義生文外”。鐘嶸是用“文已盡而意有余”來界定“興”。隱喻性是詩歌發揮藝術感染力的重要因素。在直接描述的物象之外,寄寓著更深層的意旨,這不僅使作品形象生動,而且蘊藉著無窮的深意,也正是唐宋以后詩人們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韻外之致”所采取的手段。嚴羽把“興”與“趣”連結起來,大量使用“興趣”的概念。他講的“興趣”也帶有隱喻的意味,如:“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詩辨》)作品要有“興趣”,就不能直接露出所要表達的情意和動機,即所謂的“情在詞外”。此外,中國美學所講的“味”“妙”等也都具有與“興”相類似的隱喻味道,這些概念都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都是對藝術和審美意境的表述。
三、“心與物游”與“神思”
任何藝術作品都是某種象征,藝術創作離不開想象。莊子的觀物方式是透視、洞見,亦即想象,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見獨”“明”。藝術家的功夫就在于通過想象抵達對象的本質。
《莊子》書中既沒有出現“神思”也沒有出現“想象”,但是卻大量的使用了“神”的概念。莊子使用“神”一詞,大多用于三層意思:其一是指思想、精神,其二是形容神奇、玄妙,其三是用于神人、神話。值得注意的是,莊子有“其神凝”(《逍遙游》)、“以神遇”(《養生主》)、“凝于神”(《達生》)的表達。這已經非常接近“神思”和“想象”的意思。
“神思”一詞,華核《乞赦樓玄疏》中有“宜得閑靜,以展神思”的說法;曹植《寶刀賦》中有“攄神思而造象”的說法。但將其“神思”一詞的內涵加以確定,集中展開論述,使之成為一個美學范疇的,應該是劉勰。劉勰所講的“神思”,明顯的受到了莊子“神凝”“神遇”“凝于神”概念及其思想的啟發。至于什么是“神思”,劉勰說: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4](P130)
根據劉勰的這段論述,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握“神思”的主要特征。所謂“神思”就是指具有時空跳躍性的藝術想象活動。
想象的發生需要以虛靜作為前提條件。劉勰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4](P131)這里劉勰提出了想象得以產生的五個因素,即:“虛靜”“積學”“酌理”“研閱”“訓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具備虛靜的心態。劉勰這里講的“虛靜”是來源于莊子的“虛靜”思想,主要是側重于心理學方面,指的是虛弱的、松馳的、愉快的、簡單的情緒狀態。此種心態能使精神專注守神,有利于進入“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的暢神境界。心靈的虛空為的是實現心物的交感,只有在心物融合中才能開啟想象的大門,才能使神思源源不斷而來。虛靜才能感物,因感物而情發,由情發而生想象,這是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
想象是人所具有的精神創造力的體現,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劉勰認為: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于巧義,庸事或萌于新意。視布如麻,雖云未貴,抒軸獻功,煥然乃珍。至于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后闡其妙,至變而后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作文章時,想象中的情感變化奇詭而復雜,構思的過程中,內容和方法、文體和風格也隨著想象千變萬化。想象可以使拙劣的言辭有時包含巧妙的親義,也可以使平庸的事情有時會萌生嶄新的意思。“視布如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布和麻的質料是一樣的,但經過紡織染色及藝術處理,布煥然生輝,就顯得珍貴了。“杼軸”使麻成為布,起了關鍵的作用。劉勰這里是借“杼軸”形容想象的作用,說明想象在藝術作品創作過程中的提煉和創造功能。至于想象的纖微意義和委曲妙趣,有著神奇的藝術魅力,是難以言語的。
想象不受任何時空的限制,可以大幅度地跳躍,對不在眼前的事物想象出它的具體形象。《莊子》一書本身就是想象的最典型范例,其中的想象可謂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之一瞬”。
在《逍遙游》中,莊子運用奇特的想象,豐富的幻象,巧妙的構思,創造了一個悠閑自得、無拘無束、在天地間自由往來的鯤鵬的形象。莊子暢想縱思,在哲學的沉思中伴隨著美的意象,每一具體形象都有其光彩。鯤鵬、斥鷃、鄉官、國君、列子、神人……群象飛動,生動鮮活,令人目不暇接,可謂思緒超曠,神游天外。
藐姑射山的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11](P21)這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萬物不能傷害、“無待”“無己”的神人形象。“其言猶河漢而無極”,想象奇特,令人心交意攀。
在《胠篋》中,莊子描繪了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轅氏、赫胥氏、尊以氏、視融氏、優羲氏、神農氏……”[11](P262)他把遠古切換到眼前,并加以非常具體的描繪,創造成一個可視、可聞、可觸、可游,活靈活現,維肖維妙,令人感到身臨其中的極樂社會。如此大幅度跨躍時空的描述,如不運用想象是無法完成的。
“有國于蝸左角者曰觸低,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11](P677)在一個小蝸牛的兩角上各住著一個國家,兩國進行戰爭,伏尸數萬;有一方失敗,另一方就得用十五日才能從另一國返回本國。這簡短的寓言故事雖文字不多,內容簡單,卻是整個戰國時代群雄征戰的縮影。把如此廣闊的社會背景及諸侯混戰的復雜局勢,縮小在一個小小的蝸牛上,反映出了莊子超絕的想象力和凝練的藝術概括能力。
類似的寓言還有許多。如“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11](P228)其構思奇特,創意新奇,想象大膽。“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以蔌。”[11](P135)誰見過能籠罩上千輛車和四千匹馬的大樹?這漫無邊際的夸張,卻給人以驚奇而又難忘的印象。“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本文極盡夸張想象,構思宏闊奇特。魚的聲勢驚人,用五十條大牛作魚餌,那么魚該有多大?任公子的力量又有多大?可以任憑你盡情地去想象。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堅持主客分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恪守邏輯與理性的思維至上性的哲學信仰,對充滿人類智慧的想象抱有輕視的態度和帶有理解上的誤區。他們往往依據想象所呈現出的非形式邏輯非知識經驗的特征,把想象界定為非認識論的較低級的概念,并將其置于高級形式的思維范疇之下,認為它無法接近真理。在黑格爾那里,僅僅靠想象是不能用來把握絕對精神或認識理念的。
自康德起,對想象的認識有了新的轉機。他認為想象是把現實雖不存在的東西,卻在直觀中將其表現出來的能力。在康德看來,想象力是一種心理綜合能力,是藝術創造的能力。具體的說,想象力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創造之力,其二是人格化之力,其三是產生純粹感覺形象之力。所謂的創造力就是產生新對象的能力,這具有生產性、自發性,他可以把不在場的東西讓其在場。而不在場的東西在場,意味著它是一種潛在的、非現實的在場,這個潛在的、非現實的在場就是想象。康德對想象的重新闡釋,提高了想象的地位,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舊形而上學思想的束縛。
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不同,莊子是把想象提升為一種認識形式和審美形式,而且是人類精神的最高的認識形式和審美形式。通過想象這種“心游”“神游”的絕對自由的思維和審美方式,能夠抵達物的本質,并獲得整體的把握。不僅如此,通過體道、悟道的想象活動,還可以實現對人和大自然存在意義的提升和價值的領悟,探索出宇宙生命的終極意義,從而成為生命哲學和自然哲學最根本的思維方式,也是藝術和審美最重要的體驗方式。通過想象可以進入絕對自由的虛無的道境,這正是對真理的最深認識,也是對美的最高體驗。由此可見,莊子的想象不同于感性思維,也不同于理性思維,而是一種詩性思維,是帶有直覺體驗色彩的智慧活動。
當代的現象學,對想象給予了全新的解釋。胡塞爾把想象視為把握意向性的重要途徑,“體驗”“意向性體驗”“本質直觀”“先驗還原”等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涉及到了想象的內涵。胡塞爾指出:“體驗本身的本質不僅是意味著體驗是意識,而且是什么的意識。并在某種確定的或不確定的意義上是意識。因此體驗也潛在地存在于非實顯的意識本質中,非實顯的意識可通過上述變化轉變為某種實顯的我思思維,我們把這種變樣形容為‘注意的目光對先前未被注意的東西的轉向’。”[12](P106)在胡氏看來,體驗不僅僅是意識,而且是對某物的意識,呈現出某種意向性,能使未被注意的東西進入“注意的目光”中,使不在場的東西在自我意識的“現象”中顯現出來,因此體驗(想象)是超越于理性認識的。
海德格爾的“言說”即是“思”,在一定意義上是同想象相關聯的。海德格爾認為“思”的功能在于“把某種東西展示出來讓人看;只因為如此,邏格斯才具有綜合的結構形式。”[13](P41)在海氏看來,“現象”一詞的意義就是自身顯示自身,邏格斯之為言說,就在于具有把某種東西顯現出來讓人看,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存在者的存在,亦即存在的去蔽和澄明,而通往去蔽和澄明的路徑就是“思”。海德格爾是把想象看作是構成存在者存在的前提。只有憑借想象,才能讓不在場的東西得以顯現、澄明,因此,想象意味著讓事物是其所是的發生。
一邊是幾千年前中國莊子詩意的想象,另一邊是現代西方思想家詩意的運思,雖然各自說著不同的話語,但彼此形成了對話。這說明人類的思想和智慧有著內在的一致性,盡管表達的方式不同,但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是相一致的。
莊子的“游”不僅是對物的想象,也是對心靈自身的想象。首先是心靈的凈化,通過凈化使心靈進入到一種純粹的自然狀態,然后才轉向物。也就是說,把人的心靈也設定為一個特殊的現象領域。可見,莊子的想象更為本己,是積極的心靈內省。在想象中,心靈進入到一個絕對自由的自然之境,在此境界中,真正地消除了主客之分,物我完全融為一體,這也是精神最虛無化的自然原始狀態。所以,莊子的想象是自然之想象,莊子的“逍遙游”是自然之游,是人之自然與物之自然相往來的神游。
[1] 張萬起,劉尚慈注.世說新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 謝靈運撰.顧邵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選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 姚思廉撰.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 王利器.文靜秘府論校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7] 曹溶輯,陶越刪.學海類編[M].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
[8] 楊萬里.楊萬里箋校[M].北京:中華書局,2007.
[9] 王夫之等撰.清詩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 王夫之.詩廣傳[M].長沙:岳麓書社,1996.
[11]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M].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1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責任編輯:潘文竹
On the Natural Aesthetic View Embodied in Zhuang Zi's Carefree Excursion
WANG Ka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Heaven and Earth have great beauty, for they contain the simplicity of the Tao; nature has great affection, for it has eternal impulse of life. "Everything and I are one" points to the same source of man and nature. "Observe things through things"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look at everything with an aesthetic ey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things is the effect of the naturalness of things upon the naturalness of soul.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ac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simple and pure emotions of beauty. The natural aesthetic thoughts of Zhuang Zi have enlightened and given rise to many key categor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aesthetics.
observe things through things; follow the Tao; the mind goes along with things
B83
A
1005-7110(2014)06-0110-06
2014-10-11
王凱(1957-),男,吉林延吉人,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哲學、文學和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