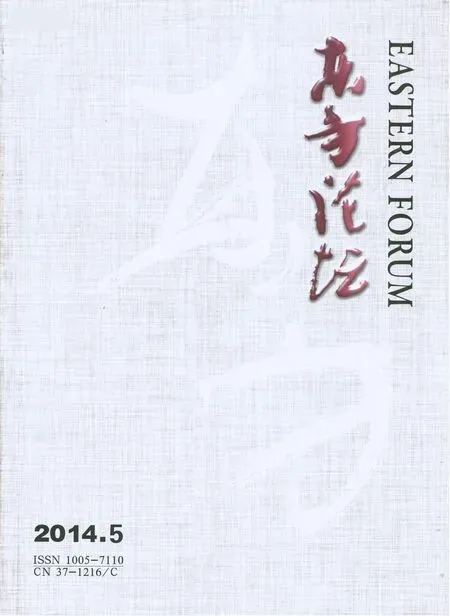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華夷之辨”及其近代轉型
韓 星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北京 100872)
華夷之辨又可以稱為夏夷之辯,主旨是就華夏族和周邊的夷族進行區別。“華”,與古字“花”通。許慎《說文解字》 釋為榮,清人段玉裁注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夏”的本義有二:一是地名,一是華美之義。禹受封為夏伯,根據孔穎達所注的《尚書》“顓頊以來,地為國號”,因此在禹子啟建立夏朝時,便沿用此“夏”號。“夏”,《說文解字》考其造形結構,認為是用繁筆大寫的“人”字,釋意為“中國人也”。段玉裁注曰:“以別于北方狄,東為貉,南方蠻,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夏引伸之意為大也。”《爾雅·釋詁》曰:“夏,大也。”《尚書》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尚書》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則為又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從上面可以看出,“夏”的意思是“大”或者“大國”的意思。
華夏對周邊的各個少數民族國家則以夷、狄、戎、蠻稱之。這些稱呼過去多有人認為是對這些少數民族的污蔑之詞,其實不盡然。“夷”,許慎的《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夷,平也,從大,從弓,東夷人也”,說明東方的民族是最早使用弓箭的部族。其實,“夷”在當時是還有指代東夷以外其他方位的少數民族,如北方的畎夷,《竹書紀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西方的昆夷,《詩·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南方的夷,《春秋公羊傳注疏》:“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統稱,非僅指東方之民族,如《尚書·大禹謨》:“無殆無荒,四夷來王。”《淮南子·原道訓》:“ (禹)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毛詩正義》:“幽王時,四夷交侵,中國皆叛。”這些“夷”均帶有“四”字,則“夷”者是四方非華夏族的統稱。可見,“夷”應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狄”字《爾雅·釋獸》解釋為有力的鹿,表示捕獵動物,是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特征。“戎”原意是指兵器,比喻少數民族是試圖說明他們生性勇猛,善于使用兵器。“蠻”字原本是指一種小鳥,在《山海經》中這樣說:“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云蠻。”在《詩經》中也作為一種小鳥名出現過。這說明當時中原華夏是依據人四方之人的實際生存狀況和生活特點來稱呼的,并沒有故意的貶低和污蔑。
當然,應該看到,華夷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禮記·王制》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華夷差別的認識:“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距,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這就從名稱(中國、夷、狄、戎、蠻),方位(五方),飲食,服飾,居住等方面指出中國與夷狄戎蠻的特征和區別。《左傳》襄公十四年,諸侯會于向,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摯幣不通,語言不達。”《淮南子·墜行訓》:“東方,其人兌行小頭,隆鼻大嘴鳶肩企行,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修行兌上,大口決齜,早壯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僂,修頸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獸而壽;中央四達,其人大面短頸,美須惡肥,惠圣而好治。”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夏”和“夷”在文化、語言、風俗、飲食、服飾,甚至是在形體方面,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
一、華夷之辨的形成、內容及實踐
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處理國家、民族關系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在華夏民族自覺和華夏文明危機情況下形成的。
華夷觀念的出現很早,林惠祥把中國歷史上的眾多民族概括為華夏、東夷、荊吳、百越、東胡、肅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瑤、羅緬、白種、黑種等16 系。[1](P9)其中,華夏族在史前即已經萌芽,早在上古時代,中華大地上就出現了大致可以按地域劃分的四大部族集群:由西而東的姜姓炎帝族、由北而南的姬姓黃帝族、由西而東的史前東夷族、由南而北的苗蠻族。它們從不同的方位向中原大河谷地和沃野平原匯集,逐鹿爭雄,經過血與火的多次洗禮,黃帝與炎帝這兩個最強有力的大部落結成了聯盟,最終不僅造成血緣部落聯盟發展為地域部落聯盟,蛻變而為國家,而且也促使不同民族部落之間發生融合,遂產生了古華夏族。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古華夏族以其占據中原的優越地理位置和先進的農耕文明,建立了夏朝,標志著我國開始進入古代民族的國家。至夏朝仍然存在著眾多的氏族部落。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部落包括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褒氏、費氏、杞氏、辛氏、冥氏等等。至商、周時期,許多經濟文化遠落后于“諸夏”民族的異族,還散布在商、周的疆域中,經春秋三百年的變遷,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部族逐步實現了華夏化,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形成了統一的華夏族。華夏族在與周邊不同部族的不斷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夏夷觀念。夏夷觀念的產生,是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的綜合產物。最早定居在中原地區的先民們依據適宜的地理條件,較早地進入了農耕文明。農耕文明的優越性在于,有較穩定的社會生活,有再生機制強勁的小農經濟與農業文化。雖然歷經世代變遷,經歷外患內憂,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農業文化也能世代傳承。中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農耕經濟所哺育的先進的農業文明,同中原周邊其他民族的游牧經濟及其游牧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此,生活在中原地區的先民們稱自己為華夏族,這種自稱自謂,無疑充盈著對本民族文化的贊美和難以言喻的文化自豪感,優越感。
三代的華夷之辨與當時的天下、國家觀念是相輔相成的,形成了一個同心圓層層遞推的模式,即王畿(國君所在地)、四方(諸侯國)、四海(夷狄),相應地構成了君天下、國諸侯、家大夫、四海夷狄的“天下為家”的差序格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這些成為維護這一文化秩序的基本原則。今人對三代夏夷問題又有新的認識,如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中認為,從地理上看,三代及近于三代前期,有著東、西二個系統,其演變的歷史憑藉地理而生,東西對峙。在夏之夷夏之爭,夷東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爭,商東而夏西。在周之建業,商奄東而周人西。這樣相爭相滅,便是中國的三代史。
春秋時期處于中國分裂狀態,見于《左傳》的大小國家有120 多個,而其時四周夷狄卻伺機強大,交侵華夏,所謂“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南北四方夷狄十分強大,中原諸國都受到威脅,甚至一些國家為其所滅。戰國時期中原形成七雄,紛紛向四周開疆拓土,置郡縣,筑長城。當時中原華夏族農耕區的最大威脅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史記·匈奴列傳》)。在這種情況下,中原華夏諸國不得不增強團結共同對付四周夷狄,于是有華夷之辨。
春秋戰國,華夷觀念得到儒家學說的改造、升華,特別是儒家始創人孔子的夏夷之辨觀念對當時和后世影響深遠。孔子明確地表示“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傳》),認為當時中原的一些國家能夠以西周禮樂制度治理社會,文明程度高,是屬于“諸夏”;而周邊各族各國則沒有禮樂制度,是屬于“夷狄”。孔子的嚴夏夷之別主要是文化之別而不是狹隘地以血統種族去區分。《論語·八佾篇》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朱熹《四書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這說明孔子對夷狄有君臣上下是持一種贊賞態度,因為這是禮樂文明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華夷之辨”并不排斥夷狄,他的七十二弟子中,子游、狄黑、左人郢、公孫龍、任不齊、秦商、秦祖、壤泗赤等皆為夷狄或來源于夷狄之國。孔子還強調夷狄與華夏文化是可以相交相容,相互轉化的。他曾經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意思是說如果在當今社會不能復興禮樂之道的話,他寧愿坐上木筏漂到海外去,那里雖然居住著落后的民族,但他們生活淳樸,也許會很自然地接受禮樂教化。《論語·子罕》又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說:“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由此可見,孔子是相信夷狄與華夏文化是可以相交相容的。夷狄可以被化,是夷狄可以進為華夏。相反,華夏僭亂,亦可以退為夷狄。華夏、夷狄是可變的。夷狄到了中原地區,習用了華夏文化習俗,他們就成了華夏族,而中原華夏族如果進入了邊遠地區,習用了夷狄的文化習俗,他們就成為了夷狄。杞國國君以夷禮去拜見諸夏的魯國,被貶為“夷”。后來杞國以周禮朝魯,則得稱為“諸夏”。又如驪戎雖是周天子的同姓,但由于不行周禮被稱為“諸戎”。楚、秦、吳越等都曾被稱為蠻夷,后來也因其禮義文明程度的提升,改被稱為諸夏。因此,是夷狄還是華夏不在于血統,而在于所習用的文化,就是說華夷之辯不是血統上的區別而是文化上的差異。孔子把禮樂作為區分華夷的標準,講究禮義德行的就是文明人,就是華夏之族;不遵循禮義德行的就是野蠻人,就是蠻夷戎狄之裔。這是把文化放在優先地位來比較評價民族差異的,后來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傾向。
后來,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中國圣王無種說”,認為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有志氣有才能,都可以統治中華成為圣王正統,他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這段話既描述了四夷文化的內漸過程,也表現了對古代四夷文化的認同,并指出如果夷獲得了夏文化就變成了夏,如果我們喪失了自己的文化也就變成了夷。但在戰國四周夷狄強大、對華夏構成巨大威脅的文化危機中,孟子不得不強調夷夏之大防,用十分強烈的民族文化優越感的口吻說道:“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要“以華變夷”,反對“以夷變華”,就是要用華夏的文化禮儀制度來改變四夷的文化禮儀制度,把四方之民納于華夏文化之下,化“夷”為“華”。“華夷之辨”就是在這種文化危機的形勢下不斷豐富深化。
儒家的華夷之辨,提倡夷狄亦可進為華夏這一個概念,使華夏文明對周圍少數民族產生了強烈吸引力、征服力和同化力,促進了這些民族對華夏文明的向往和仿效,從而增進了國內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同時,也使諸夏產生了一種文化的優越感,一種共享的文化認同,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向心力,凝聚起各地人民的歸屬感,為日后的大一統確立了最基本的思想。
概括起來,華夷之辨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地域之分。在地域上諸夏大體相當于今日之中原大地及其周邊地區,其他地方因方位之不同大體有東夷、南蠻、西狄、北戎的區分。這里有遠近不同和中心與周邊的分別,《禮記·曲禮》 篇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禮記·明堂位》篇也稱:“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夷”“蠻”“戎”“狄”分屬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而華夏則在中心地區。由此也形成中國人對“中”的重視、崇敬甚至崇拜。例如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早在殷代就有了“中國”意義之稱謂,即殷人已經有了五方、自己居中的概念,認為自己就是中國。
第二,文化或者文明的差異。諸夏文化或者文明程度高,四夷則文化相對落后,有的還處在野蠻狀態。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根本標準是道德仁義、禮儀文教。唐代人就說:“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2]這就是說,凡自我歸屬中國諸華夏族,能夠“親被王教”,也就是奉行中華文化傳統的,就可以成為中華成員,亦即成為華夏族。
第三,華夷之辨與人種、民族、血緣有關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所以,夏夷之辨不是種族主義,不是民族主義。華夷之辨與政治、外交、軍事有關系,但以文化為核心和主導,所以夏夷之辨不是權威主義,不是霸權主義。如果要說民族主義,則夏夷之辨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
第四,夷狄與華夏、夷與夏不是一個確定的界限,是可以相交相容,相互轉化,并隨著中國文明向周邊的延伸文明的范圍在不斷地擴大。在這種觀念背后,我們看到是儒家對自身傳統的認同與自信,以及天下大同這種高遠的政治理想。
總之,有以上可以看出,儒家對華夷之辨的貢獻就在于:在華夏中心主義和天下主義之間走中道。
華夷之辨在先秦的實踐。
在儒家對夏夷之辨的基礎上,從先秦政治家開始就付諸了實踐,“五服”制度就是一個例子。《國語·周語上》有詳細闡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這里不僅提出了“五服”的構想,還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禮記·王制》還提出對付夷狄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的策略,這顯然是基于對夏夷關系進一步的認識。
先秦華夷之辨的實踐主要有二:
第一,尊王攘夷。在四方夷狄十分強大,中原諸夏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一些諸侯國君主張諸夏團結在周王室的周圍,共同抵抗夷狄的沖擊,捍衛華夏文明。《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國從夷狄,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春秋左傳正義》齊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戎,禽獸也。”(《左傳·襄公四年》)諸夏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在和夷狄的交戰中得到強化,意識到諸夏國家之間應該不分彼此,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扶持,相親相愛。因此,孔子高度評價管仲佐齊桓公“尊王攘夷”,贊揚他:“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對夷狄在“中國不絕若線”之時,能夠攘除夷狄,挽救了中國,免使中國淪為夷狄,以之為王者之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第二,以華變夷。在確立華夏文明的主體性前提下,強調以發達的華夏文明改造落后的夷狄文化。這是符合文化發展基本規律的。華夏文明進步,夷狄文化落后,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所造成的客觀事實。在戰國四周夷狄強大,對華夏構成巨大威脅的文化危機中,孟子不得不強調夷夏之大防,用十分強烈的民族文化優越感的口吻說道:“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要“以華變夷”,反對“以夷變華”,就是要用華夏的文化禮儀制度來改變四夷的文化落后,把四方之民納于華夏文化之下,化“夷”為“華”,“協和萬邦”,這顯然帶有華夏中心主義的色彩。
二、秦漢以后華夷之辨的演變
秦漢以后,每當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遭遇危機之時,華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強調,甚至有圍繞華夷之辨發生的各種爭論。其主導思想是通過分辨當時華夏與周邊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狀況,防止華夏文明被滅亡,進一步確立華夏文明的主體性,這樣以華夏文明為主,兼收并蓄外來文化,使華夏文明在交流融會中不斷走向博大精深。此外,也有不同的其他傾向:文化保守的華夏中心主義和文化開放的天下主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北方少數民族的侵入,民族關系的復雜化,華夏文明面臨心得危機,華夷之辨也隨之尖銳了起來。這個時期佛道之間的夷夏之爭是中國傳統華夷之辨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是中國傳統的夷夏觀在三教關系上反映。在性質上它不是強調民族矛盾,而是強調文化矛盾。根據《弘明集》和《廣弘明集》的記載,佛道夷夏之爭集中在南朝宋、齊、梁三代,內容略有不同。《晉書·劉元海載記》談及孔憫、楊眺同晉武帝以及劉淵時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書·四夷列傳》里記晉武帝泰始年間,匈奴劉猛反,侍御史郭欽提出:“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人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西晉時期江統的《徙戎論》對東漢和曹魏時期造成的關中地區“戎漢雜處”的局面表示不滿和擔憂,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最好的辦法是“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但是,后來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對民族戰爭的慘痛經歷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則是胡漢融合對人們心理上的影響。內遷各族開始萌生消除民族隔閡的覺悟,表現出對中原傳統的強烈認同意識,并進行種種努力轉變種族觀念。他們從血統、地緣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當居中華正統的根據。例如,鮮卑拓跋氏自述為黃帝之裔,見載于《魏書·紀序》;鮮卑宇文氏自述為炎帝之裔,見載于《周書·帝紀》;鐵弗匈奴劉(赫連)勃勃,根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強調自己的夏王室血統而稱所建政權為夏等。他們還對傳統的夷夏觀念發表自己的新理解。《晉書·慕容毀載記》講前燕奠基人、鮮卑大單于慕容毀曾規勸高瞻:“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隋代大儒王通在其《中說·周公篇》中說:“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該篇還記載王通曾參與對符堅前秦王朝的辯論:“子曰:‘齊桓公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將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將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夭順命,安國濟民乎?……符堅何逆?三十余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顯然,這一時期人們的觀念因文化的相互認同而表現出幾乎一致的反應。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華夷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變化,所以到隋唐時期出現了“胡越一家”以及唐太宗對中華、夷狄的“愛之如一”,都是體現了當時民族融合的大趨勢。
唐太宗曾一再標榜自己“不猜忌異類”,對華、夷“愛之如一”,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朝提拔起用一大批蕃胡族人擔任軍事將領,有的甚至做到了高級將帥。在武將的提拔任用上,胡人甚至往往要優先于漢人。在文化生活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樂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進入了皇家宮廷;胡服胡食則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會所接受、喜好。這種社會現實,無疑對士人的思想觀念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對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也是一種新的考驗。
到了五胡亂華及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并沒有一個強勢的政權,是以各外族乘勢崛起,侵擾中原。然而這些外族雖然取得政治及軍事上的優勢,卻在文化上處于落后的位置。有些外族君主推行漢化,固然被華夏文化所吸收了;有些堅拒漢化的最終也難維持政權。由此可見,華夏文化這種向心力的厲害,令中國只會亡國,不會亡文化,免于如巴比倫文化、瑪雅文化等因外族入侵以致湮沒在歷史。在這段期間,北魏的孝文帝曾采取全面漢化:遷都洛陽,禁鮮卑服改穿漢穿,改漢語為國語,改漢姓,與漢族通婚。到了金朝的時候,也推行漢化政策,甚至有“金以儒亡”的說法。《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干當國,勸太宗改女真舊制,用漢官制度。”直至熙宗在天眷元年“頒行官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舊制。元初郝經謂金朝“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3]。
元代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馬上民族,要統治中原的話,統治者意識到要一定程度的“采用漢法”及“以儒治國”。然而,蒙古嚴分種族之別,到最后其實并沒有采納華夏文化,所以最后被逐回漠北。元末農民起義時就又援引“華夷之辨”的古訓,朱元璋在討元檄文就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北伐綱領。
清初滿洲入主中原,再次激起了“夏夷”論爭。清朝,雖然表面上不斷強調滿漢之分,甚至強迫漢人剃發、滿漢不能通婚,但內里卻全面接受了漢文化。滿人在中原生活,其實已被同化為漢人。
清末在與外國接觸時,華夷之辨的觀念發生歧變。朝廷以天朝大國自居,認為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國家俱是偏處化外的夷狄。加上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認識的膚淺狹隘,就更加強了華夏民族對外的輕視心態,結果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威風掃地,正如馬克思所說,“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而盡,天朝立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4]。不斷的外侮令中國人變成極端排外,再變為媚外,使得華夷之辨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積極意義。
三、華夷之辨的近代轉型
近代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遭遇千古奇變,出現了全面危機,華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強調,華夏中心主義與天下主義的兩極張力增大。晚近以來,面臨列強的瓜分危機,嚴復于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與歷史上不同的是,近代中國人以傳統夏夷之辨為資源,受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現代民族意識覺醒,形成了多元的民族主義思潮,諸如大漢族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反傳統民族主義與保守民族主義、大同主義與民粹主義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民族概念的形成,使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整體升華為一個自覺的整體,以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多元民族和文明當中探索發展道路。
大漢族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前者把現有的少數民族排除在外,認為中國的國只能是漢族的國,強調加快漢族同化少數民族;后者主張少數民族脫離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而獨立、自治等。反傳統民族主義和保守民族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其間,一部分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認為只有徹底破壞中國舊有的傳統,引進西方的民族和科學,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生存和發展;與此同時,又存在著民族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他們旨在通過保留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以救亡圖存。[5](P189-190)大同主義與民粹主義:前者以康有為為代表,在民族危機面前不是強調民族文化傳統的特殊性,而是強調通過制度的改革落實人類共同的普遍價值;后者以章太炎為代表,強調通過歷史文化的整理發揮其中的精粹以塑造民族靈魂,振奮民族精神。[5](P390-391)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民族概念形成于近代,但其族體已存在數千年之久,其族稱的形成與發展也經歷了數千年的演變。大約在5000年前,當中華民族開始形成時,其族稱為“華”。漢朝以后,開始出現“中華”的族稱。至19世紀末,作為近代民族學術語的“民族”概念傳入中國后,“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學詞匯也應運而生。雖然“華”“中華”“中華民族”這些族稱之間小有差異,但其內涵卻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國領土上的所有民族。[6]
“中華民族”是對“華夷之辨”的轉型和超越。在“華夷之辨”觀念形成之時,大一統思想也在逐漸形成,其中“華夷一統”就是這一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原夏人、商人、周人為基礎,吸收其他部族集團的成分,形成了華夏民族的雛形。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在春秋時期被稱為夷狄的許多民族融于華夏,至戰國時期最后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古代民族共同體——華夏族。華夏族的形成需要凸現其文化,于是有“華夷之辨”。但是“華夷之辨”實際上是為了更好的通過“夷”“華”交流而達到“華夷一統”。在這個意義上,“華夷一統”也就是“華夷之辨”的應有之意。秦漢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時期。在華夏族的基礎上,一個新的人數更加眾多的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漢族發展起來了。大一統思想的實現使表現于民族關系上的“華夷一統”思想也得到充分的發展,形成“華夷一體”的觀念。這一觀念在后來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國陷入分裂割據狀態、異族入侵、外來文化沖擊、華夏文化危機的情況下就有正統之爭,并成為這個分裂時期的思想上的重要特點。通過這些問題的爭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各民族就又找到了共同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找到了共同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這樣,往往就又一次迎來一個國力強盛、疆域廣大、多民族大團結、繁榮興盛的朝代。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指出:“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特色,距今3000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后,被其它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它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它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關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7](P1-4)這說明,中華民族是由眾多的古今各民族在形成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民族集合體。組成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各民族都有各自發展的歷史和文化,各民族長期在統一國家中共處并發展其統一不可分割的聯系,從多源交融到多元一體,自覺地聯合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
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整體升華為一個自覺的整體的過程,是以“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形成為標志的。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可能為梁啟超。早在戊戌時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對外抵制外族侵略、對內實現各民族團結的民族意識。1898年秋流亡日本之后,他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并結合中國的實際,在民族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詞。隨后,他又從民族進化和競爭的理念出發,大膽提出了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靈魂。進入20世紀后,梁氏受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發展成了較為明確的中國各民族必須一體化的觀念。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其云:“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于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1903年,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他提出“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之主張,清晰地賦予了中華民族較為科學的內涵,認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至1905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再次用“中華民族”一詞,并比較清楚地說明了此詞的涵義,雖然他認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但他“悍然下一斷案曰: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這說明此時梁氏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在他這里,“中華民族”也有了中國未來民族共同體的意味。可以說梁氏對“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和使用,體現了現代“中華民族”意識覺醒的階段性。
中華民國的建立,為國內各民族的平等融合與發展創造出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條件。孫中山、吳貫因、袁世凱、梁啟超、夏德渥、李大釗、常乃德及東、西蒙古王公這一時期都多次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并對其涵義進行了闡釋。與此同時,一些以推動民族平等融合為宗旨的社會組織如“中華民族大同會”和“五族國民合進會”也紛紛成立,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建立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民國初年,李大釗在《新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亞細亞主義》兩文中,揭示了滿、漢、藏等族趨于一體化的重要歷史文化因素、血統聯系和現實政治條件,呼吁社會認同五族合一的新“中華民族”,主張以此來培養民族精神、統一民族思想。“五四運動”之后,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在政治界、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最終確立和逐漸傳播開來。孫中山也在此時明確倡揚開放性的“大中華民族”理念。孫中山和梁啟超對于“中華民族”觀念的弘揚,從歷史功能上看正好形成一種互補,可以看作在政治思想上和學術思想上“中華民族”觀念形成了某種有效的聯動態勢。另外,當時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等其他政治、思想派別和人物,也都在中國各民族構成一個整體的意義上,頻繁地使用了“中華民族”概念。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人們認識到民族團結的重要性,于是一體化的“中華民族”觀念,滲透到各民族和各階層人民大眾的心中,最終蔚成一個不言而喻、不可動搖的神圣信念。[8]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的復興主要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當今中國面臨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沖突。文化帝國主義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借用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文化影響力自覺不自覺地推行的一種全球文化戰略,由此產生了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挑戰和文化霸權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相應地出現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不僅在官方,而且在知識精英,特別是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中和民間老百姓中都有。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的復興我認為應該以中和之道化解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沖突,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等兩重性之間找到一條既構建起中國文化的新體系,又能夠解決了人類文化問題的道路。
梁漱溟認為:“這是中國思想正宗,……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9](P166)中國人這種文化主義至上觀念,使得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觀念里。而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于是并不存有狹義民族觀與狹義國家觀,因為“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也因此,民族與國家兩者間常如影隨形,有其很親密的聯系,而使得“民族融合”即是“國家凝成”,“國家凝成”亦正為“民族融合”。[10](P23)因此,可以說“中國是一個國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它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11](P177)歷史上,夏夷之辨并沒有成為諸夏民族的民族主義,但是卻成為了諸夏文明的保護者,中國文明能傳承至今,歷經患難而不曾斷裂和滅亡,夏夷之辨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民族主義者應該有一定的啟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應該是:繼承華夷之辨的基本精神,即以文化或文明之辨而非種族之辨,是以道德禮義為核心的精神,在多元文明的世界上確立中華民族主體性,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走中道,承認世界多元文化,以儒家和而不同、忠恕之道等為理念,在實現民族振興的同時促進人類邁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境。
[1]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 郝經.刪注刑統賦序[A].陵川集:卷三十[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M].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6] 田曉岫.“中華民族”族稱考[N].光明日報,2003-10-14.
[7] 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A].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1998.
[8] 黃興濤,劉正寅.“中華民族”觀念形成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N].北京日報,2002-11-11.
[9]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北京:學林出版社,1987.
[10]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11]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