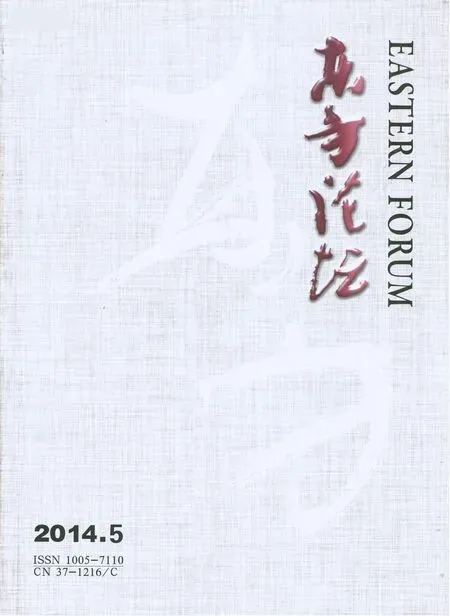莫言、諾獎、批評及批評的批評——對話《對話〈直議莫言與諾獎〉》
王金勝
(青島大學 文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莫言是當代中國最優秀、也是頗有爭議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在獲諾獎之后,褒貶毀譽的各類文字頻頻見諸報端。李建軍是一位頗具個性和影響,也由此引發了眾多爭議的當代批評家,肯定者、批評者皆不乏其人。如此二人,發生“交集”,原因自不難理解。李建軍新近于《文學報》“新批評”專欄發表了《直議莫言與諾獎》[1](以下簡稱《直議》)一文,分析莫言獲諾獎的文本內外的原因,從多方面對莫言小說、諾獎、中國文學提出了自己批評性意見。學者孟祥中針對《直議》 一文,在《東方論壇》發表《對話〈直議莫言與諾獎〉》[2](以下簡稱《對話》),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
出于對作家莫言和批評家李建軍的關注,筆者認真閱讀了《對話》《直議》兩文。總體感受是,盡管《對話》針對《直議》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結合莫言作品進行了必要的分析,可謂有理有據,但筆者并未看到一篇真正觸及《直議》關鍵論題和問題的文字。這是很讓人感到遺憾的,《對話》在很多重要問題上,并未構成與《直議》的切實而有效甚或有力的“對話”。
一、“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諾獎”“中國文學”及其他
《對話》開篇即提出一個問題:“至于說,諾獎‘頒給了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這不是儼然學者玩起了超級大忽悠嗎?”[2]作者進而“反唇相譏”:莫言獲諾獎遭到了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的李先生的否定,作何解讀?”[2]在筆者看來,這個《對話》不知“作何解讀”的“超級大忽悠”現象倒是不那么難理解。當然,這需要返回《直議》,將相關話語完整地聯系起來看,《直議》的原文是:“‘諾獎’終于在頒給曾經是中國人的‘中國人’之后,再次頒給了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1]這就是說,《直議》中所謂“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是跟前面“曾經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并舉、相對而言的。若像《對話》一般,單摘出“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1]這一句不禁讓人感覺莫名其妙,摸不著頭腦。但若放回《直議》中,問題似乎變得就容易理解了。如此一來,反倒是《對話》的“反唇相譏”讓人不知“作何解讀”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直議》為何不直說高行健,而偏偏說“曾經是中國人的‘中國人’”,不直說莫言,而偏偏說“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本來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事,偏偏繞著說?如果聯系《直議》此后的觀點和內容,倒也不難索解:《直議》對莫言、對諾獎持一種尖銳的異見,持一種嚴厲的審視和批評態度,其作者只不過運用了一種特殊的言說策略,一種讓《對話》作者感覺“不舒服”的“帶刺的油滑”方式來表述而已。
接下來,《對話》提出了《直議》中另一個貌似不合邏輯的問題,即在莫言已經獲諾獎的情況下,李先生仍然認為諾獎“不可能成為一個能夠將中國文學包納在內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1]是“一個正常人難以理解的”思維邏輯,并質問:“諾獎獎給了莫言不算包納中國文學?只有獎給了李先生推崇的一大批中國當代作家才算包納了中國文學?”[2]說實話,看到這里,筆者同樣覺得奇怪:莫言小說難道不算中國文學?莫言獲諾獎難道不是中國文學被世界文學包納的事實?如果沒有莫言或其他中國作家獲獎,中國文學就沒被世界文學包納?……帶著如此等等讓人“難以置信”的問題,筆者“細讀李文”,總算大體明白了筆者之所以覺得奇怪的緣由。其實,《直議》所側重和強調的并非諾獎是否包納了中國文學的問題,而是諾獎是否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的問題。這同樣需要照錄《直議》原文:“諾貝爾文學獎本質上只不過是一個西方文學獎,而不可能成為一個能夠將中國文學包納在內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1]就筆者的理解,《直議》的意思是,諾獎本質上是一個西方文學獎而非它所宣稱或多人所認為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其背后有西方人的眼光、視角、歷史文化和文學傳統。通讀之下,就會發現《直議》是在文化的同構與否和“語言的可轉換性”這個大問題之下,提出這個問題的,按照《直議》的說法:“正是由于這種文化溝通和文學交流上的巨大障礙,使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無法讀懂原汁原味的‘實質性文本’,只能閱讀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譯的過程中,漢語的獨特的韻味和魅力,幾乎蕩然無存;在轉換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國作家的各各不同文體特點和語言特色,都被抹平了。”[1]此為原因之一,可概括為“美文不可譯”。原因之二,就是《直議》第一部分最后一句話:“諾貝爾文學獎從一開始就有著自己的‘傲慢和偏見’,就是一個不具有廣泛包容性和絕對公正性的文學獎項。”[1]
二、一則莫言杜撰的語錄與《直議》的“修改”
莫言曾在《天堂蒜薹之歌》初版的卷首,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在《直議》中,作者將其“修改”如下:“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政治卻自己逼近了小說。小說家總是關心自己的命運,卻忘了想關心人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1]
《對話》 認為莫言所撰“語錄”“沒有任何毛病,不僅如此,而且含義深刻,富有哲理”[2]。對《直議》的“修改”,《對話》認為“一句富有哲理的話經李先生這么一改,蹩腳味陡然而出,難脫畫蛇添足之臼。如此顛黑為白,忽悠讀者,匪夷所思”[2]。那么,讓我們再次回到《直議》語境,來看看《直議》修改是否確為“顛黑為白,忽悠讀者,匪夷所思”的畫蛇添足。
莫言所杜撰的所謂斯大林語錄,其所指應為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的“悲劇”處境和命運,結合20世紀50-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期中國作家和文學的具體狀況,不難理解其具體所指性。
需要注意的是,《直議》“修改”后的話語其所指卻發生了根本的轉化,其鋒芒所指并不僅限于莫言所撰“語錄”,而應該是《直議》作者所認為的中國作家和文學的真正悲劇所在:小說家試圖通過疏離政治的方式來保全自己,而政治卻并未因此放棄對作家的緊逼;小說家關心自己的命運,試圖維持自己現世的生存,卻并未體現出對人、人類處境、遭遇、命運的思考和人道主義的悲憫、同情。用《直議》的表達便是:“小說家的主體責任:應該有所為的是人,而不是物;偉大的小說家應該勇敢地關心人類的命運,而不是僅僅關心‘自己’的利害得失。”[1]這才是中國作家和文學的真正悲劇所在。《直議》的表述的實質是從現實主義的立場、精神和內在實質出發,批判中國作家和文學的思想力度和精神力度的缺失。這在《直議》中有進一步的闡釋,如在接下來的一段中,作者寫道:“他必須有自己對善惡、是非、真假的基本態度和鮮明立場,必須確立一種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價值體系,否則,他的寫作就將成為一種游戲化的寫作,成為一種缺乏意義感和內在深度的寫作。”[1]也因此,作者認為“莫言的寫作似乎缺乏一種穩定的價值基礎,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義世界。在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泛濫的語境里,他無力建構一個批判性的敘事世界和積極的價值體系”[1]。
三、小說:自在之物?
在談論“語錄”的過程中,《直議》還提出了一個相關的問題:“‘小說’作為一個客體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1]對此觀點,《對話》是不贊同的,在孟先生眼里,小說作品顯然不能等同于普通之物:“小說是有‘生命’的創作之物。小說家在寫作過程中打上了自己思想的烙印,好的小說是嘔心瀝血之作,跳動著作者的脈搏,(按:作者在創作中?)全身心地沉浸在人物的悲喜苦樂之中。”[2]單從字面上看,《對話》的批評自有道理,這也是文藝創作的基本原理。但李建軍先生所說是不是就“大謬不然”呢?依筆者之見,孟先生在此問題上的批評也并不具備充分的合理性。原因如下:
其一,作為已經發表、出版的作品,將其視為一個創作主體(作家)創作出來,等待閱讀主體(廣義的讀者和狹義的讀者——批評家)接受、闡釋的客體,是合理的。
其二,將此客體視為“自在之物”也有其合理之處。作為作家建構的藝術性再現客體,小說不僅在形式、句式、語言等層面均已固定,并與文本所指涉的客體(社會、歷史、心理等)之間存在著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或反射或折射、或再現或表現、或秉筆實錄或扭曲變形等諸種關系。而且,作為客體的文本的意義結構也相對穩定,即使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永遠也不會被解讀為堂吉訶德、李逵或賈寶玉。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所謂“自在之物”是否可以理解為,已經發表、出版而獲得穩定形態的作品,自有其相對獨立性?筆者覺得,這似乎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
其三,盡管作品的確屬于作家嘔心瀝血的產物,其中滲透著、涌動著作家的思想、情感,但一旦作品被創作出來并進入發表、流通環節,其意義的生產(闡釋、評價、發掘)則不完全被作者所控制,作品的“意義”往往溢出作家的“意圖”,一部作品的經典性往往體現在“意義”的持續再生產中。如果作品的意義生產完全聽命于作家,完全受作家闡釋權利的控制、支配,則不會出現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現象。關于這一點,相信作為理論批評家的李先生和孟先生都會作為常識來看待。
那么,為何《對話》認為《直議》的看法“大謬不然”呢?筆者認為其間存在著《對話》對《直議》的誤讀。通觀之下,可以看出,《直議》始終注重莫言小說文本與作家(創作主體)莫言之間的緊密關系,而從未將小說家莫言與其小說割裂開來、區別對待,很顯然,李建軍先生從未將作品看做與作家無關的“普通之物”,《直議》所言:“‘小說’作為一個客體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1]所要強調的是作家的主體性,“他必須有自己對善惡、是非、真假的基本態度和鮮明立場,必須確立一種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價值體系”[1]。也就說,此“自在之物”既非康德所謂“自在之物”,也非孟先生所謂“普通之物”。 結合《直議》上下文,也許稱之為“為我之物”更合適些,只是作者為著突出作品的相對獨立性而策略性地使用了“自在之物”一詞。因此,單純地從《直議》中擇出一句話來批判,其合理性是欠缺的。
順便一提,《對話》本部分在說明作家情感對作品的滲透時,所舉“在寫到小說中的人物自殺的時候,就感到自己的口中有砒霜的苦味”[2]的例子,其當事人為福樓拜而非巴爾扎克。當然,這可能是個偶然出現的記憶性常識錯誤。
四、“敘事的平衡術”與“審美平衡能力”
這是《對話》在第五部分提出的《直議》中存在的又一個問題。
結合《直議》語境,可以看到,所謂的“審美平衡能力”,其內涵主要是指,莫言能否避免其作品中常常出現的“單向度地渲染一種情調和行為”,“清晰地區別美丑、雅俗、高下”,從而創造出“清晰、有力量的價值圖景”。[1]可見,“審美平衡能力”屬于小說敘事學范疇,是一個敘事美學問題。
這里的“審美平衡能力”與《直議》在第三部分所提到的“平衡術”所指并不相同。關于“平衡術”, 《直議》具體表述如下:“莫言小說敘事的平衡術實在太老練了。而真正的現實主義,就其內在的本質來看,是拒絕‘平衡’的,而是傾向于選擇一種犀利的、單刀直入的方式來介入現實。”[1]同樣置諸語境,此處所謂“平衡”“平衡術”所指的是世俗利害的考慮與小說敘事創造之間、美學與政治之間的權衡,作家的“聰明”、世故與“真正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本體性矛盾。關于這一點,可以參看《直議》第三部分對《蛙》的解讀,其主要觀點不妨援引如下:“如果非要說莫言的創作是現實主義的,那也不是一種純粹的、迎難而上的現實主義,而是一種軟弱而浮滑的現實主義。表面上看,他善于發現尖銳的現實問題,善于表現沖突性的主題,然而,如果往深里看,你就會發現,莫言在展開敘事的時候,通常會選擇這樣一種策略,那就是,避開那些重要的、主體性的矛盾沖突,而將敘事的焦點轉換到人物的無足輕重的行為和關系上來。”[1]概括地說,所謂“平衡術”的基本意思是,基于現實利害而在現實表現問題上趨與避的衡量。
其實,《直議》與其所引王彬彬的觀點是一脈相通的,即都認為中國作家過于發達的生存智慧、過多的現實利害權衡,導致了其作品缺乏積極的思想力度和“意義深度”,而這與“真正的現實主義”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的。因此,筆者認為,這不屬于孟先生所說的“自相矛盾的批評”:“兩處批評,兩相映照,彰顯出批評家高超的語言藝術,把莫言玩弄于股掌之上,本來是自相矛盾的批評,在語言的花樣翻新之下,似乎顯得各有其妙。”
五、“思想”“感覺”與文學:關于莫言演講中的兩個觀點
莫言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如此論及“思想”與小說藝術價值的關系:“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思想太過強大,也就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想得太過明白,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會大打折扣。因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過強大的時候,感性力量勢必受到影響。小說如果沒有感覺的話,勢必會干巴巴的。”針對此言,《直議》認為“這里的判斷其實是很靠不住的”。原因是:“在長篇小說敘事里,‘思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沒有思想的敘事,必然是淺薄而混亂的敘事,也就是說,在小說的世界里,‘思想’與‘感覺’、‘理性力量’與‘感性力量’從來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對立關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關系。在真正的文學大師那里,感覺是滲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覺,而思想則是充滿感覺血肉的思想,——他們既是理性的‘善思’的思想家,也是感性的‘善感’的詩人。”[1]
《對話》則認為莫言的這段話“沒有什么毛病”,《直議》所批判的實則是批評者自己設立的“兩個‘假想敵’”。 《對話》將莫言的這一說法進一步歸納為:“小說寫作過程中,理性力量不能太過強大,太過強大了,寫出來的作品勢必干巴巴的。”并認為“這不是莫言的創新,是老生常談”,“寫作不能忽視理性的力量,更需注重感性的力量,這有什么好非議的”。[2]
將莫言《直議》《對話》的說法逐一閱讀、加以對照,筆者同樣覺得《對話》存在著對《直議》觀點的誤讀。需要注意的是,《直議》談論思想與小說敘事的問題,同樣也是在一個更大的問題之下進行的,這個更大的問題就是《直議》第四部分的第一句話:“無思想和無深度,也是莫言寫作的一個致命問題。”[1]《直議》引述莫言原文,其目的在于將其作為一個批評的材料、例證,《直議》真正批判的對象是莫言寫作(尤以長篇為著)中的“無思想和無深度”問題,而非《對話》所言“兩個‘假想敵’”。《對話》所提到的“兩個‘假想敵’”,一是“沒有思想的敘事,必然是淺薄而混亂的敘事”,[2]另一則是“‘理性力量’與‘感性力量’,從來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對立關系”[2](按:《直議》此句的完整表述為:“‘思想’與‘感覺’、‘理性力量’與‘感性力量’,從來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對立關系”。不知為何《對話》在摘引這句話時,省略掉了“‘思想’與‘感覺’”)。在筆者看來,這兩句話并未構成《直議》批判的對象,當然,莫言的話里也“根本沒有李先生設定的這兩個問題”。不知《對話》如何從《直議》中讀出了“兩個‘假想敵’”,也不知讀者該“作何解讀”?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對話》并未與《直議》展開實質性的對話和交鋒,后者針對的是莫言小說中的“一個致命問題”,而前者談的是一般的創作理論問題。從內在本質上看,《直議》并未否認《對話》談及的基本原理問題。不同層面上的交鋒,猶如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看似雄辯滔滔,實則并未產生出耀眼的思想火花。按照筆者的理解,《對話》似應對《直議》提出的關于莫言小說的“致命問題”進行論辯和反駁。
莫言在談及“思想”與小說藝術價值的關系時,順理成章地談到了“感覺”與自己創作實踐的關系:“也有人說,莫言是一個沒有思想只有感覺的作家。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批評我覺得是贊美。一部小說就是應該從感覺出發。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覺都調動起來。描寫一個事物,我要動用我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聽覺,我要讓小說充滿了聲音、氣味、畫面、溫度。”[1]《直議》在如此引述之后,作如下分析、判斷:“就算小說寫作的確‘應該從感覺出發’,一個小說家也不能毫無邊界地描寫感覺,不能將人物寫成完全‘感覺主義’的動物。然而,莫言小說的致命問題,就是感覺的泛濫,就是讓作者的感覺成為一種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覺,從而像法國的‘新小說’那樣,讓人物變成作者自己‘感覺’的承載體。”[1]
《對話》則認為莫言的觀點及其表述“也就(按:已經?)夠全面的了”“已經辯證了”且“合乎只說正確大話的心理定勢了”[1]。看到這里,筆者不禁為《對話》作者的質樸、實在而幾乎啞然失笑了。難怪作者對李先生“在莫言沒有說只要感覺,不要思想的情況下”尚且“強烈不滿”、進而“一大串言過其實”的“指責”深感不滿。
其實,莫言在“感覺”問題上的看法與對“思想”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且這并非其原創性觀點,用《對話》的話說,就是這些看法基本屬于“老生常談”“正確大話”的范疇。因此,《對話》順承這些“老生常談”再加一些注釋性的鋪展,也并未生發出具學術啟示性的觀點。
關于“思想”與小說藝術價值問題,筆者還是比較認同《直議》的入思路徑和基本觀點。當然,這是一個極具闡釋難度的論題,筆者學力有限,僅舉幾例,權作進一步深入思考此問題的契機。
就筆者有限的閱讀,似乎很少有國外作家談及一個作家因思想過于強大而傷害小說藝術價值的問題,反倒是國內作家頻繁談及。這個反差,不禁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作家的思想已經過于強大而使小說藝術性大打折扣了,還是相反,抑或別的什么?
20世紀卓有影響的俄國思想家別爾加耶夫在其代表作之一《俄羅斯思想——19世紀到20世紀初俄國思想的基本問題》中,從哲學、歷史、文學、宗教等方面深入、系統地分析了俄羅斯民族的性格、特點及其歷史命運、地位,書中論及的重要作家也是思想家包括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赫爾岑、索洛維約夫、安德烈·別雷、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其中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是無可爭議的經典小說家,其代表性創作體裁主要為長篇小說。
20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政治思想史家,被稱為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的以賽亞·伯林在其思想史巨著《俄國思想家》中也對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屠格涅夫等俄國各時期杰出作家的思想、心靈、識見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進行了全面而生動的分析。
無怪乎學者、作家曹文軒先生①曹文軒,作家,學者,評論家,著有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天瓢》等,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小說門》等。在閱讀納博科夫②納博科夫,著名俄裔美籍小說家,詩人,評論家,其長篇小說代表作為創作于1955年《洛麗塔》和1962 的《微暗的火》,《文學講稿》是其代表性理論批評著作。《文學講稿》時“發現了一個殘忍的對照”:“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除了寫有大量的文學作品以外,還有相當可觀的文學創作理論或文學理論方面的文字(魯迅、艾略特都是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而我們當代的作家卻大多只有幾篇雞零狗碎的‘創作談’而已。這是文學素養方面的差距,上升一步說,就是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差距。”[3](P218)就長篇小說來看,卡夫卡、昆德拉、加繆、馬爾克斯、納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托爾斯泰、索爾·貝婁等大師級作家的作品中無不包含著巨大的思想容量,卡夫卡、加繆的長篇甚至成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經典文本,納博科夫、索爾·貝婁的作品則充滿“一種特殊的文學情趣”:“這種情趣的特點是冷靜,充分理性化,使用大量知識,帶有形式化、技術化傾向。”[3](P216)而魯迅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與其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創造性貢獻是分不開的,與其作品思想的深刻度和文化蘊涵的豐厚度是分不開的。當我們看到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小說先鋒性、反叛性、實驗性的美學實驗時,當我們為其形式的復雜、晦澀而感到難以卒讀時,是否會想到在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背后恰恰包蘊著作家們對當下人類更復雜、更難以索解的內在和外在的生存圖景和困境的深度解讀和整合性把握。恰恰是這些構成我們理解上的障礙或被我們所輕忽的東西,構成了現代主義小說家的主導創作動機和敘事資源與動力,構成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思想內質和敘事詩學的基本形態。
莫言的確“沒有說只要感覺,不要思想”,而且,據筆者推測,不僅莫言不會說,“聰明”的中國作家們也不會在公開場合這樣說。莫言的確是聰明的,“在一段話里用了三個不能‘太過’,設了三道防線”,但這些“正確大話”又有何益:何謂“思想太過強大”,何謂“想得太過明白”,何謂“理性力量太過強大”,相信沒人能真正把握其真髓吧。
相對于在“思想”問題上的含糊其辭、折中公允,莫言談“感覺”時更有感覺。莫言認為對其“沒有思想、只有感覺”的批評是“贊美”,這是否意味著莫言“在某種意義上”認可了《直議》中這樣的說法:“莫言小說的致命問題,就是感覺的泛濫,就是讓作者的感覺成為一種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覺,從而像法國的‘新小說’那樣,讓人物變成作者自己‘感覺’的承載體。”[1]祛除《直議》的貶義色彩,祛除莫言自己的褒義色彩,對“感覺”的突出應該是莫言小說的突出特點,這一點相信任何讀過莫言小說的人都不會否認,也早有文學史將莫言、殘雪等作家放在“感覺主義”論域中分析。到底是褒是貶,應該是揚是抑,還有褒貶抑揚辯證分析,評論家應該享有以具體文本為依據,以藝術規律為評判準則的充分自由與權利。
遺憾的是,《對話》第八部分在關于“感覺”問題也并未展開實質性的有效“對話”。其一,《直議》對莫言“感覺的泛濫”的批評,是建立在對文本的閱讀基礎上,并非如《對話》所說“在莫言沒有說……”的條件下。也即《直議》對莫言的批評盡管使用了莫言講演的內容,但只是作為自己分析、論證的材料而已,它針對的是莫言小說中的“感覺”現象而非莫言講演中關于“感覺”的說法。其二,《直議》批評莫言小說“感覺的泛濫”是以文本細讀為基礎的,所論述的是一個小說敘事詩學或形態學問題,而《對話》批評、闡釋的則是文學創作發生學和文藝創作心理學問題,如其所言:“小說寫作就是應該從感覺出發……文學寫作從感性出發,這是圭皋。思想蘊涵在寫作的過程中,隨著人物的成長,情節的發展變化逐步形成。不從感覺(生活)出發,從思想(概念)出發,那不是文學……”[2]換個說法,《對話》所論“感覺”是尚未以文本形式凝定下來的“感覺”,而《直議》所論“感覺”則是已經以文本形式凝定下來的“感覺”,這種“感覺”已經充分構成了小說文本敘事和小說敘事詩學的基本要素,成為批評家進行文學文本分析的重要對象。《直議》對《天堂蒜薹之歌》等的分析即屬此種“感覺”。因此,兩文所論同樣是屬于不同論域的兩個問題。需要注意的是,莫言談論“感覺”的路徑和方式與孟先生是一致的,即也是將“感覺”置于創作發生學和文藝創作心理學論域。就此來看,《直議》所說“就算小說寫作的確應該從感覺出發”[1],就不應簡單地像《對話》所說的那樣,僅僅是李建軍先生的“無可奈何地認可”之舉,而是一種“姑且如此”、以退為進,重新回到問題論域的策略。因此,孟先生的批判,其效果,借用《對話》的說法,就是“再批判,除了強詞奪理,不可能有奇跡出現,至多是抓雞不成,落了一把雞毛”[2]罷了。
還有一點,孟先生指出《直議》存在的普遍現象和突出問題是,李建軍先生“自己把話說絕了”。筆者認為這是有道理的。就“感覺”“思想”問題來看,就是李建軍先生認為莫言小說“無思想和無深度”“感覺的泛濫”,若用“太過”句式轉換一下,就是“思想過于貧乏”“過于放縱感覺”,且前者為因,后者為果,二者有緊密的因果邏輯關系。從上述分析中,筆者認為《對話》顯然忽略或避開了這一點。
最后,為求直觀,讓我們嘗試著用莫言談“思想”問題的方式,來模擬一下李建軍先生如何談“感覺”:“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放任感覺的泛濫,也就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毫無邊界地描寫感覺,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會大打折扣。因為作家在感性力量太過強大的時候,理性力量勢必受到影響。小說如果沒有思想的話,勢必會淺薄而混亂。”[1]試想一下,這段話有什么大毛病呢?這應該算不上創新,也許根本就是“老生常談”吧。如果上述“感覺”模擬還不算離譜的話,那么,我們就要問一下——為什么那樣說你就覺得刺耳,不能接受,這樣說你就覺得順暢、合理呢?為何會出現如此乖謬的現象,問題到底出在哪里?這時候我們是不是需要運用“理性的力量”“思想”一下呢?
六、李建軍的莫言批評、莫言獲諾獎
據筆者對《直議》和《對話》的閱讀,總感覺《對話》存在諸多對《直議》的誤讀之處,其批評看似有理有據、義正辭嚴,但時有批評錯位的別扭感。其中原因,除了分裂語句,脫離論述語境以外,還有就是《對話》的批評尚未顧及《直議》作者的莫言“批評史”。
魯迅先生曾如此談及微觀文本研究:“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4](P220)因此先生認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4](P225)據此來看,《對話》在“摘句”時存在割裂《直議》論述完整性的問題,存在未顧及《直議》“全篇”即上下文語境的問題,還有就是未能顧及《直議》作者“全人”即其批評理論、方法、立場,尤其是莫言“批評史”問題。
限于篇幅和論述的重點,本文將不對《直議》作者的文學批評做整體性的分析評價,而僅談談最后一個莫言“批評史”問題。《直議》作者對莫言的批評可謂“其來有自”且“源遠流長”。即以《直議》所重點分析的《檀香刑》為例,作者早在2001年就有《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5]一文,從文體、語法、修辭,敘事的分寸感、真實性,敘事模式、技巧等多方面批評此部小說,這篇文字也頗為作者本人看重并多次收入其論文集①就筆者所見,《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曾先后5 次收入李建軍先生本人所著《小說修辭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文學的態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文學還能更好些嗎》(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是大象,還是甲蟲》(北岳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此文還被收入李斌、程桂婷主編《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關于《蛙》,作者也于2011年撰有論文《〈蛙〉:寫的什么?寫得如何?》[6]。二文均早于莫言獲諾獎的時間。在其他非莫言專題的論文中,李建軍也多次對莫言小說提出批評。因此,盡管《直議莫言與諾獎》發表于2013年1月10日,卻是作者一貫對莫言的批評立場、思想和觀點的合理延續,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客觀事實,對于這樣的基本事實,一個批評家是不應該輕忽的。由于這個被作者忽視的事實的存在,《對話》所說的“原本一個好端端的作家莫言,只因得了諾獎,一夜之間,大禍從天而降”[2]也就成了一個“假想敵”式的問題。也正是這個貌似很不起眼的“細節”被作者有意無意放過了,使得《對話》不僅會對不明就里的讀者形成誤導,更影響了作者對文中一些問題的判斷,進而對文章本身的學理性、說服力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對話》在第一部分的最后,就對當代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的評價問題,指出《直議》作者邏輯思維的矛盾和混亂,并質疑后者:“自己如此的邏輯思維,怎么能激烈地批評他人不懂邏輯呢?”[2]關于這個問題,還是讓我們回到《直議》原文,對此《直議》的表述是:“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有的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他們的文學成就并不低。”[1](按:這是《對話》所說的“一方面如數家珍”),在《直議》的第五部分也即最后部分,作者又寫道:“我們應該明白,從整體上看,我們時代的文學并不成熟,作家們的人文修養水平和文化自覺程度都不很高。我們要知道,用嚴格的尺度來衡量,我們其實仍然是‘不配’獲獎的。與‘別國大作家’比起來,我們時代的作家,其實仍然差得很遠。”[1](按:這是《對話》所說的“另一方面”)。先看第一句,緊接此句《直議》列舉了汪曾祺、史鐵生兩位作家,加上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北島、王小波、韋君宜、叢維熙、陳忠實、路遙、章詒和、楊顯惠、蔣子龍,數量已達11 位。而在此前,作者剛剛指出:“在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俄羅斯,也只有蒲寧(1933年)、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爾仁尼琴(1974年)和布羅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獲獎,其中蒲寧是流亡作家,而布羅茨基則已加入了美國國籍,實質上應該算是美國作家的。”[1]就此來看,這一判斷是合理的。再看第二句,目前中國作家隊伍之龐大,作品產量之高,可謂世界第一,但其整體質量和國際影響力顯然也不能讓人滿意,這也是事實。僅就《直議》中提到的作家而言,試問當代中國作家中,有幾人能超過魯迅、張愛玲、沈從文、老舍、巴金,又有幾人能比肩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契訶夫、高爾基、勃蘭兌斯、烏納穆諾、卡夫卡、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在筆者看來,《直議》的這兩個判斷并不構成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也即二者并非自相矛盾的判斷。
除了上述所論,還有一些問題,如“思想”與“領導出思想”的“思想”問題、“思想”與“理性力量”及“說教”問題、“思想”與“概念”“觀念”等問題;“思想”“感覺”與作家的主體權力關系的問題等等,都有一些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姑且不論。
總體來看,《對話》因在事實材料的攝取上存在著輕忽之處,在分析、論辯的過程中存在著割裂《直議》論述的連續性和相關性及抽離具體語境和跨論域批評等問題,并未顧及“全篇”“全人”,因而該文并未達到切實而有效的“對話”目的。
[1] 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N].文學報,2013-01-10.
[2] 孟祥中.對話《直議莫言與諾獎》[J].東方論壇,2014,(1).
[3] 曹文軒.閱讀是一種宗教[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4] 魯迅.“題未定”草·七[A].且介亭雜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5]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J].文學自由談,2001,(6).
[6] 李建軍.《蛙》:寫的什么?寫得如何?[N].文學報,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