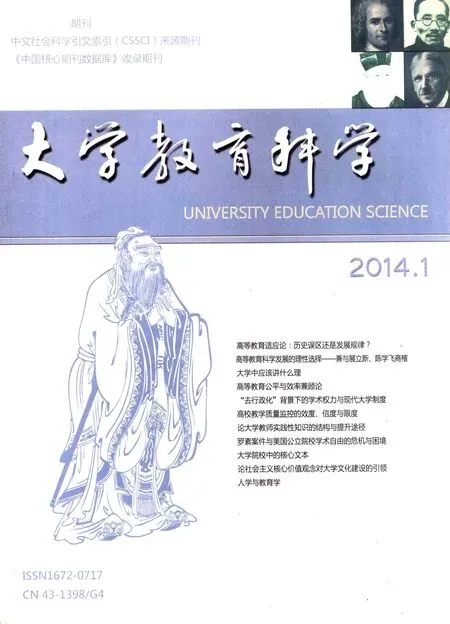高等教育適應論:歷史誤區還是發展規律?——上海師范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學術沙龍綜述
□ 劉培軍 高耀明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于2013年第1期刊發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展立新副教授和陳學飛教授合著的長篇論文《理性的視角:走出高等教育“適應論”的歷史誤區》(以下簡稱“《理性的視角》”)。作者認為:“高等教育‘適應論’是一種突出強調高等教育發展必須與社會發展需求相一致的高等教育發展觀”,“其代表性表述是關于高等教育‘兩個規律’的理論”。作者堅信,“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誤區,“是一種無奈的歷史選擇”,“它顛倒了認知理性與各種實踐理性的關系,試圖用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和傳統的‘實踐理性’等取代認知理性在教學和科研中的核心地位,使國內高等教育難于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同時,“它在選擇某種實踐理性為主導的時候,又不惜壓制其它各種實踐理性的發展,以至于在高等教育各種目標之間、不同的目標與手段之間,造成了極大的矛盾和沖突”。作者強調,“突破與超越高等教育‘適應論’,是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理性的視角》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揭示和分析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困境,是對當下象牙塔的“寧靜”遭受過分沖擊的現實之慮和對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夢的殷切之望。《理性的視角》重提、質疑和討論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理論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基本原理,更合理地處理高校、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而且對推動高等教育理論建設,完善高等教育學科將大有裨益。為此,2013年4月16日,在楊德廣教授主持下,上海師范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部分師生舉辦了一次學術沙龍,圍繞“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歷史誤區還是發展規律”進行了討論,現從四個方面將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嗎?
楊德廣教授認為,“適應論”是高等教育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是高等教育深層次發展所必須的,對推動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不是“歷史誤區”。高等教育“兩個規律”理論是符合高等教育實際情況的。《理性的視角》運用哲學概念,即以認知理性來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適應論”或“兩個規律”,甚至將它提高到高等教育的本質和核心是不恰當的。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歷史的必然而非歷史的誤區,主要理由有四:第一,從高等教育職能的演變和發展看,高等教育的職能由教學—研究—為社會服務的擴展歷程,就是高等教育不斷適應社會的過程。第二,從教育本質問題的爭論看,《理性的視角》否定“社會本位”,強調“個人本位”,提出“知識本位”,這是對教育本質問題的模糊認知。第三,從高等教育發展史看,一部高等教育發展史就是高等教育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史。第四,從我國的教育方針政策看,大學應為國家的需要而存在,所以必須適應社會。
博士生吳洪濤認為,潘先生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兩條基本規律,一條是高等教育與社會關系的規律,即高等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另一條是高等教育內部諸因素關系的規律,即高等教育內部關系規律。什么是規律?規律又稱法則,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的聯系和必然的趨勢。規律屬于現象之間普遍的本質和聯系,決定著事物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什么是適應?“適應”是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的積極的適應,通過這種適應,主體自身也得到了發展;同樣,談高等教育“適應論”,應該是高等教育主動積極地適應社會,同時通過適應社會又促進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反之,則是被動的消極的適應,稱不上是高等教育“適應論”,只能說是一種強制地服從或者被壓制。同樣,回到高等教育“適應論”上,正是由于中國的高等教育不是主動適應社會發展,本質上沒有實現潘先生所說的教育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外部規律,所以也就更不可能實現潘先生所說的內部規律,也致使潘先生提出的內部規律即使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很好實施。為此,從這個角度說,不能因為“兩個規律”沒有實施好,“適應論”沒有用好,《理性的視角》就得出“兩個規律”和“適應論”是歷史誤區,這是一種臆斷。
碩士生李煒認為,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的外部規律是教育要與社會相適應”,體現了兩個主體、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教育要適應社會,第二個過程是教育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社會。《理性的視角》過多地用特定歷史時期的錯誤來否定高等教育“適應論”的客觀規律是不可取的,它過度地曲解了第一個過程(認為適應社會就是順從社會)而忽視了第二個過程(也就是教育也在影響社會的發展,方式就是通過“人”這個重要媒介)。
博士生劉培軍認為,從社會現實來看,高校不是某個時代一般的社會組織之外的東西,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實體。高校從單純的教育實體逐步發展為日益復雜的擁有多目標、多結構、多職能的社會實體;從結構—功能的單維性走向結構—功能的多維性質,這是高校作為一個特定組織適應社會發展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從大學構成的基礎——學科的產生來看,許多學科的創設和發展動力來自社會的需要。因此,從大學結構演進的歷史來看,高等教育“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客觀規律。但從大學的本質屬性來看,“追求高深之學問”是大學理想,“象牙塔”精神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靈魂。歷史上,有著眾多的大學往往逃避著“世俗”的糾纏,甚至還扮演著與社會對抗的角色,才使得大學成為“以理智為基石的國家的神殿”。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高等教育“適應論”是一種規律,不如說,是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待。因此,談高等教育“適應論”是否是客觀規律,需要有一定的條件與視域。
羅志敏副研究員從價值關系的視角認為,高等教育與社會二者不管是并列關系,還是從屬關系,這種關系應是一種價值關系,即需要與滿足需要的關系。《理性的視角》對高等教育“適應論”的批判,實質就是否定高等教育與社會的價值關系。大學研究高深學問是為了把知識用于推動社會發展,而不是對知識采取“不受價值影響”的“閑逸的好奇”的研究態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高等教育“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理性的視角》認為“學術市場的建設,絕不是高等教育應該‘適應’的下一個社會發展目標”,若是如此,評判真理性知識的標準是什么?知識的價值何在?難道僅僅是為了追求純粹“理性”,滿足“閑逸好奇”的興趣?
高耀明教授認為,大學發展到現在,實際就是不斷適應的過程。正如阿什比所說:“大學的發展就像有機體的進化一樣,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最初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也是適應當時社會工商業發展需要而產生的。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內外部規律是文革剛結束之后,是基于“十年動亂”對高等教育嚴重破壞的教訓總結而產生。文革十年,我國高等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潘先生認為是違背高等教育規律的惡果。他認為,高等教育不應該僅僅適應政治需要,還要適應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因此,潘先生所說的“適應”,不是片面的、局部的適應,而是全面、整體的適應。《理性的視角》其實是反對大學對政治的依附,反對政治對大學的鉗制,這與潘先生提出“適應論”是一致的。《理性的視角》認為建國后我國高等教育出現的所有問題,是因為強調“適應論”所造成的,這不符合實際,犯了歸因錯誤;但這個問題,在高校規模擴張快要結束的時期以及進一步搞好高校內涵建設和建設一流大學的背景下提出,很有價值。
二、遵循“適應論”會阻礙高等教育的發展嗎?
博士生劉培軍認為,從大學改革發展史看,從中世紀培養教會人才的大學到德國洪堡改革,明確將科研作為高校重要職能,再到美國威斯康星精神——強調大學直接為社會服務的發展過程,大學從“傳統大學”到“現代大學”再到“多元化巨型大學”演進,每一次都是大學適應了社會發展,才推動了大學自身的發展。從合法性角度看,從中世紀至今,高等教育合法性滿足“宗教神學階段—近代化階段—國家化階段—工業化階段—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轉變歷程,說明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是根植于社會需要。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高等教育合法性基礎不同,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豐富的過程,也是一個滿足社會需要的過程。因此,可以說正是因為高等教育適應了社會的發展變革,作為組織機構的高等教育才得以保存、延續并基業長青。
博士生吳洪濤認為,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歷史規律而不是歷史誤區,大學唯有適應社會才不會被社會淘汰。從中世紀大學開始,大學就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的專業期望而出現:英國式的學院,是為了滿足文藝復興對人文主義的抱負;牛津、劍橋大學都是適應了當時英國社會培養紳士和自由教育的需要;德國的近代大學,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洪堡主持的柏林大學適應了大學參與科學研究以及當時德意志國家統一的需要;美國的贈地大學,它的理念就是要把人力物力用于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服務,威斯康辛大學是這方面典范,正是因為它適應了美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贈地大學才興盛起來;現在美國的創業型大學是以知識創造和科技創新為載體,麻省理工學院是這方面的代表,它適應了知識社會的需要。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時代的大學,都是因為適應了社會,才代表了高等教育先進的理念和潮流,才得以發展。
高耀明教授認為,洪堡參與建設的柏林大學,其誕生背景是當時德國處于戰敗、民族精神受到打擊,希望通過學術來振興民族精神和士氣,即柏林大學是適應當時德國的需要而建立的。再看我國高等教育遇到的問題,從文革前到文革后,再到改革開放后,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歸于“適應”,這是不對的。我們問題的關鍵是,大學不是獨立的,而是依附于行政機構的;這本身就違背了高等教育的外部發展規律。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凡是尊重大學自主權,確保大學自治的,就可能產生一流大學。法國是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國家直接干預教育,所以,法國的大學最終淪為二流;英國、美國很尊重大學的自治,所以,英美大學逐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強調“適應論”不會阻礙大學的發展,阻礙大學發展的最大問題是大學能否真正擁有自主權。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是一個官僚機構,有1500名左右的行政人員,這是十分龐大的機構,但這并沒有妨礙加州大學部分分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現今我國大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大學組織的科層化問題。大學適應社會,本身是沒有錯的;但現今我國的大學不僅迎合社會的需要,而且還需迎合行政官員的政績需要,這不是適應。適應是什么?是根據自身特點,根據社會需求,去主動地適應,而不是被迫迎合。
朱煒副教授認為,從教育政策效用角度而言,正是因為教育適應社會的需要,才為我國社會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從而提供了智力支持。假如《理性的視角》觀點成立,即高等教育“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誤區”,那么,我國《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將被全部顛覆。因此,遵循高等教育“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社會價值存在的基礎。
三、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如何認識“適應論”?
楊德廣教授認為,高等教育“適應論”是指高等教育要根據社會的需求來辦學,高等教育內容和人才培養要適應社會各方面的需要。“認知理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它不可能在教學與科研中處于核心地位,更不存在《理性的視角》所說的由于缺少了認知理性的核心地位,導致了各類高等教育難以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其次,我們講的“適應論”主要是指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大學要用知識和智慧為社會發展、為人才培養服務,《理性的視角》提出的大學發展中產生的一些問題,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造成的,而不是大學遵循了“適應論”而產生的錯誤。第三,“適應論”有時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但不會導致大學知識生產功能的邊緣化,更不會剝奪高等教育發展的自主權。
羅志敏副研究員認為,《理性的視角》理解的高等教育“適應論”是一種喪失大學知識生產獨立性的、被動和消極的適應。而從完整的意義上講,“適應”絕不僅僅是迎合或是“刺激-反應”模式的適應,真正的“適應”還應該包含一種有所選擇、有所舍取,積極主動進行價值判斷和認同抉擇的過程。
朱煒副教授認為,《理性的視角》為了確立自己的觀點,把“適應論”任意裁剪,把“適應論”狹隘化,而潘先生提出的“適應論”不是狹隘的“適應論”。因此,我們要分辨“真適應”還是“偽適應”問題。我們批判的應該是“偽適應”,高等教育對于政治的需要和權力的服從與迎合是應該改變,但《理性的視角》將建國后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歸結為“適應論”所造成的,這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
碩士生柳逸青認為,高等教育“適應”社會是必須的,但是應該考慮“適應度”的問題;哪些方面需要適應社會?哪些高校需要適應社會?哪些學校需要堅守“象牙塔”精神?這是一個需要值得思考的現實重要問題。
高耀明教授認為,“適應”分為短期適應和長期適應。現任哈佛校長福斯特曾說:“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單單或者僅僅對現在負責。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因此,大學的適應應該是長期的適應,而不是目光短淺、只為眼前利益的適應。其次,講“適應”也應分不同類型層次高校。對于研究型大學和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的高校而言(比如北京大學),應該回歸“認識理性”;而絕大多數普通院校(比如上海師范大學),則應更多地適應社會。因此,不能簡單地談“適應”,更不能“一刀切”。《理性的視角》推崇追求完全純粹的“認知理性”,這其實是一個烏托邦,但是我們又不能否認對“認知理性”的追求。就每一所大學而言,“適應”還有一個整體和局部的關系問題。局部上,對于學者個人來說,確實應該是進行不計功利的研究,學者在做研究之前不應該考慮研究能否獲利,能否得到領導的賞識。但是作為整體的大學肯定是應該適應社會的,不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可能就沒有了。
黃海濤副教授認為,《理性的視角》指出建國后中國大學出現的諸多問題,關鍵在于大學與外部特別是與政府的關系,緣于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關系不當。實際上,從大學發展史看,大學是最保守的。大學一方面在適應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在保持其自身的獨立性。自中世紀以來,大學是所存不多的古老組織機構之一,這得益于它的保守性。但是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能完全獨立于社會,大學也已經從“象牙塔”走向社會的中心,從學校走向企業。因此,從某種角度而言,“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大學作為一個特殊的、保守的機構,向往對自治精神的守護和對知識的追求是正常的,但是在大學與社會密切關聯的今天,大學能否堅守學術自由,崇尚認知理性,構建學術市場,這還需交給歷史來檢驗。
四、當代高等教育能否突破與超越“適應論”?
高耀明教授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大學已難以通過學術市場引領知識創新。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今天的大學甚至已經很少有能力引領知識的創新了。如今一些大企業的研發人員數量、經費投入,科研成果遠遠超過高校。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可以引領聯想集團嗎?非常難,因為聯想集團研發水平遠遠走在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前面。《理性的視角》認為“大學回歸認知理性、建設完善學術市場,是我國大學擺脫與突破‘適應論’思想束縛,引領整個社會未來發展的前提”,這一觀點似乎有些理想化。
胡國勇教授認為,在現今,高等教育已沒有能力突破與超越“適應論”而去引領社會發展。大學“服務社會”是為了大學的研究與教育,是為了強調自身公共性和證明大學自身存在的價值。以日本大學為例,日本政府國立、公立大學的產學合作政策初衷偏向通過產學合作,大學知識向企業轉移,促進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而其背后的真實意圖是大學通過自身的知識生產,以專利形式向企業轉移,獲取收益,而減少政府的負擔。像東京大學、首都大學東京這樣的國立、公立大學都在服務社會的路徑選擇時強調自身公共性,弱化市場化的產學合作。并且,大學知識向企業轉移的前提是大學的知識水平應該比企業更加卓越,知識活動也更加活躍。但事實上,從日本產業整體看,大學具備這種條件似乎是過去而不是現在。知識水平很難有適當的評價指標,只能參考投入因素,日本企業研究經費投入總量超過大學是1959年,研究人員數超過大學是1980年。2010年,日本企業的研究經費合計達11兆9838億日元,而大學卻只有3兆4340億日元;企業研究人員人均研究經費為2443萬日元,而國立大學研究人員人均研究經費為2161萬日元,公立大學為1469萬日元。除基礎研究領域,很難說大學研究實力優于企業。東京大學希望通過產學合作培養人才,并非自謙。因此,在現今,高等教育決不可能突破和超越“適應論”;相反,高等教育只有適應社會,才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才能更好地服務于自身發展。
博士生劉培軍認為,教育具有雙重功用,即外在的社會性和內在的學術性。雖然,教育系統有著它自身的目標和相對獨立的存在價值,但相對于整個社會大系統而言,教育子系統的存在僅僅在作為手段服務于整個民族或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時才具有意義。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的子系統,不可能超越或擺脫社會的約束與制約;高等教育對知識創新和內部結構的調整,也是在社會的驅使或拉力下進行的。恩格斯曾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求,則這種需求就會比10所大學更能把科學向前推進。”現代大學對新知的探究,來自于社會的動力遠比基于閑逸好奇的興趣更有力量。其次,大學的理念也是在適應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變遷的。以20世紀80年代美國本土面向高科技轉型為例,由于企業或社會需要伴隨著高利潤的高科技,于是他們把目光轉向大學,要求大學貢獻高科技產品,加入占領市場、淘金掘銀的浪潮。這種要求導致了大學服務社會理念的轉變,由大學自主的學術教學研究傳統,開始向為企業和市場服務轉變,于是出現了現今諸多的校企合作模式。第三,在當今社會,相較企業而言,高等教育的科學與技術創新能力越來越弱,引領社會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甚至根本無法引領社會發展的潮流與趨向。根據我國科技部科技統計公報數據顯示,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是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的三大執行部門。2011年我國企業R&D人員216.9萬,約占75.2%;研究機構R&D人員31.6萬,占11.0%;高等學校R&D人員29.9萬,占10.4%;其他9.9萬,占3.4%。從R&D人員的分布看,我國科學研究主要依賴企業和研究機構。從2011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R&D經費支出看,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6579.3億元;政府屬研究機構經費支出1306.7億元;高等學校經費支出688.9億元。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分別為75.7%、15%和7.9%。2011年我國共登記重大科技成果44208項,其中企業完成18064項,占40.9%,是主要的重大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因此,從以上數據可知,高等教育根本無法引領新知識與技術發展方向,更談不上突破與超越“適應論”了。
總之,參與沙龍討論的教師和研究生認為,《理性的視角》是一篇非常有價值的論文,使用了當前社會政治語境下較為安全的視角,討論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問題,核心是中國高等教育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必須解決的且沒有找到很好解決辦法的問題。高等教育“適應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強調“適應論”不會阻礙高等教育的發展,關鍵是要認清“適應論”的內涵。從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看,“適應”是高等教育基業長青的前提,回歸“認知理性”不僅不會突破或超越“適應論”,而且要求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遵循“適應論”。回歸“認知理性”包含在了“適應”社會之中,與“適應”社會是完全一致的。
- 大學教育科學的其它文章
- 大學院校中的核心文本——柏拉圖的《斐德羅篇》與孔子的《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