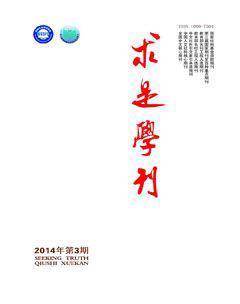“士”與錢穆的文化歷史觀
摘 要:由“以士釋史”所體現出來的錢穆之文化歷史觀,不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領導“中國史之演進”以及“歷史即文化”等觀念,還緣起于他對晚清民國史學界“考訂派”與“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評與糾偏。錢穆“以士釋史”的文化歷史觀的價值與意義在于,通過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士”來說明中國歷史道路、社會性質和文化精神的獨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觀念生硬解釋本國歷史的不當做法。但錢穆在“以士釋史”時,簡化了中國歷史演進中事實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把“士”作為一個終極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國史演進中的解釋力。以錢穆為代表的“文化史學”是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錢穆;以士釋史;文化史學;新史學
作者簡介:謝進東,男,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教師,從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
基金項目:東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校內青年基金項目“現代性與現代中國史學的演進”,項目編號:11QN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課題“中西文明歷史經驗中的公共社會價值觀研究”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2-0153-07
錢穆(1895—1990)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位重要學者,主要以研治中國歷史與文化為主。借助于文化來研究歷史,是錢穆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論,他認為研究歷史就是要研究歷史背后蘊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1](序,P1)[2](P7)那么,錢穆究竟是如何借助文化來研究歷史的?筆者通過對錢穆國史著述的考察,提出:錢穆主要是通過在他看來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士”來闡釋國史及其演變的。錢穆為何主張以“士”來闡釋國史及其演變?他又是如何通過“士”來進行國史闡釋的?其“以士釋史”之合理性依據何在?其通過“以士釋史”而表現出來的文化歷史觀之形成是否有它特定的學術史背景?此文化歷史觀在中國史學學術史上的影響如何?以上便是本文努力解決的問題。
一、“以士釋史”:錢穆的文化歷史觀
歷史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歷史認識的結果。受不同歷史觀影響的學者,對同種歷史會形成不同的認知樣貌。唯物史觀的倡導者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強調經濟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以社會生產的發展作為探討中國古代社會變遷的主線,將中國古代社會的歷程劃分為原始公社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幾個階段。[3](P154)受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影響的雷海宗,則以文化作為解析中國歷史的基本依據,以中國的“兵”文化(或稱之為兵的精神、尚武精神)的興衰、有無作為探尋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基本線索,將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為界分為兩大周,提出了“中國文化的兩周”說命題,試圖突破將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生硬地套用在中國史上的做法。[4](P131-160)基于經濟與文化的這兩種不同歷史觀,導致了對中國歷史分期的不同看法。然即便是同樣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歷史,若依據的文化內容不同,那么,所獲得的認識結果也會不盡相同。與雷海宗依據中國的“兵”文化提出“中國文化的兩周”說不同,錢穆依憑中國的“士”文化或“士”精神來闡釋國史,把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下的社會視為一個整體,稱之為由“士”階層作為“領導之基礎”的“四民社會”。[5](P561)
錢穆為何主張以“士”作為闡釋國史的依據呢?這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5](P561),“中國歷史上社會變動,主要就變動在士的這一流。士的變動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變動”[6](P108)。問題是,“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以至可以“主持與領導”中國史之演進、影響到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動?錢穆的回答,即“士是中國社會的領導中心”。他指出,士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定知識分子階層,是自戰國以后逐漸取代沒落貴族而“成為此下中國社會一領導的新中心”。[7](P121)錢穆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分合、治亂,以及學術文化之傳承、傳統社會之賡續,皆與“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息息相關。這些作用和影響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
其一,秦之統一,南北朝世運之支撐,傳統社會之賡續,學術文化之傳承,全靠士階層之擔當與堅守。在錢穆看來,士對于秦之統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論秦之統一天下,其主要動力,亦在六國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貴族。”[7](P45)錢穆認為,魏晉之后南北朝“世運的支撐點,只在門第世族身上”[5](P272)。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積貧積弱較為嚴重的一個時期,不過錢穆認為,政府貧弱并不影響學術發展,只因士階層在朝廷養士尊士的風氣中復興起來,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學術轉益興盛。[7](P49-50)元清兩代,蒙、滿入主中原,社會局勢大變,但在錢穆看來,由于士階層的堅守,中國學術文化傳統還是依然保持、傳承了下來。[7](P50-51)
其二,東漢王室之傾覆,魏晉清談之禍國,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會”,明代政治之下滑皆由士之離心力漸長、崇尚清談、輕薄及不受重用所致,盡管終未致傳統社會崩潰,文化命脈全絕。錢穆認為,東漢末年王室之傾覆,并非由于黃巾軍所致,而實為當時名士之離心力逐漸長成的結果。[5](P214-215)魏晉時期的分裂局面,在錢穆眼中亦是此一時期的名士清談禍國的結果。[5](P219-222)隋唐時期,科舉制度興起,為士階層參與政治、進入社會領導中心廣開進路,此后之社會似應漸趨開明。然錢穆以為,從唐之中葉到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個時期,或稱之為“黑暗社會”,雖然此時傳統社會猶未徹底崩潰,文化命脈尚未全絕。這一時期社會之所以黑暗,在錢穆看來,是由于當時朝廷以詩賦文學取士,造成進士輕薄,士之內在精神盡失,社會之領導中心亦隨之喪失。[7](P49)錢穆從中國傳統政治是一種士人政治的角度出發,認為明代政治“走上歧途”,是由明太祖以一己私意,逆“尊師相,抑君權”之歷史潮流而動,對士人的抑制造成的。[5](P668-669)
錢穆從中國社會中的“士”這一特殊階層出發,對中國歷史上由秦至清涵括各重要朝代的社會興衰、治亂與分合,以及這一長時期的學術傳承和社會賡續,進行了一種視角新穎而又見解獨到的通觀性文化式解讀。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運用以“士”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本國歷史進行釋讀的文化歷史觀。這種依據文化自身特點來解釋歷史的做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錢穆這種試圖僅從士的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變化來解答中國近兩千年的復雜社會歷史變化的做法,又顯得有些不夠周全。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這種歷史解釋方式,實際上是過于簡化了中國歷史演進中的復雜事實及其矛盾性,而同時夸大了士在其中的影響力。在錢穆看來,秦之統一從最根本上來講是由當時游士之“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所促成的[7](P12),雖然他也承認其中有“秦國地勢之險塞及其兵力之強盛”的因素。[5](P120)這種解釋顯然忽略了秦并六國之前的社會已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朝著統一的趨向走去。呂思勉就認為,秦之統一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8](P323)。再如,錢穆認為,西晉滅亡,天下瓦解,主要是由名士清談誤國所致。名士清談即便是西晉滅亡的原因,那么,這種原因是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根本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陳寅恪雖認為西晉社會變亂在名士清談的風氣中孕育,亦只承認“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9](P52)張齊明則認為:清談誤國只是西晉亡國的一個歷史表象,其敗亡的真正原因除了石勒等強大軍事壓力外,還有在晉武帝時就已埋下的禍根:行“封建”封諸侯,“罷州郡之兵”,對東漢以來形成的“五胡內附”的民族雜處局面缺乏足夠的駕馭能力,更為嚴重的錯誤是晉武帝所托非人,“儲后不順”。[10]
其次,錢穆在以“士”之本身地位的變化來解釋中國歷史上的社會變動時,把“士”作為一個終極原因,而未在其著述中進一步闡明士之本身變化的社會根源。在錢穆看來,中國歷史上的社會興衰與分合,實由士之不同身份及精神氣質在不同時期所產生的影響所致。然而,游士在秦并六國之時能夠抱持“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何以到了東漢末年,士之離心力卻漸長終致王室傾覆?西晉末年,名士崇尚清談以致誤國,何以到了南北朝,門第卻成為世運支撐的核心力量?又何以到了中唐至五代,進士卻又輕薄以致出現“黑暗社會”?同樣是士,為何在不同時期出現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進而造成絕大差異的社會面貌?士的不同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有何社會根源?如果不從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去探尋士之本身變化的緣由,那么,僅以士本身的變化為基點而作出的關于歷史演變的解釋,似總有一種霧里看花終隔一層的感覺。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錢穆“以士釋史”的一個缺憾。
二、“以士釋史”之依憑:“歷史即文化”
錢穆為何主張“以士釋史”?其理論依據何在?這對于他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變動”以及領導“中國史之演進”外,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將歷史與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由于錢穆主張“歷史即文化”,故研究歷史即研究歷史背后的文化,從根本上說即研究歷史背后的文化精神。而中國文化的精神,主要就體現在“士”階層上。故而,“士”的精神,即中國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中國歷史精神,亦即中國歷史的領導精神。所以,錢穆認為研究中國歷史,就應從其歷史的領導精神,也即“士”精神入手。也即,只有從“士”入手,才能探究到本國歷史的深意。
在錢穆看來,“歷史與文化,此二者實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了歷史,才有文化,同時有了文化就會有歷史。也可以說文化是‘體,歷史是此體所表現的‘相”[11](P1)。對于他來講,文化與歷史之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體、相關系,就在于它們分別是人生和對人生的記載:“文化即是人生,歷史乃是人生之記載。故可說,文化即歷史,歷史即文化。文化不同,歷史亦不同。文化變,歷史亦隨而變。文化墮落,歷史亦中斷。”[12](P123)
對于錢穆而言,“歷史即文化”不僅是因為它們都是有關人生之事,還在于它們同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現”。他認為,歷史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都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識融合而始有的一種精神”。所以,對于錢穆而言,“民族、文化、歷史,這三個名詞,卻是同一個實質”,故“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2](P6-7)而“中國歷史精神,實際只是中國之文化精神”[12](P147)。
既然研究歷史,就應找尋歷史之精神,而中國歷史之精神,即中國文化之精神。那么,何為中國文化精神?錢穆認為:“中國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則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13](P132),而這種道德精神主要即體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即“士”階層身上。錢穆認為:“士”十足地表現了中國文化傳統之完整性,擔負著中國社會人群之所以成其為社會人群之“理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充分說明了“士”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所在。[14](P87-92)錢穆還曾多次強調士對中國文化產生的意義與影響,認為士的精神與傳統即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傳統[6](P127)。對于錢穆來講,士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也即中國歷史精神。而他又認為:“所謂歷史精神,就是指導這部歷史不斷向前的一種精神,也就是所謂領導精神。”[6](P116)這樣一來,中國歷史的領導精神就具體體現在“士”的精神上。所以,錢穆認為:“中國的歷史指導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6](P129)對于錢穆而言,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士”,從根本上體現了中國歷史的領導精神,那么,由“士”切入來研究中國歷史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上述可見,錢穆探尋到歷史背后的領導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即“士”的精神。所以,錢穆雖主張“士”“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變動”、領導“中國史之演進”,但實際上強調的是“士”的精神在中國歷史演進中的關鍵性作用。知此便不難理解錢穆所強調的“士”之“大同觀念”、“離心力”、“好名”、“輕薄”對秦之統一、東漢王室傾覆、西晉滅亡、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會”所造成的決定性影響。這里的“大同觀念”、“離心力”、“好名”、“輕薄”,即指“士”的精神。其實,錢穆在其著述中經常使用“精神”、“意識”、“理性”等形而上的概念來指代歷史演進的動因。繆鳳林認為錢穆所使用的這些概念,“其義實與學術思想略同;論諸名之本身,雖富有形而上學的含義,但作者原旨,并不含形而上學的意義”[15]。即便不含形而上學的含義,錢穆在解釋歷史進程之動因時所指的“士”精神或學術思想,都表明他在思想與實踐之間更注重前者在歷史演進中的決定性作用。王晴佳就曾指出:錢穆歷史觀的基本特點,即“認為歷史的運動由一種形上的、唯心的力量操縱。與這一力量相比,表現在歷史中的所有變化,如制度的變遷、朝代的衰降、宗教的侵入,都只具有表面的意義”[16](P97)。
錢穆的這種過于看重思想的歷史觀在《國史大綱》中則又常常表現為,特別重視學術思想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曾表明:其治國史,“當于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于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著眼于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于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5](引論,P11-12)。不過,通讀《國史大綱》后就能體會到,錢穆即便在論述到秦漢、魏晉時期的歷史演變時,仍然注重的是“士”的精神或學術思想而非政治制度或社會經濟在這一時期社會變動中的影響力。對此,王晴佳亦曾做過評論,“雖然錢穆在‘引論中說他會‘于客觀中求實證……但他在實際寫作當中,則不完全能保持與他的設想一致。體現中國歷史精神的學術文化,往往成為他解釋歷史變化、朝代更替的終極原因”[16](P95)。總之,由于錢穆從精神層面來把握文化與歷史,進而將二者視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體、相關系,以致其在國史闡釋中更傾向于思想(如“士”的精神)而非實踐(如“士”的行為)在歷史進程中的終極影響,這在歷史動因的解釋問題上似有一種舍本求末之嫌。
三、錢穆文化歷史觀的緣起、意義與不足
由“以士釋史”所體現出來的錢穆之文化歷史觀的形成,除源于他所持守的“歷史即文化”、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及領導“中國史之演進”等觀念外,還有其特定的學術史背景,即主要針對晚清民國史學界之“考訂派”、“革新派”之弊病而展開的批評與糾偏。
錢穆將當時之史學劃分為三派:傳統派(記誦派)、革新派(宣傳派)、科學派(考訂派)。傳統派暫且不論,就“考訂派”與“革新派”而言,錢穆認為,這兩派之治史各有優長和弊病,但總體而言皆是弊大而優小。他指出:“考訂派”偏于歷史材料,精密有加,但“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5](引論,P3-4)。在錢穆看來,像“考訂派”這種治史方式是他極不認同的。因為如此,便不能在通曉本國史實的基礎上把握其文化獨特精神之所在,而這恰恰是錢穆所強調的治國史之第一要務。[5](引論,P11)
“考訂派”史學的上述缺陷,“革新派”似能補救,因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綰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然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錢穆同時看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彼對于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于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彼等乃急于事功而偽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于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于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于國史,乃最為無識也。”[5](引論,P4)
在錢穆看來,因“革新派”智識之不真而造成的國人最大之無識,即認為中國自秦以下之兩千年只是一個“專制政治”或“封建社會”。這些不真的歷史智識實際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國相繼發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過程中,為了其政治宣傳從胸中臆測而來,并非他們據實從歷史材料中概括得出。[5](引論,P5-6)錢穆認為,此所謂“專制政治”、“封建社會”的說法,“只是把中國歷史硬裝進西方觀念中,牽強附會,實際毫無歷史根據可言”[1](P39-40)。對于他來講,這種依據西方觀念來解釋中國歷史的做法,是難以接受的。因為中國與西方的歷史道路與特征本不相同,何以削中國歷史之足以適西方觀念之履?而這種不同從根本上說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7](P120)
基于中、西方歷史之不同,錢穆認為研究中國史不應據于西方觀念,而應訴諸本國史實,這也是他研究中國史所持的一貫立場:“研究中國史的第一立場,應在中國史的自身內里去找求,不應站在別一個立場,來衡量中國史。”[13](P281)出于對“革新派”據西方觀念附會中國歷史之做法的反駁,加上他意識到歷史受文化之影響最大,錢穆從中國史的自身內里去尋求到了闡釋本國歷史的根據,即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士”。而這種以“士”來闡釋本國歷史的做法,又能很好地展現出本國歷史的系統性和文化精神的獨特性,這對于“缺乏系統,無意義”的“考訂派”史學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糾偏作用。所以說,錢穆“以士釋史”的文化歷史觀,是在對“革新派”和“考訂派”的批評和糾偏中形成的。
此處實際上已經指出了錢穆“以士釋史”的文化歷史觀的價值與意義之所在,即通過“士”來說明中國歷史道路、社會性質和文化精神的獨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觀念強說本國歷史的不當做法。比如,針對當時在國人中盛行的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即所謂“封建社會”、“專制政治”的說法,錢穆就試圖從“以士釋史”的角度,以中國自秦以下所成立的士人政府及其通過公開察舉考試所體現出來的民主政治予以批駁[7](P46)[1](P27-28)。
說中國是“專制政治”或“封建社會”,實際上是運用根據西方歷史歸納出來的“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再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這一發展圖示來解釋中國社會形態演進的產物。在這種解釋框架下,常有人說,中國社會“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1](P43)。錢穆則反駁說:“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5](引論,P22)此所謂“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對于錢穆而言,即主要是指士人政治觀念。可見,在他看來,士人政治觀念對中國社會形態演進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主要是從中國“社會中‘士的一階層之地位變化,來指出中國社會演進之各形態”[1](P47)。具體就中國是否為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錢穆主要是在對中、西方歷史的比較中,從“士”所倡導的以“人道人心人本”為特征的文化精神和其所抱持的低水準的經濟觀兩個方面,來論說中國之所以不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緣由。
錢穆指出:“中國四千年來之社會,實一貫相承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會”,“修明此道以為社會領導中心”之“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西方社會“乃是一工商社會,進而變成資本主義之社會。與中國人道人心人本社會之本質,仍有其大不同處”[7](P63)。錢穆認為,中國士階層所持有的低水準的經濟觀,亦構成中國社會在封建政制崩潰以后不走向工商業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個根本原因。他分析說:“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即以經濟對人生之必需為最高限度。中國歷史上的各項經濟政策,也都據此來做決定。而“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故中國以農立國。這都源于“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而“西方歷史主要即在求不平”,奉行的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觀,即經濟水準超出了人生所必需之限度。“工商業,則頗易于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于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他進而指出:與工商業發達的西方社會不同,中國之所以走上以農立國的歷史道路,并與西方超水準之經濟觀不同,形成了一種以人生必需為主的經濟觀,其關鍵就在于“士”階層的人生理想與經濟理論所起的主導作用。[1](P57-66)因此,錢穆說:“中國社會決不能而且亦斷不該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及現代世界潮流趨向的人,所同樣首肯的。”[7](P39)
錢穆由“士”階層及其所持守的文化精神和經濟觀念,來說明中國歷史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無論如何不會走向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這種從中國文化及政治觀念來說明中西方歷史演進差異的做法,是一個非常獨到的觀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不過,錢穆在此論說過程中亦同樣夸大了“士”的影響力。“士”階層所奉行的文化精神和經濟觀念,對于中國歷史上長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究竟占據多大的分量,還需進一步討論。中國傳統社會以農立國,工商業未及西方那樣發達,也未必全是由“士”精神所致,如地理環境也會有所影響。黃河、長江等江河兩岸地區,陽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適宜耕種,為中國農業發展、以農立國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其實,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將中、西方文化分別定位為農業文化和商業文化時也已注意到了這一點。[17](P15)錢穆主要以“士”來論說中國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反映出他過于強調“士”在中西歷史演進差異中的影響。
結 語
何為中國“新史學”?錢穆的史學是否屬于“新史學”范疇?在許冠三看來,錢穆未必是。否則,錢穆就不應該在其《新史學九十年》中缺席了。那么,許冠三所謂的中國“新史學”有什么特征呢?許冠三在該書中指出:“從新會梁氏朦朧的‘歷史科學和‘科學的歷史觀念起,新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歷來的巨子,莫不以提高歷史學的‘科學質素為職志。”[18](自序,P2)可以看出,“科學”的質素應該是許冠三所認同的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內涵。他在論中國“新史學”時主要涉及了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料學派、史觀學派等,它們顯然都具有科學的特質。前三派都同樣注重運用科學的方法對歷史材料進行實證研究,單從以科學實證精神考訂史料的角度看,它們大體皆可歸為“史料學派”。這一派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注重史料研究而忽略對歷史的闡釋。故而,歷史的意義在這派史學研究中不易展現。“史觀學派”的科學特征,則集中表現在注重從史實中尋求歷史規則,而這種尋求在世界歷史視域下,則又傾向于追求普世性的通則。對這種普世性通則的追求,又常以犧牲事實、忽略歷史個性為代價。此“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恰與錢穆所謂的“考訂派”與“革新派”相應和。基于對以上兩派之不注重歷史意義或忽略歷史事實及個性精神的體察,錢穆主張并踐行由體現中國文化精神的“士”來闡釋國史,以求從中國史自身事實中發掘本國歷史文化之獨特精神與意義。在錢穆看來,這恰是中國“新史學”成立之基礎。他曾在《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斷言:“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已往之進程與動向”,“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已往之動態,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1](附錄,P156,159)就此而言,在《國史要義》中標舉“以禮釋史”的柳詒徵,認為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禮”是“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9](P11),也應屬于錢穆所謂“中國新史學”的一員。在此姑且稱此類“新史學”為“文化史學”。只不過,錢穆的這種“文化史學”與以“實證”和“規則”為主要特征的“科學”之間的距離略遠了一些。實際上,錢穆在治史的早期就是以“考史”成名,主要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劉向歆父子年譜》。但他很快因抗戰的關系,開始改以“著史”為業,旨在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精神的價值與意義。[20]這大概就是錢穆與許冠三對中國“新史學”的不同體認吧。或許,恰是這種不同體認,成為錢穆在《新史學九十年》中缺席的一個重要因素。然這種缺席,卻從側面反映出20世紀中國“新史學”學術史上的多元面相。實際上,在“文化史學”與“史料學派”、“史觀學派”之間原無根本性的沖突和對壘,它們在史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上本可做到相互補益,相得益彰。從這個意義上說,以錢穆為代表的“文化史學”與以史料學派、史觀學派為主的“科學史學”,可同被視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山脈中的兩座山峰。
參 考 文 獻
[1]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 錢穆:《民族與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7] 錢穆:《國史新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8] 呂思勉:《中國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10] 張齊明:《魏晉“清談誤國論”是怎樣形成的》,載《光明日報》,2011年8月25日(11).
[11] 錢穆:《中國文化叢談》,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1.
[12]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 錢穆:《歷史與文化論叢》,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14] 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5] 翟宗沛:《評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載《文史雜志》,1942年第4期.
[16] 王晴佳:《錢穆〈國史大綱〉之歷史觀分析》,載李明輝、陳瑋芬主編:《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地域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17]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8]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3.
[19] 柳詒徵:《國史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0] 王晴佳:《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系》,載《臺大歷史學報》,2000年第26期.
[責任編輯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