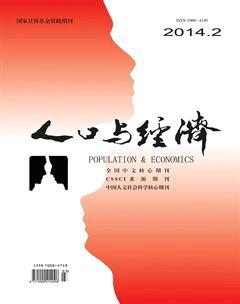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異研究
李樹茁+王維博+悅中山
摘要:農民工是否打算居留城市,不僅關系到農民工自身的發展,而且對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重要影響。本文使用2012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運用多元Logistic回歸方法,對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異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存在顯著差異,與受雇者相比,自雇者更傾向于居留城市。影響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還有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社會參與、心理融合、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自雇者居留意愿更多受到經濟因素影響,而受雇者更多受到社會、文化和心理因素影響。最后討論了上述研究結果的政策意義。
關鍵詞:自雇;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2-0012-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2.002
收稿日期:2013-09-17;修訂日期:2013-12-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民工的社會融合與心理健康研究”(13CRK015);西安交通大學985-3項目。
作者簡介:李樹茁,
工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王維博,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悅中山,管理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ttlement Intentions between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s
LI Shuzhuo1, WANG Weibo1, YUE Zhongshan2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Using data from 2012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this paper compares settlement intention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between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d migrants by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ttlement intentions. The selfemployed are more inclined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compared with the employed. Besides this, culture integrat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The economic facto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selfemployed migrants, while the intentions of selfemployed are more affected by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We discus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Keywords:selfemployed migrants; employed migrants; ruralurba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出現了大規模的增長,其中絕大部分為鄉-城流動人口,即所謂的“農民工”。農民工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農民工進入城市以后,隨著其對城市生活的逐漸適應、經濟狀況的好轉以及社會資本的不斷積累,勢必面臨著城市居留的抉擇問題。尤其是在大力推進城鎮化的當下,對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再次關注,顯得更為重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農民工被認為是城市的“匆匆過客”。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工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終將在城市定居下來,并轉化為城市人口[1]。農民外出打工出現了從半城市化的勞動力遷移狀態向遷徙式轉變的跡象,已經越來越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流動,而且有了更深刻的人口城鎮化含義[2]。農民工是否能夠居留城市,已經成為實現人口城鎮化的重要環節。國家對這一問題也非常重視。“十二五”規劃提出,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3]。因此,農民工能否居留城市,不僅對農民工個體長遠發展具有影響,而且對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特別是實現人口城鎮化具有促進作用。此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還有助于政府掌握農民工動態,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統籌城鄉一體化建設以及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意義。
以往對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研究主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大部分研究把農民工作為一個整體對待[4~5]。事實上,農民工已經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它出現了內部分化。唐燦等通過對北京“河南村”從事廢品收購行業農民工的研究表明,作為一個統一身份的農民工其內部已經出現了“二次分化”,形成若干類別群體或等級群體,并且這些等級群體在資本占有、經濟收入、社會聲望、價值取向上存在很大差異[6]。還有學者從代際認同角度分析了農民工的分化,認為農民工已經出現代際間的變化,在許多社會特征上存在差異[7]。據此,有學者從代際的視角對農民工發展意愿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表明,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在發展意愿上存在差異[8~9]。但農民工內部差異不僅僅表現在代際上,其構成正日趨多元化。有學者對自雇和受雇移民或農民工進行了研究,發現自雇者和受雇者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和發展前景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并且自雇者優于受雇者[10~13]。可見,農民工內部差異還表現在就業身份上。而這種差異其實是農民工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不同,使得自雇和受雇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上大相徑庭,從而導致在是否打算居留城市的抉擇上出現差異,可能自雇者比受雇者更愿意居留城市。
第二,多數研究將農民工居留意愿分為“打算”居留和“不打算”居留兩種決策,而把“沒想好”這部分人群從樣本中剔除[14~16]。但近期的研究顯示,“沒想好”這部分人群占有較大比重,農民工既表現出對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現出一種矛盾和模糊的心理狀態[17]。因此,這部分人群也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本文綜合考慮了農民工居留意愿所有可能的情況,將其分為“打算”居留、“不打算”居留和“沒想好”三類。
鑒于此,本研究主要有三個目的:①考察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②從個人特征、流動特征和社會融合三方面分析影響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③比較自雇和受雇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居留意愿影響因素上存在的差異。
二、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
1.影響農民工居留意愿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理論都可以用來對農民工的城市居留決策做出解釋。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只要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現代部門[18]。而托達羅模型從“成本-收益”或“收入凈剩余”最大化角度解釋農民工的居留決策,認為城市中的預期收入乘上城市就業概率減去外出的成本后若為正值,農民工才會進城。相反,一個已經外出就業的勞動力決定回流的條件,就是繼續外出將得不償失[19]。托達羅引入城市就業概率變量,完善了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此外,最具影響力的“推-拉”理論認為,農民工“留”或“返”是農村和城市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19]。還有社會學中的社會網絡理論也對居留意愿做出了解釋,認為社會網絡的多寡、強弱等都會影響農民工的居留決策[20~22]。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影響農民工居留意愿的因素是多樣化的[23]。因此,單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不足以解釋居留意愿,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合已有研究,本文將影響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個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等。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有顯著影響[24~25],而有研究則表明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不顯著[26]。可見,受教育程度對居留意愿的影響還存在爭議。第二,流動特征,主要包括流入時間、流動距離和流出地類型。進城時間越長,留城意愿越強烈[27~28]。流動范圍越大,居留城市的概率越小[29]。第三,社會融合因素。悅中山等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和發展意愿進行了研究,發現文化融合、社會經濟融合和心理融合三個維度對農民工發展意愿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30]。有學者發現社會經濟因素如職業類別、收入狀況和住房狀況也會對農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有顯著影響[31~32],由于這些因素與社會融合中的經濟融合重合,所以被劃歸到社會融合因素中了。
與悅中山等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其劃分的三維度基礎上[33~35],加入了“社會參與”這一維度。該維度是指農民工與本地市民的互動以及在流入地參加活動的情況,這也是當前反映農民工社會融合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最終將社會融合的維度劃分為四個方面,即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社會參與和心理融合。這種劃分并不一定囊括了社會融合的所有維度,但這四個維度是當前農民工社會融合研究中最重要的維度。
2.就業身份與居留意愿
泰爾沃(Tervo)通過對芬蘭勞動力市場的研究指出,勞動者就業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形式,分別是受雇(paidemployment)、自雇(selfemployment)和非就業(nonemployment)[36]。當然,我國農民工的就業也不例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已就業農民工,所以可將農民工就業身份分為自雇者和受雇者兩類。
國內外學者對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研究結果均表明,與受雇者相比,自雇者更具有優勢。有學者對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進行研究,發現自雇比受雇就業顯得更具有吸引力,主要原因是自雇比受雇能夠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能夠提高社會地位[37],并且為族裔群體中的個人乃至整個群體的向上社會流動提供了一條可行之道[38]。科爾曼(Coleman)進一步對從事自雇就業的前景做出了判斷,認為選擇自雇就業對少數族裔以及他們個人和家庭來說,是一條通向富裕的可能途徑[39]。
國內學者李培林對農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的研究表明,占有相當生產資本并雇傭他人的業主的經濟社會地位比一般進城打工者要高得多,他們中有更多的人認為自己屬于城市中等偏上階層[40]。吳曉剛的研究表明,在市場轉型過程中,自雇者在經濟收入方面是贏家,并進一步指出,從事自雇就業是實現向上社會經濟流動的一個重要渠道[41]。進城農民首先選擇易于進入但條件較差的受雇就業,但基本趨勢是由受雇就業逐漸走向自雇就業[42]。自雇就業具有一定的經濟活力和發展前途,是農民工向城市遷移和城市適應的一條可能途徑[43]。還有學者對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自雇者更主動地去投資并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44~45]。還有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傾向于通過自雇經營獲得職業階層提升,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更是如此[46]。自雇經營者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與專業技術或管理人員類似的穩定高收入階層[47]。總之,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在社會階層、經濟地位、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和發展前景上存在差異,并且自雇者優于受雇者。
雖然已有研究發現了自雇和受雇農民工兩個群體存在諸多差異,但并未關注就業身份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響。本文在總結以往居留意愿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加入就業身份變量,主要考察就業身份是否會影響城市居留意愿。
三、數據與方法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2012年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實施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該調查采取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方法在全國流動人口聚集地對那些在城市中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年齡在15~59周歲的流動人口制作了抽樣框。關于數據的具體信息,請參見《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48]。該調查數據權威性強、樣本量大、代表性好。最終樣本量為158556個。
由于本文研究對象是在業農民工,所以刪除了城-城流動人口以及就業狀態為失業、無業、操持家務和退休的樣本,最終進入模型的樣本數為118390個,其中自雇者占總樣本的32.8%;受雇者占總樣本的67.2%。表1提供了變量基本信息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2.變量設置
因變量為城市居留意愿,是一種主觀態度,指農民工對自己是否打算居留城市所做出的判斷。通過題項“您是否打算在本地(流入地)長期居住”來將其操作化,答項包括打算、不打算和沒想好。
通過題項“您現在的就業身份屬于哪一種”將就業身份操作化,答項包括雇員、雇主、自營勞動者和家庭幫工。將雇主和自營勞動者視為自雇者,將雇員和家庭幫工視為受雇者。
控制變量包括社會融合、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其中社會融合又分為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社會參與和心理融合四個維度。
基于問卷,通過“休閑方式”情況來測量農民工的文化融合。將被訪者在“看電影、電視、錄像”,“玩棋牌、麻將、電腦游戲”,“上網瀏覽、通訊”,或“讀書、看報、學習”等四類活動中至少參與三項及以上的賦值為1,即休閑方式較豐富;小于3項賦值為0,即不豐富。
由于農民工擁有自購房的比例僅有5.3%,因此,未將房產擁有納入模型。本文用收入水平和職業階層測量農民工經濟融合的狀況。考慮到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相對比較同質,且大多數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從事“臟、累、險”的工作,所以將農民工的職業階層操作化為非體力勞動者和體力或半體力勞動者,如此能夠直觀地反映農民工所處的職業地位。收入操作化為農民工平均月工資的對數。
農民工的社會參與主要包括社會交往和活動參與。就社會交往來看,主要是指農民工與本地市民之間的往來。就活動參與來看,主要是指農民工是否參加社區文體、公益、選舉活動等。本文采用社會交往和活動參與兩個指標來反映農民工在流入地的社會參與情況,這些均被操作化為二分類變量。
本文通過3個題項,分別為“我喜歡我現在居住的城市”,“我關注我現在居住城市的變化”和“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當中,成為其中一員”來將心理融合操作化。答項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基于數據,計算得到Cronbachs Alpha值為0.875。在分析中,我們將每個題項的答案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別賦值為1、2、3、4。將3個題項的得分均值作為我們對心理融合的測量。
此外,控制變量中的個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狀況。流動特征包括流入時間、流動距離和流出地類型,詳細定義及操作化見表1。
3.分析策略
首先,采用交叉表描述自雇和受雇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的差異。其次,運用多元邏輯斯蒂回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將“不打算”一類作為參照組,研究農民工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最后,對自雇和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1.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比較
表2提供了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分布情況。LR檢驗結果表明,兩個群體在居留意愿上存在顯著差別。自雇者選擇“打算”居留城市的比例比受雇者高出16.4個百分點。“不打算”居留的農民工中,受雇者高于自雇者。可見,自雇者比受雇者更傾向于“打算”居留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有29.7%的農民工選擇“沒想好”,因此,將這部分人群納入分析是必要的。
自雇者在經濟融合、社會參與和心理融合等方面均比受雇者優越(見表1),兩個群體在城市的生存狀態存在差異。此外,有近三成多的農民工選擇“沒想好”,通過對數據的分析(見表3),與選擇“打算”和“不打算”居留的農民工相比,選擇“沒想好”這部分人在文化融合、經濟融合中的職業階層、社會參與和心理融合方面均處于中間狀態。也就是說,大部分農民工主觀上渴望居留城市,只不過“打算”居留城市的農民工在各方面的條件已經成熟或日趨成熟,“不打算”居留城市的農民工在各方面的條件尚不具備,在可預見的時間里似乎也難以改觀,而“沒想好”的農民工雖然已經具備一定條件,但仍差距很大,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未來的不確定性仍很大。因此,不妨形象地把“沒想好”的人群稱之為“夾心層”。
全樣本模型中,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到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變量之后,發現就業身份對農民工居留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以“不打算”為參照組,自雇者選擇“打算”居留的可能性是受雇者的1.5倍,自雇者選擇“沒想好”的可能性是受雇者的1.2倍。多變量分析同樣表明自雇者比受雇者更傾向于居留城市。
除就業身份外,文化融合、經濟融合和心理融合對農民工“打算”居留城市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一發現和悅中山等的研究結果一致,經濟融合對農民工發展意愿具有最重要的、最具決定性的影響,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則是預測農民工發展意愿的重要因素[49]。值得強調的是,本文在引入社會參與變量后,發現社會參與和其他社會融合維度一樣也是預測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教育、婚姻、流入時間和流出地類型對農民工“打算”居留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年齡顯著地降低了農民工“打算”居留的可能性。支持了以往研究關于教育對居留意愿有影響的發現。社會參與、心理融合、性別、教育、婚姻、流入時間對農民工“沒想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收入水平、年齡、流動距離和流出地類型有負向影響。可見,社會參與、心理融合、教育、婚姻、流入時間對農民工“打算”居留和“沒想好”的影響具有一致性。將發生比一一進行比較發現,在上述相應的變量上,農民工在居留意愿的選擇上偏好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打算”居留、“沒想好”和“不打算”居留,這一點也論證了選擇“沒想好”的農民工處于“夾心層”。而年齡對農民工“打算”居留和“沒想好”均具負向影響,即年齡越大,越傾向于“不打算”居留。
在自雇者模型中,文化融合對“打算”居留有正向影響,但對“沒想好”的影響并不顯著;收入水平越高的自雇者“打算”居留的可能性越大,但對“沒想好”不存在顯著影響;職業階層對自雇者居留意愿不存在顯著影響;至少參與一項活動的人選擇“打算”居留、“沒想好”和“不打算”的可能性依次降低;與本地人來往較多的自雇者傾向于“打算”居留,對“沒想好”的影響不顯著;心理融合對自雇者“打算”居留和“沒想好”都存在顯著正向作用,但對“打算”居留的影響更大;年齡顯著地降低了自雇者城市居留的可能性;教育對自雇者“打算”居留和“沒想好”都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婚姻對自雇者“打算”居留有正向影響,對“沒想好”的影響不顯著;流入時間越長,自雇者“打算”居留的可能性越大,對“沒想好”不存在顯著影響;與流出地是西部的自雇者相比,流出地是東部的自雇者選擇“打算”居留的可能性更大,其次是中部。
在受雇者模型中,文化融合對受雇者“打算”居留有正向影響,但對“沒想好”的影響并不顯著;收入水平對“打算”居留有正向影響,但對“沒想好”具有負向影響;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比從事體力或半體力受雇者“打算”居留的可能性要大,職業階層對“沒想好”的影響不顯著;社會參與和心理融合較好的受雇者在居留意愿上的決策偏好由高到低依次為:“打算”、“沒想好”和“不打算”。性別和年齡對受雇者“打算”居留的影響不顯著,對“沒想好”存在顯著影響,男性比女性更傾向于選擇“沒想好”,年齡越大越傾向于“不打算”;在婚、受教育年限越多和流入時間越長的受雇者的居留意愿的優先順序依次為“打算”、“沒想好”和“不打算”;跨省流動和流出地是中部的受雇者更可能選擇“不打算”;而流出地是東部的受雇者在進行居留決策時的優先順序依次為“打算”、“不打算”和“沒想好”。
通過對自雇和受雇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影響因素的比較,發現影響兩個群體居留意愿的因素存在著一些顯著差異。通過影響強度來看,收入水平對自雇者的影響強度較大,而文化融合、社會交往和心理融合對受雇者的影響強度較大。另外,職業階層對自雇者“打算”居留的影響不顯著,而對受雇者的影響顯著。可能的解釋是,自雇者在居留決策時比較重視自己的經濟實力,與受雇者相比,他們對其他方面有所考慮,但重視程度不如受雇者。與自雇者相反,受雇者在做居留決策時會比較偏重對文化融合、社會交往、心理歸屬和職業階層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而對收入的重視程度則不如自雇者。
五、結論
本文使用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于2012年組織實施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綜合考慮了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面臨的三種可能情況,分析了自雇與受雇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的差異,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下面就一些重要發現進行總結。
就業身份對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顯著影響,自雇者比受雇者更傾向于居留城市。除此之外,影響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還有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社會參與、心理融合、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影響自雇者和受雇者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存在差異,主要表現在:①職業階層對自雇者“打算”居留城市不存在顯著影響,而對受雇者的影響顯著。②年齡和流出地類型中的中部地區對自雇者“打算”居留城市具有顯著影響,而對受雇者不存在顯著影響。③收入水平、社會交往、性別、婚姻和流動特征對受雇者“沒想好”存在顯著影響,而對自雇者不存在顯著影響。④收入水平對自雇者和受雇者“打算”居留城市均有顯著影響,但對自雇者的影響概率更大;文化融合、社會交往、心理融合、婚姻和流入時間對兩者“打算”居留均產生顯著影響,但對受雇者的影響概率更大。⑤收入水平、社會交往、性別、婚姻和流動特征對受雇者“沒想好”存在顯著影響,而對自雇者不存在顯著影響。⑥心理融合對自雇者和受雇者“沒想好”均產生顯著影響,但對受雇者的影響概率更大。總體而言,自雇者居留意愿更多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受雇者更多受到社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響。
以上結論對更好地推動我國農民工的市民化以及真正實現城鎮化有著重要的政策啟示。首先,針對在城市居留意愿上占比例較大的“沒想好”這部分人群,我們將其稱之為“夾心層”,他們更多地處于兩難境地,左右徘徊。但他們是實現人口城鎮化的潛在人群,政府有關部門應該更加重視這部分人群,對其進行合理引導,這有利于政府部門很好地掌握農民工在城市的數量,從而保障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其次,針對自雇者比受雇者更愿意居留城市的情況,政府應該鼓勵更多的有條件的農民工自雇創業,合理引導受雇者在積累了資本之后轉向自雇就業,并為農民工自雇就業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使更多的農民工在城市居留,這對于保持城市的活力以及推進城鎮化,尤其是人口城鎮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在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或人口城鎮化的過程中,優先考慮自雇者。最后,針對自雇者和受雇者在城市居留意愿上的差異,應該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使他們盡早融入城市主流社會,最終在城市定居。
此外,本文的研究和發現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城市居留意愿更側重的是一種主觀上的態度,但其是否真正轉變為現實行為,還有待后續研究。其次,確實存在自雇和受雇組內差異較大的情況,而將農民工就業身份單一地分為自雇和受雇兩種,不夠細致,這是本研究下一步關注的重點。
參考文獻:
[1] 謝桂華.農民工與城市勞動力市場[J].社會學研究,2007,(5).
[2] 白南生,李靖.城市化與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8,(4).
[3] 中共中央 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年)規劃綱要[EB/OL].(2011-03-16)[2013-09-14]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6/content_2156007.htm.
[4] 曾旭輝,秦偉.在城農民工留城傾向影響因素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3,(3).
[5] 熊波,石人炳.農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響因素——基于武漢市的實證研究[J].南方人口,2007,(2).
[6] 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J].社會學研究,2000,(4).
[7]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
[8]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等.徘徊在三叉路口:兩代農民工發展意愿的比較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9,(6).
[9] Yue,Z.,S.Li,M.W.Feldman,and H.Du.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10,(3).
[10] Zuiker, V.S. Hispanic Selfemployment in the Southwest: Rising above the Threshold of Povert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8.
[11] Coleman,Susan. Is There a Liquidity Crisis for Small Blackowned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2005,(1).
[12] 吳曉剛.“下海”: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轉型中的自雇活動與社會分層(1978-1996)[J].社會學研究,2006,(6).
[13] 鄒宇春,敖丹.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社會資本差異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1,(5).
[14] 同[4].
[15] 同[5].
[16] 李楠.農村外出勞動力留城與返鄉意愿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0,(6).
[17] 葉鵬飛.農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社會,2011,(2).
[18] 倪志遠.論二元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道路[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97,(3).
[19] 白南生,何宇鵬.回鄉,還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2,(3).
[20]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21] Orrenius, P.M. Return Migration from Mexico: Theory and Evidence[D].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
[22] 吳興陸,亓名杰.農民工遷移決策的社會文化影響因素探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1).
[23] 吳興陸.農民工定居性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5,(1).
[24] 同[4].
[25] 同[19].
[26] 同[5].
[27] 同[19].
[28] 任遠.“逐步沉淀”與“居留決定居留”——上海市外來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6,(3).
[29] 任遠.誰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來?——對城市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4).
[30]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研究:現狀、影響因素與后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77.
[31] 同[5].
[32] 景曉芬,馬鳳鳴.生命歷程視角下農民工留城與返鄉意愿研究[J].人口與經濟,2012,(3).
[33]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構建與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12,(1).
[34] Zhongshan Yue,Shuzhuo Li,Xiaoyi Jin and Marcus W.Feldma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s:A MigrantResident Tie Perspective[J].Urban Studies,2013,(9).
[35] 悅中山、李樹茁、靳小怡等.從“先賦”到“后致”:農民工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融合[J].社會,2011,(6).
[36] Tervo, H. Self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Alternation in Finnish Rural and Urban Labor Market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8,(1).
[37] 同[10].
[38] Bailey, Thomas and Waldinger, Rog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Enclave Labor Markets: A Training System Approach[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4).
[39] 同[11].
[40] 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1996,(4).
[41] 同[12].
[42]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的進入條件和效果[J].管理世界,2008,(1).
[43]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44] 同[13].
[45] 王文彬,趙延東.自雇過程的社會網絡分析[J].社會,2012,(1).
[46] 許傳新.農民工的進城方式與職業流動——兩代農民工的比較分析[J].青年研究,2010,(3).
[47] 任鋒,杜海峰.社會關系再構建、職業階層與農民工收入[J].人口與發展,2011,(5).
[48]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
[49] 同[30].
[5] 熊波,石人炳.農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響因素——基于武漢市的實證研究[J].南方人口,2007,(2).
[6] 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J].社會學研究,2000,(4).
[7]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
[8]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等.徘徊在三叉路口:兩代農民工發展意愿的比較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9,(6).
[9] Yue,Z.,S.Li,M.W.Feldman,and H.Du.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10,(3).
[10] Zuiker, V.S. Hispanic Selfemployment in the Southwest: Rising above the Threshold of Povert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8.
[11] Coleman,Susan. Is There a Liquidity Crisis for Small Blackowned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2005,(1).
[12] 吳曉剛.“下海”: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轉型中的自雇活動與社會分層(1978-1996)[J].社會學研究,2006,(6).
[13] 鄒宇春,敖丹.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社會資本差異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1,(5).
[14] 同[4].
[15] 同[5].
[16] 李楠.農村外出勞動力留城與返鄉意愿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0,(6).
[17] 葉鵬飛.農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社會,2011,(2).
[18] 倪志遠.論二元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道路[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97,(3).
[19] 白南生,何宇鵬.回鄉,還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2,(3).
[20]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21] Orrenius, P.M. Return Migration from Mexico: Theory and Evidence[D].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
[22] 吳興陸,亓名杰.農民工遷移決策的社會文化影響因素探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1).
[23] 吳興陸.農民工定居性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5,(1).
[24] 同[4].
[25] 同[19].
[26] 同[5].
[27] 同[19].
[28] 任遠.“逐步沉淀”與“居留決定居留”——上海市外來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6,(3).
[29] 任遠.誰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來?——對城市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4).
[30]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研究:現狀、影響因素與后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77.
[31] 同[5].
[32] 景曉芬,馬鳳鳴.生命歷程視角下農民工留城與返鄉意愿研究[J].人口與經濟,2012,(3).
[33]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構建與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12,(1).
[34] Zhongshan Yue,Shuzhuo Li,Xiaoyi Jin and Marcus W.Feldma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s:A MigrantResident Tie Perspective[J].Urban Studies,2013,(9).
[35] 悅中山、李樹茁、靳小怡等.從“先賦”到“后致”:農民工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融合[J].社會,2011,(6).
[36] Tervo, H. Self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Alternation in Finnish Rural and Urban Labor Market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8,(1).
[37] 同[10].
[38] Bailey, Thomas and Waldinger, Rog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Enclave Labor Markets: A Training System Approach[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4).
[39] 同[11].
[40] 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1996,(4).
[41] 同[12].
[42]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的進入條件和效果[J].管理世界,2008,(1).
[43]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44] 同[13].
[45] 王文彬,趙延東.自雇過程的社會網絡分析[J].社會,2012,(1).
[46] 許傳新.農民工的進城方式與職業流動——兩代農民工的比較分析[J].青年研究,2010,(3).
[47] 任鋒,杜海峰.社會關系再構建、職業階層與農民工收入[J].人口與發展,2011,(5).
[48]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
[49] 同[30].
[5] 熊波,石人炳.農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響因素——基于武漢市的實證研究[J].南方人口,2007,(2).
[6] 唐燦,馮小雙.“河南村”流動農民的分化[J].社會學研究,2000,(4).
[7]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
[8]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等.徘徊在三叉路口:兩代農民工發展意愿的比較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9,(6).
[9] Yue,Z.,S.Li,M.W.Feldman,and H.Du.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2010,(3).
[10] Zuiker, V.S. Hispanic Selfemployment in the Southwest: Rising above the Threshold of Povert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8.
[11] Coleman,Susan. Is There a Liquidity Crisis for Small Blackowned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2005,(1).
[12] 吳曉剛.“下海”: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轉型中的自雇活動與社會分層(1978-1996)[J].社會學研究,2006,(6).
[13] 鄒宇春,敖丹.自雇者與受雇者的社會資本差異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1,(5).
[14] 同[4].
[15] 同[5].
[16] 李楠.農村外出勞動力留城與返鄉意愿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0,(6).
[17] 葉鵬飛.農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社會,2011,(2).
[18] 倪志遠.論二元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道路[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97,(3).
[19] 白南生,何宇鵬.回鄉,還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2,(3).
[20]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
[21] Orrenius, P.M. Return Migration from Mexico: Theory and Evidence[D].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
[22] 吳興陸,亓名杰.農民工遷移決策的社會文化影響因素探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5,(1).
[23] 吳興陸.農民工定居性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5,(1).
[24] 同[4].
[25] 同[19].
[26] 同[5].
[27] 同[19].
[28] 任遠.“逐步沉淀”與“居留決定居留”——上海市外來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6,(3).
[29] 任遠.誰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來?——對城市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4).
[30]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研究:現狀、影響因素與后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77.
[31] 同[5].
[32] 景曉芬,馬鳳鳴.生命歷程視角下農民工留城與返鄉意愿研究[J].人口與經濟,2012,(3).
[33]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構建與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12,(1).
[34] Zhongshan Yue,Shuzhuo Li,Xiaoyi Jin and Marcus W.Feldma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s:A MigrantResident Tie Perspective[J].Urban Studies,2013,(9).
[35] 悅中山、李樹茁、靳小怡等.從“先賦”到“后致”:農民工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融合[J].社會,2011,(6).
[36] Tervo, H. Self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Alternation in Finnish Rural and Urban Labor Market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8,(1).
[37] 同[10].
[38] Bailey, Thomas and Waldinger, Roger. Primary, Secondary, and Enclave Labor Markets: A Training System Approach[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4).
[39] 同[11].
[40] 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J].社會學研究,1996,(4).
[41] 同[12].
[42]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的進入條件和效果[J].管理世界,2008,(1).
[43] 萬向東.農民工非正式就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44] 同[13].
[45] 王文彬,趙延東.自雇過程的社會網絡分析[J].社會,2012,(1).
[46] 許傳新.農民工的進城方式與職業流動——兩代農民工的比較分析[J].青年研究,2010,(3).
[47] 任鋒,杜海峰.社會關系再構建、職業階層與農民工收入[J].人口與發展,2011,(5).
[48]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
[49] 同[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