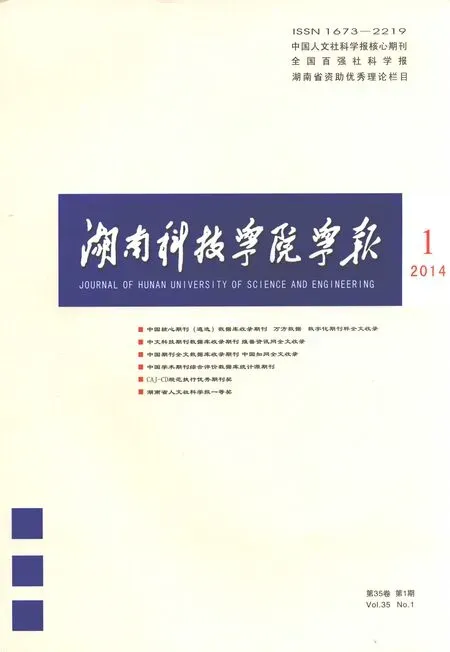《直報》時期嚴復自然法思想探析
張志杭
(西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重慶 401120)
嚴復是我國近代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的大師,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大的影響,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些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對嚴復的評價及其具體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不但沒有統一的認識,就是互相對立的觀點也很難為對方所認可,也就是說,對嚴復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雖然有相當深入和科學的研究,但基本上可以說是缺乏對話的,每一個研究方面都可能合理,但確無助于對嚴復思想本來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抵制了對嚴復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嚴復的翻譯影響太大,直接壓制了自己思想的獨創性,從而使嚴復對中國,對人類作出的富有見地貢獻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所幸的是,人們已經開始了新的反思,有許多新的評價,認為嚴復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文化巨匠。[1]當前,學術界有一種立足本土化的趨勢,這又對嚴復思想研究有極大的促進,我們相信,嚴復思想的普遍意義在新的視角,新的學術模式下會迎來一個全新的質的飛躍。本文就是立基于以上最新的學術趨勢,采取一個新的視角,來研究嚴復思想中的最為重要的一面,也就是現代中國從器物文明向制度文明轉化時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現在流行的說法叫富強或自由問題,我個人覺得實在應該是自然法問題的集中思考,這些問題是嚴復在尚未全面開始翻譯西方名著之前在《直報》上發表的政論文章的集中處理的,他可以有效地顯示嚴復獨特的思想和價值。我認為只有從細微處著手,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嚴復,也才能最為妥善地處理嚴復自己的文章和嚴譯名著之間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才可以將嚴復的獨特貢獻突出出來。
一 何為《直報》時期
對嚴復地位和作用的評價總與嚴復活動的時期有密切的關系,但學者們總將嚴復思想的創作與他翻譯作品的時期與清末變化多端的政治事件混淆在一起,所以很不容易給嚴復思想一個清晰的階段,從而難以梳理嚴復思想的基本內容和內在的邏輯。應該說,除嚴復最早期接受了儒家教育之后,很快就進入了西式學校的教育,然后就是在近代海軍供職,無論是青年時代順船出海,或留學英國,或回國后充當福州船政局教員或在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其前期的活動都是清晰的,這段時期對嚴復思想應當說有很大的影響,他的許多思想在這段時期應該說也有萌芽,也有相當的史料可以佐證,不過,現在整個說來該階段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而且整個說來,該階段嚴復的思想也難以說得上系統化,影響應該說也是有限的,除非找到新的史料,比如研究嚴復在水師學堂對那些后來在民國時期有眾大影響的北洋派學生的影響。因此,雖然嚴復并不是1895年在《直報》上才開始闡述自己的思想,在此之前也有作品,但以1895年作為嚴復思想前期的總結是可以的,因為在此之后嚴復就開始了規模龐大的翻譯工作,雖然有很多按語和其他文章,但整體上說都被翻譯的作品掩蓋了。所以,選擇這一段時期作為嚴復思想研究的起點和終極目標,應該說意義是多方面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直報》之前,嚴復的作品確實引不起足夠的重視,而在此之后的作品則建立了嚴復啟蒙思想家的地位,特別是從《天演論》譯作的流行之后。這種情況使我們往往忽視了嚴復在《直報》上發表的作品的重要價值。因此,我認為嚴復在《直報》上發表的論文已經全面體現了嚴復的思想,隨后的譯作不過是來補充和論證他的思想。
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嚴復作為北洋總教習很難說沒有受到非難,當然他還不可能如李鴻章一樣受到彈劾,但受到攻擊可說是再所難免的,否則以嚴復的謹慎小心,是不大可能在如此的非常時期連著發表幾篇重要的政論文章的,問題的另一面是,嚴復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深入的思考,也不可能在這么段時期內能寫作出來這樣邏輯清晰的作品。在《直報》上發,嚴復在短時期內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四篇文章,其中只有《原強》既有續篇又有修訂,當可認為嚴復思想的變化和完善。這四篇文章之后,嚴復就開始了他的翻譯之路,他自己寫作的文章主要也是1897年開始的《國聞報》了,因此,這四篇文章可以說一個獨立的單元,既沒有使用他后期翻譯的作品,更沒有民國建立之后認為共和完成,需要強調民族性質的讀經尊孔這樣的事件,可以說,他在這幾篇文章里無所顧慮的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我把這段時間稱為嚴復的《直報》時期。那么,在這些文章里,嚴復主要表達的思想從法學來看是什么,我認個是全面的展示了自然法的思想,這些自然法思想有的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內容,有些是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比較,處理的問題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廣。
二 《直報》時期自然法思想
古典自然法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建立和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產物,它構成了現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嚴復的自然法思想與清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國家間的對抗有關,他在《原強》中最為強烈地進行了中國歷史和中國與西方對法的比較,這是他法哲學中的歷史視野的展現,如果沒有進行歷史比較,嚴復的自然法思想將缺乏歷史的使命感,他在該文強調了有法與無法之區別,而這種對法和法律制度的認識正是自然法學得以成立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自然法學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在這里就已經預設了嚴復的激進和保守兩方面的認識,這并非嚴復性格使然,而是其理論本來就具有的內在矛盾。
(一)自然法思想的自由主義基礎
自由主義是近代民族國家建立以來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但自然法思想并不一定必然以自由主義為基礎,霍布斯就反對自然法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但他的自然法理論卻是近代以來自然法學最主要的支柱之一,而且他的自然法內容對后來自然法理論體系的建立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從總體上說,自由主義是自然法理論的基礎,自然法理論最基本的特征是啟蒙運動時期建立起來的,除了追求個人的權利和利益外,在啟蒙運動時期理性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其基本的主張就是主張個人權利的至上性,政治與法律和道德的分離,實際上就是近代化以來政治哲學家主張的個人主義和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在嚴復的前期文章里,嚴復也持這種基本主張,主張個人自治是國家富強和發展的基礎,法律和道德應該分離,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就沒有強調民智和民德,而是主張應該將兩者區別看來。也因此,嚴復在高度概括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和法律理論時,強調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意義,但中西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自由。在政治和法律領域,在《論世變之亟》里,強調中國與西方國家和社會最根本的區別就是自由的有無,西方強調自由的重要性,而中國政治傳統中卻缺乏對自由的研究,“未嘗立以為教”,對自由的冷漠或仇視成為中國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但什么是自由卻是需要界定的問題,在后來翻譯密爾《論自由》時嚴復對此作了認真的學理探討,不過,在這里,他已經對自由進行了說明,指出,自由是一種自然權利,是自然(天)賦給人的,如果說這是對自由本體的解說,那么,嚴復接著卻說明了自由的政治意義和實踐價值,指出,人人都有自由,國家也有自己的自由,這應該說是對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后對個人與國家關系的高度升華,國家自由主要是主權意義上說,當然學術界對自由和自主等的概念的區分還不是太清楚[2],但這并沒有損害嚴復在這方面的洞察,而且,自由主要是“令毋相侵損”[3],這就是后來伯林強調的消極自由。
所以自由既是民主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是人存在的意義所在,因此,自由是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核心范疇。嚴復在《直報》時期表達的自由主義思想,不僅僅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還有社會意義上的東西方社會異同因“自由不自由”的區別而決定,甚至包括了強調自我保存的自然法上的自由,即嚴復所謂“必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進化,必兼愛克已,而后有所和群利安”這種不變之道。總之,一切都與自由有密切的關系。所謂富強就是利民,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反是且亂。”而要人們能自由,則必須提高人民的力,智和德。從這里,嚴復開始轉入到對個人自然權利的強調。
(二)自然法思想的權利內容
如同斯賓塞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之前就開始闡發其政治主張一樣[4],嚴復在未充分吸收西方進化論之前也開始提出其自然法學說,至少是在未系統吸收進化論之前,這應該說與他留學英國時關注英國的社會問題有密切的關系,當然,嚴復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個斯賓塞的門生,之所以這樣說,是強調沒有赫胥黎的《天演論》,條件成熟,嚴復還是會發展出自己的學說的,只不過,進化論更讓他的學說找到科學的根據,不易受到清末保守人士的攻擊,也便于傳播。從嚴復與郭松燾及曾紀澤交往的資料來看,對一個以傳統儒家學說立論作文得到贊賞從而接受西學的人來說,到敢于觀察,直言表達自己看法的勇敢的年輕人,這種轉變說明嚴復在英國的幾年里不得受到了教育,而且對英國獨立自主、勇于進取、自我承擔責任的精神,特別是維多利亞精神的理解是深入骨髓,從而顯現于外的,所以嚴復在談到自然法時,就處處主張個人的首要地位是有其社會背景和個人經歷的。嚴復在1895年首先提出了基于自由的自然權利說(過去一直稱為“天賦人權”,這個譯法突出了權利的來源是天,也指出了人民權利的獲得是天賦的,當然權利內容是人的權利,然而與西方的自然權利比較起來,其抽象意義還差得太遠,并不準確,因為當近代天作為最高的哲學范疇被取消了之后,天賦人權也很容易成了無源之水,從而無法準確表達出權利作為人所固有的這層抽象意義,應該說,翻譯成“天賦人權”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儒家學說主張天人合一和君權神授是有緊密關系的)。他認為,個人作為自然的產物,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命運和權利,但只有獲得自由,才能算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即,“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在這里,可以說,自由在嚴復的政治哲學中充當了一個基礎,起到了本體的作用。由于自由首先是屬于個人的,作為整體的國家的自由則應該從個人自由的方面來理解,這就是嚴復極力主張的“身貴自由,國貴自主”[5]的邏輯所在,而得到“全受”的自由權則表達了人的倫理本性,所以嚴復與梁啟超討論“Rights”的譯法,認為“民直”是最好的翻譯,也就是說在嚴復的權利思想中,自由是最核心的要素,其他讓自由運動起來的權利則是派生出的權利。因此如果說在《論世變之亟》中嚴復主要是提出自由的本體論基礎,那么,如何將自由這個本體運動起來,則成了《原強》的中心所在,也正是在這篇文章里,嚴復提出了更具體的權利內容。
前面說過,《原強》跟嚴復另外三篇文章不同,它有續篇和修訂,從這點看,可以看出嚴復對這篇文章的重視。首先,“強”這個洋務運動以來具有時代特色的術語,也在儒家經典中有其重要意義,嚴復選擇了這個概念來表達他的主張,那就是“保身治生”,“利民經國”。我們都知道,這兩個目的更是西方自然法理論的中心內容,亦是古典自然法學中強調權利時主要訴諸的目的。洛克強調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同時只有維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的社會和國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國家。因此,嚴復認為講西學和談洋務都必須以此為目標。然而自由如何體現呢,嚴復認為必須以民力,民德和民智為標準。這里,我們涉及到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此時,嚴復還沒有與張之洞就“體用”展開爭論,所以用體用說來論證嚴復的自由和權利思想不能說有充分的根據。但從《原強》的結構可以看出,他緊跟著介紹達爾文和斯賓塞之后就提出了這三者,他稱之為“生民之大要三”,具體解釋為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和德行仁義之強,顯然沒有我們熟知的“三民”概括,但這正好說明了嚴復在此是持個人主義的方法論的,因為這三者只有在物質性質上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杜鋼建論證了嚴復提出的三民理論與權利內容的對應關系,即民力與人身自由權的關系,民智與思想表達自由權的關系,而民德與民主權利有密切的關系。[6]他這種一一對應關系,未必準確,如對民力的理解更應該聯系當時的戰爭失利和晚清鴉片泛濫的社會危機,以及嚴復在北洋海軍教學這個事實,因此,嚴復必須更為強調更多的英勇尚武的德性,這是古希臘和馬基雅維里強調的公民共和精神的一種,而不能過分的對應西方自然權利的三分法或四分法,但基本思路是成立的,可以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從而拓展嚴復要強調的人的自然權利的內容,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派生的,哪些應該是無條件的,哪些是應該受到限制的,各種權利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對個人的權利進行論證之后,嚴復開始思考權利的來源問題,這就是《辟韓》要處理的問題。嚴復通過對韓愈君權神授學說攻擊論證了權利的自然來源,即他所謂“民之自由,天之所畀”。
(三)自然法思想中的國家與個人
如果說上面主要還是從個人主義來為個人權利論證的話,那么嚴復在強調自由的同時,也強調了民主一面。什么是民主,現在較為清楚了,但嚴復寫作的時代則是不太清楚的。不過,作為主權意義上的民主,也就是人民主權論上的民主在洋務運動時期已經被知識分子開始使用了,從嚴復的思想中看,他也應該在主權意義上使用民主這一概念,而不是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上的民主。在此意義上,民主內在的含義當然要求個人的理性和社會的公平,因此,嚴復強調“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可以說,這是嚴復對歐洲近代歷史和歐洲啟蒙運動最高度的概括。
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與自然法有密切的關系,嚴復在集中論述了國家的強大與個人自由的關系之后,自然而然關注到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這在自然法理論中是以社會契約論的形式表現的。嚴復關于這個問題的闡述集中于《辟韓》中。該文篇幅并不長,但其重要意義并不亞于《論世變之亟》,首先,他直接與中國古代著作學者,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韓愈進行了交鋒,這體現了嚴復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的深入了解,嚴復政治哲學思想的歷史視角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可以說,嚴復作為中西會通學者,該文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嚴復在這篇文章深入處理了自然法和政治哲學理論最基本的幾個問題。首先就是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儒學傳統一直強調圣人立法,對君臣民之間的關系在政治哲學上已經形成了共識,主張君主是萬能的,大臣是代表君主進行統治的,而人民是勞動者,在政治上并沒有什么發言權,不能過問政府和社會事務,否則就是刁民。嚴復對這種政治理論進行了批判,提出應該用社會契約論來解釋君臣民相互之間的關系,主張君主是因為社會混亂而建立起來的,如果社會運行良好并不需要君主,人民也能自行生活良好,所謂“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而且主張人民有反抗的權利,即“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
嚴復通過對韓愈政治理論的批判,隨即跟古典自然法學家一樣,指出政府是一種惡,不得已才需要,因此,“君臣之倫”是“不足以為道之原”的,但又是一種必要的惡,是必須的。為此,嚴復甚至舉例說西方國家作為先進發達國家,都還是需要政府的,只是政府應該把自己的職能限于較小的范圍,對社會事務,公民個人自我管理和行使占十分之七,政府只占十分之三,因此,應該是典型的小政府,政府處理的事務也主要是維持國內秩序和治安和國家安全的“明刑治兵”兩件大事。總之,政府主要職責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只有這樣,社會和國家才能進步,繁榮和強大。這就是嚴復在《辟韓》中所表達的主要思想。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嚴復對西方的自然法理論有非常準確和深入的認識,特別是描述了在人民尚未進入社會之前,處于自然狀態下,享有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按照韓愈的說法也是必須由人民先享有,才可能由人民交納給官府的,否則,讓人民繳納稅賦將無以說起。而且,嚴復在處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還多次強調真偽對政治和法律的影響,“華風之敝,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有學者以此認為嚴復仍然崇尚格物致知,務實求真,為學以政,知行合一的理學精神[7],以此彰顯嚴復對中國傳統本土資源與精神動力的關注,那么,可以說在對西方社會發展背后關系的討論中,嚴復不自覺的實證精神為此后《政治講義》的實證分析已經打下了最好的預設,當然這種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嚴復沒有象西方自然法理論家那樣重視到自然權利的自然性,從而在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否定儒家學者所持的主張較多,而其建設性的國家理論相對較弱。
(四)自然法與制定法
在自然法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強調自然法與實在法之間的區別,認為自然法代表人類理性,普遍適用,高于并指導著政治社會的國家和法律,即高于人類有意識制定的法律,后者通常稱為制定法或實證法或實在法。可以說,還很少有學者象嚴復這樣關注這個問題,只是嚴復用的范疇是“法”與“無法”這兩個術語,前者主要指有外在表現形式的法律,后者指的是沒有外在表現形式的法律,而不是所謂“無法無天”意義上的真的沒有任何規范性質的法律。在中西進行比較或中國移植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有很多總結,如從本體論上說,梁啟超總結了中國近代對西方認識而形成的從器物-制度-文化文明這個視角,這種視角確實有相當的價值,但缺乏歷史的深度,是一種實踐活動的總結,缺乏規范性的向度。而嚴復對此的看法則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具有一種規范性的指向,是一種理論訴求的表達,有學者已經對嚴復的自然法和人為法進行了研究,也有相當精辟的看法,但主要立足于嚴復翻譯作品及其按語[8],從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嚴復對自然法和實證法的分析是有意識進行的,只是在后期隨著對《法意》的翻譯有一些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自然法與實證法的區別和聯系應該成為中國近代法律和政治改革的標準和目的所在。
首先,嚴復在《原強》中花了相當的篇幅對自然法和實在法進行比較研究,并舉出了歷史上的匈奴和當時的西方國家進行了說明。對法律的分類,嚴復是作過深入的思考的,在翻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時,他指出西方的法在中文術語中應該從理禮制刑的角度進行理解,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嚴復對近代中國法制改革為何有一種冷靜的態度,一種法律制度的改革顯然不僅僅是紙面上的法律條文的侈譯就可以解決的,必須涉及法律制度背后的價值目標。嚴復對自然法和制定法的分析,在中國與匈奴之間采用的是文質這對概念,文勝和質勝都是可能的,這取決于有無“自治”,即強調自由的有無,而在中西對比時,他將這種分析闡述得更為明確,指出晚清中國與西方比較,無論是自然法還是制定法都處于落后的地位,因為在自然法中,西方法強調自由平等,君民之間通過社會契約已經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已經形成了一個政治社會和民族國家,而在制定法方面,法律對社會的活動都作詳細的規定,人們有規則可以遵守,而且法律不會朝令夕改,個人不會覺得沒有法律可以遵守,從而大大降低了社會交往的成本,法律上已經勝過中國很大了。此即“西洋者,無法與法并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則其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方,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備而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皆有常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可以說,這段話是嚴復對東西方時行比較的又一經典之作,這個比較在實踐和理論方面甚至超過在我們熟知的《原強》中有過論述的中西文化比較。因為,這里既有描述性,又有規范性的論述,是對西方近代以來政治和法律領域理論和實踐領域的總體研究。
其次,在《救亡決論》中,嚴復指出了制定法的可變性與自然法的不可變性,“能自存者資長養于外物,能遺種者必愛護其所生,必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進化,必兼愛克已,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來不變者也,此所以為不變之道。”在這段話中,嚴復提出了自然法的幾項重要原則,對生命的愛護,對自由和同情心的強調,以及建立在同情心上的社會合作,這些都是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或重要預設。在這些不變的自然法指導下,中國傳統儒家認為不變的政治一法律制度都是可變的,“君臣之相治,刑禮之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號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維者,皆譬諸夏葛冬裘,因時為制。”[9]可以說,嚴復的這些看法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基礎和制度模式。西方自然法學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理想通過這些制度的建立,完全可以實現由理想轉到現實的法律。
三 結 論
總之,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到嚴復在《直報》上發表的文章可以說已經較為完整系統的表達了他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是他對中國近代問題的認識和反思的總結,其后的翻譯都基本上是來驗證和升華他的理論的,不先處理好這些自然法問題,那么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是缺乏基礎的,只能是在術的意義上,而不是在道的意義上的現代化,整個社會都只能是社會和技術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沒有倫理和文化上的實質進步。嚴復的自然法思想既是對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引介,又結合了中國傳統政治和法律理論,也提出許多自然法復興時提出的重大問題,其中對自然法與制定法關系,法律的性質,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法律的起源及其權威、君權神授、社會契約論等古典自然法理論的主要論題都有相當深入的論述,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的挖掘,以反省近代以來中國法治的建設得失,從而為中國法治文明和社會進步提供更全面的學術資源。
[1]郭常英.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概述[J].近代史研究,1998,(4).
[2]章清.“國家”與“個人”之間-略論晚清中國對“自由”的闡述[J].史林,2007,(3).
[3]嚴復.論世變之亟[A].嚴復文選[C].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4.
[4][英]歐內斯特·巴克.英國政治思想[M].黃維新,胡待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57-89.
[5]嚴復.原強修訂稿亟[A].嚴復文選[C].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20.
[6]杜鋼建.論嚴復的“三民”人權法思想[J].中國法學,1991,(5).
[7]林怡.以學為政:從朱熹到嚴復-以“理學”實踐品格的歷史傳承及其當代啟示[J].東南學術,2009,(5).
[8]林平漢.嚴復對中國近代法制思想的貢獻[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4,(2).
[9]嚴復.救亡決論[A].嚴復文選[C].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