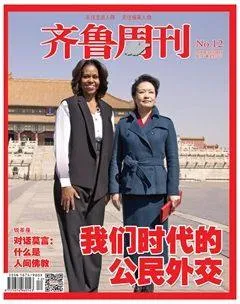慧寬法師:從“人間佛教”到情緒管理
吳永強


現代人被科技綁死了
一個銀行行長告訴慧寬法師,周一到周五她會很怕接電話,怕客戶的抱怨、講述理財產品的各種問題。但是到了周末,卻又很怕沒有電話。有一次到了中午,還沒有電話打進來,便很緊張,打電話給移動,問是不是沒有話費了,客服告訴她一切正常。她說不可能,肯定會有人打電話的,又去問朋友,朋友都說沒有給她打電話。這位行長還患了嚴重的失眠癥,以至于每天晚上痛苦得在地上打滾。
慧寬法師用情緒管理幫她解決了失眠的問題。“活在當下、自我覺察、善觀因緣,都是佛教的東西,但在我的演講里面卻不容易感覺到,把佛教的理論細化到生活里去。”慧寬法師說。在星云大師的鼓勵下,情緒管理課程講了四五百場,最近剛去美國、加拿大講課,收到良好的效果。
《齊魯周刊》:您寫過一本《開創智慧人生——談情緒管理》,是否傳承了星云大師的一些理念?
慧寬法師:這本書大部分是講情緒管理,關注家庭教育、感情觀、人際溝通、抑郁癥、自殺等問題。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也是希望我們把佛教的智慧用在人生當中。
《齊魯周刊》:您怎樣理解“人間佛教”?
慧寬法師:佛教和其他宗教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佛教講因緣法,佛陀在悟道的過程中,看到世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人間佛教”是真正的佛教,力圖恢復佛教的本來面目。很多寺廟存在的算命、燒高香之類的做法,都是不對的。
《齊魯周刊》:星云大師對“人間佛教”的解釋是,凡是佛說的、人要的、凈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現在的人為什么覺得離佛教很遠?
慧寬法師:很多佛學書籍是文言文,一般人會覺得很深奧,再加上有些法師說法說的很難,讓人聽不懂。但佛陀講的很多東西其實很生活化,我們讀懂它后,要用現代語言去表達,這也是大師提倡的。
“善美”已經不錯了,是對人的正面的引導,
(上接第41頁)
從“善美”到“凈化”,能夠做完一件事后,不戀名利,付出不那么執著,就是“凈化”。比如有信徒送給我一串念珠,隔天就會在意,法師你的手上有沒有戴我送你的念珠。直到他并不在意這件事,才不容易煩惱。人的煩惱很多在于執著、比較、在意。其實這個東西不是沒有了,而是在你的心中沒有了。
《齊魯周刊》:現代社會,人們似乎越來越焦慮。
慧寬法師:臺灣有種“已讀焦慮癥”,你給朋友發信息,對方收到,顯示“已讀”,卻沒有任何回復,然后你再問他收到沒,又是“已讀”,但他還是沒有回復。這樣就產生焦慮,他明明看到了,為什么不回復你呢?現代人被科技綁死了,科技是為了幫助人活得更方便(不是更快樂),但卻讓人活得不自在。
禪修就像房間里的擺設,讓你的生活更有智慧
2月17日,臺灣藝人高凌風去世。兩年前,高凌風離婚后很郁悶,極度痛苦,不到一年便患血癌。“在短時間內極度的壓抑,很容易讓身體和心理產生病變,但世界是很公平的,一般沒有同時判定你得抑郁癥和癌癥。”慧寬法師說。
一次,慧寬法師開車出去,一個保安吼道:“你這個假和尚,不要亂停車。”慧寬法師沒有動氣,對他笑了笑。他卻說,“你還在笑,還不快走。”慧寬法師也沒在意。
有些人常常問他莫名其妙的問題,你也坐高鐵?你也坐飛機?“我這個人,問我我會回答,你堵住他的問題,倒不如去疏導。”
《齊魯周刊》:有些人得病后,皈依宗教。您怎么看佛教與疾病的關系?
慧寬法師:有些人遇到生病就會抱怨,但學了佛教智慧之后,改變了對生病的看法,生病是讓人知道最近的生活習慣不好。前幾年,日本將癌癥改為“生活習慣病”,癌癥其實跟某種生活習慣有關,比如胃癌,焦慮、緊張的生活習慣會讓胃的收縮不正常,從胃炎、胃潰瘍發展到胃癌。
面對疾病,佛教讓你主動接受,而不是被動抱怨。我現在正在研究一個課題,人在得癌癥之前的三到五年的生活習慣,和他得癌癥有很大關系。有些人的壓力很大,并沒有轉向精神疾病,而是從生理上發病。
《齊魯周刊》:佛教和我們的生活有什么關系?
慧寬法師:大師在演講里面會講很多故事,佛教只是人的一種信仰,一種智慧,并不是要人信教之后就不工作,不要家庭,就沒有希望了。
比如一間客廳,墻壁是白的,什么都沒有,只有一組沙發,會覺得很單調,但掛了幾幅畫,擺了一些如意,就覺得活潑很多。禪修就像這些擺設一樣,讓你的生活更有智慧,添加一些更有趣的東西,減少一些煩惱。
《齊魯周刊》:您怎么看“有神論”與佛教的關系?
慧寬法師:佛陀跟孔子類似,只是修行的東西不一樣,領悟也不一樣,孔子領悟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佛陀領悟的是“覺”,人與自我的關系。有些人把有神論和宗教聯系在一起,但佛陀不是神。你信了佛,會得到一些智慧,去用了,會有一些幫助,但至于幫助多少,要看你自己。大師曾說,有佛法就有辦法,這句話不好理解,把“佛法”換成“智慧”就好理解了。
信仰高過政治
星云大師曾多次說過,自己的年紀已經大了,希望早日看到兩岸統一。
2002年,西安法門寺的佛祖舍利,去臺灣佛光山供奉了37天。當時還是陳水扁執政,一個多月時間,有500多萬人前去瞻仰。“沒有人說佛祖舍利是大陸的,不能供奉,在佛教信仰之下,政治問題淡化了,信仰高過政治。”慧寬法師說。
《齊魯周刊》:有人說,星云大師是“一位影響深遠的社會教育家,一位果斷的、身體力行的宗教改革家,一位慈悲的、普及佛理的創意大師”,您怎么看?
慧寬法師:星云大師有1300多個徒弟,每個人的專長不一樣,有的人很會寫書,有的人會演講,有的人會唱誦,有的人會園藝。大師從未讓我們去比較。
大師一生在意的不是法會等儀式的東西,而是人的心靈的變化,宗教不能停留在“宗”,而要放在“教”,凈化人心,讓人自我改變,而不是改變別人。大師一生辦了很多教育,包括信徒教育、學校教育甚至美術館。有人問大師為什么辦美術館?大師說很簡單,佛教本來就是重視美術,比如敦煌藝術。
他還是一個改革家。只要符合佛教的精神,弘法的方式可以改變。比如黃色長衫,以前沒人敢穿這種衣服,都穿灰色、黑色,但到了國外,人家會以為你在辦喪事,所以我們就穿成黃色。剛開始別人以為我們標新立異,現在全世界的漢傳佛教僧人都在穿這種衣服。
他還是一位創意大師,組織合唱團,寫了很多歌詞,讓年輕人譜曲,合成“人間音緣”。現代的寺廟里為什么老是唱誦那些傳統的曲目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