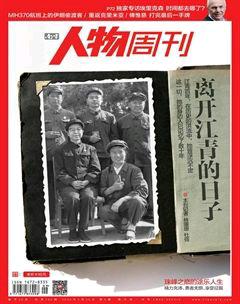與死亡恐懼和平共處
游識猷
3月8日這天,我不停地刷微博、twitter和航空業者云集的airliners.net,試圖知道MH370航班有沒有最新消息。下午6點仍然沒有任何好消息,一個搭飛機的朋友發信息說飛機晚點,而我不得不出門參加一個討論轉基因的沙龍。天很冷,我邊掛心機上239人的命運,邊琢磨朋友今晚要等多久,邊疑心有沒有人會在這種冷天來參加沙龍,邊擔憂會不會根本找不到沙龍地點……
從演化角度來說,恐懼是種心理適應器。恐懼、焦慮、壓力等負面情緒都是大腦的本能。事實上,意識到“自我”存在那一刻起,我們就要面對有朝一日自我將消亡的恐懼。而以下問題也開始揮之不去——“真實的我”是什么模樣?“真實的我”為何還沒有成為“理想的我”?還有,我何時會以何種方式死去?
繁衍后代也好,修行來生也好,著書立說也好,維護自尊、強化世界觀也好,與他人建立社會關系也好,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我們創造文化,建立宗教,在其中找到些許安慰。而當災難襲來,被迫直面死亡與不確定性,我們的大腦就會自動啟動種種防御機制。
第一層防御來自親密關系。荷蘭研究者曾做過一個實驗,讓一組人想象自己的死亡,另一組人則想象自己看電視,然后安排兩組人參與小組討論。結果發現,想象死亡的人們傾向于彼此坐得更近。另一個研究則顯示,想象過死亡的人愿為親密關系付出更高代價。來自伴侶的怨言平常會讓人不滿,但如果此前剛想過生死,人們的容忍度便會升高。
對于安全型依戀者,親密關系是最優先也最重要的屏障。但有些人可能還需第二層防御。時刻憂懼被拋棄的焦慮型依戀者,倘若自覺沒有得到足夠的愛與支持,往往會開始捍衛自身世界觀,對于“三觀不合者”表現得比平常更加“不寬容”。至于習慣于壓抑感受的逃避型依戀者,則會對親密關系無動于衷,倒是致力于提升“自尊(self-esteem)”——加倍努力地試著 “看得起自己”。
倘若執著于“同一個世界,同一種三觀”,我們會更偏執,更歧視他人,更容易受刻板印象影響,甚至連無辜受害者都開始責備——“如果他們不那么做,就不會遇到災難”,殊不知,這種想法只是我們為了消除不確定性。
至于“自尊”,往往與成功、魅力等外來評價掛鉤。為了確信自己是“有價值的人”而給自己設下目標,萬一未能如愿,這種危險的掛鉤就很可能從自責轉變成對自己的低估,重者還會陷入所謂的“習得性無助”,相信自己不論如何努力都沒法改變結局。
如果相信每件事的成敗都會影響自己的“好壞”,再堅強的人也不免恐懼。而讓你恐懼的,常常并非“恐懼源”本身,而是來自心中對失敗和無助的預感。每個人都必有一死,但最令人害怕的是死亡無法掌控,不知何時發生、不知如何發生。
你可以放棄,可以購物、游戲、回避挑戰,可以用其他刺激不斷轉移注意力,但你真正想逃開的“恐懼感”卻依然深植于內心。惟有承認,才能原諒,進而超越。承認自己的一切感受,原諒會心跳加速冷汗直流的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直面你最害怕的事物。正如埃莉諾·羅斯福所說,“當你駐足停留、直面恐懼時,你能從每一次經歷中獲得力量、勇氣和信心。你能夠對自己說,‘我經受住了恐懼的考驗。我能夠承受將會發生的一切。’”
不安的日子里,我們會本能地渴求信息,但要在死亡深淵面前活出有意義的生命,方法其實很老套——愛人,愛自己,愛冒險。絕不冒險的“百分百安全人生”并不存在。哪怕存在,亦不值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