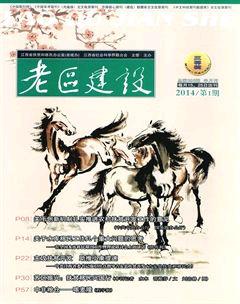古代官訓瑣談
賈鳳姿
我國傳統官訓內容豐富,涉及官員道德修養、公務處理、立身處世等方方面面,官員修身遵訓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
慎言重行、言行一致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對官員的言行作了許多具體規范。首先,官員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員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難以挽回,如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漢代賈誼說:“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他認為能否恰當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是區別智與愚、賢與不肖的標志。其次,官員要言行一致。《論語》:“言必信,行必果。”《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之寶也。口言善,身行惡,國之妖也。”善言善行的人是國家的瑰寶,說話冠冕堂皇卻干盡壞事的人則堪稱妖孽。再次,官員要身教重于言教。《后漢書》說:“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天有些領導干部熱衷于形象工程、熱鬧場面,臺上一套臺下一套,這樣的干部講話沒人信,做人沒人服,干事沒人跟,遲早會被組織識破、遭到群眾唾棄。
見利思義、先義后利
義利問題是官員價值觀的核心問題。《論語·為政》認為:為政要講求道義,“譬如兆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以道義處理政事會像北極星被群星環繞周圍一樣受人擁戴。《孫臏兵法》說:“將者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力。”宋代蘇軾說得更具體:“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缺乏道義的威信是建立不起來的,無德者的智慧,不能令人信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將人分為圣人、君子、小人:“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強調為官者要有良好的道義修養,才能為君治國、為民造福。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在利益面前要先考慮是否合“義”,然后決定是否取之,反對用不正當手段謀取私利或見利忘義。《墨子·非樂》:“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義和利的矛盾統一起來,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以求官與民、民與民關系的融洽和國家的安定富強。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義利觀,黨員干部肩負著帶領人民實現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在利益面前應首先思考:我該不該得?能不能得?能夠做到見利思義,先義后利。
以能求職、量能授官
關于官員德能與職位的關系問題,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借鑒意義的思想。首先,“稱身就位”,所謂稱身就位是說任職之前要衡量自己的德與才能否滿足職位的需要,量才受職。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記》中說:“才不稱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達不到職位要求的能力不可去占據那個職位,不稱職就不要去拿那個職位的薪俸,否則就會“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貿然接受自己能力所難適應的職位,將貽誤政事,危害國家,殃及百姓,自身也難逃失敗的下場。才能是做好工作的基礎,才疏者不可志過大。唐代羅隱認為有識之士“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不必擔心沒有職位,而應擔心自己品德修養不足。有志者要積極蓄積才能,以高超的才能和淵博的學識靜待職位的降臨。其次,“睹賢不居其上”。所謂睹賢不居其上是說看到比自己有才能的人,不要讓自己的職位高居其上,否則就會“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呂氏春秋·遇合》說:“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這是告誡那些能力素質不具備的人,莫要抱僥幸心理去取得權位,沒有本事而接受任用,只會招致禍患。《淮南子·人間訓》指出:“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德才低下的人不要爭官、討官、跑官,甚至不惜人格求官、買官,不依德能得到的官位終將得而復失。
達窮不移、寵辱不驚
人在追求目標的旅途上有順境也有逆境,古人稱順境為“達”,逆境為“窮”。首先,官員必須正確面對“達”與“窮”。不必通達顯貴而趾高氣揚,也不因窮窘困厄而垂頭喪氣。孟子《盡心上》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使在不被重用之時,也要像《論語》中說的“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次,官員必須辯證面對“達”與“窮”。自古英雄多磨難,功業都從苦中來。司馬遷指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些豪杰志士在難以想象的逆境中,克服了異乎尋常的痛苦與困難,在磨煉自己的過程中實現了人生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窮”乃造就人才佳境。故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當今的領導干部要做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貧賤不移,寵辱不驚。
責任編輯:上官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