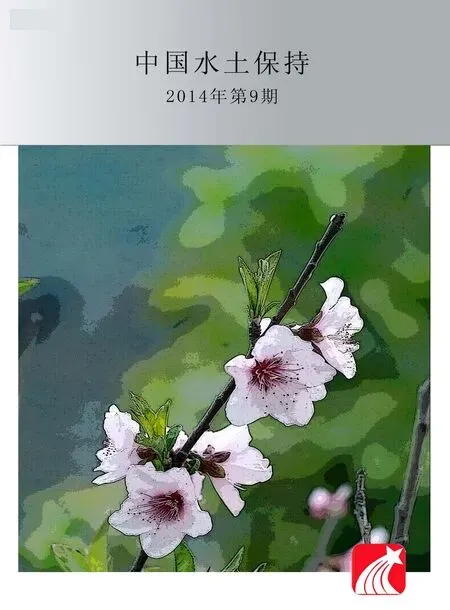祁連山北坡生態現狀與治理對策
汪有奎,李進軍,楊全生,李世霞,袁 虹
(1.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甘肅 張掖 734000;2.甘肅省林業工作站管理局,甘肅 蘭州 730046)
祁連山北坡是黑河、疏勒河、石羊河三大內陸河的發源地,冰川穩定的水源補給和林草植被的水源涵養功能相依互補,為河西走廊綠洲和北部荒漠生態系統提供了穩定的水資源。正是由于祁連山獨特而穩定的水源補給,才使得深居我國內陸腹地的河西走廊干旱區形成了許多人類賴以生存的綠洲,也使得我國干旱區有別于世界上其他地帶性干旱區。這種山地—綠洲—荒漠景觀及其相關的水文和生態系統穩定和持續存在的核心是穩定的山區水源,沒有祁連山就沒有河西走廊干旱荒漠區中的綠洲,也就沒有千百年來在那里生息的人民[1]。近年來,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和人為破壞雙重影響,祁連山北坡生態保護與建設仍存在許多問題,面臨巨大壓力。加強祁連山北坡生態保護與綜合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緩[2]。為此,筆者調查分析了祁連山北坡生態保護與治理的現狀和存在的主要生態問題,提出了生態保護與綜合治理的對策,供生態保護管理部門決策參考。
1 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研究法和“3S”技術,搜集整理祁連山北坡生態保護與建設研究文獻資料,調查分析祁連山北坡生態保護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根據國家和甘肅省有關生態保護法規、規劃和實際情況,提出祁連山北坡生態修復與治理對策。
2 研究結果
2.1 祁連山生態保護與治理現狀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人們在祁連山北坡林區盲目擴大耕地面積和牲畜數量,導致森林面積減少,草場退化嚴重。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停止天然林采伐、設立自然保護區、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行為、積極開展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和退牧還草等措施,祁連山北坡生態退化趨勢有所好轉,主要表現如下。
2.1.1 森林資源顯著增加
1980年甘肅省政府批轉了省林業廳《關于加強保護和發展祁連山水源林的報告》,全面禁止祁連山區林木采伐,實施封山育林。在祁連山、鹽池灣、連城3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立后,祁連山北坡80%以上的林地劃入保護區內,森林資源得到更加嚴格的保護。2000年以來,祁連山區森林納入了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和重點生態公益林建設范圍,林地林木管理進一步規范,通過不斷打擊違法毀林行為,有效遏制了亂砍濫伐林木、亂開濫墾林地現象,通過退耕還林、荒山造林及封山育林,森林面積逐年增加[3]。應用“3S”技術調查表明,2011年與1980年相比,祁連山北坡林地面積增加了999 518.6 hm2,增加了215.5%,具體變化詳見表1。森林蓄積量由1 700萬m3增加到3 200萬m3,增加了88.2%。
2.1.2 局部區域草場退化趨勢有所緩解
20世紀90年代以前,祁連山區草場放牧形式主要是以村為單位的混牧,由于放牧牲畜數量增加過快,造成草場急劇退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草場包產到戶和草原圍欄的推行,草場混牧現象得到控制[4]。2000年以來,逐步實行以草定畜制度,牲畜數量無限制增加的態勢有所控制。2004—2010年,祁連山北坡的天祝、肅南、山丹、肅北、阿克塞5縣約有251.8萬hm2草場被列入國家退牧還草工程試點區域(表2),實施了禁牧、休牧、輪牧和補播改良,在禁牧、休牧草場拉設了刺絲圍欄進行草地保護與恢復[5]。

表1 祁連山北坡1980年至2011年各類型林地面積變化 hm2

表2 2004—2010年祁連山北坡退牧還草面積 萬hm2
監測調查表明,肅南縣東祁連山地項目區,禁牧3年后草甸草原牧草種數、植物群落高度、蓋度、生物量、草群密度分別增加了7.4%、12.90%、4.3%、11.09%、21.12%;祁連山中山區季節性休牧的項目區,封育3年后山地干旱草原植物種數、植被蓋度、生物量、草群密度分別增加了27.3%、6.94%、16.36%、10.37%。經補播改良的草地相對于對照草地,植被覆蓋度、牧草平均高度、可食牧草比例、地上生物量分別提高34.5%、52.6%、74.8%、92.2%[6]。天祝縣禁牧休牧區植被蓋度在當年度就有明顯提高,草原草場、草甸草原類分別提高了8、12百分點;草原草場、山地草甸草場當年鮮草產量分別平均提高300、525 kg/hm2;禁牧區、休牧區牧草絕對高度分別提高了10~15 cm、8~12 cm。草甸草場、草原類草場植物種的飽和度分別比工程實施前增加14、4種/m2,優良的禾本科牧草和莎草科牧草種群蓋度由工程實施前的48%增加到60%左右[7]。肅北縣實施退牧還草工程后,天然草場植被覆蓋度增加了10~15百分點,牧草高度提高10%~20%[8]。
另據戴聲佩等[9]研究,1999—2007年祁連山草地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呈緩慢增加趨勢,說明草地覆蓋度整體呈改善趨勢。典型草原和平原草地植被年均NDVIy和生長期NDVIg增加速率高于高寒草甸草地和沙漠草地。祁連山草地植被NDVI增加的面積為69 776 km2,祁連山北坡植被NDVI增加的區域分布在冷龍嶺、走廊南山、托來山、托來南山等地區。
2.1.3 部分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顯著增加
新中國建立以來,過度放牧、毀林開荒導致的棲息地破壞和無限制的獵殺,致使祁連山區野生動物分布范圍大幅度縮減,種群數量急劇下降。至20世紀80年代末,野生動物種群數量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特別是馬鹿、馬麝、水獺等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野生動物數量減少嚴重,雪豹、野牦牛等動物處于滅絕的境地[10]。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國務院批準成立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后,祁連山區野生動物得到了保護,有些動物的數量開始回升,如藏野驢、馬鹿、巖羊、藍馬雞、狍、猞猁、斑翅山鶉、石雞、各種山雀的數量和分布面積逐年擴大,處于良好的發展趨勢[11-12]。保護區建立前,藏野驢的分布范圍退縮在祁豐保護站高崖泉、野馬大泉一帶,數量已下降到100只左右;保護區建立以后,由于加強保護,藏野驢的數量不斷增大,數量已超過1 000只,分布范圍逐漸向東擴展,已翻過分水梁,跨過陶萊河,到達了大小烏蘭、陶萊河、白水河子、九個青羊、東干河。現在護林人員在巡山時經常見到巖羊、藍馬雞,遇見率是20世紀90年代的4~7倍;馬鹿、狍鹿、斑尾榛雞、血雉等林棲性動物遇見率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2~4倍,分布范圍也明顯擴大。20世紀90年代以前,昌嶺山、大黃山等保護站的巖羊幾乎絕跡,護林人員都很難見到,而現在幾乎天天都能見到。多年蹤跡罕見的雪豹,近年來在肅南、山丹馬場、天祝林區均被發現了蹤跡,在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和鹽池灣自然保護區的多處地方紅外照相機均拍到了雪豹實體,說明有恢復態勢。20世紀因大肆捕殺絕跡的灘黃羊,2005年在山丹馬場自然保護區的山地草原發現了13只。
2.2 祁連山北坡的主要生態問題
隨著人口增長,生產經營活動對生態的干擾破壞日益增加,加之氣候變暖,祁連山北坡的生態環境仍呈現出局部治理、整體惡化的趨勢,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2.2.1 氣溫上升顯著,冰川持續退縮
根據祁連山地區20個氣象站氣溫觀測資料分析,1960—2009年的50年間,祁連山區年均氣溫累計上升了1.67 ℃,年際變化率為0.033 4 ℃/a,1987年之后氣候明顯變暖;氣候從1976年開始,逐漸由干旱向濕潤轉變,年降水量呈增加趨勢,但增加趨勢不太明顯,在50年間累計增加29 mm,年際變化率為0.570 2 mm/a;極端高溫天數增多,日最高氣溫升高,山區旱、洪災害頻繁發生[13]。由于氣溫升高、冰川表面沙塵物質導致反照率降低等因素影響,致使冰川消融加速,雪線上升[14]。1956—2006年間,對甘肅省水資源影響較大的石羊河、黑河、北大河、疏勒河、黨河和哈爾騰河6個內流區和大通河流域的冰川總面積減少了308.1 km2,冰川面積縮減率達17.7%(表3);冰川冰儲量減少7 km3,為1956年冰川儲量61.54 km3的11.4%;冰川厚度減薄5~20 m,雪線(平衡線)上升幅度達100~140 m[15]。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冰川萎縮程度是1956年以來最強烈的時段,冰川積雪的“固體水庫”作用削弱。

表3 祁連山區各流域冰川變化
2.2.2 森林草原退化,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程度加劇
祁連山北坡有林地、灌木林地面積有所增加,但是森林質量呈下降趨勢。目前,祁連山、鹽池灣和連城3個自然保護區內結構完整的林分面積只有2.6萬hm2,占有林地總面積的11.4%;結構較為完整的林分面積19.7萬hm2,占88.1%;有56.3萬hm2灌木林退化成蓋度為30%~49%的稀疏灌叢草地,占保護區灌木林總面積的71.4%。林緣下線海拔2 300 m以下的灌木林大部分被開墾為耕地,剩余的也退化為低覆蓋度草地。3個自然保護區內毀林毀草墾荒種地5萬hm2,使土壤蓄水能力降低,土壤有機質、全氮、全磷和速效養分含量下降,導致土壤嚴重退化[16]。山區內多數林地實際上均被牧民作為草場進行放牧,植被退化,蒸發量增加,積雪貯水能力下降,野生動物的生境受到嚴重破壞,水土流失加劇[17-18]。
山區草場載畜量由20世紀50年代的70萬羊單位發展到現在的764萬多羊單位,超載率達70.2%,草原“三化”面積逐年擴大[19]。有85.9%的草地退化,1/3以上嚴重退化;與40多年前相比,草層高度下降了50%,植被覆蓋度由65%~95%下降到了25%~60%,草地載畜能力下降了50%至70%[20]。烏鞘嶺、大通河、石羊河、黑河、北大河、疏勒河等河流河谷區域植被覆蓋退化的面積17 784 km2,其中草地植被NDVI減少的面積有15 928 km2,占89.6%[21]。草原退化還誘發鼠蟲危害[22]。據蟲鼠害監測調查,肅南縣蟲鼠害發生面積達34.9萬hm2[23]。因坡地開墾和草地超載放牧嚴重,致使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加重:石羊河流域上游天祝縣水土流失面積達54.5萬hm2,占總面積的76.2%;黑河上游肅南縣水土流失面積33.3萬多hm2[22];西段疏勒河流域鹽池灣保護區水土流失面積69.8萬hm2,占保護區面積的37.7%;黨河上游地區已形成近3 000 hm2流動沙丘,沙漠面積不斷擴大,已危及周邊草場[24]。
2.2.3 人為干擾嚴重,生物多樣性仍存在很大威脅
20世紀以來,山區經濟資源開發速度和強度顯著提升,主要表現為水電資源開發、礦產資源勘探開采、生態旅游、封育圍欄、道路建設等經濟建設和生態工程設施對保護區生物資源進行包圍、蠶食和侵占,將自然生態系統切割成不連片的“孤島”,使祁連山區野生動物棲息環境惡化[25]。馬麝、野牦牛、白唇鹿等野生動物仍處于瀕危狀態[10],狼、棕熊等野生動物種群數量仍呈下降趨勢[11]。
3 祁連山北坡生態修復與治理對策
祁連山北坡生態修復與治理應以生態系統自然修復為前提,以退牧還草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生態公益林建設、自然保護區建設等重點生態建設工程為依托,加強對冰川、森林、草原、濕地、荒漠等生態系統和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加快植被恢復。
3.1 上、中、下游聯合行動,實現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的耦合與協調發展
祁連山山地水源涵養生態系統、河西綠洲生態系統、北部荒漠生態系統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功能互補的復合生態系統,必須將祁連山山地生態系統、河西綠洲生態系統和北部荒漠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上、中、下游統籌,農業、林業、水利、土地、環境等各部門之間相互協調,國家、地方、個人共同努力,才能達到生態保護的目的[26]。上游山區應加強森林、草原、濕地、冰川的保護和修復,通過實施封山育林、退牧還草、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工程,主要依靠生態系統自然修復能力恢復植被,增強生態系統穩定性,涵養水源,保持水土[27]。在中游綠洲區應實施節水工程,大力發展節水農業、現代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加快城鎮化進程,轉移安置山區和荒漠區農牧民,為荒漠區下泄足夠的生態用水,促進山區和荒漠區生態恢復[28]。荒漠區應禁止和限制開荒放牧行為,減輕人為干擾破壞,加快植被恢復,最大限度地固定和阻擋流沙移動,減輕風沙對綠洲的危害,實現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的耦合與區域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29]。
3.2 合理布局土地類型,提高生態系統整體服務功能
從祁連山北坡自然地理條件、生態保護與治理的要求及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出發,科學編制祁連山區土地利用規劃,科學區劃森林、草原、濕地、耕地、建設用地等分布及面積比例。應將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退耕還林區、封山育林區、生態極度脆弱區土地,有重要科研價值的草場,冰川、沼澤、湖泊、河流等濕地,由省政府頒發生態用地使用權證,落實土地權屬,嚴格保護,實行用途管制和分級管理,規范利用程序,實行生態用地面積占補平衡。落實生態用地保護利用責任制,將生態用地保有量、占用生態用地定額作為政府目標考核的重要內容[30]。
3.3 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擴大生態補償范圍
2011年,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國家林業局批準將保護區所在地張掖市和天祝縣作為西部地區生態文明示范工程試點區,2012年國家發改委將祁連山區列為國家生態補償示范區。應盡快建立健全祁連山區森林、草原、濕地、流域和礦產資源開發等領域的生態補償機制,將祁連山北坡水源涵養區的林地、草地、濕地、冰川等水源地全部納入生態效益補償范圍,適度提高生態效益補償標準;建立以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為主體的生態補償機制,并進一步健全省級公共財政體制、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中對祁連山水源涵養區的生態補償力度,落實長期穩定的生態效益補償渠道。進一步完善祁連山水源涵養區水、土地、礦產、森林、濕地等各種資源費的征收使用管理辦法,加大各項資源費使用中用于生態補償的比重。根據水資源保護開發的實際需要,逐步提高水資源費征收標準,調整優化水資源費使用結構,加大生態保護資金投入。科學編制流域和區域相結合的水資源配置方案,完善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積極探索建立水資源取(使)用權出讓、轉讓和租賃的交易機制[31]。
3.4 實行生態移民,減輕人類對生態的干擾
當前,造成祁連山北坡生態退化的主要因素是超載放牧和開荒種地,因此近期應首先把在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內生產生活的4.1萬多居民安置到保護區外。加強安置區農牧民培訓,提高農牧民職業技能,增強牧民自我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幫助其逐步轉換身份或轉產實施舍飼養殖,收回其原承包的耕地、草場,從根本上解決過度開墾和超載放牧造成的生態退化問題。同時,加快山區產業結構調整,建立以農牧產品開發和深加工為主的工業園區,提高畜牧產品的附加值,加快小城鎮建設,讓移民安居樂業,脫貧致富[32]。
3.5 加強監測研究,為生態保護與治理提供可靠依據
爭取國家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網絡綜合研究中心建立專門的祁連山水源涵養生態系統監測研究站,設立東、中、西三個長期生態定位監測站和地質、水文、氣候、植被、水保監測網絡,對祁連山生態系統實施長期、規范、系統監測。建立祁連山區綜合地理信息系統,納入政府決策專網,為黨政部門科學決策管理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服務。加強祁連山水源涵養生態系統結構功能及優化調整技術研究,深入研究祁連山不同生態系統水源涵養機理及大氣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及冰川相互轉化的水土氣生過程及不同生態系統涵養水源結構優化調整技術,調整優化不同生態系統結構,增強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生態服務功能[33]。
[參考文獻]
[1] 陳昌毓.祁連山生態功能巨大[J].氣象知識,2006(4):28-31.
[2] 江澤慧.加強祁連山北麓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工作[J].今日國土,2009(3):6-7.
[3] 郭生祥,汪有奎,張建奇,等.基于“3S”技術的祁連山自然保護區森林資源調查分析[J].林業實用技術,2011(3):47-49.
[4] 張子廉,曹永林,王樹青,等.天祝縣牧區開發示范工程項目草地圍欄建設及其綜合效益[J].草業科學,1999,16(2):41-43.
[5] 李文卿,胡自治,龍瑞軍,等.甘肅省退牧還草工程實施績效、存在問題和對策[J].草業科學,2007(1):1-6.
[6] 白潔,王學恭.肅南縣退牧還草工程的實踐與績效[J].中國水土保持,2010(1):21-23.
[7] 天祝縣畜牧局.天祝縣草畜平衡和退牧還草工程情況[EB/OL].http://www.gstianzhu.gov.cn/tianzhu/Html/bmncy/10215495079.html,2008-03-17.
[8] 酒泉日報.肅北打造草原生態保護利用示范區記略[EB/OL].http://jq.gansudaily.com.cn/system/2013/07/29/014565434.shtml,2013-07-29.
[9] 戴聲佩,張勃,王海軍,等.基于SPOTNDVI的祁連山草地植被覆蓋時空變化趨勢分析[J].地理科學進展,2010,29(9):1075-1080.
[10] 王善舉,魏建輝.祁連山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戰略研究[J].甘肅林業科技,2009,34(1):62-65,75.
[11] 安雪峰,梁生江,任國玲.祁連山自然保護區康樂自然保護站野生動物調查與研究[J].野生動物,2009,30(1):14-17.
[12] 陳應鋒.祁連山物種多樣性研究與保護[J].中國園藝文摘,2012(5):187-188.
[13] 賈文雄,何元慶,李宗省,等.祁連山區氣候變化的區域差異特征及突變分析[J].地理學報,2008,63(3):257-269.
[14] 趙力強.冷龍嶺冰川表面沙塵及冰川近期變化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9.
[15] 張九天,何霄嘉,上官冬輝,等.冰川加劇消融對我國西北干旱區的影響及其適應對策[J].冰川凍土,2012,34(4):848-854.
[16] 趙錦梅,張德罡,劉長仲.祁連山東段高寒地區土地利用方式對土壤性狀的影響[J].生態學報,2012,32(2):548-556.
[17] 盛海彥,張春萍,曹廣民,等.放牧對祁連山高寒金露梅灌叢草甸土壤環境的影響[J].生態環境學報,2009,18(3):1088-1093.
[18] 湯萃文,張忠明,肖篤寧,等.祁連山石羊河上游山區土壤侵蝕的環境因子特征分析[J].冰川凍土,2012,34(1):105-113.
[19] 閆月娥,王建宏,石建忠,等.祁連山北坡草地資源及退化現狀分析[J].草業科學,2010,27(7):24-29.
[20] Hou F J,Nan Z B,Xie Y Z,et al.Integrated crop-livestock production systems in China[J].The Rangeland Journal,2008,30(2):221-231.
[21] 戴聲佩,張勃,王強,等.祁連山草地植被NDVI變化及其對氣溫降水的旬響應特征[J].資源科學,2010,32(9):1769-1776.
[22] 顧自林,趙忠.祁連山北麓草原生態環境現狀及保護對策[J].草原與草坪,2009(5):80-832.
[23] 趙忠,何毅,李青,等.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草原資源調查[J].草業學報,2010,19(6):231-247.
[24] 趙華,竇志剛.鹽池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存在的生態問題及研究對策[J].甘肅林業科技,2009,34(4):53-56.
[25] 霍玉俠,吳官勝,仝紀龍,等.小孤山水電工程對祁連山自然保護區的生態影響及對策[J].中國水土保持,2010(12):13-15.
[26] 孫鴻烈,李秀彬,樊江文,等.西北干旱區生態建設的若干科學問題[J].科學,2005(6):48-50.
[27] 鄭度.中國西北干旱區土地退化與生態建設問題[J].自然雜志,2007,29(1):7-11.
[28] 程國棟,張志強,李銳.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建設的若干問題與政策建議[J].地理科學,2000,20(6):503-510.
[29] 任繼周,侯扶江.山地—綠洲—荒漠的系統耦合是祁連山水資源保護的關鍵措施[J].草業科學,2010,27(2):4-7.
[30] 李雪梅.我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研究[D].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08.
[31] 趙建林.打造祁連山生態特區[J].發展,2011(3):33-34.
[32] 趙宏利,陳修文,姜越.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發展模式研究——以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例[J].生態經濟,2009(7):105-108.
[33] 李建軍,張會儒,王傳立,等.水源涵養林多功能經營結構優化模型初探[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2,32(3):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