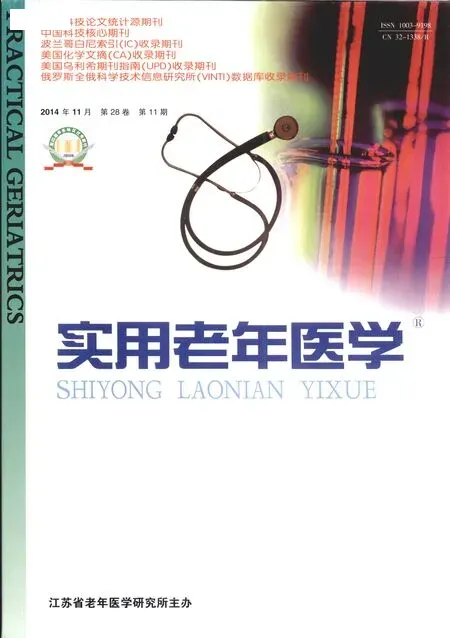以呃逆為主要表現的圍手術期相對低血壓1例報告
劉秀琴 謝麗金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72歲,因“腹痛腹脹5 d、惡心嘔吐2 d”急診入院,診斷為“右側嵌頓疝”,需行手術治療。既往有高血壓病史8年,最高血壓220/120 mmHg,平時不規則服用降壓藥,血壓控制差。否認有冠心病、糖尿病、腦卒中病史。本次入院前可以耐受輕體力勞動,心功能2級。入院后相關檢查:血常規、凝血功能、肝功能未見明顯異常;尿常規:尿蛋白(++);腎功能:尿素氮(BUN)14.41 mmol/L,肌酐(CRE)182.5 μmol/L,尿酸(UA)583.1 μmol/L;心電圖(ECG)示竇性心律,頻發房早,左室高電壓;胸片示右下肺感染。因急診入院,未行心臟彩超檢查。
患者于22:15進入手術室,開放靜脈,常規監測心率(HR)、血氧飽和度(SpO2)以及ECG,無創血壓(NIBP),每2 min 1次。入室時血壓235/110 mmHg,ECG示頻發房早。詢問患者晨8:00左右最后1次服用硝苯地平緩釋片10 mg。擬行椎管內阻滯,考慮到可能發生的血壓下降,未行特殊處理。適當擴容,選擇L1-2進行連續硬膜外阻滯,穿刺成功后給予試驗劑量1.6%利多卡因2 ml,觀察5 min麻醉平面出現,未見并發癥,再次追加上述藥液3 ml,5 min測得痛覺消失平面T10,再次追加2 ml。22:45切皮,阻滯平面上界T8。在此過程中血壓逐漸下降至180/90 mmHg左右,患者未訴明顯不適,麻醉效果滿意。至22:53左右血壓繼續下降至178/85 mmHg,患者出現呃逆,無其他不適。囑患者深吸氣后屏氣無明顯效果。大約10 min后當牽拉腸管時血壓突降至140/75 mmHg,患者出現打哈欠、疲倦面容,馬上給予麻黃堿6 mg靜脈推注,2 min后血壓升至185/92 mmHg,并逐步上升。在此過程中觀察到患者呃逆消失。23:25血壓230/110 mmHg。考慮到血壓過高可能導致心腦血管不良事件,靜脈推注鹽酸烏拉地爾2.5 mg,患者血壓逐步下降,當降至179/88 mmHg時患者再次出現呃逆,但無其他任何不適。密切觀察血壓未進一步下降并逐步回升,約5 min后升至術前水平,呃逆也逐漸消失。后患者血壓一直維持在200/100 mmHg左右直至手術結束。
2 討論
呃逆常見的原因包括胃腸道疾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化療以及相關藥物的不良反應等[1-4]。該患者存在腸管嵌頓,但追問病史并無呃逆癥狀,且2次呃逆都發生在血壓下降時,血壓回升后呃逆即消失,因此推測呃逆的發生與血壓下降有關。當血壓進一步下降時患者出現打哈欠、面容倦怠等癥狀,與諸多患者低血壓早期表現極為相似[5]。呃逆中樞位于腦干,分布廣泛,與孤束核、疑核等多個神經核團以及結構有關[6],當腦干血供受到影響時,患者便會出現呃逆。部分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甚至以呃逆為唯一或者首發癥狀[7-8]。
高血壓是腦出血和腦梗死最重要的危險因素[9]。老年患者大動脈彈性減退,調節血管能力差,圍手術期要求血壓平穩,避免血壓急劇波動導致心腦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10]。無論是椎管內用藥還是靜脈用藥均應采用“滴定”的方法,從小劑量開始緩慢增加,爭取以最低有效劑量達到治療效果。高血壓患者在麻醉誘導和氣管插管期間,血流動力學往往不穩定。無論術前血壓控制到什么程度,大部分高血壓患者麻醉誘導后和氣管插管后會出現低血壓[11]。基于這一考慮,本例將連續硬膜外阻滯作為首選的麻醉方法。硬膜外間隙和順應性隨年齡增長不斷下降,獲得相同麻醉平面所需的局麻醉藥劑量也呈下降趨勢。本例硬膜外的給藥方式,劑量較小但仍取得滿意阻滯。
烏拉地爾是α-受體阻滯劑,降壓緩和,常用劑量為0.6 mg/kg,持續時間短暫,必要時還需重復用藥[12]。本例患者烏拉地爾用量僅為2.5 mg,收縮壓下降即達50 mmHg,說明老年患者對藥物敏感性增加。收縮壓達180 mmHg已經屬于高血壓3級,極高危組,需要盡快給予強化治療,但該患者血壓低于這一水平即表現出腦缺血癥狀,說明腦血流自主調節功能已經發生改變,盲目降壓可能影響腦灌注,導致嚴重腦血管并發癥的發生。對于這類患者,如何尋找適當的平衡點,既能降低后負荷減輕心臟負擔以減少心臟不良事件,又能維持正常的腦組織灌注,同時還能避免出血性腦血管病的發生,是一個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臨床上許多治療呃逆的方法并不適于本患者。比如氯丙嗪靜脈注射可能會導致血壓進一步降低,利多卡因可能會加重對心臟的抑制[13],因此在圍手術期處理過程中除使用屏氣治療外主要以觀察為主,隨著血壓的逐步回升患者呃逆也得到緩解。
控制欠佳的老年高血壓患者急診手術時風險較大,本例患者ECG、尿常規、腎功能等檢查結果均提示長期高血壓導致的靶器官損害。呃逆作為低血壓不典型的臨床表現需要引起警惕,及早控制血壓波動有助于降低風險,減少心腦血管并發癥的發生,保證患者生命安全。
[1]汪生梅.胃癌術后發生頑固性呃逆的原因分析及護理對策[J].實用臨床醫藥雜志:護理版,2008,4(1):17-18.
[2]叢林,梁慶成.腦干梗死伴發呃逆與血氯的關系及其損傷部位的研究[J].哈爾濱醫科大學學報,2010,44(6):623-624.
[3]黃方,方放,張瑗,等.巴氯芬治療高齡老人胃管相關性呃逆的臨床研究[J].實用老年醫學,2013,27(10):876-878.
[4]池迎迎,李文峰.昂丹司瓊和托烷司瓊致化學療法病人頑固性呃逆20例[J].中國新藥與臨床雜志,2005,24(5):390-391.
[5]陳敏章.中華內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4038-4041.
[6]李振洲,郎森陽.呃逆與腦血管病[J].國外醫學腦血管病分冊,2004,12(3):198-200.
[7]程啟明.以呃逆為唯一癥狀的腦血管意外1例報告[J].山東醫藥,2008,48(42):41.
[8]李繼,王倩,張狀.以呃逆為首發癥狀的視神經脊髓炎一例并文獻復習[J].中華神經醫學雜志,2011,10(12):1284-1285.
[9]吳江.神經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154.
[10]姜馨,呂卓人.老年高血壓的治療進展[J].中國老年學雜志,2005,25:1429-1431.
[11]G.Edward M,Maged SM,Michael JM.摩根臨床麻醉學[M].岳云,吳新民,羅愛倫,譯.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386-388.
[12]戴體俊.麻醉藥理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133.
[13]王月華.腦血管病合并頑固性呃逆的內科治療[J].青島醫藥衛生,2006,38(3):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