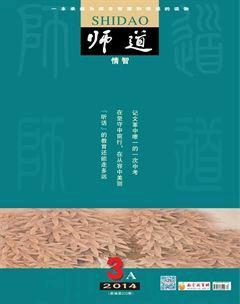記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中考
時間回溯到42年前夏天,文革中,貴州省沿河中學。
“崔某某栽了!”——平地一聲雷,頃刻間傳遍了沿河中學校園,震得我們目瞪口呆。
崔某某何許人也?沿河中學1972屆高中畢業生、叱咤風云的紅衛兵領袖、沿河中學革命委員會學生成員,老師們見了都要點頭堆笑、同學們見了都要行注目禮、牛鬼蛇神見了差不多要魂飛魄散的人物,根正苗紅,前途無量。怎么會栽呢?
知情人說,他栽在舞弊上。
文革中期,沒有考試,何來舞弊之說?1966年“文革”開始,1966年到1969年期間,中國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中小學停課三年,到1970年才復課。從1970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陸續招生開學。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招收“具有相當于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因此這些人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者“工農兵學員”。不需要高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即可。既然上大學不用考試,那么順理成章,上高中也不需要考試。再說,我們初中兩年,除了天天勞動,批判資產階級外,并沒有正規地學習過文化課,就算要考試,我們也沒有什么文化拿來應試。
正當大家都認為知識無用的時候,意外發生了。1972年夏天,貴州省銅仁地區教師進修學校成立到沿河中學招生,居然需要考試。(注:1972、1973屆沿河中學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都是文革前的農村籍初中畢業生,文革中回鄉勞動了幾年,所以不需要下鄉鍛煉兩年,可以直接參加考試;城鎮非農業戶籍的畢業生幾乎沒有,因為1970以前就下鄉當知青去了)這批高中畢業生有點文化課底子,大部分不怕考試;可是崔某某就怕考試,一來是因為文革開始時他才剛上初一,沒有學到多少知識;二是推薦到沿河中學讀高中以來,天天忙于斗批改,沒有正經學習過文化課;真刀真槍考試他必然吃虧。別看他當下在學校紅得發紫,一旦考不上,他就得回鄉下修理地球。怎么辦?他思來想去,終于決定鋌而走險:偷試題!地區教師進修學校的入學考試試卷已經運到沿河中學,封存在教務處,負責看管試卷的是右派教師湯某某。于是在考試前某天夜里,崔某某以校革委委員、紅衛兵領袖之尊去視察教務處,威逼之后,右派湯某某乖乖偷了一份試題給他。本來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的,不知道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敗露了。這下,所有飽受他欺凌的“臭老九”們一致要求嚴懲他。處理結果:崔某某品質惡劣,膽大包天,竟敢舞弊,情節嚴重,影響極壞,不得錄取!平時叱咤風云呼風喚雨的他,此刻回天無力,從此落魄終生。
班主任趁機對我們進行理想前途教育:看見沒有?光政治表現好是不保險的,文化課也要過硬。父母也幫我分析形勢,看樣子今后上高中、上大學也是要考的,文化課不能丟,要重視。于是從1972年秋季起,沿河中學在文革中首次掀起學習文化課的高潮。
不能不佩服老師們和父輩的先見之明,大約在1973年元月,就傳來了1973年大學招生采取群眾推薦與入學考試相結合的消息。高中招生向來跟著高校走,文革當中也不例外。有高考肯定就有中考。學校指示,初、高中畢業班除了每學期到校辦農場勞動一個月不能省外,其余臨時性勞動取消,全力以赴應付高考和中考!
班主任兼數學老師肖毓榮為我們班制定了初中數學全面復習計劃,將數學知識進行分類。編口訣幫我們記住數學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要用上,項數定要有三項。其中兩項能平方,二倍前后中間放。
平方差公式:
兩項和乘兩項差,等于兩項平方差。
和的立方公式及差的立方公式:
四項兩項能立方,兩個三倍中間放。三倍前平方乘后,三倍前乘后平方。符號相同和立方,正負正負差立方。
……
化學老師如法炮制,也幫我們編了元素化合價口訣:
氫銀鉀鈉正一價,鈣鎂鋅,正二價;
鋁三硅四磷五價,碳鉛錫,正二正四價。
……
語文教師陳昭樸,則注重因材施教,針對每個同學的特點進行個性化的輔導。我的每篇作文,他都要寫下密密麻麻的批語。如:敘事要有點有面,光有點沒有面,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文章就缺乏廣度;光有面沒有點,文章就顯得空泛,沒有深度。你的文章點有余面不足,篇幅雖長卻缺少全局視野。又如:文章思路混亂,應圍繞一個中心來談;用中心來統率材料,做到觀點鮮明,言之成理。又如:你的語文程度不低,但是你的進步緩慢。為什么?因為你的每次作文都是在重復自己,跟推磨一樣,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沒有向前跨出一步。要學會謀篇布局,要學會多種表達方式的綜合運用!
在全體任課老師的精心輔導下,我們如期迎來了1973年7月的中考。
中考之前,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這次高考比一年前貴州省銅仁地區教師進修學校招生嚴格得多,除初中應屆畢業生外,其余學生提前放暑假離校。校門口拉了一條大大的紅底白字橫幅:“貴州省1973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沿河中學考場”。吸取一年前崔某某舞弊之教訓,高考試題封存在縣教育局,由縣武裝部派出一個班的戰士全副武裝地看守。考試那兩天,作為考場的兩棟教學樓的入口和出口都有解放軍戰士持槍站崗。在七月絢爛的陽光下,年青的戰士是那樣英姿颯爽,草綠色的軍裝是那樣綠,領章帽徽是那樣紅,半自動步槍上的刺刀閃著銀光。場面極為莊嚴。
高考剛一結束,中考馬上登場。考生由成熟的高中生換成滿臉稚氣的我們。考場門口沒有解放軍持槍站崗,但是我們的神圣感并沒有減弱。第一場考語文:只考一篇作文,兩題選一:1.家鄉的變化;2.我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我們那時的習慣,家鄉就是祖籍。我的祖籍在松桃,五歲時隨父母回去探過一次親,沒有太深的印象,之后十年再也沒有回去過,有沒有變化不曉得。這個題目不能寫,只得選第二個題目:我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既然是“愛”,那就要以抒情為主,我的強項是敘事,當然抒情也不是弱項。特別是陳昭樸老師平時對我進行多種表達方式的綜合運用的訓練,此刻真的派上了用場。成串妙語在腦海跳躍:endprint
東風萬里,紅旗飄揚。看我們偉大的祖國,正欣欣向榮,昂首闊步地前進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啊,祖國!您山河壯麗,繁榮富強。我們生長在您的懷抱,感到無限幸福,無尚榮光。我們愛您,就像愛自己的母親一樣……。
接下來每一段都以“我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開頭,結構模仿剛剛流行的歌曲《我愛這藍色的海洋》,且一韻到底,全押ang韻,韻律和諧。現在回頭去看那篇應試作文,有明顯的時代印跡,也比較幼稚;但是在當時學生寫作能力幾乎沒有得到開發的年代里,我這篇作文就算是水落石出了。寫完以后我又從頭至尾細細檢查了兩遍,確認無誤。于是交了頭卷,幾乎是跳著走出考場。
之后還考了政治、數學、理化等。一切正常。
那年中考,除沿河中學、沿河二中設了考場外,各區中學都設了考場,一共是11所考場,多少人參加中考不知道,應該不少于1500人。考試結果出來,我們班考了三個全縣第一:語文第一:楊建華;數學第一:田維明;理化第一:王發坤。當年的三科狀元都出在我們班,可惜那時候不興宣傳狀元,我們的老師也沒有得到一分錢的獎金。
中考后的某一天,我和父親在縣城街上走,迎面走來一位中年男子,老遠就和父親打招呼:“老楊,你家兒子考得好哎!”父親忙告訴我,這是教育局長張加鵬同志,快叫張叔叔。張局長看著我,喲!就是你呀!了不起了不起,文章寫得好,字也寫得漂亮。各區來閱卷的語文老師都在用復寫紙謄抄你的作文呢!父親忙替我謙虛。我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我讀高中應該沒有問題了。
又過了不久,《人民日報》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一則報道:《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遼寧省的一位考生物理化學考試只得了6分,這位考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準備了一封信,在考場上把信抄在試卷的背面。他在信中一方面聲稱工作忙,為了集體利益,沒有時間復習功課,同時表示“對于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另一方面,他又說上大學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說:“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他的信得到當時左派領導人的贊賞,夸他是個英雄,敢反潮流。不僅上了大學,還入了黨,人們后來稱他為“白卷英雄”。結果,大學招收進行文化考試在第一年試行時就腰斬了。高考一廢止,中考自然也就不見蹤影了。
幾十年以后才知道,文革當中那唯一的一次中考是沾了那唯一的一次高考的光。背景是林彪事件后,周恩來總理試圖整頓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試行推薦和文化考試相結合的方法。卻不料交白卷的成了英雄,周恩來總理整頓教育的希望落了空。全國千千萬萬企盼進入大學深造的學子更是希望落空。
但是我仍然感謝文革中那唯一的一次中考,當時我父母都屬于挨整的對象,沒有那一次中考,沒有語文考第一的成績,我就不可能被高中錄取。雖然高中兩年仍然沒有學多少文化課,但是中考的經歷,讓我認識到:無論世道如何變化,有文化總比沒文化好,知識多總比知識少好。學校不開文化課,我就自學。懷著這一信念,我終于熬到了文革結束,迎來了1977年冬天恢復的首屆高考,在成千上萬的考生中脫穎而出,跨入了高校的大門。
責任編輯 李 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