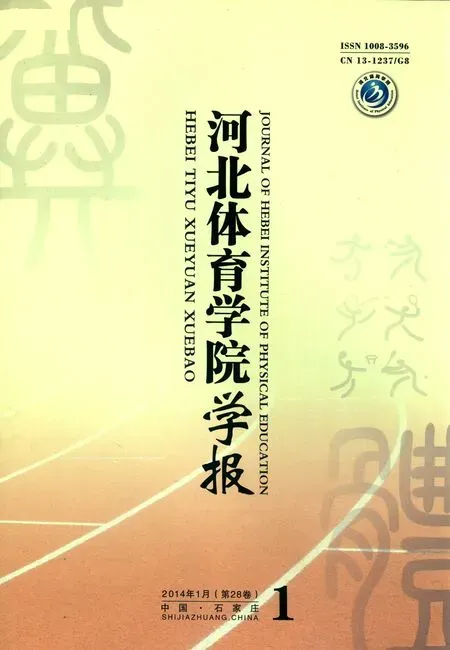傳統武術文化生存思辨
曹紅敏
(池州學院 體育系,安徽 池州 247000)
2006年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又發出《關于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通知》,批準了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少林功夫等7項傳統武術位列其中。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又有峨眉武術、紅拳等11個拳種。2011年的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又增加了通背纏拳等4個拳種。目前,各級政府正在制訂的國家、省、市、區(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傳統武術占據了重要位置,據不完全統計,進入各級第一批和第二批文化遺產名錄的傳統武術有80多項。一個項目或一個拳種被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很顯然,它已經處于滅絕或頻臨滅絕的狀態,拳種的失傳,也伴隨著其相應文化的消失。20世紀80年代國家大力挖掘武術文化,統計出拳理清晰、傳承有序的拳種129種。為什么在短短的30多年中,竟有如此多的傳統武術拳種及其文化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處于娛樂健身手段如此之多的現今社會,面對國外競技體育項目以及文化的沖擊,伴隨著國內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需求和品位的提高,傳統武術怎樣繼續生存是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因為“研究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礎,又是其保護的重要方式”[1]。
1 西方體育思想文化對中國傳統武術的沖擊
1.1 傳統武術軍事地位的喪失
曠文楠認為:“武術與軍事是同源之水,同本之木。”然而,火器的發明與使用使原本在軍事戰爭中主要依靠肉搏的武術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積極搏殺功能。面對西方列強火炮的強烈攻擊,清政府的軍隊在此面前已不堪一擊。為此,清政府開始整編軍隊、編練新軍,操練以列隊、刺殺、戰陣、戰術為主的兵操。到1903年,清政府設練兵處后全面裁汰綠營,編練新軍。至此,以技擊武術為主要操練手段的清軍完全變了模樣,武術在軍事中的決定性地位完全喪失;同時,武舉制的廢除更是把練武之人的仕途之路堵死了。
1.2 傳統武術價值觀的改變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在給中國帶來屈辱和痛苦的同時,也讓中國人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入,西方傳教士、軍人和商人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國,他們開辦學校,傳入了西方的體育項目,同時也把西方的體育競技思想一并傳入。但這種競技體育思想與傳統武術的價值觀截然不同,中國武術注重倫理道德、內外兼修、修身養性和觀賞性,而西方的競技體育則注重公平、公正、更高、更快和更強。面對西方體育文化的沖擊與其對中國體育市場的侵占,中國武術要想要與世界融合、與奧林匹克精神融合就必須改變自己,競技武術應運而生,但它又背離了中國傳統武術的價值取向和技擊本質。西方競技體育對傳統價值觀的沖擊導致傳統武術價值觀的喪失,使傳統武術的發展陷入尷尬的境地。
2 傳統武術生存環境的變更
“中國武術的最原始的本質,必然就是擊技。”[2]武術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衛的需求才產生的。武術自其產生后在歷朝歷代中都受到重視,人們為了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就練習武技,除了懲惡揚善,還求自保。武術順應了這種社會發展的需求。明清時期,武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不但拳種繁多,而且功法理論也自成體系。武術技擊的展現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一旦外部條件發生變化,其技擊就缺少理想的展現空間,而社會前進的步伐永遠不會停息,因此這也注定了武術技擊的表現方式必然逐漸被異化。誠如葛兆光先生所說:“很多似乎天然合理的事情,其實細想起來未必是 ‘天經地義’,只是在一段歷史時間中逐漸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同罷了,追根究底的話,它并不見得是在堅不可摧的基礎上。”[3]所以,隨著現代法治社會的建立,人們的人身安全有了法律的保障,武技生存的外部環境也就發生了改變,當武技不再是人類生存的必需手段時,武術的發展也就緩慢前進,甚至停滯。
2.1 傳統武術傳承方式的改變
中國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有其特定的傳承方式。武術的傳承方式基本遵循家族式、家庭式和師徒式的傳承模式。武術家族、家庭式的傳承大大增加了民間習武的人數和規模,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武術村,河南溫縣陳家溝的太極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時間的長期性,使民間武術的傳承必須是師徒傳承。”[4]這是因為武術作為非物質的、無形的文化,其傳承方式必須是口傳身授,而且這種傳承需要較長時間才能保障技藝的整體傳承。正如民間老拳師李仲軒所言:“功、理是很 ‘身體化’的東西,得身教方能體會得出,講是講不明白的,靠著在練武場上喊幾句口訣,即使是古代秘傳真實不虛,做學生的也很難體會。”[5]然而,學校體育制度的確立改變了武術的傳承方式,家族式的傳承被武術館校和學校體育取代,師徒制的傳承被課堂教學所代替。
2.2 傳統武術傳播場所的消失
“村落、廟會、慶典和節日等文化同構體是以地域性、血緣關系或社會、經濟結構為基礎的,擁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主要方式。這些共同體是民族傳統體育不可或缺的生存空間,表現出時間的節律性,場所的定點性,成為了傳承武術語言、武術傳統、武術思想、武術信仰和武術價值的重要場域。”[6]然而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武術的傳播場所正大幅度縮減,甚至消失。以前傳授武術的村落改建了高樓大廈;廟會上出現的不再是武術藝人的拳腳功夫,而是農貿交易活動;慶典上昔日生龍活虎的舞獅舞龍表演、跌宕起伏的對打對練表演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式的歌唱舞蹈。
3 傳統武術的生存優勢
雖然傳統武術的發展受到了西方競技體育的嚴重沖擊,加之傳統武術生存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改變,致其喪失了其原有的主導地位,進而使其發展受困,但傳統武術自身所蘊含的文化內涵,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載體,正如王崗教授所說的:“今天的中國武術已為當代人解讀傳統文化充當著載體和途徑,為我們探究傳統文化思想精髓提供了便利。”[7]
3.1 傳統武術的健身娛樂優勢
傳統武術的健身娛樂功能從古有之。古代記載中有“執干戚舞”的傳說:“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說此舞蹈可以治百病。再如宋元時期,商業相對比較發達,人們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出現一片繁榮景象。此時的瓦舍藝人把武術的健身和娛樂功能通過表演完全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在當時,不管是廟會還是節日,都會看到武術藝人的表演,甚至在軍中也征召了一些精于武藝、擅長雜技百戲的藝人,專習技藝,以供表演之用。明清是武術集大成時期,武術的花法表演、套路演練以及對練表演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傳統武術的健身娛樂功能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而如今,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社會負擔以及心理壓力越來越大,各種疾病也越來越多。中華養生觀認為,各種養生方法都是通過調身、調息、調心等以修煉人身三元——精、氣、神。把“精、氣、神”視為人體生命存亡的關鍵所在,認為只要精足、氣充、神全,自然能夠祛病延年。這正是傳統武術練習時所要求的“內三合”,即:“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這也是傳統武術練習的精、氣、神。最能體現這一理念的典型就是太極拳,練習太極拳時講究情神貫注、意守丹田、不存雜念,進而達到人與自然的相通,最終達到鍛煉體魄、愉悅身心的目的。除了太極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傳統拳術也都具有此功效。所以,傳統武術獨特的健身娛樂功能是其最為實用的功能,也是傳統武術在當今社會繼續存在的最重要依據。
3.2 傳統武術的教化優勢
“尚禮崇德”是古代俠士倫理道德的基礎,也是習武之人生活的基本準則。明代的戚繼光也曾把能否確立“師道”看成習武者能否有德的一大條件,他說:“敬習之道,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而不悅,師道廢而教無成矣。”[8]武諺還有云:“未曾學藝先識禮,未曾習武先明德。”為此,許多拳種門派都強調修德,并制定了各家簡繁不一的門規戒約。而且,傳統武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練成的,要求練武之人不怕嚴寒酷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這就培養了練武之人堅毅、果敢、豁達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所以,我們今天把習武的這種精神用于培養青少年正確的社會榮辱觀和正義感,培養青少年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尊老愛幼、尊師重道、樂于助人、堅韌不拔的優良品格,同樣行之有效。
4 傳統武術文化的生存策略
“特定的文化空間產生了特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依賴特定的文化空間而生存。”[9]所以,我們要想使傳統武術文化繼續生存下去,為今所用,就必須為傳統武術文化的傳承保護創造有利的環境。
4.1 國家需要是傳統武術文化傳承的最有力保障
從遠古部落之間的戰爭開始,技擊就成為部落制勝的法寶。在夏商周,農業的發展使產品有了更大的“過剩”,奴隸主為了掠奪更多的財富就會發動戰爭,而戰爭的勝利必須依靠武技本領。因此,國家的需要使武術的應用被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封建社會同樣也是如此,統治階級一方面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就必須用武力鎮壓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要擴大疆域和防御外敵入侵,就必須大肆興兵、大練武技,這就促使武術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尤其是唐朝武舉制的建立使練武之人有了展示自己的平臺,最大程度地激發了練武人的熱情,促使民間武術和軍事武術迅速發展。
縱觀武術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國家需要并大力支持是武術得以迅速發展的最有力保障。所以,要發展武術,弘揚武術文化,就必須依靠政府的支持,這種支持不僅僅是物質的和政策的,更重要的把發展武術納入法律的范疇。
4.2 傳承人的銜接是傳統武術文化傳承的生命線
生存環境的變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娛樂手段。人們不再像先輩們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閑來無事打打拳、聽聽戲,所有的技藝都有源源不斷的傳承人,而現在高樓大廈的建立、城鎮化生活方式的推進,很多年輕人都跑到大城市打工、生活,留守的都是些老弱病殘,人們都在為錢而拼命,已不知傳統技藝為何物,傳統技藝的傳承在人的問題上出現了斷層。正如文化學者王文章所言:“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形成一條永不斷流、奔騰向前的河,人,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一旦老藝人離世,他身上承載的某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隨之消亡,所以,解決傳承主體即傳承人的問題,乃是當務之急且是重中之重的大事。”[10]王崗教授也認為:“作為口傳身授的武術文化,作為活態所展示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人的因素比以前所傳授的技術體系、理論體系、文字記載等更重要。”[11]所以說,傳承人是傳統武術文化傳承的核心環節,是傳統武術文化得以傳承的生命線。因此,我們對待傳統武術的傳承人不能單純地從精神上給予鼓勵,更重要的是從物質上給予保障,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傳統武術文化沒有傳承人而致使其失傳的后果。
5 結語
縱觀傳統武術的發展歷程,對傳統武術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必須依靠國家,而傳統武術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正是改變我國現存的某些不良社會現象所需要的。真正使傳統武術文化得以保護和傳承,就必須把保護傳統武術文化納入法律的體系,用法律約束力來執行傳統武術文化保護的相關政策,同時對傳承人的保護與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1]張國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模式研究[J].海軍工程大學學報:綜合版,2009(2):88-92.
[2]張震,楊麗.武術本質層次論[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4-37.
[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44.
[4]郭玉成.傳統武術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2):51-57.
[5]李仲軒,徐皓峰.逝去的武林:1943年的求武記事[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54.
[6]王春光,祝偉明.文化社會學視域下武術群體研究[J].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12(6):86-88.
[7]王崗,潘冬法,包磊.中國武術的當代勢力[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9,33(5):27-32.
[8]周偉良.師徒論——傳統武術的一個文化現象詮釋[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4(5):583-588.
[9]張玉強,陳有忠.我國傳統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述評[J].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12(5):86-90.
[10]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347.
[11]王崗.關注武術傳承的主體:人[J].搏擊·武術科學,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