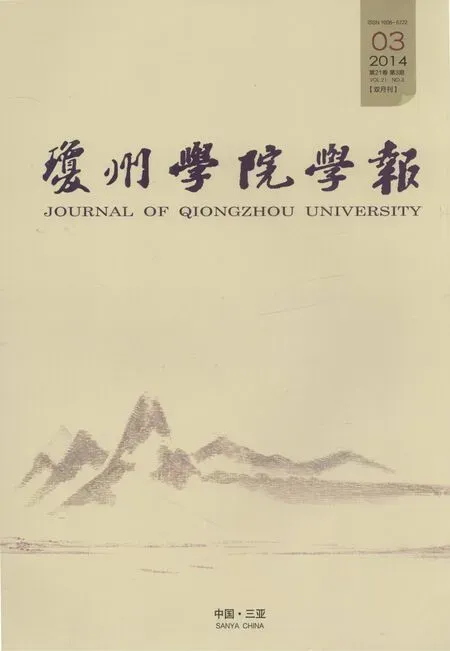宇文所安五言詩論——以《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為藍本
李明華,胡良萍
(瓊州學(xué)院 人文社科學(xué)院,海南 三亞572022)
從古至今,對于五言詩的起源與成熟的論斷由于學(xué)者對史料的理解不同,從而產(chǎn)生了不同的見解。目前文學(xué)史上關(guān)于五言古詩來源最主流的說法是“東漢說”。五言詩歌是否真的起源于東漢,或是更早的時期,亦或是東漢之后的另一個時期。我們還不得而知,學(xué)術(shù)界的學(xué)者們還在探索中前行。
其中,宇文先生和木齋先生對古詩的起源及其形成和發(fā)展進行了新的探討,產(chǎn)生了對傳統(tǒng)文學(xué)史約定俗成的對古詩起源及其形成和發(fā)展觀點的質(zhì)疑,并結(jié)合史料分析研究,從而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在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和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這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后,就像是一塊石頭投入了平靜的湖面,使得傳統(tǒng)的五言詩起源于“東漢說”的觀點面臨重組或解構(gòu)的挑戰(zhàn)。與時代傳統(tǒng)主流觀點相悖的觀點總會飽受爭議,但同時新舊觀點的碰撞、融合才會促進傳統(tǒng)觀點的發(fā)展。宇文所安關(guān)于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生成的研究成果為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研究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
本文就以宇文所安先生的新作《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為藍本,討論宇文所安對五言詩的一些觀點和看法。宇文所安所著《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一書并非簡單的研究詩歌的體裁和作者的問題,而是深入的探究詩歌是借鑒哪些材料并通過何種方式創(chuàng)作而成的。此外,作者在書中還辨證的分析了這些出現(xiàn)在公元二世紀后半期的修辭等級低俗的古典詩歌是如何被保存下來的。
我們現(xiàn)在所使用的有關(guān)古詩的教材,教師們教授的有關(guān)古詩的知識,以及我們對古詩的論斷和認識,似乎都是不變的真理,很少有人會對它們產(chǎn)生懷疑。就算有過一絲的懷疑,卻也沒有想要打破這一知識體系的想法。但宇文所安卻對這穩(wěn)定的知識體系產(chǎn)生了懷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宇文所安對所謂“漢魏”詩歌的質(zhì)疑
“我們通常認定我們所讀的是“漢魏”詩歌,但我們實際上是無法直接接觸到那些所謂‘漢魏’詩歌的。”[1]9“我們對于早期古典詩歌直到三世紀晚期的理解,是經(jīng)由兩個世紀之后一個具有不同文化特質(zhì)的時代的中介而得到的。”[1]27這一中介便是五世紀末六世紀初那一特殊的文人群體。他們孜孜不倦地對早期的詩歌進行修訂、保存、確定作者歸屬并以此來給詩歌進行排序,以及給詩歌編史。多虧了他們的勞動成果,我們才對“漢魏”詩歌有所了解。但是宇文所安抱著謹慎的態(tài)度對早期中古文學(xué)史進行反思后,對現(xiàn)存的所謂“漢魏”產(chǎn)生了質(zhì)疑。因為,我們不知道的是,在三世紀晚期到五世紀末六世紀初的這段時間里,詩歌在流傳的過程是否原封不變地被保存下來,或者是因為編者們的個人原因或受到了某一時代的成規(guī)的制約而產(chǎn)生變化。并且我們普通人在接觸閱讀“漢魏”詩歌時,也不會對其真實度進行懷疑,盡管有過懷疑,也不會對其進行過多地探討研究。
(一)手抄文本
就“漢魏”詩歌真實度這一問題,宇文所安認為,現(xiàn)存的來自手抄文本的文學(xué)體系并非其最原始的形態(tài)。他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早期抄寫者和編者,以及他們所處的抄本文化時代。從遺留下來的文本可以看出,當時編者和抄手們對于文本的復(fù)制的精確度并不是很在意。“因為手抄文本具有隨意性,抄手們在編輯和抄寫文本的過程中,會依據(jù)自己的喜好,隨意地對文本進行修改。或者是在抄寫的過程中依照其所處時代的審美情況來對詩歌進行抄寫保存。由于是人為的操作,在抄寫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錯字、漏字、借字、衍文等情況。”[1]29此外,“還有問題太多、意義難通以至于根本無法標點的文本”[1]67。
“我們不知道那些手抄本的抄寫質(zhì)量究竟如何。梁代僧人僧佑曾經(jīng)向我們證實了他閱讀佛經(jīng)寫本是如何的凌亂不堪。”[1]5并且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同一資料的來源越多,那么它遺留下來的異文也就越多。“我們看到無數(shù)異文,看到一個文本以多種不同的‘版本’存在。增減幾個對句,或使用不同的詩行,似乎都是家常便飯,不僅后期的抄本如此,六世紀之前的文本傳統(tǒng)也同樣如此。”[1]65同一種詩歌出現(xiàn)了不同的版本。“我們?yōu)g覽一下隋志即可發(fā)現(xiàn),文集的卷數(shù)和題目都會經(jīng)常發(fā)生變化;這種情況正如僧佑在整理佛經(jīng)文本書所言,‘或一本數(shù)名,或一名數(shù)本’。”[1]31這時,我們也就不能確定哪一個才是“原本”。
“鐘嶸在《詩品》中提到提到的五十九首‘古詩’顯然大部分不符合六世紀初人們對于‘古詩’所持的觀點和標準”[1]42,并且“在鐘嶸的心里,對于古詩應(yīng)該是何模樣有了自己的見解和標準,所以他在選編作品時,會依據(jù)自己的愛好和當時社會對‘古詩’所持的觀念和標準來對詩歌進行取舍和品級”[1]42。所以我們不知道是怎樣的詩歌被鐘嶸淘汰掉了。“大概沒有比這更有力的證據(jù),說明我們現(xiàn)有的‘早期詩歌’是按照某種特殊的標準從一大堆材料中挑選出來的,打上了從事挑選的時代所特有的文化觀和歷史觀的烙印。”[1]42
此外,“蕭統(tǒng)在處理有問題的作品時,總的來說還是很謹慎的,他沒有收錄那些質(zhì)量低劣但是可以確信為東漢時期的五言作品”[1]60,然而,“徐陵在編纂《玉臺新詠》時覺得并沒有謹慎行事的必要。他編纂這部詩集是為了閱讀的愉悅”[1]60。
“他們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詩歌‘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強烈意識對其加以挑選,有時甚至是改寫”[1]44,盡管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早期詩歌的文本是經(jīng)過挑選的,但它們還是可以代表早期詩歌的,只是它們的文本形式和寫作年代和作者還有待商討。
此外,“編者和抄手們在抄錄文本有時不是很細心,而且往往只是給出片段和節(jié)錄,目的只是提供適合他們需要的范例。但同時,這些材料卻沒有像那些被編輯整理多中介過的文本那樣,動輒收到‘校正’”[1]68-69,“我們知道當時的學(xué)者會訂正寫本中的錯誤,但是一個六世紀學(xué)者所認為的‘錯誤’對二十一世紀的學(xué)者來說有可能是價值連城的證據(jù)”[1]7。到了近代,“這類‘校正’通常會被編校者小心地標注出來,但我們有清晰的證據(jù)表明,在印刷文化初期,編選者們對其認為錯誤的地方往往根據(jù)自己的想法加以改正,卻不加注明”[1]69。所以我們不清楚,編者和抄手們在抄錄文本的時候,對哪些地方做了改動和刪減。
早期的詩歌除了通過手抄文本進行傳播,有時也通過口頭傳播。同樣的,這種傳播方式同樣具有隨意性。
再者,“在西晉淪陷和北宋印刷文化興起之間,皇家的藏書機構(gòu)遭受過一次又一次的損毀”[1]32。書籍遭受了的損壞或遺失,使得我們必須從其他的渠道來重新收集文本。而這些渠道收集來的文本可信度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二)編寫者們是怎樣來對詩歌進行排序
接下來,我們在來看看編者們是如何對詩歌進行排序的。書中,宇文所安用“恐白”一詞來形容人們對于五言詩歷史的態(tài)度。所謂的空白,是因為害怕空白,所以想法設(shè)法的去填補。由于五言詩的歷史太過于單薄,而為了填補五言詩歷史中的空白,出現(xiàn)了把詩歌安放在知名作者之下,然后并以作者的所處的年代來給詩歌進行排序的現(xiàn)象。而這種做法并沒有事實作為有力的證據(jù)。“人們覺得某一特定的歷史人物很適合于做某首詩中的主人公,以至于二者之間的轉(zhuǎn)化不知不覺就完成了”。[1]51
“無論是《詩品》《文選》《文心雕龍》,還是《玉臺新詠》都是按照作者的年代的先后順序來給詩歌進行排序的。”[1]43
既然是以作者的先后順序來個詩歌進行排序,那么首先就要為詩歌確定作者。但是這時編寫者們遇到了一個難題,對于無名的古詩文本,它們到底應(yīng)該是放在有名的詩作之前還是之后呢?這時他們就會以常理來判斷,無名“古詩”的寫作年代會比有名有姓的作者的作品要早。
第一部完整的對五言詩史進行敘述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其中也包含了五言詩的起源。“劉勰認為五言詩起源于《詩經(jīng)》。并且他對于系于班婕妤和李陵名下的詩作歸屬產(chǎn)生了質(zhì)疑。他也提到了枚乘,我們看到了之前未有的一種說法,劉勰把“古詩”歸于枚乘名下,并把他們排序在李陵之前。”[1]53劉勰做出這么個排序,似乎遵循的是:無名“古詩”產(chǎn)生的年代早于那些有作者歸屬的詩作。為了給無名“古詩”找到作者,他著眼于早期西漢著名文人。經(jīng)過一番推測之后發(fā)現(xiàn)枚乘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很多早期的作者都被提及到,但是劉勰本人并沒有明確地說明這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以自己之口來陳訴他人的觀點。劉勰也書中也明確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兩漢之作也/乎”。但這一觀點容易造成歧義。這句話既可以作為肯定的理解,也可以作為不確定的理解。也有一種可能是劉勰本人對于“古詩”早期斷代的不確定。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繼《文心雕龍》之后出現(xiàn)的又一對五言詩的起源做了重要敘述的作品——鐘嶸《詩品》。與劉勰意見不同的是,“鐘嶸對于署名班婕妤和李陵的詩作確信無疑。并且明確的指出無名‘古詩’是漢代的作品,而且大概是西漢之作,并且引述了這些來自漢代的‘古詩’作品出自曹氏父子和王粲之手”[1]57。由于五言詩的歷史實在單薄。為了湊數(shù),鐘嶸把西漢末年的酈炎和趙壹的詩作也收錄進來,盡管兩人的詩作質(zhì)樸而少文采,但為了填補五言詩史的大部分空白,對于鐘嶸來說,作此決定也是別無選擇的。此外,鐘嶸也選取了班固的一首五言詩《詠史》取代了張衡的四言詩《怨詩》來代表東漢。
“劉勰和鐘嶸在對于五言詩史的敘述產(chǎn)生了真正的分歧是在建安之后。在劉勰看來,建安是詩歌衰弱的時期,并且西晉的情況更為糟糕。而唯一能在這糟糕情境下使詩歌產(chǎn)生一絲亮色的是嵇康和阮籍的作品。與劉勰不同的是,鐘嶸認為漢魏時期詩歌開始衰微,但是西晉卻是詩歌興盛的開始。”[1]58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五言詩的歷史存在著大片的空白,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文人學(xué)者和批評家們便想盡辦法來填補這一空白。空白消失了,但是把詩作和作者名聯(lián)系在一起的做法并沒有有力的證據(jù)作為支撐,而是編者們心甘情愿做出的推測罷了。
(三)擬古詩作
“最早對古詩十九首進行模擬的人是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紀后期的陸機。對于‘古詩’表現(xiàn)出的贊賞和喜愛,使得陸機對其進行模擬。對‘古詩’的模擬在五世紀的時候發(fā)生了變化,詩人們有‘心機’的在模擬的過程中注意修辭的使用,并加入了典故,這使得模擬出的詩歌變得更加典雅。書中,宇文所安列舉了謝靈運模擬王粲大概寫于二世紀,題為“七哀詩”中一組作品的第一首來加以對比。”[1]38-39從謝靈運的擬作與王粲的原作對比,謝靈運在擬作中加入了典故,并且也更注重修辭的使用。
隨著模擬早期詩歌進行創(chuàng)作這一文化風(fēng)氣的發(fā)展,“詩人對個人風(fēng)格和時代風(fēng)格之間的差異有了更清楚的認識”[1]39。正如“江淹指出:讀者不應(yīng)只根據(jù)自身所處時代的標準作出判斷,而必須對于審美情趣的變化和差異抱有理解和同情”[1]46。“他要求讀者應(yīng)能夠欣賞和理解不同時代不同風(fēng)格的詩歌,而不要作出‘彼優(yōu)此劣’這樣缺乏歷史精神的價值判斷。”[1]46
“在不斷發(fā)展和增多的擬作中,大部分是對特定作者的仿真。那么,編者們在給詩歌進行排序的時候是依照其模擬的特定的作者所處的時代來給詩歌排序。”[1]39正如鐘嶸所說,“是擬作引起了人們對原作的注意,是原作變得更加引人矚目”[1]41。
“雖然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作者們早于齊梁文人兩個到三個世紀,可是這一詩歌在同樣程度上也是起齊梁的創(chuàng)造。齊梁的文人在某些情況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比較近期的詩歌置于較早的時期,用以補充早期詩歌的總體數(shù)量。”[1]4“以前的五言詩作少得可憐,現(xiàn)在卻一下子多出了許多——其中似乎不少是近代的擬作,是一個詩歌極大豐富的時代對一個詩歌短缺的時代做出的慷慨捐贈,……空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經(jīng)典’。”[1]60-61
手抄文本和口頭傳播的主觀隨意性,詩作保存的成規(guī)性,詩歌排序的不確定性,詩歌資料來源的多渠道,擬古詩的成熟發(fā)展等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所接觸的“漢魏”詩歌是否是真正的“漢魏”詩歌。
二、關(guān)于無名“古詩”寫作年代的思考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紀的猜測之外——表明無名‘古詩’的年代早于建安的確鑿證據(jù)。”[1]26
(一)“古詩”一詞所指
“古詩”二字最早指的是《詩經(jīng)》中的詩篇。但在陸云給其兄弟陸機的一封信中我們看到了對于“古詩”一詞的另一種說法,“‘古詩’即‘古五言詩’”[2]135。但這種說法有可能是建立在與當前的詩作作比較的基礎(chǔ)上而得來的,所以我們還不能很肯定地說,“古詩”就是“古五言詩”。
(二)五言“古詩”的來源
書中,宇文所安引述了《漢書》中戚夫人的歌,列舉了《漢書》中街陌謠謳、關(guān)于“臭名昭著的趙飛燕姐妹”的詩還有一首“據(jù)說是語言王莽篡漢”的詩歌。從以上列舉的詩歌我們唯一可知的是,“五言句式在公元一世紀下半葉已經(jīng)被人使用,當時是和低微的社會低微聯(lián)系在一起的”[1]73。
“在西漢晚期已經(jīng)有了固定節(jié)奏的五言詩句,但是在可確信為西漢的作品中,并沒有使用“古詩”的文體形式。”[3]175-176此外,約瑟夫·阿倫在《以他者的聲音:樂府詩研究》中認為,將“古詩”歸于漢代純屬假設(shè)。這只是編者們的推斷,而這些推斷并沒有有力的證據(jù)作為支撐,經(jīng)受不住不是“古詩”不歸屬于漢代的考驗。[1]26
那么,“古詩”一詞是何時被大眾所知曉的呢?《世說新語》中有這么一則軼聞: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最佳。”[4]276
我們不能確定這則軼聞敘述的事情是否真實,但我們可以由此推斷出的是,如果是真實的,那么應(yīng)該是發(fā)生在公元四世紀后期,并且這時“古詩”一詞已經(jīng)被大部分人所共知。盡管“古詩”被大部分人所了解并欣賞,但是它們在詩歌的歷史上卻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它們不知道產(chǎn)生于什么年代,也不知道作者。它們并不引人矚目。當“古詩”在五世紀被模擬時,由于修辭層次大大提高,并在詩歌中加入典故,這使得詩歌變得更加的典雅。有可能就像鐘嶸所言:“是擬作引起了人們對原作的注意,使原作變得引人矚目。”[1]41
(三)學(xué)者們對于五言古詩來源的探討
對于五言古詩來源的說法大致有三種:東漢說、西漢說和建安說。較早提出“建安說”的學(xué)者是徐中舒。他認為“不論是歸為西漢還是東漢的五言詩作,其真實度不能讓人信服”。因此,“五言詩的成立,要在建安時代”[5]。此外,木齋也贊同“建安說”。因為一個時代的文學(xué)和這個時代的社會背景、風(fēng)氣是息息相關(guān)的。在建安時代,統(tǒng)治者對于詩歌寫作的倡導(dǎo)與支持;社會風(fēng)氣的開放,大批的有才者如雨后春筍般涌出。此外,詩人在創(chuàng)作詩歌時注重情景交融,也更注意辭藻的使用。“那些沒有主名的所謂古詩,主要都應(yīng)該是曹植之后的作品,包括《古詩十九首》、蘇李詩、傳為班婕妤的《怨歌行》,也包括一向含混不明的所謂漢魏樂府詩歌中具有濃厚文學(xué)色彩的那些優(yōu)秀五言詩作品,例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等,都不是兩漢之作。”[6]宇文所安也支持“建安說”。他認為“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紀的猜測之外——表明無名‘古詩’早于建安的證據(jù)”[1]62。學(xué)者們對于“古詩”起源于建安之前的推斷是沒有可靠的事實依據(jù)作為支撐的,經(jīng)不起否定觀點的推敲。
給無名“古詩”進行排序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編者們所持有的一種信念“相信文學(xué)發(fā)展從簡單到復(fù)雜,有質(zhì)樸發(fā)展到典雅”[1]64,“用修辭層次較低的語言風(fēng)格寫成的作品,被認為早于那些修辭層次較高的作品”[1]64。但是“雖然在三世紀社會上層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中,詩歌的語言大致經(jīng)歷了一個修辭越來越講究的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修辭層次較低的詩歌完全被修辭程度較高的詩歌所取代”[1]64。因為“有證據(jù)表明,用修辭層次較低的語言寫作的詩歌,一直貫穿于整個三世紀的文學(xué)寫作之中”[1]64。
編者們在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編寫詩歌史:編寫者們在給詩歌進行排序時,會綜合分析時間、地點、社會背景以及作者的親身經(jīng)歷,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來確定把詩歌和其可能的作者聯(lián)系到一起,但是在假設(shè)的一切因素中看似完全符合的情況下,卻還有一種情況我們也應(yīng)該考慮到“假借他人之口所做的詩,詩中說話者也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下說話,但卻不是詩的作者”[1]65。此外,“同一詩歌出現(xiàn)不同版本”這一問題。“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在《玉臺新詠》和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用的材料中,某些文本進行加工,以適應(yīng)當代的詩歌標準。”[1]65用這些人為主觀意念加工過的文本來進行排序,就不可能接近真實。
三、宇文所安對漢魏詩作的具體解讀
被收入班固《漢書》里的一首系于李延年名下的五言詩作[1]74-75:“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再難得!”宇文所安認為,首先,“這首詩化用《詩經(jīng)·瞻仰》的成句:‘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在《詩經(jīng)》里,女性的摧殘力量還沒有成為美貌的同義詞。因為這則故事明顯在暗示漢武帝對歌曲中《詩經(jīng)》典故的警告缺乏覺悟,完全有可能是在班固模仿他心中的一人風(fēng)格編造了這首歌。”[1]73此外,“這首詩中只有第一行用了‘古詩’、樂府中熟悉的程序”[1]74,“并且混合和真正的五言句式(第1、3、4、6句)和加上一個虛詞擴展成五言的四言句”[1]74。再者,“這首歌以及《漢書》收錄的街陌謠謳里,五言詩中常見的詞組和模式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詞組和模式在后代五言詩中太習(xí)見了,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要么這些詩產(chǎn)生在一個這些傳統(tǒng)還并不存在的年代,要么它們就是出自一個社會階層較高、因此不熟悉五言詩傳統(tǒng)的作者之手(比如班固)。”[1]74
“大約在半個世紀之后,我們在一篇碑文中看到了這些缺失的傳統(tǒng)。”[1]74接下來我們在看看為名為費鳳的人寫的碑文。在碑文中出現(xiàn)了這么一個日期:公元143年。“但是碑文本身可能寫于公元二世紀后半葉”[7],詩中有一部分為敘事,文采質(zhì)樸無華,卻“為一些系于曹操名下的樂府提供了先例”[1]74。“但是這首詩既包括了長短多變的句子(這些句子常常是從《詩經(jīng)》中的成句變形而來的),也包括了在樂府和‘古詩’中常見和經(jīng)典的程序句。”[1]74比如,碑文中“丹陽有越寇”比較曹操《嵩里行》中“關(guān)東有義士”。
具體看下碑文中詩的中間部分,在寫到費鳳在臨死時,我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句子:“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下。”詩的結(jié)尾是這樣的:“壹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在費鳳碑詩中,我們看到了與著名樂府《陌上桑》中“耕者忘其犁”一模一樣的描寫,“表現(xiàn)了耕者對費鳳的去世感到悲哀”[1]75。從這,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是一個可以被不斷重新表述并用不同語境的‘話題’,無論語境是一個重要人物之死還是一個采桑女的美麗”[1]75。
此外,我們再把這首詩與《古詩十九首》第一首的幾句詩做一下對比:“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古詩十九首》中,“相去萬余里”與碑文中“相去三千里”相比,“也許最好地顯示了費鳳碑詩是對五言詩傳統(tǒng)的一種‘實現(xiàn)’方式,因為一句本來是描寫‘生離’的詩現(xiàn)在用來描述‘死別’,但是非常精確地給出生者和死者之間的距離”[1]76。此外,“在費鳳碑詩的結(jié)尾,詩人表現(xiàn)完全被悲哀情緒所征服,不能再寫下去。這可以說是‘古詩’里面常見的結(jié)尾形式”[1]76。但是,在碑文中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細節(jié),“詩中的敘述者說他‘絕翰’停下手中的筆——這非常明確地指出向以書寫形式進行創(chuàng)作。這是我們在傳世的早期詩歌里面看不到的。”[1]76宇文所安把費鳳碑詩與“古詩”、樂府作比較,“并非是想說‘古詩’、樂府以及現(xiàn)存的形式一定可以被追溯到公元一世紀或者二世紀,而是為了告訴我們:到二世紀中葉,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一系列詩歌常用手法的存在,它們是許多‘古詩’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并且同樣的手法在整個公元三世紀都一直被人使用。”[1]77
有些作品在確定作者時是依據(jù):“作者未知但似乎適合某個特定歷史人物的詩歌”。就比如《古詩十九首》中[1]264-265:“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無乃’即恐怕是,想必一定是。這種論斷是依靠直覺來把詩中的敘述者與作者聯(lián)系到一塊,把詩中的敘述者當作詩的作者。”[1]265接下來要分析的一首被系于班婕妤名下的《怨詩》(或怨歌行)同樣屬于這樣一種情況。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首詩:“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恩情中道絕。”班婕妤是漢成帝在沒有遇見趙飛燕姐妹之前的寵妃。可能是她對于最終會失寵的一種預(yù)見,使她作出了這首詩歌。這預(yù)見的時間可能是在失寵之前,也可能是在新寵的時候便開始了。“當皇帝感到‘炎熱’時,妃子可以充一時之用,但她意識到他的熱情終將冷卻(‘秋節(jié)至’),她會被棄置一旁。”[1]265因為“這首詩與班婕妤的歷史聯(lián)系非常緊密,以至于即使當學(xué)者們不再相信班婕妤是這首詩的作者,他們?nèi)匀幌M@首詩采取了班婕妤的聲口,或至少采取了一位受寵妃子的聲口。”[1]268這種解釋聽起來似乎十分的合理。此外,“人們愿意將這首詩讀作是宮人的聲音,和其中隱含的權(quán)利落差很有關(guān)系”[1]268。但是,宇文所安認為還有另一種可能,“這首詩可能并沒有把宮人比作團扇,而就是描寫了一把扇子,而在最后一聯(lián)中把它含蓄地比作宮人。至少從三世紀起,職業(yè)詩人就要被要求賦詩詠物”[1]270;并且“班婕妤的詩在早期文獻材料中有時被引作《扇詩》或《詠扇》,似可支持這種假設(shè)”[1]268。
此外,從中文的語境中來研究這首詩,需要很謹慎的把“作者”和“權(quán)威”聯(lián)系起來。因為在中文的語義里,二者并沒有一點聯(lián)系。“這首詩是以‘團扇’為中心意象展開描寫”,“團扇不僅被比作女子,而且還裝飾著‘合歡’的圖案——合歡代表了情人的聚首,正如團欒的明月(詩中對團扇的一個比喻)也代表團圓和聚首一樣。扇子會產(chǎn)生‘微風(fēng)’,而‘風(fēng)’也是一個用來指稱詩歌與‘諷’——委婉的諷諫(對皇權(quán)的諷諫)——的語匯。”[1]269正是由于詩中對于“團扇”的巧妙運用,并且把感情的深度蘊藏在其中,使人們認為這首詩作極大的可能創(chuàng)作于三世紀。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兩首在敘述者上不存在爭議的同名長詩——《悲憤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敘述者就是作者本人嗎?這兩首詩講的是同一個故事,但卻以不同的體裁版本出現(xiàn)。一首是五言詩,另一首是“楚騷”詩。這兩首詩都是在真實的歷史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而成的。敘述者是東漢著名學(xué)者和作家蔡邕的女兒蔡琰。這兩首詩表現(xiàn)的是在“蔡琰在漢末的戰(zhàn)亂中被掠至匈奴,后來被曹操贖回中原,但她不得不將所生的二兒子留在匈奴。在她返回中原之后,發(fā)現(xiàn)所有的佳人親屬都已經(jīng)過世。曹操將她改嫁他人”[1]278的這一時期的故事。對于蔡琰是這兩首詩的敘述者的身份,學(xué)者們是肯定的。但卻在蔡琰是否是這兩首詩的作者產(chǎn)生激烈的爭議。傅漢思相信這兩首《悲憤詩》都不是蔡琰所作,宇文所安也同意這一觀點,但這個問題卻一直都沒有得到確證。
“雖然《悲憤詩》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早期詩歌中最著名的詩篇之一,而且被所有的選集記錄”[1]280,但是在此之前,它卻沒有得到學(xué)者和編者們的欣賞。“兩首《悲憤詩》都沒有被《文選》或《玉臺新詠》收錄,《文心雕龍》或《詩品》也沒有提到蔡琰。考慮到《后漢書》在當時的易得,和齊梁學(xué)者在搜集和評論早期詩歌方面的勤勉,這一缺席意義重大。”[1]279究其原因,我們至今還不得而知。“也許這只是出于對長篇敘事詩的偏見,而長篇敘事詩似乎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通俗傳統(tǒng)。”[1]291我們就其中的一首五言《悲憤詩》來進行分析比較。對于這首詩創(chuàng)作時間的上限,我們可以從五言《悲憤詩》的第一句中開頭的“漢季”來進行推測。“‘漢季’意味著漢朝已經(jīng)滅亡,因此也就是在曹操死后。”[1]286五言《悲憤詩》有一段對董卓之亂的描述,我們可以在曹操的《露》中找到相似的詩句:“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悲憤詩》中“漢季失權(quán)柄”與“惟漢二十世”相比較,我們可知,詩人們對于在漢代即將滅亡和沒滅亡之前的稱呼是不同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詩中直捷的敘述風(fēng)格與其他詩作的比較:“海內(nèi)興義師,欲共討不祥。”曹操的《嵩里行》也可以讀到類似的句子:“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同樣的,我們在費鳳碑和《古文苑》中系于孔融名下的一首六言詩中也出現(xiàn)直捷的敘述風(fēng)格。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五言《悲憤詩》的開頭和石崇的一首描寫王昭君遠嫁匈奴所經(jīng)歷的遭遇的代言詩:“我們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qū)已抗旌。仆御涕流離,轅馬為悲鳴。”詩中,“流暢的風(fēng)格和‘同情’的意象標志著五言詩發(fā)展史上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1]288這首五言《悲憤詩》把五言詩具有的敘事能力這一優(yōu)點很好的表現(xiàn)出來。詩中,孩子直接與母親進行對話:“己得自解免,當復(fù)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fù)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nèi),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fā)復(fù)回疑。”此外,詩中還敘述了蔡琰與一起被掠去的同伴們的告別;敘述了被贖回后回到家中得知家中親人都已經(jīng)去世的消息和如廢墟一般的家;同時也敘述了她的再婚以及對于婚后害怕由于自己被掠至匈奴的這一經(jīng)歷而遭遇丈夫的嫌棄。“這首詩用‘古詩’的傳統(tǒng)方式結(jié)尾,發(fā)出‘人生幾何時’的感嘆,最后以表達悲傷收束全詩。”[1]289
詩中也出現(xiàn)了對詩句的變體的句子:“回路險而阻”和《古詩十九首》中的第一首“道路阻且長”;“悠悠三千里”與費鳳碑“想去三千里”(也可以對比《古詩十九首》第一首中“相去萬余里”);“何時復(fù)交會?”與《古詩十九首》第一首中“會面安可知?”[1]290。
在五世紀早期,一組關(guān)于離別的詩作被系于李陵名下。而把李陵和這組詩作聯(lián)系在一起的依據(jù)是《漢書》中記載了李陵與蘇武相見與離別的場景。但是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可信的證據(jù)表明,這組詩作與作者的聯(lián)系。
“在《隋書·經(jīng)籍志》記錄了一部兩卷本的《李陵集》。”[1]292對于李陵是這組詩作的作者這一說法當時大家并不是很認同。并且劉宋最早對這本集子的真?zhèn)翁岢鲑|(zhì)疑,“他稱其‘總雜’而且懷疑它是‘假托’,但他并未全盤否定每一首詩(‘非盡陵制’)。”[1]292“李陵的作者身份被大家普遍接受是在五世紀末和六世紀頭四十年這一關(guān)鍵的時期。”[1]292
宇文所安顯然也不贊同李陵詩作的歸屬,他認為,按照常理進行判斷,一個人在同一個場景創(chuàng)作了兩卷詩是荒謬的,并且,就算李陵真的就在同一個場景一首詩歌接一首詩歌的創(chuàng)作,那么作為收件人和寫信人的蘇武對于這一不斷重復(fù)的現(xiàn)狀不會感到厭煩嗎?
接下來我們看看在《玉臺新詠》中收錄了秦嘉和他妻子徐淑之間的贈答詩。宇文所安認為,這三首贈詩和一首答詩“產(chǎn)生的時間不早于五世紀下半期,而秦嘉的詩可能不會早于梁初。”[1]300
宇文所安之所以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jù)是:第一,通過這兩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離別的場景。但是,這三首贈詩和一首答詩中所描繪的故事在早期的歷史文獻中并沒有記載。“《后漢書》沒有提到秦嘉,如果他們的往來信件和詩歌在五世紀中期已經(jīng)廣為流傳,很難想象范曄會遺忘他和敘述,因為范曄特別喜歡這種能夠激發(fā)讀者情感的場合和事件。”[1]300第二,“江淹在五世紀晚期模擬的詩作組詩中沒有模擬秦嘉和敘述的詩,我們可以理解他為什么沒有擬徐淑的詩,因為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五言詩;但是他如果見過秦嘉的詩,應(yīng)該一定會有模擬之作。”[1]300此外,鐘嶸在《詩品》中也曾經(jīng)提到過徐淑的這首答詩,宇文所安據(jù)此推測:“在六世紀早期,人們已經(jīng)知道秦嘉任‘郡上計’之職,他的妻子在娘家病重,無法送他離開。這些情況可以從徐淑的書信和詩中得知。徐淑的詩是一首答詩,因此需要與之對應(yīng)的‘贈詩’,這些‘贈詩’顯然在六世紀前半期被發(fā)現(xiàn)或被提供——從而大大增加了東漢五言詩的數(shù)量。”[1]300
我們可以從秦嘉的第一首贈詩中得出,“至少有一封徐淑的信在這首詩寫作的時候已經(jīng)存在”[1]303。宇文所安認為,是先有徐淑的答詩,之后為了填補與徐淑答詩的空白,對應(yīng)的贈詩才出現(xiàn)。而我們也不能確定的是,系于秦嘉名下的這三首贈詩是以秦嘉之名的代作還是齊梁的學(xué)者們依據(jù)詩歌史的敘事而把它們系于秦嘉名下。并且,齊梁學(xué)者在對早期詩歌進行編排整理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對早期詩歌中,他們認為不滿意的地方進行修改。
班固《詠史》這首詩講述的是緹縈為救父上書皇上,自愿為父親甘受刑罰的舉動感動了皇上,并釋放了她的父親的故事。(原詩略)這首詩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被確定在班固名下,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梁代的選集和隋唐類書并沒有把這首詩收錄其中。鐘嶸對這首詩的描述是“有感嘆之詞”。宇文所安假定,如果這首詩是后來才被確定在班固名下的,那么這首詩是為什么被按上班固的名字的呢?結(jié)合鐘嶸對這首詩的描述,我們可以找到答案,這首詩之所以被系于班固名下是因為班固對于歷史上所發(fā)生的相似的事件與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之間的撞擊有感而發(fā)。“班固死于獄中,而他有一個入宮為妃的妹妹。”[1]306他是在借著這一事件來哀嘆自己的命運。
結(jié) 語
當今這個時代,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是需要勇氣的,并且這一見解是與主流思想相異的有價值的獨特見解更值得鼓勵。在新思想與傳統(tǒng)的主流思想碰撞的瞬間,或許一時之間讓大家難以接受,但是,這對于我們學(xué)術(shù)的研究是有推動作用的。宇文多按所提出了有關(guān)五言詩的新觀點對于詩歌的研究史是具有很大意義的。他不僅為詩歌史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泉,給予的學(xué)者們反思,同時,也給讀者們帶來了新的看點。
[1][美]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2.
[2][晉]陸云.陸云集[M].黃葵,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135.
[3]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175-176.
[4]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76.
[5]徐中舒.五言詩發(fā)生時期的討論[J].東方雜志,1988,24(1):18.
[6]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反思[J].社會科學(xué)研究,2012(2):54-66.
[7][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逯欽立,編.北京:世界書局,1963:112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