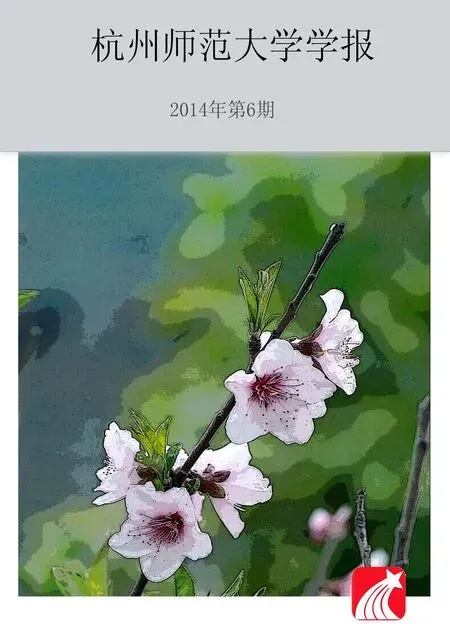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亞細亞狂人》的跨國族同理心
唐 睿
(復旦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433;香港浸會大學 語文中心)
《亞細亞狂人》是無名氏首部長篇小說,跟以往的小說相比,《亞細亞狂人》的主題更為集中、明確,脫去了《火燒的都門》的練筆意味。《亞細亞狂人》以韓國的命運為經,以韓國光復軍李范奭將軍的一生為緯,但當時無名氏的視野,已逐漸超出了對一國一人的關心,而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關懷人類的整體命運。這種肯定國族差異,但同時又能把人類視為一個共同體,強調彼此平等和尊重的觀點,實際是世界主義精神的基礎觀念。無名氏在《亞細亞狂人》的一些章節,如《露西亞之戀》和《狩》中其實已分別借韓人與白俄遺民、金耀東與白俄將軍及史上許多名人的命運,表現出“人類普遍命運”的訊息。這些作品,都是把握無名氏藝術思想的重要參照。
《露西亞之戀》①《露西亞之戀》既是短篇小說集的名字,又是該小說集中一篇小說的篇名。本文集中討論短篇小說的內容,除非特別注明,所言《露西亞之戀》皆指短篇小說,而非小說集。于1942年1月完稿,較寫于1943年11月的《北極風情畫》完成得早。篇末附有“這是一個未完成長篇的斷片”,是《亞細亞狂人》中的一個片段,可銜接《北極風情畫》的內容。雖然這篇小說只是一個殘篇,但孤立作為一個短篇小說來看,亦有其鮮明集中的主題。《狩》則是《亞細亞狂人》第五部《荒漠里的人》的一個章節。故事發生在1929年至1931年中國東北的外興安嶺,主要講述主人公金耀東在吉林奉天從事革命失敗以后逃亡到黑龍江西北部的故事。《露西亞之戀》講述韓國光復軍在柏林巧遇白俄遺民,因彼此同為亡國人民的身份,而產生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的感情。《狩》則講述金耀東抗日失敗,退居中國東北外興安嶺狩獵為生時的一個片段,當時金耀東想起多年抗日的努力,似乎是命運跟他開的玩笑,最后他想起古今中外許多被命運揀選的巨人,自我開解。《露西亞之戀》和《狩》兩篇小說都展現了強烈的跨國族同理心,見證了無名氏作品中,世界主義精神逐漸成熟的過程。
一、《露西亞之戀》的跨國族同理心
《露西亞之戀》的寫作日期雖較《北極風情畫》早,但故事內容,卻是《北極風情畫》之后的情節。《北極風情畫》以主角離開蘇聯托木斯克轉往歐洲作結,而《露西亞之戀》正好就承接這旅程,講述韓國獨立軍轉往德國的一個夜晚。《露西亞之戀》的主角雖然也是以李范奭為藍本,是一位“與馬占山李杜一行從蘇聯托木斯克出發,越過波蘭,初踏入這日耳曼的都門”[1](P.134)的韓國軍人,卻不是《北極風情畫》的林軍官,而是名字短寫為“金”的韓國軍人。故事另有一位韓國角色,名字短寫為“明”,是金“在柏林大學教書的同鄉”,一位哲學講師。《露西亞之戀》主要講述金與明在柏林一家白俄咖啡館——“白熊咖啡館”遇到一群從蘇聯逃出來的白俄遺民的故事。當夜雙方彼此提及自己亡國的命運,然后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跨國族同理心。《露西亞之戀》共分八節,除韓國軍人與白俄遺民外,篇章還提及其他國族。由中韓以及東北少數民族混合編制的馬占山軍隊自不待言,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第一節里,筵席上提到的波蘭民族。韓國軍人未有直接跟波蘭民族交往,但金的演說不斷以波蘭民族的命運來觀照韓國的命運。
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在陽光中跑著跳著的波蘭孩子。我永遠忘不了波蘭的自由的原野。我永遠忘不了波蘭的陽光。我永遠忘不了再生的華沙。華沙一切全是嶄新的。在華沙,一花一草一本一石全在嘲笑我、諷刺我,在譴責我們那些甘心做東京奴隸的同胞。……華沙是一只剛從灰燼中再生的鳳凰,在昂著驕傲的頭,在搖著驕傲的尾巴,在向我責問:我們,曾遭三次瓜分悲運的民族,現在是再生了,你們這些“檀君”子孫(指韓人)呢?[1](P.136)
金以波蘭和韓國作比較,因為這兩個民族都遭遇過亡國的命運。盡管韓國沒有跟波蘭在政治或軍事上有直接瓜葛,但對于韓國民族而言,波蘭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他者”,而是一個跟自己擁有相同特質、可以互相理解的“他者”,即一個能夠投以跨國族同理心的對象。
波蘭與韓國的命運,僅僅是《露西亞之戀》的一段插曲。《露西亞之戀》的主調是韓國光復軍與白俄遺民的惺惺相惜之情。在故事起首的歡迎會上,“德國華僑們對這群抗日英雄備致頌詞滿座響起雷樣的掌聲”,但金的內心卻異常寂寞,“在他聽來,每一句話全是最刻薄的諷刺”。[1](P.138)金覺得華僑的頌辭刺耳,因為他雖被尊為英雄,但韓國復國的希望仍然遙遙無期。韓國的亡國和復國問題始終困擾著金,以致他不停地在心里反復自問“為甚么我是韓國人呢?為甚么我是韓國人呢”?[1](P.138)對國族的憂慮無從排解,于是金才在柏林的街上疾走,希望借此揮走這些思緒。可是“這些思想仍緊緊纏著他、不放松他、折磨著他”。[1](P.138)因此,明將金從紛亂思緒中喚醒的一句話便別具象征意味,他問金:“我們究竟往哪里跑呀?”這句話第一層意義是問金要往的方向,而結合故事的敘述后,則產生第二層意義,即韓國獨立軍的命運將會如何。對此,金回答說:“隨便跑吧,直到疲倦為止。”這話落在敘述的語境里,也可以作兩個層次的解讀:字面義道出金對奔跑目標的茫然,象征義則可理解為金對韓國復國的茫然。如此詮釋,并非捕風捉影,從金與明稍后討論當夜要在哪里歇息的對話,便可繼續追索國族討論的線索。當明問金:“‘今晚你愿意和甚么樣的人在一起?’金沉吟了一下,緩緩的道:‘這里有流浪民族嗎?——今晚的情緒,是只容許我和流浪人在一起的。’”[1](P.140)由此可見,故事內容始終圍繞著國族問題在推進,而金與明稍后走到“柏林的流浪人之街”,步入白俄遺民聚集的“白熊咖啡館”亦非偶然。
“白熊咖啡館”并非金與明在柏林的白俄聚居處最先見到的咖啡館。步入“白熊咖啡館”之前,“金走過幾家咖啡館”,但都沒有跨進去,原因是“從它們的門面裝潢看來,這些咖啡館與他的靈魂之間,似乎尚缺少某種神秘的聯系”。這種“神秘的聯系”具體所指甚么?這可從金最后步入的“白熊咖啡館”得到回答。
首先,吸引金注意“白熊咖啡館”的,是咖啡館的“燁煒光華”。作為一家“流浪民族”聚集的咖啡館,“白熊咖啡館”不見半點破落氣息,相反,它華麗得讓作者愿意花一段頗長的文字去描繪裝潢。除了金碧輝煌的裝潢,“白熊咖啡館”還有一個神龕似的樂壇,容得下二十幾個白俄樂師在上面演奏。此外,咖啡館內還有一張壁畫深深吸引住金的視線,這張畫便是俄國名畫“莫斯科大火”的模擬品。作者對畫作了仔細描述,強調了畫作的重要性。“莫斯科大火”描述的是1812年拿破侖占領莫斯科的一段歷史故事,其時拿破侖以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將會于莫斯科淪陷后迅速投降,豈料莫斯科突然發生大火,法軍糧草燃盡,局勢迅速扭轉。一度瀕臨亡國的俄羅斯在這場大火之后,乘勝追擊,最后更在1814年成功反擊法國,直抵巴黎,逼使拿破侖下臺。“莫斯科大火”一畫,記錄了俄國從幾近亡國,到復興的曲折歷史,它在《露西亞之戀》中之所以吸引住金,是因為畫中的歷史呼應著金的家國民族哀思,喚醒了金的跨國族同理心。
金注視“莫斯科大火”一畫,是一筆側寫;這段敘述的重點,是金向白俄遺民說著地道的俄語,引起俄人注意,并借由“祖國”二字,令整個咖啡館變得莊嚴肅穆的描寫。這描寫道出韓俄兩國的共通民族感情,具點題之效,金和明兩個韓國人與“白熊咖啡館”一眾白俄遺民的情感交匯,即由此而起。起初,金道出的“祖國”二字,勾起了白俄遺民許多痛苦的回憶,而金完全理解這種痛苦,俄人“這些陰暗的面孔與微微抖顫的粗壯的白色胳膊,暴風雨樣掀起金的感情,一剎那間,一道神秘的熱烈的陽光像閃電似地從他身上掠過,他自己一生的坎坷與悲哀完全解了凍,像千萬條雪水般從一個高峰上奔流下來,奔流下來”。[1](P.150)
早前金因未能在其他咖啡館找到“神秘的聯系”,所以過門不入,而現在他在“白熊咖啡館”里卻找到了一道“神秘的熱烈陽光”,前后互相呼應。這種“神秘”的感覺更在金緊接其后的話里得到闡明:
請不要問我對于沙俄或蘇聯的意見,請不要向我提出道德問題或社會問題……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在我們之間,一切的理論全死了,現在只存在著純人與純人之間的深厚的同情。[1](P.151)
這段話可說是《露西亞之戀》的核心話語。首先,它點出了牽引著金在柏林一夜奔走的“神秘”感情,實際就是“純人與純人之間的深厚的同情”,而這種“同情”,即是跨國族的同理心。在進入“白熊咖啡館”之前,金就明確說道:“今晚的情緒,是只容許我和流浪人在一起的。”[1](P.140)而“白熊咖啡館”的白俄遺民在俄國變成蘇聯之后,就正是流落異鄉,寄居他國,有國歸不得的“流浪人”。
此外,“白熊咖啡館”有別于其他白俄咖啡館,它華麗的排場,都可說是俄羅斯帝國的輝煌象征。“莫斯科大火”一畫,記錄了俄羅斯民族浴火重生的歷史和精神,至于館里的樂團、音樂、歌舞、酒食,以及由敘事者或角色提到的風情習俗,在在皆述說著俄羅斯民族的偉大。“白熊咖啡館”的白俄遺民,對自己的國族文化,充滿著十足的自信,而這亦與金對韓國民族文化的看法完全一致。當金在《露西亞之戀》開首憶想故國的時候,他對祖國的描述是“圣潔泉水的祖國,那開遍杜鵑花的故鄉原野,那說不盡的美麗的‘槿花之國’,展開在他眼前的是銀白色的樸淵瀑布,露梁津的碧柳深深低垂……”。[1](P.134)跟“白熊咖啡館”的白俄遺民一樣,金對祖國懷著無限戀眷,以及十足的自信。“白熊咖啡館”的相遇,給予金和白俄遺民不少的慰藉,而這種慰藉,即跨國族的同理心。
MTHFR和MTRR基因多態性與陜西地區漢族人群冠心病發生的相關性研究 ……………………………… 白曉丹等(22):3125
《北極風情畫》的跨國族同理心,有男女情愛因素摻雜其中,而《露西亞之戀》的跨國族同理心,僅僅是由一夜的一次偶遇所引起,更為純粹、更為聚焦于國族間的同病相憐情懷,突出國族能夠在毫無利害關系下,互相理解,體現出世界主義精神的基礎特質。
二、《露西亞之戀》的歷史原型
過去,由于學界對《無名書》之前的創作缺少認識,且資料掌握有限,所以難以全面解讀無名氏的早期創作。然而,隨著無名氏部分佚文的重新發現——特別是1942-1943年發表于《中央日報》(貴陽版)的《荒漠里的人》*關于《荒漠里的人》,有幾筆需要補充的數據。無名氏正式在《中央日報》(貴陽版)連載《荒漠里的人》之前,曾在1942年8月19日和24日的《中央日報·前路》(貴陽版)中表示“《荒漠里的人》是我的正在寫作的長篇《創世紀》的第五部。這個長篇共分八部”。這部長篇的總題目,在連載之初名為《創世紀》,無名氏晚年卻多稱之為《亞細亞狂人》,詳見汪應果、趙江濱《無名氏傳奇》,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4、341頁,以及無名氏著《在生命的光環上跳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所收的《〈無名書〉寫作經過記略》。的重新發現,《露西亞之戀》及《龍窟》各個篇章的深層訊息,便得以進一步詮釋出來。
1942年8月,無名氏計劃撰寫《亞細亞狂人》*無名氏早期亦有構想將《亞細亞狂人》這部作品稱為“創世紀”,為免令讀者混淆,本文僅在引文里保留“創世紀”的篇名稱謂,其他的論述部分則一概稱之為《亞細亞狂人》。的長篇,而這部長篇的第五部,就是無名氏稍后連載于《中央日報》(貴陽版)的《荒漠里的人》。重新發現并整理《荒漠里的人》連載稿的李存光、金宰旭提出,《亞細亞狂人》第四部應該敘述了有關李范奭在1921-1928年的故事,“寫李范奭隨軍進入蘇聯,加入蘇聯紅軍所屬高麗革命軍步騎混合兵隊,和蘇聯紅軍合作攻擊斯巴司卡亞的白俄軍”,[2](P.11)并認為《露西亞之戀》的《騎士的哀愁》“應該是這一部結尾的斷片”。[2](P.118)
誠如無名氏在《關于〈荒漠里的人〉》里的表示,《亞細亞狂人》這個長篇是講“一個韓國革命者的一生奮斗史”。*無名氏《關于〈荒漠里的人〉》,載《中央日報·前路》(貴陽版) 第609期,1942年8月19、24日。而熟悉無名氏作品的人都知道,這個“韓國革命者”,就是李范奭。根據《李范奭將軍回憶錄》:1921年6月,李范奭隨韓國獨立軍進入俄國,參加革命武裝,希望借助俄國革命黨的力量對抗日本,但不久之后俄國革命軍與日本達成合作協議,俄單方面解除韓國獨立軍的武裝,李范奭和金佐鎮等人逃亡到中國東北。1922年,李范奭得心臟病到俄羅斯治療,并于1923年“參加高麗革命軍,擔任高麗革命軍的騎兵司令官。高麗革命軍與蘇聯定有密約,幫助紅軍打仗,蘇聯則支持武器裝備,高麗革命軍變成了‘合同民族軍隊’”。[3](P.320)1925年,蘇聯與日本簽訂漁業協議,日本政府承認蘇聯政府,但同時要求解散西伯利亞的韓國獨立軍武裝。1月,蘇聯強行解除韓國獨立軍武裝,韓國奮起反抗,李范奭頭部中彈,送到安寧縣寧古塔治療。傷愈后,李范奭在滿洲軍閥隊伍中當了四個月雇傭兵,直到7月接到金佐鎮電報后,再到寧古塔。8月李范奭在寧古塔結婚,9月起開始組織高麗革命決死團,以種鴉片來賺錢再向俄人購買武器,自此,李范奭一直帶領決死團與日軍對抗,直到1928年12月,決死團在日軍和中國軍閥的鎮壓下,被迫解散,李范奭亡命外蒙古。可以說,1921-1928年是李范奭與蘇聯武裝往來得最緊密的時期,蘇韓雙方因各自的利益互相利用,又在利益關系消失后瞬即反目。有關內容,在《騎士的憂郁》和《露西亞之戀》中都可以找到線索。
無名氏曾經明確表示,《北極風情畫》的內容是從《亞細亞狂人》這篇小說中的第六部改編而來。《北極風情畫》寫馬占山軍隊離開托木斯克轉往歐洲,從內容來看,《露亞西之戀》寫馬占山軍隊從托木斯克經東歐抵達柏林的故事,正好在《北極風情畫》之后。盡管兩篇小說的主角名字不一,但詳細分析內容,不難發現,兩者皆是以李范奭為原型。換言之,《露西亞之戀》的故事,發生在李范奭和蘇聯紅軍聯合攻擊巴司卡亞的白俄軍之后。
梳理清楚《亞細亞狂人》的故事時序,便能深入解讀《露西亞之戀》里金為何要對“白熊咖啡館”的白俄遺民說“‘請不要問我對于沙俄或蘇聯的意見,請不要向我提出道德問題或社會問題,請不要逼我批評什么或譴責什么’”,“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在我們之間,一切的理論全死了”,并特別跟白俄遺民強調,不要在當晚提及政治、社會、道德等問題,因為金的原型——李范奭曾聯合蘇聯紅軍,攻擊白俄部隊,而“白熊咖啡館”的俄人之所以流落他鄉,金可謂有一定的責任。金理應最清楚作為亡國奴、異鄉客的痛苦,然而他為了自身國族的命運,卻讓一群跟自己毫無關系的百姓,淪落到跟自己一樣的痛苦處境,這對金而言,是一種極大的諷刺,難怪他會說“生命原是痛苦的、不可解的”。
可是,這夜在“白熊咖啡館”的相遇,金和白俄遺民并未因金曾經追擊白俄軍隊,或者與蘇聯軍隊串聯而發生齟齬甚至沖突。進入“白熊咖啡館”,遇到白俄遺民之后,金便被“暴風雨樣掀起”一種跨國族的同理心;至于白俄遺民在得悉金來自“俄羅斯母親”,看到金以哥薩克人的架勢喝酒,并喝過金請客的伏特加酒后,他們均對金表示深深的敬愛。一時間,國族憂思、異鄉客的感傷更使金希望能夠和白俄遺民緊緊相連在一起,表現了一種超越了政治立場、社會問題乃至道德常理 (跟亡國仇敵共飲)的跨國族同理心。這種“純人與純人之間的深厚的同情”可以超越國族偏見和政治見解。這正如當代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闡述世界主義這一概念時所指出的:“將他者既作為與己相異又作為完全平等的人來看待。”
三、《狩》的跨國族同理心
《狩》是長篇小說《荒漠里的人》*《荒漠里的人》是《亞細亞狂人》的第五部。中的一個篇章(第二章第四節至第九節),現收于《龍窟》并有所刪改,剔除了金耀東獨自獵鹿茸的一段,但除此之外,《狩》的主要情節未作其他修改,與原載在《中央日報》(貴陽版)的版本大致相同。《狩》共分五節,主要講述金耀東帶著獵犬貝爾特在哈拉蘇獵狍子的故事。敘事者除了著力描繪金耀東狩獵時的所見物事,亦對金耀東的心理活動作了細膩的描寫。在孤獨狩獵的過程里,金耀東想起了自己過去的經歷,并聯想到“一幕幕生命的大悲劇浮雕”,包括“跋涉在恒河畔的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釋迦,蘇格拉底的毒藥,冰天雪地中的華盛頓的悲慘大潰退,貝多芬的聾瞶與命運交響曲,尼采的瘋狂……”。[4](P.26)
其中,作者花了整整一章,敘述一位俄國名將的亡命故事。
故事講述一位“曾任華沙方面總司令的沙俄名將”,他在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之后,輾轉流落到美國洛杉磯,成了一位好萊塢演員。機緣巧合下,他獲得了一個演出的機會,所演角色,正是一位帝俄將軍。這是一出巨額投資影片,電影公司花了一百萬美金來重現帝俄時代的宮廷面貌,而片中最重要的一幕,就是耗費20萬美金來制作的閱兵儀式。正當電影拍攝閱兵式的敬禮畫面時,這位俄國將軍竟突然從馬上滾跌下來離奇去世。這部影片最終并未完成,而以“最后的命運”的名字發行歐美。
金耀東對這位俄國將軍的故事無從釋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歉疚:
過去率領韓籍雜色軍在濱海省附近追擊白軍的一幕,又凸顯在他的記憶里。他覺得自己就是促成這白俄將軍演悲劇的因素之一。如果不是他們的猛烈攻擊,謝米諾夫遠東共和國的崩潰不會那樣快。[4](P.33)
對于俄國將軍的悲慘命運,金耀東自覺難辭其咎,這種自責的心情,就跟《露西亞之戀》里金面對白俄遺民時所萌生的歉疚心情一樣。作為軍人,戰場上各為其主難免需要跟陌生或者與自己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勢力發生沖突,金耀東本毋需對俄國將軍感到歉疚或者同情,然而有一種高于軍人道德的因素讓金耀東為對方感到難過,這就是“同理心”。
在敘述完俄國將軍的故事后,敘事者敘述道:
他(金耀東)不禁痛苦的想起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一幕——EGCO HOMO*《龍窟》排版為“EGCO HOMO”,應為“ECCE HOMO”之誤。(看這個人啊!)
俄羅斯亡命者是“這個人!”他自己也是“這個人!”[4](PP.32-33)
金耀東對白俄將軍的悲劇命運感到內疚,一方面是因為白俄將軍與金耀東一樣,遭遇亡國和流亡的困苦﹐經歷十分相似;另外也因為韓國獨立軍為了換取紅軍的武器,曾在遠東的俄國革命戰里,追擊跟自己素無嫌隙的白俄軍隊。金耀東深知,這種基于一己私利,出賣他者利益,將自己深有體會的苦痛加諸白俄軍隊身上的行為,實在有違道德與正義的立場。
除此之外金耀東心生愧疚,還是基于一種“命運意識”。對金耀東而言,白俄將軍的悲劇命運,并非偶然,而是命運特意的揀選。金耀東對自己的命運,也有類似的感悟。當他想起俄國將軍的悲劇時,他對自己的命運作了一番提問:“他(金耀東)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孽?受生命如此狠毒無情的詛咒與報復?”[4](P.33)基于這種“命運意識”,金耀東想起了耶穌受難的圖畫,想起“ECCE HOMO”這句話,然后總結道:“俄羅斯亡命者是‘這個人!’他(金耀東)自己也是‘這個人!’”這些聯想并非巧合,而是源自一種世界主義精神的覺醒。“ECCE HOMO”是拉丁文,意謂“這個人”,亦有譯作“瞧!這個人”,專指圣經故事里,耶穌受難的形象。除了基督教淵源外,尼采亦曾以“ECCE HOMO”作為他自傳式思想論著的標題——漢譯書名為《瞧!這個人》。尼釆借書名暗示自己也是被時代和歷史所揀選,借此展現出一種命運意識。這種命運意識在《狩》還被聯系到人類文化歷史里,另外幾位被命運召喚或揀選的人:
跋涉在恒河畔的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釋迦,蘇格拉底的毒藥,冰天雪地中的華盛頓的悲慘大潰退,貝多芬的聾瞶與命運交響曲,尼采的瘋狂……[4](P.26)
耶穌、尼采、釋迦、蘇格拉底、華盛頓、貝多芬等人的故事,跟俄國將軍的悲劇一樣,被金耀東歸類為“一幕又一幕的生命大悲劇浮雕”。這些人物似乎都蒙命運的召喚,注定遭受極大困苦,嚼透生命的悲苦。至于金耀東對這種苦難,亦深有體會。他為民族吃苦,退居外興安嶺,韓國獨立運動似乎已經遙不可及,但金耀東仍無法擺脫困苦,彷佛命運已經將他選定,去演繹這出生命的悲劇。金耀東對這些陌生人表現出一種超越時空國族的同理心,實際是一種世界主義精神的極致體現,就如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的概念一樣:
羅馬人憑借直覺而實行的普世政策及其傾向也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之中。法蘭西人在革命中所贏得的最好的東西,也是德意志特性的組成部分。[5](P.51)
就文化傳承的角度言,日耳曼民族并非羅馬文化的嫡系繼承者;至于當時的法國,則是德國的入侵者,是日耳曼民族的敵人。然而諾瓦利斯的觀點卻超然于國族的偏見,站在普世人類的高度指出,國族間的文化實際互相交融影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在國族文化之上,尚有一更高層次的單位,即人類文明的總體。《狩》的金耀東,也就是站在人類文明的總體高度,才在想起白俄將軍的同時,聯想到耶穌、釋迦、華盛頓、貝多芬和尼采等人。在此,無名氏作品的世界主義精神,已得到全面的展現,這是一種超越國族、政見、宗教信仰,乃至時代的同理心,當金耀東想到“俄羅斯亡命者是‘這個人!’他自己也是‘這個人!’”的時候,“你”、“我”、“他”的界線頓時被打破,剩下的就只有“我們”這個集體。
四、結 語
《亞細亞狂人》的世界主義精神,讓無名氏作品在主題和寫作風格上逐步確立出個人的特點。世界主義精神主張肯定“他者”與“自我”有著同等的價值,并肯定“他者”的文化。從《露西亞之戀》和《狩》等文可以看出,《亞細亞狂人》肯定國族之間的差異,但國族之間仍然可以互相理解、體諒和尊重。國族之間不應互相輕視,而是應該站在對等的地位彼此對話和欣賞。這種平等觀念,成為無名氏作品的一大核心思想,從而為無名氏作品的主題和風格奠定出一種獨特的基調。沿著《亞細亞狂人》的世界主義精神,無名氏萌生出“寫作‘全部人類歷史’的計劃”,也就是《無名書》的寫作計劃。1945年無名氏放棄《亞細亞狂人》,并在1946年動筆寫《無名書》,轉向展望人類未來的存在意義,東西文化的融合,以及人類未來的理想社會形態,這種創作取向,實際是對《亞細亞狂人》世界主義精神的延續探索。
[1]無名氏.露西亞之戀[M].臺北:遠景出版公司,1976.
[2]李存光,金宰旭.解開無名氏的長篇小說《荒漠里的人》之謎[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7).
[3]李范奭.李范奭將軍回憶錄[M].龍東林,樸八先編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4]無名氏.龍窟[M].香港:新聞天地雜志社,1976.
[5]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M].孟鐘捷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