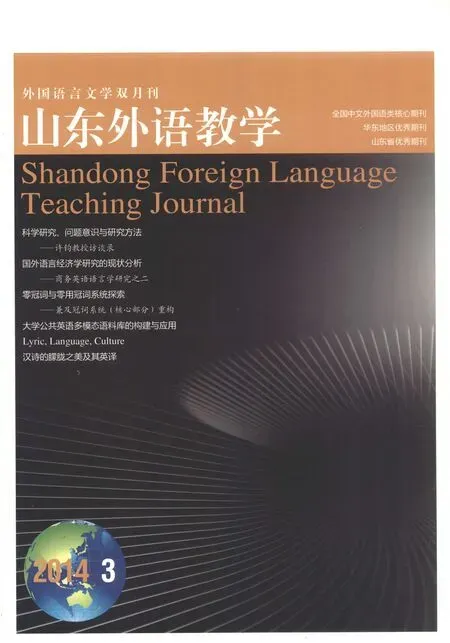從“愛麗絲”到“哈利·波特”: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創作主潮述略
舒偉
(天津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384)
從“愛麗絲”到“哈利·波特”: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創作主潮述略
舒偉
(天津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384)
從英國童話小說發展史的宏觀視野看,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經歷了興起和發展的四個歷史時期: 1)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期(1840-1910);2)兩次世界大戰前后(1910-1949);3)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4)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英國童話小說。本文力圖從中國學人的視角對英國童話小說現象進行整體審視,從發生論的視野去梳理其發生和發展的脈絡及其時代背景,以呈現英國童話小說主潮發展的宏觀圖景,并力求在英國兒童文學的文化語境中把握其社會歷史背景。
英國;童話小說;創作主潮;綜述
1.0 引言
在世界童話文學史語境中,“童話小說”(fairytale novel)是指現當代作家創作的短篇和中長篇文學童話。它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作為同源異流的幻想文學中的一種特定文類,童話小說是與傳統童話有著血脈關系的幻想小說;2)童話小說體現了傳統童話的藝術升華,是童話本體精神與現代小說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從童話文學發展史看,18世紀末期興起的德國浪漫派童話小說與19世紀后期異軍突起的英國童話小說標志著世界文學童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升華階段。18世紀末期以來,在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歷史語境中,眾多德國浪漫派作家對童話母題、童話精神及童話藝術情有獨鐘,掀起了一場童話小說創作運動,推出了許多卓具藝術成就且風格各異的童話小說。這浪漫派童話運動標志著傳統民間故事 (volksm?rchen)向文學童 話(Küntsm?rchen)的激進轉變,書寫了世界童話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同時開創了政治童話或成人童話小說的先河。從早期的文學(藝術)童話到后來的政治童話小說,其代表性作家包括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 ieland),穆塞烏斯(Johann Karl August Mus?us),諾瓦利斯(Ludwig Tieckand Novalis),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 isso),E.T.A.霍夫曼(E.T.A.Hoffmann),威廉·豪夫(W ilhelm Hauff),施托姆(Theodor Storm),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托馬斯·曼(Thomas Mann),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沃爾夫·比爾曼 (Wolf Biermann),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等等。新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杰克·齊普斯高度評價了德國浪漫派作家用童話藝術來表達其政治思想的創作實踐,指出:“幾乎所有的浪漫派作家都被童話故事所吸引,并且以非常獨創的方式對這種形式進行試驗。事實上,童話故事已如此根深蒂固地沉淀在德國的文學傳統之中,以至于從19世紀初以來直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個重要的德國作家沒有以某種方式運用或者創作過童話故事。”(Zipes,2002:62)
隨著時間的前行,在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和兒童文學革命這雙重浪潮的沖擊下,張揚想象力和游戲精神的英國童話小說異軍突起,成果斐然。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年,英國童話小說創作開創了一個星云燦爛的“黃金時代”,從此形成了一個綿延至今,繼往開來的童話小說創作主潮。與德國浪漫派童話創作運動不同的是,英國童話小說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兒童文學語境中異軍突起的幻想文學,但它發端于兒童文學而又超越兒童文學,根植于傳統童話而又超越傳統童話,因此不僅具有鮮明的童趣性,而且能夠滿足不同年齡層次讀者(包括成人)的審美需求。童話小說一方面要體現童話文學在當代社會背景下對兒童成長的意義和價值,不能像寫一般幻想小說那樣隨心所欲;另一方面,作為歷久彌新的童話本體精神與現代小說藝術相結合的產物,童話小說具有獨特的藝術彈性,能夠滿足不同年齡層次讀者(包括成人讀者)的閱讀需求,以及認知需求和審美需求。
從英國童話小說發展史的宏觀視野審視,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言,從維多利亞時期的兩部“愛麗絲”小說到20世紀末的“哈利·波特”小說系列,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經歷了興起和發展的四個歷史時期:1)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期(1840-1910);2)兩次世界大戰前后(1910-1949);3)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4)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英國童話小說。本文力圖從中國學人的視角對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現象進行整體審視,從發生論的視野去考察和梳理其發生和發展脈絡及其時代語境,以呈現英國童話小說主潮發展的宏觀圖景,并力求在英國兒童文學的文化語境中把握其社會歷史背景。
2.0 異軍突起 星云燦爛: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1840-1910)
從維多利亞時代后期興起的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是英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英國兒童文學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英國童話小說創作主潮的發生始于維多利亞時代中后期,是在工業革命和兒童文學革命的雙重浪潮的沖擊下發展起來的。
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使英國農業文明迅速向工業文明轉型,給英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社會變革和動蕩,不僅造成了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結構明顯的雙重性(差距越來越大的富人和窮人被稱為“兩個民族”),而且導致了人們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代表的新思想的發表和傳播,人們傳統的思想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震蕩,并由此引發了維多利亞人的精神迷茫和情感危機。這種精神危機又激發了“重返童年”的時代思潮。諸多英國文人、作家開始關注兒童和童年。從19世紀中期以來,許多著名的英國作家都開始懷著重返童年的懷舊心態為孩子們寫作,客觀上推動了英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就“重返童年”而言,英國文壇上出現了兩種創作走向:以狄更斯作品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的童年敘事和以劉易斯·卡羅爾作品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敘事。前者直面冷酷的社會現實,大力表現“苦難童年”的主題,不過仍然以溫情的基調為讀者展現出希望之光。而后者成為英國童話小說的卓越代表,革命性地顛覆了長期以來在英國兒童文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恪守“事實”,堅持理性說教的兒童圖書寫作教條。
英國童話小說的崛起是兒童文學領域兩極碰撞的結果。我們知道,在英國,自覺的兒童文學始于18世紀中期。18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英國人的食品供應與他國相比得到較好的保障;同時隨著醫學的進步和衛生條件的改善,兒童的生存率大為提高。從1750年以來,英國的人口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增長率比歐洲平均值高出50%。(Harvie&Matthew,2007:183)在維多利亞時代,多子女的家庭是比較常見的。多子多女、人丁興旺通常被看做完善家庭的標志。此外,維多利亞時代變動不居的環境因素使人們的家庭觀念得到強化,家庭對子女的關注日益增加,無論社會還是家庭在教育投資和感情投入方面也相應增強,這也在客觀上為英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和思想基礎。英國兒童文學的標記性人物是出版家約翰·紐伯瑞(John Newbery,1713-1767)。1744年,紐伯瑞在倫敦開設了同時經營印刷出版和發行銷售的書店。紐伯瑞不僅經營成人圖書和雜志的出版,而且致力于開拓兒童讀物市場,不久便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專為兒童出版讀物的出版商。哈維·達頓在《英國兒童圖書》中將紐伯瑞的1744年比作歷史上“征服者威廉”的1066年,把紐伯瑞稱作“征服者紐伯瑞”。(Darton,1958:7)到1815年,約翰·紐伯瑞及其繼承者總共出版了約400多種為兒童及青少年讀者創作和改編的各種讀物。從總體上看,紐伯瑞及其繼承者的出版理念和圖書內容還恪守著道德與宗教等教育主題。從17世紀后期以來,英國清教主義對于幻想文學和童話文學采取的是堅決禁忌與壓制的態度。進入18世紀以后,直到19世紀60年代,堅持道德訓誡與理性說教的兒童圖書在英國一直是占壓倒優勢的主流趨勢。這與英國社會普遍流行的思想觀念有很大關系。19世紀30年代英國下院通過的“選舉法修正法案”擴大了下議院的選民基礎,增強了中產階級的勢力。保守的中產階級人士與以往堅持清教主義觀念的人們一樣,也竭力排斥“異想天開”的童話故事,包括那些輕松幽默的廉價小書,結果使“理性話語”繼續成為兒童文學中的主導話語。隨著時代的前行,兒童圖書領域內“為什么目的而寫”,“怎么寫”和“寫什么”的問題突顯出來,形成了兩種對立的創作傾向,那就是應當遵循“理性”原則還是張揚“幻想”精神的價值取向。人們面臨的問題是,兒童文學提供給兒童的,應當是那些能夠真正吸引他們的東西(讓他們喜聞樂見的“奇思異想”的產物),還是那些成人們認為對兒童而言恰當的東西(理性教育和道德訓示的故事)。由此形成了英國兒童文學領域的兩極碰撞。
直接推動英國童話小說興起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進步及其新思想、新變化的影響。工業革命所導致的社會巨變客觀上推動了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兒童文學及童話文學的發展。工業革命時期那些由新思想和新觀念引發的震蕩和沖擊不僅動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信仰基座,而且動搖了英國清教主義自17世紀后期以來對幻想文學和童話文學的禁忌與壓制——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化思潮有關童年崇拜和童年概念的確立,沖破了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加爾文主義壓制兒童本性的原罪論宗教觀——這兩種合力為英國童話小說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文化條件。
其次,英國兒童圖書市場的興起以及出版業對童話和幻想故事的需求,為英國原創童話小說的興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動力。在英國,議會于1709年通過了西方出版史上的第一部《版權法》(The Copyright Acts)。這部于1710年生效的版權法雖然并不完備(各種牟利性的盜版活動仍然打著“鼓勵獲取知識”的旗號大行其事),但它首次明確了作者和出版者的權益,規定由書業公會負責全國的版權登記,為出版業創造了合理競爭的環境。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英國圖書出版業的組織結構也產生了很大變化。出版商與書商也進一步向專業化方向發展。而且,19世紀以來英國小說的繁榮推動了小說出版的多樣化格局;除了傳統的出版形式,許多小說采用雜志、報紙連載或小分冊等形式發表,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群,這對于出版商發行幻想性兒童圖書具有啟發意義。進入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穩定的兒童圖書的讀者市場已經形成,以中產階級子女為主體的新讀者群成為兒童圖書出版商心目中的出版對象。出版商知道有眾多讀者希望讀到童話故事和幻想文學,這成為推動英國童話與幻想小說發展的原動力之一。爾后隨著歐洲經典童話的翻譯引進出版,浪漫主義和幻想因素濃厚的童話故事與新童話故事也大量出版,市場前景十分看好。
在英國,精明的出版商發現兒童讀者喜歡童話和幻想的故事,這是促使他們出版此類圖書的直接動因。用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杰(Jean Piaget)的“兒童認知發展階段論”解釋,兒童在6到8歲時已經從“前運演階段”進入“具體運演階段”,他們的語言運用能力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發展,已經可以通過詞語和其他象征符號表達較為抽象的概念;而經典童話及幻想故事的內容和形式正好呼應了這一年齡段的兒童感應世界的方式,包括泛靈論、自我中心論、意識與物體之間存在的魔法般的關系、報應式的正義、抵消性的懲罰、并列性的因果關系,不能將自我與外部世界區分開來,相信物體會響應他們持續的愿望呼應而發生移動,等等,所以對他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Zipes,1983:177-178)
而歐洲大陸及東方經典童話作品的翻譯引進深受讀者歡迎也證明了童話和幻想故事的市場前景。這些經典童話包括意大利童話、法國經典童話(如貝洛的《鵝媽媽故事》和多爾諾瓦夫人童話故事)、《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等。隨之出現的是,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國,童話故事重新成為兒童讀物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經典童話故事在英國大受歡迎,這使有識之士認識到有必要,也有可能為兒童創作獨立于傳統童話的文學幻想故事。而英國小說藝術的日臻成熟又為英國原創童話小說的創作提供了充足的文學敘事的借鑒與支撐。18世紀以來,英國小說在文壇大展身手,出現了諸如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遜、菲爾丁、斯摩萊特、斯特恩、簡·奧斯丁等作家創作的杰出小說。19世紀以來,英國的小說創作更是成為英國文壇上藝術成就最大的文學類型。在此背景下,英國本土的原創童話小說獲得了必要的藝術借鑒,得以帶著充足的自信進行創作。眾所周知,傳統的民間童話大多注重事件進程的描寫,對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寫是忽略的。而現當代童話小說則比較注重人物(兒童主人公)的心理描寫,這一變化是與英國同時期的小說創作傾向基本同步的。正如C·N·曼洛夫(C.N.Manlove)指出的,隨著喬治·愛略特,安東尼·特羅洛普,喬治·梅瑞狄斯等作家取代了薩克雷和狄更斯,英國當代小說更加注重心理現實主義。(Manlove,2003:26)而在表現兒童人物的心理方面,現當代兒童幻想文學無疑具備了超越早期傳統童話敘事的獨特優勢。如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風聲》就通過卓越的動物體童話小說藝術呈現了少年兒童心向往之的理想生活狀態;他們內心渴望的驚險刺激之遠游、歷險愿望的滿足;他們無不為之感到快意的游戲精神的張揚;以及對于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各種互補的人格心理傾向和深層愿望的形象化投射。
維多利亞后期,英國兒童幻想文學借助現代小說藝術的翅膀,從傳統童話中脫穎而出,大放異彩。這一時期的名篇佳作數量之多,藝術水平之高,令世人矚目,其代表性作品有:F.E.佩吉特(F.E.Paget)的《卡茲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1844);羅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1851);薩克雷(W.M.Thackeray)的《玫瑰與戒指》(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兒》(1863);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865)和《愛麗絲鏡中世界奇遇記》(1871);麥克唐納(Gorge Macdonald)的《乘著北風遨游》(1871)、《公主與科迪》(1883);王爾德(Oscar W ilde)的童話集《快樂王子及其它故事》(1888)和《石榴之家》(1891);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傳奇》(1894 -1895);貝特麗克絲·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1902);伊迪絲·內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個孩子與沙精》(1902)、《鳳凰與魔毯》(1904)、《護符的故事》(1906)、《魔法城堡》(1907);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飛俠彼得·潘》(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清風》(1908),等等;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英國兒童文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卡羅爾的兩部“愛麗絲”小說不僅是對維多利亞時期說教性兒童圖書寫作傾向的激進反叛與顛覆,而且是對包括歐洲經典童話在內的所有傳統童話的突破和超越。內斯比特的幻想文學創作形成了以五個孩子為主人公的“集體人物”以及有限定條件的魔法等“內斯比特傳統”,對傳統童話的敘事模式進行了更新與發展,預設了各種現代社會語境下主人公進入幻想世界或魔法世界的方式,對后人影響深遠。在這一時期,眾多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內省性的,其主題一般被批評家歸于尋找田園牧歌式的“阿卡迪亞”,從本質上可以看做工業化給英國社會帶來巨大變化,對人們思想帶來極大沖擊而產生的一種反應。這個“阿卡迪亞”的基本意象表現為蘊涵著宗教救贖意味的另一個世界(如金斯利的《水孩兒》);充滿荒誕美學情趣的地下奇境世界(如卡羅爾的《愛麗絲奇境漫游記》);激發探險精神的魔法城堡(如內斯比特的《魔法城堡》);與普通世俗社會相對立的永無島(如巴里的《小飛俠彼得·潘》);能滿足愿望的精靈(如內斯比特的《五個孩子與沙精》);會說話的動物或玩偶(如格雷厄姆的《柳林清風》),等等。此外,這一時期的表現動物小說的主題和回到過去時光的主題也是很有特色的。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名家名作奠定了英國童話小說傳統的堅實傳統,成為影響深遠的英國童話小說經典。
3.0 承前啟后: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英國童話小說(1910-1949)
兩次世界大戰前后是英國童話小說發展歷程中一個承前啟后的階段,英國童話小說成為兒童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類,其主要創作特征更趨于童趣化。其主要創作特征表現為從奇崛奔放走向平緩凝重,而且更趨于童趣化,體現了自覺的兒童文學意識。
從1911年至1949年,兩次源起于歐洲的世界大戰幾乎席卷全球,空前慘烈,對于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社會同樣產生了難以磨滅的重大影響。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之后,昔日稱雄世界,無比輝煌的大英帝國分別經歷了國力衰弱的陣痛,都要用很長時間才能從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與此同時,戰爭及其嚴重后果也促使英國政府比以往更加重視兒童與青少年教育,客觀上對英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物質條件。英國議會于1918年通過了新的《教育法案》,將接受義務教育的最大年齡定為14歲,而14歲以后離校的兒童還應當繼續上學,要每年接受320個小時的教育,直到年滿18周歲。這一法案對于提高英國低齡兒童的讀書識字率具有積極的作用。1941年,丘吉爾政府任命巴菲特為教育大臣,由他主持制定了于1944年頒布實施的《英國教育法案》。這部新法案將接受義務教育的離校年齡提高到15歲;同時把政府的教育制度劃分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個階段。這部新法案體現了對于幼童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視。客觀地看,英國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由此延續至今,影響深遠。從總體上看,對適齡兒童及青少年教育的重視對提升他們的文化水平及閱讀水平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為英國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和接受提供了有益的外部環境。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和40年代,英國文壇上正是現代主義小說流派興起和盛行的時期。其中意識流小說無疑是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其重要作家包括弗吉尼亞·吳爾夫和詹姆士·喬伊斯等人。由于英國童話小說主潮的兒童文學性及其兒童和青少年讀者本位的特性,也由于以劉易斯·卡羅爾為代表的維多利亞時期童話小說作家們所奠定的堅實傳統,英國童話小說的創作仍然秉承著張揚幻想,解放想象的童話審美理想而沿著自己的軌道繼續前行。事實上,戰爭的沖擊和戰后的變化使許多人心中的懷舊情感和逃避愿望變得更加急迫,更富有吸引力。這些情緒自然會在兒童圖書的創作中找到適宜的表達。這一時期的童話小說代表作有休·洛夫廷(Hugh John Lofting)的《杜立德醫生》系列(1920);A·A·米爾恩(A.A.Milne)的《小熊溫尼·菩》(1926);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的《午夜的人們》(1927)和《歡樂盒》(1935);特拉弗絲(P.L.Travers)的《隨風而來的瑪麗·波平絲》系列(1934-1936);J·B·S·霍爾丹(J.B.S.Haldan)的《我的朋友利基先生》(1937);J·R·R·托爾金(J.R.R.Tolkien)的早期作品《霍比特人》(1937);厄休拉·莫莉·威廉姆斯(U.M.W illiams)的《小木馬歷險記》(1938);T·H·懷特(T.H.White)的《石中劍》(1938);20世紀40年代的重要作品有皮皮(BB,D·J·Watkins-Pitchford)的《灰矮人》(1942),等等。
由于受到戰爭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童話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尋找避難所。這一傾向也被一些批評家稱為“逃避主義”。分別創作于兩次大戰期間的兩部童話小說,休·洛夫廷的《杜立德醫生歷險記》(1920)和皮皮的《灰矮人》(1942)就寄托著典型的追尋避難樂土的理想。前者講述的杜立德醫生不善與人交往,繼而轉為動物看病,后來又遠赴遙遠的非洲叢林去醫治那里患病的動物——由此引發的種種故事無疑發生在充滿童趣的逃離戰爭的理想之國。后者講述的是3個灰矮人前往愚人河的源頭尋找其失散兄弟的歷險,在更深的層面寄托了作者在慘烈的二戰期間,在英國城鄉遭受納粹空軍瘋狂轟炸的背景下,致力于尋求安寧與和平的愿望和理想。
這一時期的動物故事創作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到20世紀30年代,托爾金的《霍比特人》(1937)開了英國兒童幻想文學變化之風氣。它對尋寶歷險的傳統主題進行了拓展,注入時代精神和作者的思考。托爾金通過本人在真實戰爭中的經歷,對本時代的幻想文學作品的倫理道德觀,價值觀及傳統的英雄主義等進行了拷問。小說的主人公比爾博在巫師剛多爾夫的安排下,踏上跟隨小矮人遠征隊前往惡龍盤踞的巢穴,奪回被它搶走霸占的財寶的歷險征程。這個故事從幾個層面揭示了人性的復雜。蘇格蘭作家、政治家約翰·布坎(John Buchan)創作的《神奇的手杖》(1932),以及發表于1939年的兩部講述返回過去時間的旅行故事——希爾達·劉易斯(Hilda Lewis)的《飛船》和阿利森·厄特利(A lison Uttley)的《時間旅行者》也開拓了新的主題(題材)。40年代出現了不少描寫想象世界的作者,如伊麗莎白·高奇(Elizabeth Goudge),沃金斯·皮奇福德(Watkins Pitchford),克羅夫特·迪金森(Croft Dickinson),埃里克·林克萊特(Eric Link later),朗默·戈登(Rumer Godden),貝弗利·尼科爾斯(Beverley Nichols),等等。從總體上看,如果說維多利亞時期的經典童話小說呈現了奇崛厚重的魔法因素(地下奇境和鏡中世界,能滿足愿望的沙精,魔法護符,神奇的鳳凰,以及其他使現實與幻想交替互換的魔法因素),那么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英國童話小說表現出從奇崛奔放走向平緩凝重的趨向,同時更趨于童趣化;魔法因素則趨于平淡化或日常生活化,那些具有神奇魔力的物件往往是兒童熟悉的日用品或玩具,如手杖,模型船,木馬,等等;具有神奇魔法的人物及魔法因素也出現了日常生活化(故事可置于現代社會的平民化生活背景之中)的走向。
4.0 第二個收獲季: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
20世紀50和60年代是英國童話小說創作的又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也被稱作英國童話小說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作家們探索了新的表現題材、敘事方式和表述話語,取得了豐碩厚重的創作成就。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英國民眾蒙受了巨大的苦難。隨著這慘絕人寰的戰爭的結束,民眾期待著清理戰爭廢墟,開始新的生活。激進的工黨政府在1945年舉行的大選中上臺執政,體現了廣大民眾要求變革和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工黨政府所推行的國有化(包括英格蘭銀行、煤礦、電力、鐵路、公路等部門行業)和福利社會的基本政策使戰后的英國人享受了公費醫療保健,公費教育,國家住房和就業保障措施等福利待遇。對于教育的高度重視也是變化之一。1944年頒布實施的《教育法案》使中下層階級家庭的子女能夠獲得政府的資助去求學,于是大批工人子弟得以進入英國的高等學府接受教育,其中不少人日后成為英國文壇的新秀(艾倫·加納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然而從本質上看,無論是經濟的復蘇還是國有化的進程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結構,因此也無法根除英國國內固有的階級矛盾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蕭條。此外,就國際局勢而言,二戰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嚴峻的東西方兩大敵對陣營的冷戰格局。英國在特定意義上成為了美國的跟班,卷入了兩大敵對陣營之間的冷戰。從總體上看,在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社會,面對可能發生毀滅全球的核戰爭,面對生態破壞、人口過剩、政府和工業巨頭的權力強化、嚴重的經濟危機等等新的挑戰,人們的兒童教育觀念及社會觀念都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幻想文學在西方社會成為具有特定功能的文學類型,正是在這種時代語境之下,50年代以來的兒童幻想文學更注重應對恐懼的替換性想象敘事及其娛樂性。
在動蕩的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為兒童及青少年讀者而寫作的這一特殊性,英國兒童幻想小說仍然秉承著童話幻想敘事的宗旨探索著新的表達題材和表述話語,從而進入又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也被稱為英國兒童文學的第二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瑪麗·諾頓(Mary Norton)的《小矮人博羅爾一家》(1952);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的《湯姆的午夜花園》(1958);C.S.劉易斯(C.S.Lewis)的《納里亞傳奇》系列(《獅子·女巫和衣櫥》1950、《凱斯賓王子》1951、《“黎明踏浪者”號的遠航》1952、《銀椅子》1953、《能言馬和王子》1954、《魔法師的外甥》1955、《最后之戰》1956,獲卡內基獎);J·R·R·托爾金(J·R·R·Tolkien)的《魔戒傳奇》系列(1954-1955);法姆(Penelope Farmer)的《夏季飛鳥》(1962);布里格斯(Mkatharine M Briggs)的《霍伯德·迪克》(1955)、《凱特與胡桃夾子》(1963);瓊·艾肯(Joan Aiken)的《雨滴項鏈》(1963);R·達爾(R.Dahl)的《小詹姆與大仙桃》(1961)、《查理和巧克力工廠》(1964)、《魔法手指》(1966);阿倫·加納(Alan Garner)的《布里森格曼的魔法石》(國內譯為《寶石少女》,1960)、《伊萊多》(1965)、《貓頭鷹恩仇錄》(1967,獲卡內基獎);露西·波斯頓(Lucy M.Boston)的《綠諾威莊園》系列《綠諾威莊園的孩子們》(1955)、《綠諾威莊園的不速之客》(1961,獲卡內基獎);海倫·克雷斯韋爾(Helen Cresswell)的《做餡餅的專家》(1967)、《路標》(1968)、《巡夜者》(1969)、羅斯瑪麗·哈利斯(Rosemary Harris)的《云中月》(1968)、《日中影》(1970)、《閃亮的晨星》(1972),等等。
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童話小說相比,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在創作的主題方面進行了新的重要拓展。作家對于時間的關注突出地體現在對“過去”時光的把握和思考方面,正如批評家漢弗萊·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所言:“在這一時期創作的絕大部分英國兒童小說都具有同樣的主題:對過去的發現或重新發現。”(Carpenter,1985:217)這一時期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創作趨向:1)表現時間穿梭的題材,故事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發生互動。菲利帕·皮爾斯的《湯姆的午夜花園》講述湯姆在午夜時分當老爺鐘敲響13下時進入了一個存在于過去的美麗花園,與一個叫做海蒂的小女孩玩耍,由此穿梭于現在與過去的時空之間。露西·波斯頓的《綠諾威莊園》系列也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作者巧妙地運用了“時間旅行”的要素來講述故事。雖然故事的敘述時間是現在,但通過敘述者——如《綠諾威莊園的孩子們》里的男孩托利——時間回溯到了17世紀。表現此類題材的還有佩尼洛普·萊弗利的《諾漢姆花園中的房子》、佩尼洛普·法姆的《有時候是夏綠蒂》等作品;2)歷史奇幻小說的興起。代表性作家包括利昂·加菲爾德和瓊·艾肯等人,作者從充滿想象力的視域去改寫歷史,重寫歷史。此類題材的作品還包括艾倫·加納的《紅色轉移》和《貓頭鷹恩仇錄》、威廉·梅恩的《草繩》和《安塔和雄鷹》等。英國歷史奇幻小說對于過去所進行的重新書寫,或者在一個虛構的地理空間建構龐大的歷史的第二世界,在本質上都是借助想象在時間、歷史和過去中進行新的敘事構建,表達作者對人類基本問題的深切關注與思考,以及對理想社會的期望和追求。這一時期出現的托爾金現象值得關注。《魔戒傳奇》于1954年問世,到1965年出平裝本后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品。托爾金的《魔戒傳奇》作為宏大的假想性歷史幻想小說,創造了一種“替換性的宗教”,體現了作者對邪惡本性的持續關注和探索。在托爾金的幻想世界里,正直善良的主人公仍然像傳統童話敘事的主人公一樣,通過出自本心的細微善舉而獲得出乎預料的理想結果。然而正如批評家指出的,當邪惡勢力被消滅以后,主人公發現他們自己最后的家園霞爾,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精神家園,正遭受著另一種邪惡力量的侵襲和蹂躪,那就是“工業化的破壞”。托爾金的幻想文學創作是繼往開來的,他一方面繼承了西方幻想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又對西方當代幻想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5.0 繼往開來雜色多彩:20世紀70年代以來
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童話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不少作家汲取了新的文學表現因素,英國童話小說創作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總體上呈現出雜色多彩,繼往開來的格局。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各種新的可能性伴隨著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憂慮出現在英國人的視線里。作為一個科技先進,但資源貧乏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國內非生產性的第三產業與生產性的制造工業之間對于原本就短缺的資源、資金和勞力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結果使制造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由于70年代以來發生在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波及到英國,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采取了竭力縮減各種社會福利和社會公益性服務的做法來緊縮財政開支。與此同時,日益向右轉的撒切爾夫人還致力于削弱工會的力量,公開聲稱要摧毀英國政治生活中的社會主義。而左派人士則提出了在更大范圍內實行經濟的社會化要求。從1984年持續到1985年的英國煤礦工人舉行的大罷工極大地震撼了整個島國,再次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出現在英國的各種爭議和矛盾反映了這一時期英國經濟的困境。與此同時,隨著全球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多極化發展格局,以及各種新思潮的涌現,傳統的思想觀念繼續發生著裂變。保守的英國文化遭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沖擊,從甲殼蟲樂隊、搖滾樂、流行音樂和爵士樂到玩世不恭的嬉皮士文化,各種流行文化風靡英倫。而民族主義的抬頭,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發出的抗議,還有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等等,各種社會問題和新的思潮,新的文化現象劇烈地改變著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保守觀念和文化心理,這將影響到包括兒童文學作家在內的當代英國作家們的思考和創作。
在英國兒童文學創作領域,幻想文學創作在進入1970年代以后獲得進一步發展。首先,大量優秀的英國作家介入兒童文學的創作,隨之涌現出眾多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其次,兒童文學的創作文類空前繁榮,兒童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內容,所表達的主題思想更加復雜并貼近時代,正如英國當代著名女兒童文學評論家伊萊恩·莫斯(Elaine Moss)所指出的:“1970年代是一個教育領域以兒童為中心的時代;這是一個英國逐漸從后帝國向多元文化帝國角色轉換的時代;這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不同于非性別歧視)的時代。所有這些事實都對這一時代的兒童文學內容有著影響。”(Moss,1980)從一個更大的語境去看,當代童話文學的創作也出現了新的熱潮。1970年代以來,大量作家——特別是女權主義作家——意識到童話及想象力對意識形態的巨大“塑形作用”,從而在英美等國出現了以創作或重寫童話為中心的創作潮流,史稱“童話文藝復興”(Marchenrenaissance)。大量童話變體出現,如安妮·舍克頓(Anne Sexton)的女權主義童話詩集《蛻變》(1971)、羅伯特·馬休(Robert Munsch)的兒童童話繪本《紙袋公主》(1980)、簡妮特·溫特森(Jeanette W interson)的童話小說《吻女巫》(1989),等等。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風靡歐美的托爾金和C ·S·劉易斯作品的影響下,英國童話小說創作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人們能夠看到各種兒童與青少年幻想文學的變體,如童話奇幻,英雄奇幻,科學奇幻,超人英雄奇幻,寶劍與魔法奇幻,等等。此外,羅爾德·達爾的“狂歡化”童話小說創作;彼得·迪金森探索“變幻莫測”的世界的童話小說;佩內洛普·利弗里的以“時間、歷史與記憶”為特色的童話小說創作;海倫·克雷斯韋爾的童話奇幻創作的原創性與多樣性特征;黛安娜·瓊斯的童話奇幻創作;以安吉拉·卡特為代表的成人本位的新童話敘事;蘇珊·庫珀的代表作的傳統因素與創新;J·K·羅琳的長篇童話小說力作《哈利·波特》系列,等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佩內洛普·利弗里、艾倫·加納、黛安娜·溫尼·瓊斯和蘇珊·庫珀等新一代兒童幻想小說作家均于上世紀50年代就讀于牛津大學。正如查爾斯·巴特勒所指出的,他們是在托爾金和C.S.劉易斯等人的講座和演講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呈現了二者的影響。(Butler,2006)從《霍比特人》到《魔戒傳奇》系列,通過將小說、童話和傳奇三種因素融合起來,托爾金開創了兒童與青少年幻想小說創作的成功之路。與《霍比特人》相比,《魔戒傳奇》系列是更具雙重性特征的幻想小說,打通了兒童文學、童話文學和奇幻文學之間的界限,使之成為這一時期幻想文學創作中最有活力的文學樣式之一。
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有蘇珊·庫珀(Susan Cooper)在《大海之上,巨石之下》(1965)之后的另四部系列作品:《黑暗在蔓延》(1973)、《綠巫師》(1974)、《灰國王》(1975)、《銀裝樹》(1977);彼得·迪金森(Peter Dickinson)的《變幻》三部曲(1968-1970)、《金色的城堡》(1980);海倫·克雷斯韋爾(Helen Cresswell)的《在碼頭上方》(1972)、《波利·弗林特的秘密世界》(1982);佩內洛普·利弗里(Penelop Lively)的《阿斯特科特》系列(1970)、《托馬斯·肯普的幽靈》(1973);理查德·亞當斯(Richard Adams)的《沃特希普荒原》(1972);科林·達恩(Colin Donn)的《動物遠征隊》(1979);萊昂內爾·戴維森(Lionel Davidson)的《在李子湖的下面》(1980);R·達爾(R.Dahl)的《魔法手指》(1970)、《查理和大玻璃升降機》(1975)、《好心眼的巨人》(1983)、《女巫》(1985)、《瑪蒂爾達》(1989);黛安娜·W·瓊斯(Diana Wynne Jones)的《豪爾的移動城堡》(1986)、《克雷斯托曼琪世界傳奇》系列等;迪克·金·史密斯(Dick King-Smith)的《狗腳丫小豬戴格》(1980)、《牧羊豬》(1983)、《哈莉特的野兔》(1994),等一系列農場動物小說,以及J·K·羅琳(J.K.Row 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哈利·波特與魔法石》(1997)、《哈利·波特與密室》(1998)、《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1999)、《哈利·波特與火焰杯》(2000)、《哈利·波特與鳳凰社》(2003)、《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2005)、《哈利·波特與致命圣徒》(2007)。菲利普·普爾曼(Philip Pullman)的《黑質三部曲》,包括《黃金羅盤》(1995)、《魔法神刀》(1997)、《琥珀望遠鏡》(2000),《發條鐘》(1997),等等。
蘇珊·庫珀繼承了托爾金開創的現代夢幻性幻想小說的傳統,將托爾金的中洲神話世界轉換為當代的威爾士鄉村世界,并且富有創造性地采用了許多英格蘭和威爾士民間文化和文學的傳統因素。作為這一時期英國童話小說的最重要作家之一,黛安娜·溫尼·瓊斯創作了30多部童話小說,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豪爾的移動城堡》(1986)。而被稱為20世紀最具想象力的兒童文學作家達爾在70年代以來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勢頭。作者通過采用“人體特異功能”(《瑪蒂爾達》),能導致變形的化學藥劑(《女巫》),以及新計謀(《了不起的狐貍爸爸》)等幻想因素拓展和強化了童話敘事的故事性。當然,20世紀后期英國童話小說創作的最大奇觀是“哈利·波特”現象——無論是它無與倫比的流行熱潮還是它引發的激烈爭論(激烈的批評者稱之為“文化幼稚病”甚至“愚昧的文化潮流”等)。1997年6月《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由布魯姆斯伯利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該系列的第四部《哈利·波特與火焰杯》在英語國家同步發行,由此在全球掀起了“哈利·波特”熱潮。2007年7月,該系列的終結篇《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面世,為這一奇觀劃上了一個驚嘆號。《哈利·波特》系列始于哈利11歲時發生的故事,分別講述了這個從小寄人籬下的孤兒在入住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后的不平凡經歷。在最后一部小說里,17歲的哈利終于在經歷風雨后成為一個真正的魔法師。新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杰克·齊普斯做了這樣的評價:
盡管并非《哈利·波特》小說系列使兒童文學回歸其在文化版圖中應當擁有的地位,但它們確實鞏固了兒童文學在文化版圖中的地位,而且將繼續使普通讀者認識到,兒童文學才是最受歡迎的流行文學。兒童文學是真正的民間文學,是為所有民眾創作的文學,是無論老少都在閱讀的文學,它對于兒童的社會化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對于發展孩子們的批判性和富有想象力的閱讀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齊普斯,2010:230)
想象力的原動力來自于人類拓展自己經驗視野的深切愿望。而想象力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創新與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對英國童話小說創作主潮的研究無疑是一個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1]Butler,C.Four British Fantasists:Place and Culture in the Children's Fantasies of Penelope Lively,Alan Garner,Diana Wynne Jones,and Susan Cooper[M].Metuchen:Scarecrow Press,2006.
[2]Carpenter,H.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5.
[3]Darton,F.J.H.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 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4]Harvie,C.&H.C.G.Matthew.19世紀英國:危機與變革[M].韓敏中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5]Manlove,C.From Alice to Harry Potter:Children's Fantasy in England[M].Christchurch: 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2003.
[6]Moss,E.The seventies in British Children's Books[A].In N.Chambers(ed.).The Signal Approach to Children's Books[C].London: Kestrel,1980.48-82
[7]Zipes,J.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M].London:Heinemann,1983.
[8]Zipes,J.Breaking the Magic Spell: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and Fairy Tales[M].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2.
[9]杰克·齊普斯.沖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間故事和童話故事的激進理論[M].舒偉主譯.合肥: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2010.
From“Alice”to“Harry Potter”: A Com 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M ain Trends of M odern 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
SHU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This paper i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main trends ofmodern 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phases of development:1)the Golden Age of 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times(1840-1910); 2)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 between the twoWorld Wars(1910-1949);3)the Second Harvest Season:Into the 50' s and 60's;4)Colourful and Diversified Spree: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 since 1970's.The macroscopic inspection of themain tread of British fairytale fiction has been made i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smuch as possible and its developmental process is surveyed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UK;Fairytale Fiction;themain trends;comprehensive survey
I109
A
1002-2643(2014)03-0084-08
2013-03-28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項目編號:08BWW003)的階段性成果。
舒偉,天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外國兒童與青少年文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英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