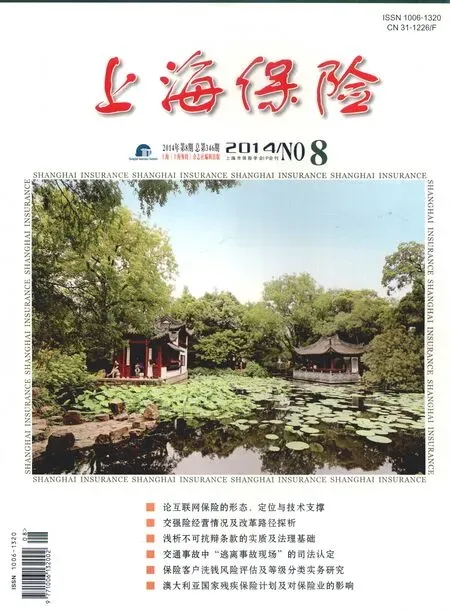交通事故中“逃離事故現場”的司法認定
符 望 王 珊
交通事故中“逃離事故現場”的司法認定
符 望 王 珊
【裁判要旨】
交通事故發生后,車輛駕駛人不得逃離事故現場,并負有保護現場的義務。如駕駛人以身體受傷就醫為由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判斷其是否屬于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約定的“逃離事故現場”,則應根據其受傷情況的嚴重性、結合生活經驗和通常情理來審查駕駛人離開現場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如駕駛人僅是一般的身體傷害或者身體不適,其離開事故現場就醫就缺乏合理和必要原因,可認為該行為屬于“逃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可以據此免責。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陳甲。
被告(上訴人):某財產保險公司(以下簡稱保險公司)。
2011年2月,陳甲就其所有的滬FG****小轎車在某保險公司處投保了車輛損失險,保險金額為1335100元,保險期限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2月13日。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約定,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逃離事故現場,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2011年9月2日4時31分,上海市公安局指揮中心110接警處接到路人報案,稱G50(往西)A30(往金山衛方向)處有一輛轎車側翻,未看到司機,對交通影響不大。5時54分,事故駕駛人陳乙(陳甲之子)亦報警稱其駕駛滬FG****小轎車撞隔離帶后翻車,無人傷,其棄車自行至醫院就診。后被保險人陳甲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公司以本起事故符合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之情形向陳甲作出拒賠通知。陳甲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賠償其車輛修理費等損失共計51萬余元。
【審判】
一審法院認為,駕駛人在事故發生后從事故現場趕往醫院就診的過程中及時向110報了警,且當時側翻的車輛并未影響道路的正常通行,應該認為駕駛人已對事故采取了一定措施,駕駛人離開現場只是出于對生命安全的考慮前往醫院就診看醫,并非遺棄車輛,故對事故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應予賠付,遂判決保險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付陳甲保險金、牽引費等共計51萬余元。一審判決后,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最關鍵的爭議在于發生交通事故后,駕駛人是否采取了合理措施,其離開現場是否有合理理由。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駕駛人陳乙發生翻車事故后需要“保護現場并立即報警”。陳乙自認凌晨3時發生事故,但在事故發生近3小時后才報警。對此,陳乙解釋為“事故后昏睡了2小時”。但保險公司提供的電話記錄顯示,事故當日4時14分至5時54分之間,陳乙共撥叫和接聽15個電話,每個電話之間的間隔時間不超過15分鐘。此外,從陳乙病歷記載看,本次事故僅導致其受輕微傷,在生命安全未受影響的情況下,陳乙離開現場去就醫的理由并不充分。法庭認為,陳乙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未立即報警的理由,應認定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逃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免責事由成立。故二審改判對陳甲全部訴請不予支持。
【評析】
本案系一起因車輛駕駛人在交通事故后“逃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拒賠引發的糾紛,涉及的法律爭議是事故車輛駕駛人陳乙棄車離開現場是否屬于保險合同約定的“逃離事故現場”,保險人是否能據此免責。
一、基本原則:駕駛人不得逃離事故現場并負有依法采取措施的義務
交通事故發生后,與之伴隨的往往是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駕駛人首先應及時搶救傷者、防止財產損失的進一步擴大。如駕駛人為逃避法律責任離開事故現場,可能導致傷者傷情加重甚至死亡,以及財產損失的擴大,極具社會危害性。故法律對此予以嚴格限制并課以嚴厲的法律責任。情節嚴重的交通肇事逃逸行為甚至要承擔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它特別惡劣情節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法領域,交通事故通常還涉及事故責任的認定及損害賠償問題。故為確保查清事故真相和及時認定保險責任,車輛駕駛人原則上不得離開事故現場,并負有依法采取措施的義務。如何“依法”采取措施,應當結合相關交通管理法律法規來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標明位置。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傷亡,當事人對事實及成因無爭議的,可以即行撤離現場,恢復交通,自行協商處理損害賠償事宜;不即行撤離現場的,應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八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應當保護現場并立即報警:(一)造成人員死亡、受傷的;(五)碰撞建筑物、公共設施或者其他設施的;(八)當事人不能自行移動車輛的。”
就本案而言,陳乙駕駛車輛翻車之后,車輛碰撞了公共設施(防沖桶),車輛翻車不能移動,這些都屬于《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中需要“保護現場并立即報警”的情況,不能隨意離開現場。“立即”應當是一個較短的時間段。保險公司提供的陳乙以往出險記錄表明,陳乙曾經駕駛涉案車輛發生過交通事故,因此應該知道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要求和報警義務。但在本次事故中,實際情況是據陳乙陳述,事故于3點發生,而電話記錄顯示其于5時54分撥打110報警。該行為顯然不屬于“立即報警”,而且此后陳乙又自行離開現場。因此,除非陳乙能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則應認定其未能依法采取措施。
二、審查例外:駕駛人離開事故現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駕駛人在交通事故發生后棄車離開現場,其原因復雜而多樣,如一律認定為“逃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均可免責,則未免失之偏頗。從詞典解釋來看,“逃離”一詞的涵義指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環境或事物而離開。從這個意義上分析,“逃離”不僅應具備駕駛人離開了事故現場這一客觀要件,還應符合駕駛人故意逃避事故責任這一主觀要求。如何判斷駕駛人是否具有逃避事故責任的故意,審判實務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以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為準。交警對事故現場的判斷具有及時性和專業性,且其認定意見系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章作出。若交警不認定為“逃離事故現場”,則保險人免責不能成立。另一種觀點認為,法院應區分不同情形,綜合判斷駕駛人是否具有離開現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進而判斷其是否具有逃避事故責任的主觀故意。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為合理。首先,在車輛事故保險糾紛案件中,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本質上屬于證據,其是否可以采信、如何運用等均需法院進行審查判斷,應歸入法院的事實審查范圍,不能直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比如在本案中,交警部門在作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時,陳乙并未到場,事故認定完全由陳乙的朋友張某代為辦理和簽署。由于非本人到場,有可能出現認定錯誤的情形,如本案保險公司對陳乙是否為真正的事故駕駛人就提出了質疑。其次,在實踐中,交警部門可能對事故現場情況僅作客觀描述而不作主觀判斷,比如《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記載為“駛離現場”“棄車離開”等等,沒有認定駕駛人主觀狀態。
至于離開現場的合理和必要原因,需要結合生活經驗和通常情理予以解釋。舉例而言,如果車輛事故中發生重大人員傷亡,而受傷人員包括駕駛人生命垂危或者有其他緊急情況需要及時醫治,離開現場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生命權高于財產權。如果不及時救助有可能危及生命,保險公司在此種情況下也不應苛求駕駛人。但是,這并不等于一旦駕駛人遭受傷害或者感覺遭受傷害,就可以自行離開現場。一般的身體傷害或者身體不適不能作為離開事故現場的理由。因此,應根據受傷情況的嚴重性來判斷駕駛人離開現場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本案諸多細節表明事故駕駛人陳乙并未遭受嚴重傷害。首先,在事故發生后至就醫前,陳乙曾經通話十余次這表明其神志清醒。其次,根據陳乙的陳述,其發生事故后曾在高速公路上走了一段路。假如該陳述屬實,亦能說明陳乙身體正常,并未受到重大傷害。再次,從門急診病歷記錄來看,陳乙并未對醫生陳述其曾經昏睡2小時,僅陳述其體表受傷。醫生對其檢查后的描述也表明陳乙精神、體力均正常,無骨折,最后治療方案也僅僅是開具云南白藥膠囊。綜合上述情形,筆者認為,在醫療需求方面,可以判斷陳乙離開事故現場缺乏合理性與必要性。
除因救助自身或他人需要暫時離開現場情形外,在涉及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中,如由于現場傷亡者家屬的激烈言行而受到威脅,駕駛人出于自身安全考慮先行離開;又如在比較偏遠、人跡罕至的地方發生交通事故,駕駛人離開事故現場尋求救助等等,均可認定為駕駛人具有離開現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這應由駕駛人盡到相應的舉證責任。如駕駛人于事故發生后感到害怕等原因而逃離,則無論其是否自首或又主動回到現場,都不應認定為具有離開現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事實查明:當事人陳述及交叉質詢的重要性
在英美法系國家,當事人被當作證人對待,當事人陳述亦是證人證言的一種。如《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601條規定,“每個人都有資格作為證人”,其中的“每個人”自然也包括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本人在內。原因在于當事人是案件的親身經歷者,最了解案件的真實情況,允許其到庭陳述有利于還原案件的真相,從而在訴訟中發現事實。正如學者所言,“現代美國有關當事人作證的規則產生了深刻的效果,因為它使許多本來缺乏證據而失利的請求可能得以提出”。當然,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當事人可能進行虛假陳述或僅作有利于自身的片面陳述,其可信度受到質疑。為了保證當事人陳述的真實性,當事人與其他普通的證人一樣需要在作證陳述前進行宣誓,并接受直接詢問和交叉詢問。當事人如進行虛假陳述,還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
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陳述是一種獨立的證據形式。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法律賦予了當事人陳述的證據功能,然而司法實踐中并未對其探明事實的作用給予足夠的重視。比如很少對當事人本人陳述進行交叉質詢,以發現其中的不實之處。尤其是在車輛事故保險糾紛案件中,許多當事人作為駕駛人本人不出庭,基于各種原因委托律師參加訴訟。當庭審中問及保險事故細節時,代理律師往往含糊其辭或是干脆“一問三不知”,給法院查清案件事實帶來較大的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建議從三方面完善。首先,遇事實不清、存在疑點之時,如果當事人本人為駕駛人,法庭應責令其本人當庭作出陳述,而不能由代理人陳述。其次,在此類案件中,作出陳述之時,無論駕駛人是當事人本人或者作為證人身份出現,應至證人席陳述,而且不能是宣讀材料式的陳述。這是西方民事訴訟普遍采取的規則。因為這種做法可以使陳述者不受律師的影響(比如其律師在旁邊可能用明示或者暗示方式影響其陳述的準確性與真實性),并讓各方更清楚地觀察到其陳述過程,以判斷陳述的可信性。同時限制其宣讀已經準備好的證詞,有助于發現其先前陳述與當庭陳述中存在的不實之處。再次,要保障各方當事人交叉質詢的機會,通過交叉質詢,發現當事人陳述不實之處。鑒于律師現階段對于交叉質詢規則尚不熟悉,法官可以發揮更大作用,通過詢問以及察言觀色,查驗證人陳述的可信性并形成內心確信。
本案中,針對事實疑點,合議庭就積極運用了上述辦法。二審法庭專門傳喚事故駕駛人陳乙出庭作證,并組織了交叉質詢,從而得以發現駕駛人對事故陳述的前后矛盾之處。首先,陳乙陳述未能立即報警原因與其手機通話記錄不一致。陳乙在一審中陳述事故于凌晨3點發生,并昏睡過2小時,至5點多鐘才醒來,以證明其有合理理由未及時報警。但其兩部手機通話紀錄顯示,事故發生當日4時14分至5時54分之間,陳乙共撥叫和接聽15個電話,每個電話之間的間隔時間不超過15分鐘,通話對象包括其妻子、兩名陳姓朋友、張某等。其中,陳乙與張某的通話是最后一個,也是通話時間最長的電話(約為8分鐘)。此后,陳乙才報警。這與陳乙先前所述情況完全不符。其次,陳乙陳述昏睡醒來時現場狀況與現實情況不符。陳乙稱事發后,其昏睡至5時許醒來時,發現車輛已經沒有了才報警。而根據路人報警后交警部門指令前往現場作業的牽引公司的記載,接令時間為事故發生當日4點50分,到達時間為5點05分,撤離時間為6點45分。而陳乙稱5點鐘之后報警離開現場,應能看到車輛。再次,針對涉案事故,陳乙本人曾分別對上海廣瀚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員、一審法院作過兩次陳述,而在二審庭審陳述時,針對是否曾昏睡、報警的地點等與前兩次陳述均存在互相矛盾之處。最后,陳乙的陳述與醫院就診記錄產生矛盾。依據常理,車禍后如曾昏睡2小時,至醫院就診時會主動向醫生提出(該陳述極有可能會引起醫院檢查項目有所不同,比如進行腦部CT)。而從門急診病歷記錄來看,陳乙僅陳述其體表受傷,并未提及昏睡情況。醫生對其檢查后的描述也表明陳乙精神、體力均正常,無骨折,最后治療方案也僅僅是開具云南白藥膠囊。上述這一切讓合議庭內心確信,陳乙所陳述的昏睡2小時可能并非實情。基于上述疑點,二審法院最終認定,陳乙無合理理由自行離開事故現場,其行為屬于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約定的“逃離事故現場”情形。據此,保險公司無需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