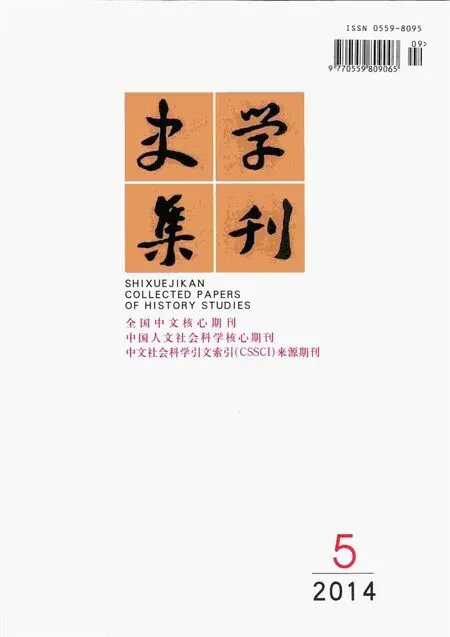釋 “明醫”
董 琳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300071)
“明醫”是對醫生的褒稱,今日仍常見諸報端。也偶有學者對“明醫”一詞的用法進行辨析和溯源,但考證略顯粗疏,尚未揭示出歷史上“明醫”的特殊意義。①余瀛鰲指出,與“名醫”側重名望相比,“明醫”更強調醫術高明,《傷寒明理論》是最早出現“明醫”一詞的醫學文獻,明代是“明醫”說發展的高潮,參閱余瀛鰲:《雜談“明醫”》,《中國中醫藥報》,2010年4月29日,第8版。邱仲麟在考察明代擇醫心態時,引用了許多擇“明醫”的材料,指出這顯示了士人對醫者掌握書本知識的正面評價,卻沒能進一步探討“明醫”的具體內涵,參閱邱仲麟:《醫生與病人——明代的醫病關系與醫療風習》,李建民主編: 《從醫療看中國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53-296頁。又據陳元朋介紹,Paul U.Unschuld(文樹德)按身份類型將古代中國的醫者分為儒醫、明醫、專醫與鈴醫。陳元朋還指出,儒醫超越明醫之處在于“其思想、行為、技藝上的多重意義,不僅限于醫療技術良否之一端”,而明醫“看重醫者技藝的美善與否”。參閱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年版,第27、41頁;陳元朋:《宋代的儒醫——兼評Robert P.Hymes有關宋元醫者地位的論點》,《新史學》,第6卷1期,1995年。不過,Unschuld原書的注釋實為“名醫”(ming-i),并指出“名醫”未經專業訓練,只憑醫療常識和經驗治病,且不以行醫為主業,多數收入來自農業生產;大生產年代的赤腳醫生也屬這一范疇。參閱Paul U.Unschuld,Die Praxis des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Heilsystems:Unter Einschluss der pharmazie dargestellt an der heutigen Situation auf Taiwan,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73,p.177.細繹“明醫”一詞在不同時代的用法,亦可見其內涵的復雜性。本文即從概念演變角度對“明醫”做一考釋。
一、佛經中的“明醫”
有關“明醫”形象的記載,較早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經中。佛經故事常用明醫譬喻佛陀,以明醫診治疾病比喻佛陀弘揚佛法。十六國期間,北涼的天竺高僧曇無讖譯成《大般涅槃經》,影響遍及南北,梁武帝也曾講解和注釋此經。②《梁書》卷三《武帝下》,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57頁。一則經文通過講述明醫善解乳藥的故事,啟發弟子眾生如何修習佛法。《涅槃經》講道:“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眾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以種種味和合眾藥,……以療眾病,無不得差。”③(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二《壽命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2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78頁。佛經意在借助明醫善用方藥、善解治法,比喻佛陀洞明諸法之真相,依照諸佛之法解除眾生苦患。后世注解者對“明醫”的理解大同小異。寶亮法師注解:“善療眾病者,知眾生根根也;知諸方藥者,善解法相也。”①(南朝梁)釋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七《哀嘆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7冊,第408頁上。慧遠法師釋為:“明醫,喻佛如來。能宣治法,故說為醫。曉八種術者,喻佛如來明識根藥。”②(隋)釋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二《壽命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7冊,第649頁下。可見,佛經中的“明醫”,與其說是辨證識病的醫者,不如說是明辨是非的智者。
南本《涅槃經》中還有一則佛陀啟發力士尋佛珠的經文,被后世多部佛典傳抄。經文講道:
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余力士角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觸之,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為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失去耶?是珠今者為何所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斗時寶珠入體,今在皮里,影現于外。汝等斗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③(南朝宋)釋慧嚴譯:《大般涅槃經》卷八《如來性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2冊,第649頁上。
佛經同時使用“良醫”、“明醫”、“醫王”三種說法形容智慧高明的醫者,并以此譬喻佛陀,表明在譯經者看來,這三個詞匯的內涵有著相近之處。
“良醫”早已見諸史籍。《左傳》載,晉景公請秦醫緩診病,緩指出“疾不可為”,并解釋何謂膏、肓,啟發病人辨識病源;④(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六,成公十年,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06頁下。還記載,晉平公請秦醫和診病,和指出“疾生于淫而不可為”,且對病因、病理、病相做了詳細說明,借此闡發君主作風與國運興亡的關聯。⑤(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六,昭公元年,第2024-2025頁。《韓非子》稱扁鵲為良醫,是因扁鵲能從細小精微處審察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提醒桓侯防微杜漸。⑥(清)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七《喻老》,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61頁。山田慶兒指出,良醫對疾病產生根源的辨析和解釋,表明醫學理論已顯現出雛形,“醫術漸漸要脫離經驗性水平的階段”。⑦[日]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40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良醫”與“明醫”均強調著眼于內因的診治原則,但佛經故事并非只顯示了明醫診治身體疾病的能力,更強調明醫啟發人心智、解除內心病苦的做法。
“醫王”是佛教術語,佛經中,佛陀常被稱為醫王。⑧陳明:《沙門黃散:唐代佛教醫事與社會生活》,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頁。《無量經》:“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⑨(南齊)曇摩伽陀耶舍譯:《無量義經·德行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第384頁下。“醫王”也是古印度對神醫的稱呼,世俗觀念中,耆婆就是醫王,印度醫典和文學作品均有對耆婆形象的描述。[10]陳明:《耆婆的形象演變及其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影響》,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文津學志》第1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64頁。唐代及以前翻譯的佛經中,“醫王”一詞十分常見,此外,在唐代士大夫的詩文中,也多以此形容佛門中的善醫者。[11]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2頁。
然而,“明醫”既鮮見于歷史文獻中,亦非佛教術語。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佛教術語類有對“醫王”的解釋,還收錄了“明處”、 “明匠”、 “明師”等詞,[12]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書店1991年版,第2796、1490-1494頁。卻未見“明醫”一詞。古印度有“五明”,指世俗教育的五種學問,“醫方明”是其中一門,盡管佛教僧徒并不以學習“醫明”為正業,但醫學也是寺院教育的一部分。[13]陳明:《古印度佛教醫學教育略論》,《法音》,2000年第4期。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僧徒也有學習“五明”且精通醫術者,然而,直至唐代,醫學才被納入學校教育之內。[14]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71、86-88頁。唐代科舉科目眾多,常舉中有明經、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為選拔醫術人才設立的科目稱“醫術科”,而非“明醫”。[15]彭炳金:《墓志中所見唐代弘文館和崇文館明經、清白科及醫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由此看來,“明醫”與“醫方明”也沒有直接關聯,表明“明醫”并非印度佛教中的固有詞匯,很可能是由譯經者意譯而來。那么,譯經者為何會選擇“明醫”一詞,本土醫學文獻中有無相關論述?
二、養生論中的“明”醫
醫學文獻中,以“明”形容醫者的記載,較早見于《靈樞經》。《靈樞》曰:“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①劉衡如校:《靈樞經》卷一《邪氣臟腑病形第四》,人民衛生出版社1964年版,第19頁。所謂“見色知病”,表明“明”醫在診法上并不采用切脈這一觸摸身體的方式,而是借助視覺、聽覺等其他感官模式判斷疾病產生的根源。②參閱許小麗:《脈,視覺到聽覺再到觸覺診查:運用“身體感”對漢代早期醫學手稿的新解讀》,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64頁。“明”強調醫生感知身體內氣血運行情況的能力,反映了古人的數術身體觀。③李建民:《發現古脈——中國古典醫學與數術身體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45頁。數術思想并非一般知識階層所能具備,因此,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寫道:“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肯自治。故桓侯怠于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非但識悟之為難,亦信受之弗易。”④(南朝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一《序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頁。可見,陶弘景對“明醫”的認識延續了《靈樞》的看法,強調明醫在審察病源方面的高明智慧,故認為現實社會并不存在明醫,一來普通醫者的領悟力有限,二來病人也不會輕易接受“治未病”的做法。
不過,有關明醫的認識卻借由養生論述傳至后世。陶弘景《養性延命錄》載《明醫論》關于服氣養性之法的一段闡述,寫道:
凡病之來,不離于五臟,事須識根,不識者勿為之耳。心臟病者,體有冷熱,呼吹二氣出之。肺臟病者,胸背脹滿,噓氣出之。脾臟病者,體上游風習習,身癢疼悶,唏氣出之。肝臟病者,眼疼,愁憂不樂,呵氣出之。以上十二種調氣法,依常以鼻引氣,口中吐氣,當令氣聲逐字吹、呼、噓、呵、唏、呬吐之。若患者依此法,皆須恭敬用心,為之,無有不差,愈病長生之術。⑤(南朝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頁。
《明醫論》可能是秦漢以前的養生文獻,東晉南朝時既已散佚,但服氣法卻作為養生知識流傳下來,北宋編成的道教類書《云笈七簽》⑥(宋)張君房輯:《云笈七簽》卷三二《雜修攝部一》,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187頁。和明代日用養生書《遵生八箋》⑦(明)高濂著,趙立勛校注:《遵生八箋校注》卷二《清修妙論箋下》,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均有記載。朱越利指出,《養性延命錄》的資料取自《養生要集》,后者由張堪、道林等人輯成,⑧朱越利:《〈養性延命錄〉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但他認為“明醫”是“名醫”的誤寫,則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此處的“明醫”并非醫者,而是洞明醫理,即道家以調節氣息保養心神、預防和祛除疾病的方法,這種修養內心的做法與佛經中明醫啟發人心智的做法有著同一旨歸。
據記載,梁武帝時,凈土宗大師曇鸞患“氣疾”,特意到江南向陶弘景學習“服氣法”。⑨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43頁。清代俞樾也指出:“陶隱居《百一方》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10](清)俞樾撰,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續鈔》卷二一《百一方》,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61頁。可見,道教醫學與佛教醫學確有借用對方理論和詞匯的情況。陳兵指出:“佛學在哲理和觀法上深化了老莊學說,六朝隋唐時期,許多道教養生家兼通佛學;道教仙學對佛教禪學也有不小影響,南北朝時期,佛教禪僧學行道教養生術甚多。”[11]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420頁。由此推斷,無論從內涵的相似性,還是佛道互參的文化背景來看,譯經者在翻譯印度佛教中的特有概念時,很可能借用了道家意旨和詞匯。“明醫”應源自古代醫學文獻,并隨著道家養生論述流傳下來,在南北朝佛道互參的文化背景下,譯經者解讀佛經時盡量尋找本土的類似概念,因而,借用養生論述中“明”醫的意涵對譯佛經中的相關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六朝隋唐時期,“明醫”僅出現在宗教典籍中,幾乎未見以此指稱世俗醫者的用法。馬堪溫認為:“唐代以前,尚未出現醫生這個社會職業階層。”①馬堪溫:《歷史上的醫生》,《中華醫史雜志》,1986年第1期。這是一個解釋的角度。或如陶弘景所論,現實社會中鮮見宗教典籍描述的圣賢醫者。到宋代,以“明醫”指稱醫者的用法偶見于士大夫的著述中。陸佃對《鹖冠子》“(扁鵲)中兄治病,其在毫毛”的注解是,“此明醫也,治之于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②(宋)陸佃:《鹖冠子解》卷下《世賢》,《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4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237-238頁。周行己為王良弼的母親毛氏作墓志銘寫道:“夫人之疾,其初甚微,雖明醫不能察。”③(宋)周行己:《浮沚集》卷七《王君夫人毛氏墓志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3冊,第668頁上。這是兩則宗教典籍以外的記載,不過,從“明醫”一詞的內涵來看,仍然延續著早期道家論述的原意。
三、“明醫”內涵的轉變
宋代以后,士大夫的著作對“明醫”有了較多提及,使其內涵逐漸發生變化。南宋陳宓記錄安溪縣成立惠民局時寫道:“嘉定庚午冬,始為和劑局于中門之內,招明醫一人,躬診視……。”④(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九《安溪縣惠民局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31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頁上。陳宓稱地方醫藥機構征召的醫師為“明醫”,表明“明醫”已較普遍地指稱現實社會中醫術高明的醫者。這里使用“明醫”而非“名醫”,也有特別用意。宋代史籍對官方差遣或征召的醫者多稱“名醫”,《續資治通鑒長編》:“京師大疫,貧民為庸醫所誤者甚眾,其令翰林醫官院選名醫,于散藥處參問疾狀而給之”;⑤(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一,仁宗嘉祐五年,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622頁。《朝野類要》:“國醫,此名醫中選差,充診御脈,內宿祗應,此是翰林金紫醫官。”⑥(宋)趙昇撰:《朝野類要》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頁。醫官雖不入流,但職位是判斷名望高低的標準之一,不同職銜的官醫所診視的病人身份亦有差別,歐陽修在描述其求醫感觸時就曾寫道:“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然,請他不得。”⑦(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書簡》卷六《與梅圣俞慶歷初》,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1284頁。可見,陳宓使用“明醫”一詞,言外之意是,不重名望,只求醫療技術水平較高的醫者。
除此之外,真正使“明醫”內涵逐漸豐富,使用漸趨廣泛的推動力是醫學自身的演變。金朝成無己撰《傷寒明理論》,嚴器之為該書作序:“余嘗思歷代明醫,回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圣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序文還提到“聊攝成公,家世儒醫。”⑧(金)成無己撰述,(明)吳學勉校閱:《傷寒明理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這個說法已隱約顯現出醫者對儒家的攀引。⑨杜正勝指出,直到北宋,儒者仍多以鉆研六經之旨、文章之事為畢生志業,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之書,秦越人、淳于意、皇甫謐、張機之論則罕有學習。而到明清時期,葛洪、孫思邈的醫方在專業醫家看來,已不合《本草》、《傷寒》的繩墨,醫者對儒家的攀引則顯而易見。參閱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并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第6卷1期,1995年。“儒醫”之稱一方面反映了棄儒從醫者希望保持原有社會聲望的心態,[10]余新忠:《“良醫良相”說源流考論——兼論宋至清醫生的社會地位》,《天津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另一方面也強調依賴書本知識的醫學傳承方式對醫者評價標準的影響。宋代以后,醫學學術傳統“儒學化”的趨勢日益顯現,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以《內經》、《傷寒論》為經典的醫學知識譜系和理論脈絡的確立。[11]李建民稱為“正典化”,指出中國醫學是以文本為核心的正典醫學,《內經》、《傷寒論》是中國醫學的宗祧所在,參閱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頁。醫者提高醫術水平的途徑,不是簡單地背記驗方,而是更為重視研讀醫經和提高理論修養。元代揭傒斯的文集中有一則記載就很典型:
安成有士而隱于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國亡科舉廢,……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12](元)揭傒斯撰,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卷七《奔清甫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頁。
士人的棄儒從醫,推動了經典醫學知識的傳承,《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作為原理性醫學論著,成為醫者接受學術訓練的必讀書目。而另外一些僅閱讀入門書或背記湯頭歌訣的醫者,則被視為缺乏學術訓練。①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頁。醫者所閱讀醫學著作呈現出的“層級性”,②祝平一指出,醫學文本的層級性,即以古代醫經為核心,圍繞這個核心既有對各種醫經的注釋,也包括從醫經衍生出來的文本,而文本的層次關系造成醫者的社會區隔和階層化,參閱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3分,2006年9月。反過來影響了醫者分類和評價標準。
明代醫家徐春甫從技藝精粗的角度指出:“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于醫者曰明醫”;還認為,世人心目中的時醫、福醫、名醫,其實多為不讀醫經、不明脈理的醫者。③(明)徐春甫,余瀛鰲等編選:《古今醫統大全精華本》,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龔信闡述“明醫”的行醫之道為:“心存仁義,博覽群書,精通道藝;洞曉陰陽,明知運氣;藥辨溫涼,脈分表里;治用補瀉,病審虛實;因病制方,對證投劑;妙法在心,活變不滯;不炫虛名,惟期博濟;不計其功,不謀其利。”④(明)龔信纂輯、龔廷賢續編,王立等校注:《古今醫鑒》卷一六《明醫箴》,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472頁。龔信指出“明醫”應研讀醫經,精通脈理;既不膠柱鼓瑟,亦不自負奇功,是奉行經權之道且名實相符的專業醫家。不過,他對“庸醫”的理解卻不同于一般認識,指出“庸醫”并非沒有知識、不讀書的醫者,反而是憑借知識和經驗炫耀醫術者。⑤(明)龔信纂輯、龔廷賢續編,王立等校注:《古今醫鑒》卷一六《庸醫箴》,第471-472頁。可見,身為御醫,龔信對醫者的分類偏重于道德上的評判,認為醫者的道德和學術修養相當重要,甚至決定著技術水平。這完全是以“儒醫”為標準,來制定優秀醫生的行醫準則。由此也可以發現,“儒醫”逐漸取代“明醫”在醫家統緒中的榜樣地位,而“明醫”則更多地指稱精通醫理且醫療技術高超的專業醫家。
這里還須特別指出,醫學文本的撰著者出于構建各自學術源流的需要,對同一位醫家的歸類亦有不同。李梴《醫學入門》將歷代醫家分為上古圣賢、儒醫、明醫、世醫、德醫、仙禪道術六類,“儒醫”一類中多為兼具儒者身份或政治地位較高的醫家,“明醫”一類中則多是在醫理研究上有所建樹的醫家。⑥(明)李梴,田代華等點校:《醫學入門》,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3頁。值得一提的是,李梴將張元素列入儒醫類,除了從身份類型角度考慮之外,還與他對醫學傳統的定義有關。通過祝平一的研究可以發現,李梴《醫學入門》意在構建以李湯卿為宗的醫學道統,而儒醫類中所列醫家,無疑是道統中的核心人物,這也是他為何將“法宗劉河間”的張從正改置于“明醫”之列的原因。⑦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3分,2006年9月。與李梴的歸類不同,李時珍則稱張元素、李杲師徒為“明醫”,他在梳理歷代諸家本草的基礎上,構建出上自《神農本草經》,下至《本草綱目》的藥物學理論脈絡,其中,張元素所撰《珍珠囊》亦占有一席之地。⑧(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序例》卷一《歷代諸家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9頁。這表明,李時珍推崇東垣學派,不只是對學問、技藝、聲望、道德的籠統認識,而是對其診治策略和方法的認同。
醫家關于何謂“明醫”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這正是學術復古之風漸起之時。⑨謝觀著,余永燕點校:《中國醫學源流論》,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因此,晚明以降,不僅著名醫家注重對《內經》、《傷寒論》等古代醫學經典的研究和闡發,[10]“金元四大家”理論上均本于《內經》,各承一旨,加以闡發;明代醫學在學說上的分異也是“金元四家”門戶之分的余波。參閱嚴世蕓主編:《中醫學術發展史》,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55頁;劉伯驥:《中國醫學史》下冊,華岡出版部1974年版,第490頁。提倡在祖述經典的基礎上立方、用藥,社會觀念亦體現出對這一傾向的回應。明代孔貞時就曾指出:“‘名醫’不少,‘明醫’少,‘名醫’而‘明醫’則尤少,名不有其名,而明不恃其明尤少之少”,原因在于,診治方法多元化造成醫家各明其家,因此,要真正成為精通醫理的“明醫”,必須秉承醫經之旨,在此基礎上選擇對應病癥的診治策略和方法。[11](明)孔貞時:《在魯齋文集》卷三《許培元〈傷寒論祖〉序》,《四庫禁毀書叢刊》第16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頁。
清代顏元的論述也很典型,他指出:“《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制藥、針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制藥、針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①(清)顏元撰,王星賢等點校:《顏元集·存學編》卷一《學辯》,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0頁。顏元意在批評理學教育,但恰可由此反觀當時社會對“明醫”的一般認識。時人觀念中,醫者“學問精”比“技藝精”更能獲得較高評價。至此可以發現,正是由于“儒醫”這個稱號的出現,“明醫”的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開始更多地指稱在醫學理論研究上頗有建樹的專業醫家。金朝成無己所撰《傷寒明理論》,是較早體現出“明醫”概念脫離宗教傳統,開始尋求儒家認同的醫學文獻。
綜上,“明醫”在歷史上的涵義,遠較我們現在的理解更為豐富。古代醫學文獻中的明醫并非一般的知識階層,而是探究身體與疾病本源,且注重內心修養的圣賢。南北朝佛道互參的文化背景下,佛經翻譯者借取養生論中“明”醫的意涵對譯印度佛教中的相關概念,以“明醫”譬喻佛陀,強調佛陀對人心智的啟發。宋至明清,隨著社會文化變遷,“明醫”的內涵也發生了很大轉變,更多地指稱精通醫理的專業醫家。不僅如此,“明醫”在醫家統緒中的榜樣地位也為“儒醫”所取代,漸漸成為對醫者職業水平的評價。“明醫”之稱的實質是評價標準,反映了古代社會對醫者乃至整個醫學體系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