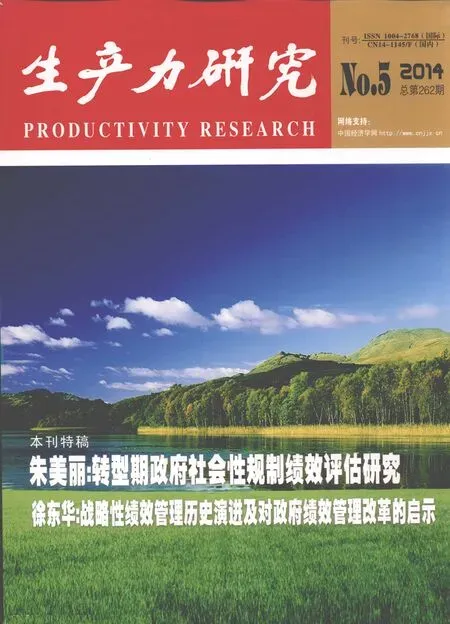BOT投資立法現狀的法律問題分析
楊帆
(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伴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經營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基礎建設經營項目采用BOT方式開始運營。因此,我們應該從思想上掌握有關BOT投資方式法律知識,為進一步推進BOT投資方式順利開展而營造法律環境。
一、BOT投資方式的概念
BOT即建設——經營——轉讓,是私人參與一國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的一種方式。BOT具體內容是指:國外公司或企業遵循特許協議,其負責籌資和建設歸屬于東道國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主要包含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電廠、地下通道、電站、高速公路、港口碼頭、鐵路、飛機場等);待到建設竣工完成BOT項目之后,在規定的特許期限范圍內,投資方的效益主要是依靠擁有、運營和維護此項基礎設施建設從中獲取使用費或管理費、維護費以此回籠投資并且可以獲得合法利益;待其特許權期限到期后,東道國政府將收回該項目設施的所有權。
二、BOT的法律特征
BOT投資方式的“新”在于它既是投資方式又是融資方式。其中投資性質沒有融資性質明顯。BOT投資方式成為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方式,是集融、投資——建設——經營——轉讓,為一體的系統工程,區別與以往的其他融投資方式。
(一)BOT投資方式的核心問題是東道國政府的特許
BOT投資方式是一項重大的、關乎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公共基礎性項目,通常包含能源、交通、資源、環保、土地、通訊等。基于特許協議的約定,外國投資者才能夠通過BOT方式進入東道國基礎設施領域,假如東道國政府未特許,外國私人投資者就不能進入這些公共部門壟斷專營的行業的。
項目公司的設立及其權利義務的確定都以政府特許為前提,項目財產權的形成必須以東道國政府的特許權為中介,項目經營期滿,項目財產必須無償地移交給東道國政府,是專屬于東道國的某種權利有條件地讓渡給BOT項目公司經營。因此,BOT項目財產權始終受東道國政府的制約。
(二)BOT項目工程主體的多元性與特殊性
BOT投資是涉及公眾利益的大規模的系統工程。其主體的多元性在于牽涉很多相互之間需要良好協調與合作的主體,且多個主體有可能跨越不同國境。主要有:東道國政府、外國的項目投資人、金融機構、保險公司、承建公司、機器租賃公司、設計公司、原材料供應商、項目經營管理公司等等。對于其主體的特殊性表現在:在眾多的主體當中,最主要兩個特殊的當事人的就是東道國政府和項目工程公司,東道國政府具有項目工程招標身份,項目工程公司是投資方。其實東道國政府在整個項目招標實施過程中,既扮演項目工程的招標人角色又扮演監督者和特許專營期滿后的項目工程的所有人;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項目工程公司也扮演多重身份,即作為項目工程的投資人又是項目工程的建設者,在特許的經營期范圍內是具有項目財產的所有權人,并且待特許經營期結束時項目工程公司有作為移交人,東道國政府將擁有項目工程的所有權。
(三)特許權期限屆滿時,東道國政府享有無償收回項目的權利
外國投資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經營管理方式,在項目規定的特許范圍之內,收回自己的投資成本,并且在特許范圍后期歸還銀行的貸款,實現獲取自己的利潤,待特許期滿后,BOT項目結束時,可以不進行相應的清算,東道國政府將有權收回項目,東道國政府將擁有由外國投資者運營到期的基礎設施的所有權。BOT投資方式就是利用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促進東道國本國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也就是在短期內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經營和所有權讓渡給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從而待特許期滿后,東道國政府將擁有新建基礎設施長久所有權。
(四)法律關系的復雜性
BOT投資方式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投資模式,其內容涵蓋了建設、經營、投資、融資、轉讓等多項活動,參與人與當事人具有明顯的多元化和特殊性,所以由其構成的法律關系也呈現復雜化。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項復雜的合同安排,通過合同來確定下來各方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義務關系。貸款協議、建設合同、特許協議、經營管理合同、回購協議和和股東協議構成了這些合同的主要部分。
三、我國有關BOT方式的立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BOT方式的立法現狀
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統一的BOT的專門立法,跟BOT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尚且不夠完善,穩定性相當差并且位階低。有些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協調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所以,在BOT運作實施過程中,必須要要顧忌到不斷變化的政策法規所帶來的法規風險。
1.有關B OT投資方式的中央政府部門相關的規范性文件。由中央政府部門制定關于在實踐中指導外商投資BOT相關規范性文件是在1995年頒布的,分別有《關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經貿部《通知》)和《關于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以上通知分別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與國家計委、交通部、電力部頒發,目的是指導和規范外商投資。同時,為輔以外商投資BOT項目的試點工作,2002年2月21日我國政府公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和分別在1995年和1997年下發的《關于境內機構進行項目融資有關事宜的通知》和《境外進行項目融資管理暫行辦法》,其均是國家層面上的,分別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和國家計委、國家外匯管理局頒發。其中規定有關BOT項目在內項目融題等問題。這些規定主要強調了政府的優先權、審批程序、項目規模、投資方的安全性以及各方利益和外匯管理等問題。
另外,《能源供應和消費的規定》、《關于借用長期國外貸款實行總量控制下的全口徑管理的范圍和辦法》、《電力法》、《關于外商投資電廠建設的暫行規定》、《外匯控制規定》等這些都是與BOT方式相關的法律。《民法通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各方出資若干規定》、《關于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注冊資本與投資總額比例的暫行規定》、《擔保法》、《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等規定同樣適用于BOT項目實施的過程。
總而言之,我國關于BOT方式的法律體系基本是由上面闡述的規定通知構成,這些通知規定從很大程度上指導推動我國BOT項目正常健康運作,但是細究起來,上述規章效力層次還比較低,只是一些原則性的規定,沒有可操作性,所以不同的地方政府在項目實施建設中會受到法律層面的限制,這些都會影響到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
2.地方立法性文件。我國許多省和市政府結合自身實際特點,制定了一些的地方性法規或規章,主要是為了解決關BOT特許經營過程中的可操作性問題。大多是特指某一項目,比如在1994年,由上海市頒發了《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此辦法是對延安東路隧道項目建設進行可操作性的規范。這是也我國具有針對性關于BOT方面第一個地方立法性文件。
關于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實施辦法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實施辦法分別在深圳、北京、成都、濟南、天津、邯鄲、合肥、貴州、東莞、濰坊、武漢等省、市地方政府出臺,這些規定頒發與中央部門規范有重復的地方,但是這些辦法比較詳細的規定了監管事項、價格因素等可操作的事項。
(二)現行BOT立法存在的問題
1.中央政府部門相關的規范性文件
(1)BOT投資適用主體范圍過窄。BOT方式一方面包含引進國外投資者投資方式的國際BOT方式,另一方面包含國內吸收國內投資者投資的BOT方式。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通常情況下BOT方式是引進國外資本的方式,在我國也有很多的民營企業經濟實力比較雄厚,也有可能承擔BOT項目。例如在1996年,刺桐大橋工程的建設項目就采用BOT方式由泉州市民營企業名流實業有限公司承擔,所以,應該刻不容緩的對國內的BOT方式予以規定。
(2)兩《通知》的內容存在一定沖突和矛盾。在BOT方式中,兩《通知》在關于項目所有權轉移問題具有一定的分歧,聯合《通知》第2條明確指出,凡是在特許期內項目的所有權歸屬于項目公司,很明顯將BOT看作為BOOT(BOOT:即建設——擁有——運營——移交,這個規定對BOT方式的所有權進一步明確,也就是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既有經營權又有所有權)模式,并且將轉移項目所有權被認為BOT方式中所包含。但是外經貿部的《通知》狹義認為BOT方式是“建設—運營—轉讓”的狹義模式,很明顯是承認在BOT方式中不應包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
又例如,兩《通知》在擔保問題上的觀點也是不一樣的,聯合《通知》明確指出:項目公司償還貸款本金、利息和紅利匯出等方面,國家保證其外匯能兌換和匯出境外,可是經貿部的《通知》第三條則指出:一般政府機構不會擔保或承諾項目作任何形式,其中也包含了外匯兌換擔保”,兩部規章內部上是存在一定的分歧和矛盾,這些分歧必然會影響實踐的進行,也會對BOT方式在我國的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
(3)法律位階太低,都屬于第四層立法。兩通知都是由國家政府機構制定,這些政府機構均隸屬于國務院下屬的部委。對BOT方式來說,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并且涉及面相當廣泛,是一種新興的國際投資模式,所以部委發布通知的形式盡管規范但很不權威。法律環境被認為是投資環境的重要構成因素,外商也是通過這些法律來判斷東道國政治風險,BOT方式需要消耗相當大的資本,因此法律環境相當重要。法律環境對BOT項目進行統一管理也有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國局部地區項目建設跟現行法律法規和規章產生了較大分歧,所以,應該用國家法律的形式來規范這些問題。
(4)立法操作性不強。兩個《通知》均為涉及到比如特許協議的法律性質、特許協議的形式、特許協議與其他合同的關系等內容,缺乏實際操作性,只是對BOT項目公司的設立方式、項目審批程序以及政府保證等問題作了原則性規定。
2.地方規范
從內容的規范程度上來看,在稱呼名稱命名上不太規范,《深圳市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條例》稱為撤銷其特許經營權,而《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將其命名為收回特許經營權。撤銷與收回表面看相差不大。好像撤銷與收回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處分行為。
四、結論
BOT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國際投資方式,總之,對投資者和東道國來說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雙贏的投資方式,即解決了本國政府無法經營諸如資金缺乏,費用成本高、建設難度大、技術要求高的基礎設施工程項目的問題,又能為那些經濟實力雄厚,技術力量高的國家對外進行資本和技術輸送提供了更大的機會,然而,因為BOT投資模式運行時間比較短,缺乏相關經驗,不同國家沒有統一完善的立法,特別是在我國尚未有關于BOT的專門立法,根據在BOT實踐中所產生的相關問題,所以構建相關法律尤為迫切,盡早盡快制定出一部完善的、可操作性強的、能夠對BOT投資實踐起積極指導作用的BOT法律或法規,實現BOT項目發展的合理化、合法化。
[1]姚梅鎮.國際投資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2]余勁松.國際投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于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BOT)與行政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孫潮,沈偉.BOT投資方式在我國的適用沖突及法律分析[J].中國法學,1997(1).
[5]蔡奕.BOT投資方式的若干法律問題探[J].現代法學,2000(12).
[6]曹軍,朱國祥.BOT政府保證的法律分析[J].中國律師,2002(10).[7]劉炳君.BOT投資方式的法律特征及其立法完善[J].法學論壇,2003(3).
[8]張國平.我國BOT投資制度設計中的若干問題[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4).
[9]杜宇.中國將開放公共交通市場,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投資[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1102/02442085731.shtml.
[10]瞿昕.我國BOT方式立法研究[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6).
[11]繩麗娜.論政府在BOT項目中的法律角色[J].地質技術經濟管理,2004(5).
[12]吳明龍.BOT特許協議的性質與我國BOT的立法現狀[J].法制與社會會,2006(11).
[13]劉寧.論行政合同中的行政優益權[J].法制與社會,2007(1).
[14]李冬曉,張健華.我國BOT項目融資的立法思考[J].理論界,2007(10).
[15]郭佳寧.BOT核心法律問題研究[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