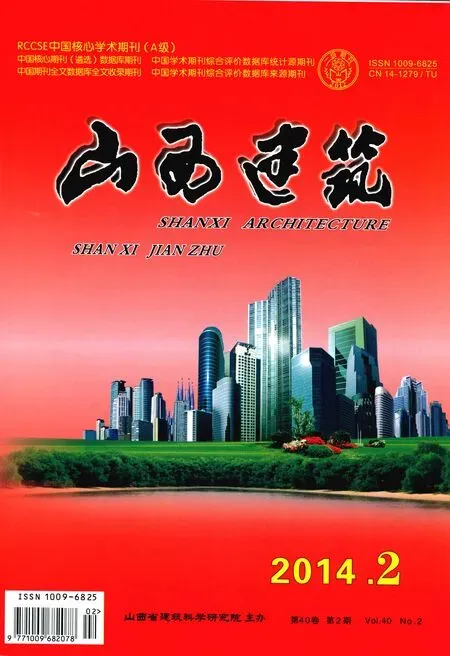建筑用磚源流考★
高 正
(1.信陽師范學院美術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2.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1 磚的起源
現今,在建筑的營造中,磚主要被用于建造墻面,那么,這些磚是怎么產生的,要解開其起源,還得先從地面談起。穴居和巢居為中國建筑的兩大起源。穴居,發端于黃河流域,后來發展成為木骨泥墻式建筑。木骨泥墻是先搭好木架,然后以泥填充,在泥里面常常拌以植物莖葉,以增強抗拉性能。在地面的處理上,常常是以草拌泥摻合紅膠泥鋪設,然后再進行燒烤,燒烤的目的是為了使其變得堅硬,燒烤后的地面被稱為紅燒土地面。1977年,在河南密縣莪溝裴李崗文化遺址,發現了6座新石器時代的半地穴式建筑。穴底地面上鋪墊著一層2 cm~6 cm厚的灰白色墊土,加工成平整光滑的堅實居住面[1]。甘肅永靖馬家灣新石器時代遺址居住面鋪有一層用草拌泥摻合一種紅膠泥的硬面,質地堅硬,表面平整。有些房子的地面經過燒烤呈紅褐色,使居住面顯得更加堅固而光潔[2]。有的建筑還在紅燒土地面上涂抹以白石灰,顯得整潔美觀。棗陽市鹿頭鎮北部雕龍牌遺址建筑室內地面修筑得非常平整堅硬。底層是墊基的紅燒土塊,上面用加工過的含有石灰成分的青灰色細泥涂抹三層,每層厚2 cm~4 cm。最上一層則為厚二三厘米的石灰面[1]。但是,紅燒土地面的處理方式是對地面進行整體焙燒,經驗告訴我們,這樣必然會使地面產生很多不規則的裂縫。而在地面上劃上格子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在河南新鄭倉城戰國遺址中,就發現一種紅燒土地面,它即是先將泥土平鋪以后,然后在平鋪泥土上劃一些不太整齊的方格,再焙燒而成。對于木構建筑來說,防火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紅燒土地面是以火焙燒地面,故易引起火災。這就要求必須先處理完地面后才能蓋房子,這對于建筑的施工是極不方便的。同時,紅燒土的火候較低,耐磨性能差。這就啟發著先民能不能把地面劃的格子,單獨焙燒,然后再拼砌在一起,于是,一個偉大的發明——磚就出現了。故“我國古代建筑上用磚,最早是出現在鋪地工程上。磚鋪地面的出現,很可能是受到紅燒土地面的啟發”[3]。
2 異形磚
也許是受紅燒土地面啟發而發明磚的緣故,早期的磚,主要用于鋪地。《詩·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堂有甓”,中堂是廟內的正路,甓指的即是鋪地磚。《考工記》中也有“堂涂十有二分”的記載,東漢末鄭玄對這句話的解釋是“若今令甓裓也”,“裓”指堂前的道路,“令甓裓”者,就是用磚鋪成的道路。但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的磚的實物還只是西周晚期的。陜西扶風縣云塘張家村出土了西周時期的磚,長36 cm、寬25 cm、厚2.5 cm,背面四角各有高2 cm的乳釘狀陶榫,陶榫主要為了防止滑動[4]。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的遺址中,也發現過構造原理相似的鋪地磚,表面有米字紋、繩紋、幾何形紋等。這些磚均把底面設計成乳突或凸棱,其目的均是讓磚能嵌緊于泥土底層。但是,隨著地面墊泥層慢慢干燥,鋪地磚仍會翹起來,地面又會變得不平整。
中國建筑很早就發明了榫卯結構,解決了木構框架的接合問題,浙江河姆渡就發現了我國迄今最早的建筑榫卯構件。那么,是否可以像建筑一樣,利用榫卯結構來解決磚與磚結合,先民這樣想過,也這樣做過。在秦咸陽宮遺址中,挖掘出一種截面為鋸齒形的平行線紋磚,磚大50 cm×33 cm×5 cm,邊寬1.7 cm,厚2.5 cm,磚的兩長邊,有子母榫相接[5]。但是,這種磚鋪砌起來要求磚的外輪廓要十分規整,故其邊緣常常需要打磨光滑。在望都一號漢墓中,用扇形磚鋪地[6],也同樣有使磚互相咬結的道理。這些磚在鋪砌時,一正一反,弧線相接嚴密,應是經過磨制的。這樣的磚雖然都進一步解決了地面平整的問題,但是制作和鋪砌起來都很復雜,特別是對磚的外輪廓要求特別高,而經過高溫燒造的磚,很難保證不會變形,故這些異型磚慢慢的被淘汰了。
3 磚的定型化和規格化
異型磚漸被淘汰,代之的是條磚和方磚,這個轉變發生在漢代,因為漢代解決了磚的定型化和規格化問題。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統一了貨幣、文字、度量衡。度、量、衡分別是用來測定長度、容量和重量的。度量衡的統一,奠定了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計量器具統一的基礎。漢代進一步發展了秦的計量制度。王莽時期設計一種銅方升,還制作了一種銅制游卡尺,用來進行精密器物的加工,表明當時的手工業已達到十分精細的程度。特別是西漢末年,劉歆將秦漢度量衡制度整理成文,使之更加規范化,條理化,后被班固收入《漢書·律歷志》,成為我國最早的度量衡專著。計量系統的完備化,為器物設計的規格化、系列化打下了基礎。河南澠池縣出土了漢魏時期大量窖藏鐵制工具,其中的六角軸承,其徑長從6.5 cm~15.5 cm之間,有17種規格,相鄰兩種規格的徑長相差均為0.5 cm,可見其規范化程度。
漢代的條磚也是這樣,孫機先生根據對漢代條磚的統計表明:至西漢中期,條磚已形成大小兩種類型:大型條磚長約40 cm,寬約20 cm,厚約10 cm;小型條磚長約25 cm,寬約12 cm,厚約6 cm。它們的長、寬、厚之比都接近4∶2∶1,即為整數倍,又是等比級數。條磚規格的定型化,為條磚排列組合創造了前提,漢代條磚的排列方法主要有橫排通縫、人字紋、橫直相間、大人字紋、橫直雙行通縫等排列方式。特別是人字紋排法,約出現于王莽時期,因其排列組合方式能使磚與磚之間緊密結合,不易松動,且施工方便,在東漢時已得到迅速推廣,且一直沿用至今。故孫機先生說:“條磚規格的定型化,是漢代制磚業的重要成就,從而為砌縫的合理化和墻體的整體化奠定了技術基礎[7]”。同時,條磚規格的定型化,也為磚的批量化生產奠定了基礎。當時,專業制磚的工匠稱作“甓師”。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中的磚窯,按當時的技術水平估算,每年約可生產條磚60多萬塊[3]。但條磚在漢代主要是被用來建造墓室。這可能與漢代墓室的設計也有一定的關系。“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書之哉”[8],這段話是《禮記》中對墓葬的文獻定義。文中所描述的為槨墓,槨墓的主體即為棺和套于棺之外的槨,一般埋于一條豎穴的底部,即所謂“葬也者,藏也”,故在考古文獻中稱為“豎穴墓”。豎穴墓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開始,持續使用了大約兩千年。直至西漢初期,以大型墓為代表,傳統槨墓形制經過三階段發展變化,最終完成,定型于橫穴式墓。之后將近一百年內,室墓又面向漢帝國領域各大地區推廣和普及[9]。室墓的建造,是漢代“事死如事生”觀念的反映,它的建造比棺槨墓要復雜得多,對磚的要求也更高,而漢代磚的規格化、定型化,恰恰使室墓的建造成為了可能。
4 磚在建筑領域的發展及應用
1)漢代的室墓采用條磚進行建造,這勢必也啟發著人們把條磚運用到地上建筑上來。這樣的嘗試首先始于魏晉時期的宗教建筑。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磚構式塔。除了塔剎部分用石雕以外,其他部分全部用灰黃色的磚砌成,標志著磚結構建筑技術的巨大進步。塔高約39.5 m,底層直徑約10.6 m,內部空間直徑約5 m,壁體厚2.5 m。此塔為我國現存唯一的十二邊形平面的塔。在塔身中部,用挑出的磚疊澀將塔身劃分為上下兩段,而上段建于疊澀上,比下段稍大。在四個正面有貫通上下兩段的門,門上在半圓形拱券上做成尖形券面裝飾。下段其余八面都是光素的磚面。塔身以上,用疊澀做成15層密接的塔檐。根據各層塔身殘存的白灰面,可知此塔外部色彩原為白色。之后,磚塔的營造技術不斷進步。從現存實物看,魏晉至初唐為磚塔發展的早期,代表作是西安大雁塔。五代、兩宋時期,為磚塔發展的盛期,塔的形式多樣、造型優美,磚作技術的提高使磚塔的高度相應增高,河北定縣開元寺塔,建于北宋皇佑四年,高84 m,是中國現存最高的磚塔。南宋以后進入晚期。但明代雖屬晚期,塔從結構技術方面看又有新發展,南京報恩寺塔建于明初永樂十年至宣德六年間,塔高三十二丈四尺九寸四分,按明營造尺計算已達102 m,按塔身與塔剎的比例,磚砌體高度約達90 m以上,磚身用多種彩色琉璃體砌面,可惜在19世紀50年代毀于戰火中。
至于條磚為什么這么遲才被用于地面建筑上來,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古代建筑的夯筑技術和木構框架技術已很成熟,對于砌磚墻承重的要求并不迫切,這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建筑中條磚的使用和制磚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即使擁有先進的磚造建筑技術,其進一步運用和發展也不是容易的。漢代室墓雖已創造了發券和穹窿頂結構,但是在魏晉建造佛塔的時候卻并沒有運用這些技術來解決塔內的樓層問題。而且魏晉時期,造磚的主要目的似乎不是主要服務于佛塔的建造,而還是墓室的建造。《晉書·孝友·吳逵傳》卷八十八載:“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
2)隨著磚在墓葬建筑和佛教建筑中的應用,對磚的認識逐步提高,一些較大的城市如江夏、成都、蘇州、福州等地在隋唐時期相繼開始用磚甃城。唐寶歷中,牛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筑之費,歲十余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筑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10],牛僧孺以磚筑城,提高了城墻質量。高駢,字千里,幽州人,“南詔蠻寇巂州,渡滬肆掠。乃以駢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磚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云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11],高駢同樣也是以磚砌城,使之堅固。宋代延續了唐代以磚砌城的方式。這在《營造法式》中,有著詳細的記載,當時的城墻用磚主要有三種:走趄磚、趄條磚和牛頭磚。走趄磚是一種側面有收分的磚;趄條磚是丁面有收分的磚;牛頭磚是楔形磚。走趄磚用于順砌磚,趄條磚用于丁砌磚,牛頭磚可能是用來砌城門的平口券的。對于這三種磚的使用方法,《營造法式(第三卷)·壕寨制度·城》載:“筑城之制,每高四十尺,則厚加高二十尺;其上斜收減高之半。”而且,在“卷第十五·窯作”中還列有用于臺基周邊的壓闌磚、比其他磚厚將近一倍的方形磚錠和帶有“系”的鎮子磚。關于鎮子磚,據“卷二十五·諸作功限二·窯作”中“粘鎮子磚系”的記載推測,鎮子磚可能是用在磚砌壁面內部,鎮子磚上的“系”可能是用來綁扎鋪在土墻內的竹網等拉結物,這樣做使磚壁面和土墻連接更好,整體性更強。
3)把條磚大量運用到宮殿式建筑上來,是到了明代,這種建筑被稱作無梁殿,是因其全部用磚砌成,無傳統木構建筑之梁架形式,故以無梁殿稱之。中國現存的無梁殿主要有明洪武年間修造的南京靈谷寺無梁殿、明代萬歷年間修造的蘇州開元寺無梁殿、無錫市保安寺無梁殿、山西五臺山顯通寺無梁殿、句容市隆昌寺無梁殿。滁州市瑯琊寺無梁殿,年代不詳,據明萬歷年間《滁陽志》載:“玉皇殿在城西南十裏瑯琊山,不知何年建,梁柱皆以磚石為之,規制巍然,為諸殿冠,”說明其年代應早于萬歷年間。至于為什么要建造無梁殿,估計應是對建筑永久性的要求,因為無梁殿主要是用來存放皇室的檔案文件及佛教經書,如蘇州開元寺無梁殿就是藏經書之用的,原為木構,經火焚燒后才改為磚構的無梁殿。但最能代表明代制磚業成就的是宮殿建筑的鋪地磚。明人張問之于嘉靖甲午年著述的《造磚圖說》記載:“自明永樂中,始造磚於蘇州,責其役於長洲窯戶六十三家。磚長二尺二寸,徑一尺七寸。”其土取自蘇州城東北陸墓所產乾黃作金銀色者,“掘而運,運而曬,曬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篩,凡七轉而后得土。復澄以三級之池,濾以三重之羅,筑地以晾之,布瓦以晞之,勒以鐵弦,踏以人足,凡六轉而后成泥”。對于其制作工藝,“揉以手,承以托版,砑以石輪,椎以木掌,避風避日,置之陰室,而日日輕筑之。閱八月而后成坯。其入窯也,防驟火激烈,先以穅草薰一月,乃以片柴燒一月,又以棵柴燒一月,又以松枝柴燒四十日,凡百三十日而后窨水出窯”[12]。由此可以看出,其燒造需經過選泥、制作磚坯、熏燒、運輸、砍磨、鋪墁等復雜細致的工序,故叩之聲震而清。但是其費不貲,“窯戶有不勝其累而自殺者”,連宣德皇帝也感慨:“陶甓非易事”,故這樣的磚有“一兩黃金一塊磚”的說法,這種磚也被后人稱為“金磚”。同時,《造磚圖說》還記載了在嘉靖中營建宮殿,即是由蘇州陸墓供磚的,“凡需磚五萬,而造至三年有馀乃成”。《明史·食貨志·燒制》也記載:“嘉靖十六年(1537年),作七陵,造內殿、醮壇”“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磚廠”。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也記載了蘇州燒造供皇宮正殿用的細料方磚。明正德宰相王鏊主修的《姑蘇志》“窯作”中也記載:“出齊門陸墓(土質)堅細異他處,工部興作多于此燒造”。修建于明清兩代的故宮,即用這種顆粒細膩、質地密實、斷之無孔、敲之有聲的金磚墁地的。根據現存的金磚實物測量表明,明代金磚的規格大多為長度66 cm、寬66 cm、厚8 cm;清代規格大多為長72 cm,寬72 cm、厚10 cm;同時,乾隆年間生產了一種小規格的金磚,長55 cm、寬55 cm、厚8 cm,金磚的規格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的形式。
4)在宮殿建筑鋪設方磚的形式,并非明代才出現,至遲在漢代已經出現。漢代的鋪地方磚分為兩類:一類用于鋪砌室外的散水或露道;另一類用于鋪砌室內的地面。鋪砌室外散水或露道的磚,是卵石紋方磚,它可能是對商周以來用卵石砌筑散水形式的模仿。鋪砌室內地面用的方磚,常常模印以精美的花紋,以幾何紋樣為主,且不同地區風格各異,如漢長安城出土的鋪地花磚,其紋樣有回紋、菱格紋、網格紋、方格紋等,漢魏洛陽城南郊禮制性建筑遺址出土的鋪地花磚,磚面主要為“五”字紋和直線紋相間的紋樣;在廣州南越國官署遺址出土的鋪地花磚,其紋樣主要為耳杯形菱格紋和菱格紋間飾實心凸菱塊。公元前634年開始建造的大明宮,位于長安城外東北的龍首原上。在唐大明宮含元殿、麟德殿、含光殿、興慶宮、太液池及其附近廊院區域、龍尾道等遺址及一些磚瓦窯址均出土了大量的鋪地方磚。這些方磚大多模印或刻劃有精美的紋樣。主要有蓮花紋、蔓草紋、四葉紋、團花紋、梭身合暈紋、瑞獸植物紋等。其中尤以蓮花紋樣最為豐富,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據花蕊之不同就可分為7型,每1型又可分為3式~12式。關于方磚的用法,從現有的考古發掘情況來看,大明宮三清殿基臺高10余米,西側慢道長40余米,坡度約為1∶3,上面滿鋪海獸葡萄紋磚[13];驪山華清宮湯池大殿北面慢道,坡度亦近1∶3,用蓮花磚鋪裝[14]。故一些專家推斷當時宮中路面,平直處用素面方磚,斜坡、踏道、階級處便用花磚以防滑。現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復原也基本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相關文獻記載,唐代也有在殿內鋪地中鑲嵌花磚以標示人員站位的做法[15,16]。唐代的一些重要的宗教建筑,其地面也采用花紋方磚鋪地,現存世界最早的版畫——中國唐代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為我們呈現出地面滿鋪花紋磚后輝煌美妙的效果,從圖像上看,磚面花紋為四葉紋。在敦煌莫高窟的窟前殿堂遺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鋪地花磚方磚,主要有大八瓣蓮花紋、寶相四瓣花紋、聯珠復瓣蓮花紋、石松紋、桃心十二卷瓣蓮花紋等。同時,敦煌地區的隋唐墓葬也出土了大量的模印花磚,紋樣主要有九格柿蒂紋、寶相四瓣花紋、寶相如意紋、聯珠復瓣蓮花紋、四分之一蓮花紋、卷草蓮花紋、寶相卷草紋、寶珠卷草紋、繩紋、編織紋等[17],尺寸大多為34 cm×34 cm ×6.5 cm。
宋元時期,在敦煌的壁畫和石窟中繼續使用鋪地花紋方磚,磚面花紋出現了火焰寶珠紋、繩結紋等新的紋樣題材,尤以火焰寶珠紋為特色,圖案格局常為左右對稱式。唐代熱衷表現的蓮花紋樣也有所發展,如幾何形尖角蓮和卷瓣蓮,變得更加新穎耐看。同時,在一些重要的官署建筑,也繼續采用花磚鋪地,杭州發掘的南宋臨安府衙署建筑遺址,其正廳地面滿鋪“變形寶相花”花紋方磚[18]。《營造法式》卷二十五“磚作功限”條記,殿堂地面磚上雕鑿成斗八圖案。這種斗八圖案通過卷二十九“石作”中對殿內斗八圖樣的描繪可見其樣式。明代仍有少量建筑的廳堂采用花紋磚鋪地,從明代的少量插圖、繪畫作品中可以看到,紋樣比較單一、一般為八瓣的小花紋,地面與墻的交界處有時以幾何紋作邊飾處理。從總體上看,從宋代開始,鋪地磚從對原來紋樣的關注,轉變為對磚作技術的革新上。花紋方磚使用越來越少、紋樣也越來越簡單,同時,素面方磚的制作技術卻越來越高。
到了民國時期,鋪地磚在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這便是以瓷器花磚和釉面磚代替了陶器花磚。南京總統府建筑地面、上海外灘重要建筑的地面、浙江海寧徐志摩故居地面,都以花磚拼砌成精美的圖案,且很多圖案都是把外來的圖案與中國固有的傳統圖案相結合,具有中西合璧的特點。
時至今日,我們居住的建筑中還是主要采用方磚鋪地,公共建筑的大堂還常常采用拼花的形式。建筑的墻面還采用條磚砌筑。而這正是先輩世世代代艱辛探索的結果。
[1]史仲文.中國藝術史·建筑雕塑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9.
[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馬家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J].考古,1975(2):31-35.
[3]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180,254.
[4]羅西章.扶風云塘發現西周磚[J].考古與文物,1980(2):66.
[5]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筑遺址簡報[J].北京:文物,1976(11):12.
[6]楊 泓.望都一、二號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7]孫 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3.
[8][清]阮 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0:1292.
[9]黃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2003:130.
[10][后晉]劉 昫.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二·牛僧孺[M].北京:中華書局,1975:4470.
[11][后晉]劉 昫.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三十二·高駢[M].北京:中華書局,1975:4703.
[12]四庫全書總目[Z].史部·政書類存目二.
[13]馬德志.唐長安城發掘新收獲[J].考古,1987(4):78.
[14]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湯池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J].文物,1990(5):39.
[15]李 肇.唐國史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6]葛 洪.西京雜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殷光明.敦煌模印花磚藝術初探[J].敦煌學輯刊,1988(1,2):128.
[18]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南宋臨安府衙署遺址[J].文物,2002(1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