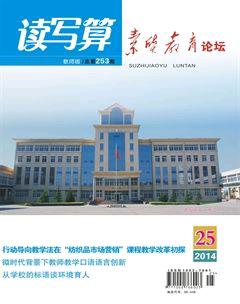中國傳統美學元素在文學翻譯中的運用
摘 要 縱觀中國悠久的翻譯歷史,不難發現眾多翻譯泰斗在各自譯論多有提及美和翻譯的結合,翻譯中更應該把美當做最高的追求。這樣的現象與中國傳統的哲學基礎和國人的審美傾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在研究翻譯理論的同時若能深入透徹地挖掘這些美學因素,不僅可以在理論上推進翻譯學的發展,更可以在實踐中指導翻譯創作,為文壇增添更多傳世譯作。
關鍵詞 中國傳統;美學;文學翻譯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對美的追求在中國由來已久,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美”字。先秦時期的孔子、孟子、莊子、老子等從不同角度討論美,先后闡發了“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充實之為美”(《孟子·盡心下》),“美者自美。”(《莊子·山木》)等美學思想。人類求美的共性延伸到語言中也要求語言表達美、形象美、朦朧美和幽默美等。中國悠悠數千年的歲月中,儒家、道家和佛家對什么是美各有建樹,對傳統譯論的塑造都功不可沒。三家的美學思想各有長短,然在文學翻譯的不同層面中均有體現。
一、儒家美學思想在翻譯中的運用
1.以“情”為美
中國古代美學中以“情”為美的思想大多得到儒家的肯定。《荀子·王霸》中指出:“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意思就是情是客觀存在,不可主觀地去除。表明了儒家對情欲的肯定和理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把“情”和“美”統一起來,明確提出:“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文學之美源自于深厚自然的真情流露,而不是感情空洞的辭藻堆砌。
2.以“和”為美
“和”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根基,這么說一點都不夸張。以“和”為美的思想最早出現在《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體現的是儒家提倡禮教,以禮來維系社會的和諧與安寧。
翻譯涉及兩種語言,因此翻譯中有兩個審美客體:原文和譯文。兩個審美在翻譯中地位不同,譯文依照原文傳遞美,原文是譯文產生和創造美的來源和框架。只有原文本身具備美才能為譯文傳遞和創造美奠定基礎、提供條件。原文的審美構成是構成作品特色的審美要素,按其性質可以分為形式美和內容美。原文的形式美表現在語言形式上,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包括音美(頭韻,腹韻,尾韻,擬聲),結構美(平行,反復,聯珠,回文,突降,倒裝);原文的內容美首先應從詞說起,詞是篇章最小的語義單位,它構成句子再由句子構成語篇。篇章內容美的升華起于詞義美。詞義美包括比喻、借代、擬人、夸張、委婉語、矛盾修辭和雙關等。著名翻譯家許淵沖關于原文和譯文美的的和諧有過這樣的見解:“信”或忠實的譯文能使人“知之”;“信達”的譯文能使人“好之”;“信達雅”的譯文才能使人“樂之”。換句話說,“意似”相當于“知之”;“意美”相當于“好之”;“神似”或“三美”才相當于“樂之”。也就是說譯文在傳遞原文形式美和內容美時,在保證內容美得到充分傳遞的時應保留原文形式美,從而降低原文美在譯文中的損耗,達到和原文的統一和諧,這樣的譯文才是完美的選擇。
以“和”為美的觀念在翻譯審美中,指引譯者尋求原文美和譯文美的契合,在眾多的實現手段中作出取舍,選擇最佳方式去發揮原文在結構,音韻,意象和主題思想的美。對于讀者也有一定的牽引意義,即使讀者在接觸不到原文的情況下,仍然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對譯文的選詞、行文等作出評判,然后傾向于能夠為自己產生深刻印象,即美的體驗的作品。譯者要贏得讀者的認可和歡迎,不得不在這一點上花足功夫。
二、道家美學思想在翻譯中的運用:“自然”為美
“自然”之美是道家“無為”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美學范疇,它的主要涵義是“自己如此的”,“無意識的”。“自然”作為美學范疇最早由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的眼中,“自然”是“道”生萬物的基礎。莊子在繼承老子的前提下,又將自然美上升為“既雕既琢,復歸于樸”的返璞歸真思想。
翻譯中的“自然”之美其實也受到很多翻譯家的肯定,在主張意譯和重視譯文文采的譯論中屢見不鮮。鳩摩羅什在我國佛經翻譯史上地位極高,所譯經文也得到后世極高的評價。他也是在中國譯論史上最早提出如何表現原文的文體與語趣的重要問題,宋僧贊寧說:“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馬建忠主張翻譯者應當“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再此基礎上“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領神悟,振筆而書。”“能使閱讀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兩年后,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開宗明義提出“譯事三難”。他認為翻譯首先應該求信,但是如果不達就等于沒譯。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音、形、語法、修辭、文化背景和美感經驗上迥然有別,康有為指出:“凡譯書者,將使人深知其義,茍其意靡失,雖取其文而刪增之,顛倒之未為害也”。最理想的翻譯是既保存原文的內容美,又不失其形式美。退而求其次,如果內容美和形式美有沖突,只好徑達原意,用流暢而自然的語言再現原文的風姿和神韻。否則就會流于硬譯、死譯,譯文中到處充斥“翻譯腔”。
三、佛家美學思想在文學翻譯中的運用:“寂滅”為美
譯者作為翻譯審美中的主體,不同于作者可以天馬行空任意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在翻譯活動的開始就肩負著雙重任務:既要對原文的審美信息進行解碼,又要對譯文編碼。這兩個活動的進行都是以原文作為基礎,原文對譯者的客觀束縛貫穿翻譯活動的始末。有人將翻譯形象地比喻成“帶著鐐銬跳舞”,原文的種種限制不僅使譯者受盡折磨,加之語言承載的文化影響,譯文的意思傳達的飽滿度也受到折損。羅新璋先生就曾感嘆道:“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里,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挫傷。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確實,由于國與國之間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差異的客觀存在,翻譯中存在一定意義上的不可譯現象,包括:endprint
(1)語言文字本身成為敘述的對象。
(2)在文字游戲中,語言文字的形式特點起主要作用。除非巧合,不然一般不可譯。
這樣看來,譯文在傳達原文的意思上,損耗是在所難免的,但并不是說不可以彌補和挽救的。前蘇聯現實主義翻譯家卡什金說得好:“富于創造性的翻譯,才算得上是崇高的藝術。”“然而,翻譯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必須接受原作的約束,否則就不成其為翻譯,而成了隨心所欲、自由發揮了。當然,譯者理應享有一定的自由,即有根據的自由。”為了盡量減低譯作的損耗程度,要把翻譯當做是一種創作,以創作之力來彌補缺失。原作通過譯者的創造在另外一種語言中重生,像鳳凰涅槃后的新生。“涅槃”是佛家思想,指的是“寂滅”“圓寂”。佛家以“寂滅”為美,佛陀用詩一樣的語言來贊頌死亡之美:
我們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暫,
看著眾生的生死就像看著舞步,
生命時光就像空中閃電,
就像激流沖下山脊,匆匆滑逝。
在平常人眼中,死亡時讓人害怕的,恐怖的。怎么佛家會這樣贊揚死亡(涅槃)呢?(1)死是生之痛苦的結束。佛教的“四圣諦”即“苦、集、滅、道”揭示了人生的痛苦真諦,人要擺脫這些痛苦,最好是“不生”。這一點和翻譯有幾點相似,譯者必須忍受其“折磨”,苦苦尋思,反復推敲。而最后的解脫辦法是在譯文中使原文脫胎換骨,獲得美的最大化。(2)死是新生的開始。佛家認為,人的生命不只一次,而是無限的循環。肉體可以衰老腐朽,但靈魂則是永恒不滅。翻譯不也是如此嗎?原文從一種語言進入到另一種語言,它所依附的語言必將死亡,而在譯者的富有創造力的筆下作者思想以另一種形式獲得新生。
四、總結
真是“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在向先祖的“問美”過程中才了解到:中國恢弘的翻譯史竟和傳統美學有如此深的淵源,中國翻譯事業歷久彌新的秘密原來是在對美孜孜不倦地追求中獲得的。同時還啟示當代的翻譯工作者們,中國的翻譯事業要獲得大的發展,須得繼承先輩未盡的事業,在翻譯中實踐美、創造美,追求美,讓美的譯文千古流芳。
參考文獻:
[1]毛榮貴.翻譯美學[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2]祁志祥.中國美學原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3]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作者簡介:胡青松(1980-),男,陜西安康人,安康學院外語系教師,翻譯碩士,主要從事翻譯與英語教學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