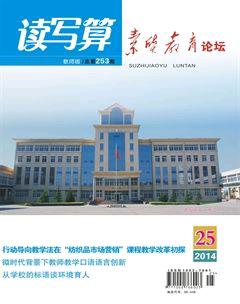仲冬的思念
胡賢均
今年秋季開學,因工作需要,我離開了奮戰多年的三尺講臺,走上了教研工作崗位。一個周末的的晚上十一時許,我剛走進臥室,家里的座機電話響了,我連忙起身去接(從臥室到客廳的間隔里,我在想:這么晚了,是誰的電話?住在外地的老人生病了嗎?)電話,當我急切的拿起話筒,耳邊傳來的是稚嫩而熟悉地聲音:“老師,您好!我是韓小明,打擾您了,我有一道幾何題不會做,又要請教您了。”我連忙說:“沒事,把題目告訴我吧。”接下來的半個多小時的通話里,我們沉靜在解題的討論中。
回到臥室,我半躺在床上,心里難以平靜。看看床頭上的臺歷,心中一陣感慨:離開學校之前,我教初二的孩子們的數學課,并兼任他們的班主任。又有三個多月沒有見到班上的孩子們了,真想他們啦!過去與孩子們一起學習、活動和歡聚的場景,一幕一幕地浮現在眼前……
我思念,課堂上每一個孩子在學習的不同階段留在我的腦海的眼神。當我提出一個有挑戰性的問題,讓同學們思考后回答時,有的孩子眼睛里充滿疑惑的眼神;有的孩子像是有了答案,但又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確時,所表現出來的忐忑的眼神;有的孩子像是早就知道我要提出這個自己會回答的問題,信心十足地等待著我請他回答時,所表現出的自豪的眼神。我熟悉孩子們的這些眼神,也是有備而來的回應著他們的眼神:時而走到他們面前,給予適當提示或分析;時而鼓勵他們向全班同學說出自己的想法;時而我和班上的一員交換位置,他(或她)站在講臺上,層次清楚地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大家聽。這時,我又看到了:有的孩子恍然大悟的眼神;有的孩子找回了自信的眼神;有的孩子幸福的眼神。
我思念,和孩子們在校園的林蔭道上交心的畫面。印象深刻地就是前面提到的,打電話問數學題的那個韓小明同學。那是這些孩子上初一約一個月的時候,一天下午課外活動時間,小明約我來到校園的林蔭道的較為僻靜的地方,急切地對我說:“老師,我覺得我們班里的大多數同學,已經是‘不可救藥了,你說咋辦吶?”聽了他的話,我雖然有些吃驚,但并沒有在臉上表現出來,而是走上前去,摸摸他的頭后慢慢地說:“小明,先別急,說說具體情況。”說話間,小明從口袋里拿出來一個小本子遞給我看,上面詳細的記載了,每節課班上同學違反課堂紀律,下課后一些同學的不文明舉止等等情況。小明見我看得很認真,又說:“我是班里的紀律委員,一個星期之內,必須杜絕這些現象的發生。”說到這里,我的腦海里閃現出一個人(剛剛走上講臺的我),眼前的小明不就是當年的我嘛!接下來,我就把自己管理學生時,經常與孩子們做朋友、嚴寬適度等心得告訴了他。邊走邊談中,我見小明頻頻的點頭,就順勢問道:“小明啊,你有信心和老師一起把我們班上的同學帶好嗎?”小明并沒有馬上回答(我心想:怎么,小明還有思想顧慮),而是轉過身去,“啪”的給我敬了個隊禮,我連忙還了不正規的禮,此時,我們倆都笑了。
我思念,與孩子們一起參加運動會日子。孩子們舉著“為班級爭光”的牌子,踏著整齊有力的步伐,唱著蓬勃向上的班歌通過運動會的主席臺。我拿著相機,記錄下運動場上孩子們你追我趕、奮力沖刺的精彩瞬間,還抓拍到了同學們快樂地戲嘻的畫面。那次,全班同學的集體留影,成為我的《同學影集》的最后一張,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張。
我思念,由孩子們自己確定主題的班會。依照多年和孩子們打交道的經驗,每接一屆新同學,我都要先向同學們敞開心扉,要求孩子們要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當他們在管理的路上行進到確實需要幫助時,老師就是他們的“拐杖”、“靠山”。從班會中走出的一個個:“紀律標兵”、“衛生標兵”、“學習標兵”、“體育健將”、“街舞兄弟”、“小歌手”、“知心哥哥”、“愛心妹妹”,都是形成良好班風的“帶路人”。有段時間,音樂老師病了。我就把自己填詞的一首《我是柳中好學生》教給同學們唱。下課后,一群孩子圍著我說:“老師,我們評你為班里的‘老歌手,你同意嗎?”我說:“好哇!不過我還要努力呀!”
離開同學們的幾個月里,許多孩子給我寫信,猶如春風細雨滋潤著我的心田,讓我重溫了那段難以忘懷地師生情。秦芳芳同學來信中的那段話,道出了我此時心聲:燕子去了,有再飛回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