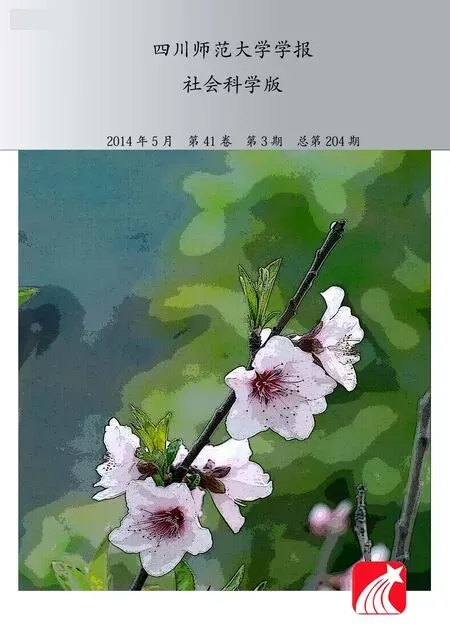笛卡爾的空間觀念及其現代意義
(四川師范大學 政治教育學院 成都 610066)
“空間”既是哲學論題又是科學論題。從古希臘開始,哲人們就對空間進行了探討。原子論提出了“虛空”,以其作為“原子”存在和運動的場所。亞里士多德認為所謂的“虛空”根本不存在,他主張空間是物體存在和運動的場所,他甚至提出了“共有空間”和“特有空間”。笛卡爾的空間觀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空間觀,他也根本否認“虛空”存在。下面,我們將詳細論述笛卡爾的空間觀點及其現代意義。
一 笛卡爾的空間觀點
與對“時間”的態度不同①,笛卡爾從各個方面詳細地論述過“空間”。笛卡爾涉及空間的領域非常廣泛。作為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笛卡爾都涉及到空間。就空間科學而言,笛卡爾創立了解析幾何學,突破了歐幾里德幾何學的限制,對現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物理學方面,笛卡爾用坐標幾何學研究光學,提出了物質運動的相對性原理;在天文學領域,他用慣性理論與漩渦論來解釋宇宙間天地運動的成因。
在哲學上,笛卡爾討論空間是因為有廣延的實體。他說:“具有長、寬、高的廣延構成了有形實體的本質,思想構成了能思實體的本質。”[1]LIII廣延(空間的一部分)是有形實體的本質,所以研究空間是為了研究廣延即物體的本質。物質的事物是指有廣延的實體或形體及其性質,它包含了體積,長、寬、高三維,形相,運動,位置,部分的可分割性等。但是,在這多種性質中,笛卡爾認為只有長、寬、高三維是最重要的:“長、寬、高的廣延構成了有形實體的本性。……凡能歸屬于物體的任何其他東西,皆以廣延為前提,而且只是有廣延的事物的某種樣式(mode)。”[1]LIII
在《哲學原理》的第二部“物質事物的原理”中,笛卡爾詳細論述了“空間”。他首先在第四節繼續強調,物體的本性不在于重量、硬度、顏色等,而只在于廣延。然后,他分析了兩種先入為主的意見即“稀化”(rarefaction)和“虛空”(vacuum),認為它們使關于物體本性的真理不能彰顯。先說“稀化”。一種流行意見認為,大多數物體是可以稀化或壓縮的,稀化后物體的廣延比壓縮的物體的廣延要大。笛卡爾反駁了這種觀點,他認為,所謂“稀化的物體”就是其各部分之間有許多間距,而其中充滿了別的物體;反之,“壓縮的物體”則是指各部分之間的間距較小。不過,物體稀化以后,盡管包含了較大的空間,可是它的廣延并沒有增大。因為,我們不能把它在稀化時各部分所不占的空隙或間距的廣延歸于它,只應把那些空隙的廣延歸于充滿這些空隙的別的物體[1]VI。笛卡爾的意思是,原有的物體占有自己的廣延,你把這個物體稀釋后,它的廣延并不增加。比如,你把一個黃豆用水泡漲,黃豆原來的廣延并沒有增加,因為增加的是水,水也有自己的廣延。這樣一說,似乎有道理。但是,我們反過來想,問題就出現了。我現在把這顆黃豆壓縮,變成像一粒米那么大,這顆黃豆的廣延改變了嗎?按笛卡爾的觀點,應該沒有,因為一個物體無論稀化或壓縮都不改變它的廣延。顯然,笛卡爾在這里隱含了一個前提:一個物體的通常情況(自然狀態)下的廣延是它的“標準廣延”。所以,通常情況下的一個干黃豆的廣延就是它的標準廣延,泡漲或壓縮后的黃豆都不能改變這一廣延。
在討論空間之前,笛卡爾討論了數量與有數量的事物、數目與被計數的事物的關系。他認為,這兩者是不能分離的,甚至是無分別的,它們的差別只存在于思想中。“只有在思想中,數量和數目才不同于有數量的事物和被計數的事物。因為數量之不同于有廣延的實體,數目之不同于被計數的東西,并不是在實在中而只是在思想中。”[1]VIII比如,在思想上我們可以考察一個10英尺空間所包含的一個物質實體的本性,而不必同時注意到10英尺的量度,因為那件東西不論在那個空間的一部分還是全體,其本性都是一樣的;同樣,我們也可以單獨設想10這個數目,以及10英尺長的一段連續的數量,而不必同時想到這個有限定的實體。但是,在實在方面,我們減少了數量或廣延部分,就減少了實體,而減少了實體就要減少相應的數量或廣延。顯然,笛卡爾認為,在客觀上數目或數量是不能獨立存在的。舉這樣一個例子,笛卡爾想要得出一個結論:“有形(corporeal)的實體,當與其數量區分開來時,就會混亂地被認為是無形(incorporeal)的東西。……當他們(笛卡爾批評的人——引者)把有形實體與廣延或數量區分開來時,他們或者用有形實體這個詞不指稱任何東西,或者在他們心中僅僅形成了一個混亂的無形實體的觀念,而將此觀念錯誤地歸于有形實體。”[1]IX笛卡爾強調的是,關于無形實體(比如心靈)的科學不能用數量來表達,數學在此領域無能為力②;而有形實體或物質是不能同數量分離的,這意味著所有關于物質的科學都是數量的科學,都能用數學來研究和表達。
我們下面來討論“空間”概念。
空間(space)或內部場所(internal place)是什么呢?空間或內部場所,同其中所含的有形實體,實際上并無差異,只在我們設想它們的方式(mode)上不同。因為事實上,同樣的長、寬、高的廣延,不但構成了空間,也構成了物體。它們之間的差異只在于,在物體中我們認為廣延是特殊的,并且設想它隨物體而變化。反之在空間中,我們把概括的統一體歸于廣延,所以,當從某一空間移走占據它的物體后,我們并不認為同時移走了那一空間的廣延。因為在我們看來,那一段廣延只要具有同一的體積和形相,只要同我們借以確定這個空間的四周的某些物體保持其相同的位置,則那段廣延仍是不變的。[1]X
在這段話里,笛卡爾的意思是明白的:“空間”或“內部場所”等于其中所含的有形實體(物體)的廣延,只是思考它們的方式不同;物體是特殊的廣延,空間是統一的廣延。
在接下來的幾節,他對這一基本觀點進行了論證。他重申,空間與有形實體實際上并無差異,同一廣延既構成物體的本性也構成空間的本性。他以石頭為例,認為我們可以排除其硬度、顏色、重量、冷熱等性質,排除這些東西之后,“物體觀念中沒有剩下別的東西,只剩下長、寬、高三向延伸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僅包含在充滿了物體的空間觀念中,甚至包含在被叫作虛空的空間觀念中”[1]XI。
在第12節,他論證在我們設想空間的方式中空間如何不同于物體。簡言之,實際的空間總是被物體(特殊的廣延)占據著,但是我們在思想上可以設想“一般廣延”(extension in general)或“一般空間”(笛卡爾本人沒有使用這個詞匯)。當某一空間中的物體(比如石頭)被移走以后,就留下了“一般廣延”或“一般空間”,它可以繼續由木頭、水、空氣或任何別的物體來占據。這樣說來,笛卡爾好像是在主張,特殊空間(具體空間)是客觀存在的,而“一般空間”只是人腦抽象的產物,是主觀的東西。但是,實際上,笛卡爾談的是具體空間的相互比較,由此而產生了“一般空間”,“一般空間”仍然是客觀存在的,盡管我們感知不到它而只能通過理性的抽象或思考來形成。
笛卡爾還考慮到了“參照系”的問題,他說,同一物體在同一時間既改變空間又不改變空間。比如,一艘航行于海上的船的船尾坐著一個人,如果從船的各部分看,這個人的空間(場所)沒有變化;但如果從岸上看,他的空間(場所)就變化了。
有意思的是,笛卡爾提出了“外部場所”(external place)的概念,這一概念會引來一些麻煩。他在第14節討論了空間與場所的差異。他說,“場所”較為明確地指位置(situation),很少指體積、形相,相反談到“空間”時,我們想到的是體積和形相。
接下來,他討論了“外部場所”、“內部場所”與空間的關系:
實際上,我們從來不把空間與長、寬、高的廣延區分開來。然而,我們有時認為場所在占據場所的事物以內,有時認為場所在該事物以外。內部場所與空間全無差異,而外部場所可以被認為是直接圍繞那個占場所的事物的表層(superficies)。應當說明的是,我們用的表層在這里不能理解為周圍物體的任何部分,只是圍繞物體和被圍繞物體之間的界限,而這一界限僅是一種樣式。[1]XV
這樣從邏輯上說,“場所”概念大于“空間”概念,場所分內與外,“內部場所”等于“空間”,“外部場所”就不在“空間”中。這與前面提出的“一般廣延”(“一般空間”)顯然是矛盾的。然而,事實上,“外部場所”的廣延與“內部場所”的廣延又沒有區別。一個石頭占據的“空間”是“內部場所”,而圍繞這個石頭的表層就是“外部場所”。“外部場所”實際上是一個物體的邊沿、兩個物體之間的界限,所以與“內部場所”的廣延相等。盡管內外場所的廣延相等,但“外部場所”作為邊界把一物與他物分開來。這樣,任何一物都有自己的內部場所(空間),又同他物區分開來,所以“一般廣延”(“一般空間”)仍然是成立的。笛卡爾關于“一般廣延”(“一般空間”)與“特殊廣延”(“特殊空間”)的觀點涉及到了空間的整體性與可分性問題。
由于笛卡爾持實在空間的立場,他批評了“虛空”的觀點:
要說有一個絕對無物體的虛空或空間,那是令理性反感的。說到哲學意義上的虛空,即其中沒有實體的空間,這種東西顯然不存在,因為空間的或內部場所的廣延與物體的廣延并無區別。既然我們只從物體有長、寬、高的廣延就有理由得出結論說,它是一個實體,那么,說無 (nothing)擁有廣延那是絕對矛盾的。[1]XVI
笛卡爾接著分析說,“虛空”一詞的通常用法并不排除一切物體。比如,熱水瓶里沒有水只有空氣時,我們說它是空的;魚池里沒有魚,盡管裝滿了水,我們說里面什么也沒有。同樣,當空間沒有包含可感知的事物時,我們也說空間是空虛的(void)。我們由這些通常的感覺形成了“虛空”的錯誤觀念。還有,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distance)只是廣延的一種樣式,不是空無一物的虛空,離開有廣延的實體,就沒有距離。
由否定“虛空”,笛卡爾繼而否定“原子”的存在。“我們還發現,根本不可能存在具有不可分本性的原子或物質的部分。因為不論我們假設這些部分是如何之小,它們既然必定是有廣延的,我們就總能夠在思想中把任何一部分分出兩個或較多的更小部分,并因此承認其可分性。”③[1]XX既然物質是無限可分的,那就沒有不可再分的“原子”。笛卡爾在那個時代根據其廣延理論就斷定了物質的無限可分性,這是了不起的。而且,更了不起的是,笛卡爾考慮到了實際分割物質的困難(技術瓶頸,尺度越小的物質越難分割),所以他說我們總能夠“在思想中”分割出更小的物質。
笛卡爾否認“原子”和“虛空”,顛覆了原子論的觀點,倒是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地點(空間)是包容物體的界限”。笛卡爾的“外部場所”不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容器”或“外包裝”嗎?笛卡爾的“一般空間”和“特殊空間”不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共有空間”與“特有空間”④嗎?
由無限多的、具體的物體的廣延,笛卡爾還得出了“世界的廣延是無限的(indefinite)”結論。“我們進而發現,世界或有形實體的全體(整體)是無限地伸展的,因為不論我們在何處設一界限,我們不僅仍然可以想象它之外的無限伸展的眾多空間,而且能感知到這些空間是真正可以想象的;換言之,它們實際上就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因此,它們所包含的有形實體也是無限伸展的”[1]XXI。物質空間是無限的,這是唯物論堅持的觀點。不僅如此,笛卡爾由此否定了亞里士多德的“天上的物質”與“地上的物質”有區別的結論,認為它們都是一樣的,并斷言“不可能存在多個世界”。
這是一個驚人的結論。笛卡爾相信,宇宙間所有的物體都是由同一種物質組成的,它們都是由有三維的廣延組成的,可以計算的,因此數學適用于整個宇宙。英國學者E.A.伯特對此有一段精彩的解讀:
他(指笛卡爾——引者)發覺,空間或廣延的本質是這樣的,以致于其關系不管多么復雜,總是可以用代數公式來表示,反過來,數量真理(在某些冪內)也可以完全在空間上加以表達。作為這個著名發明的一個并非不同尋常的結果,笛卡爾在心靈產生了這一希望:或許可以把整個物理學王國還原為純粹幾何特性。不論自然界會是什么別的樣子,它顯然是一個幾何世界,它的對象是在運動中出現和擴展的數量。如果我們能夠去掉所有其他特性,或者把它們還原為數量,那么明顯的是,數學必定是開啟自然真理的唯一合適的鑰匙。[2]92
這就是笛卡爾為什么那么重視數學的根本原因,原來物理世界都可以還原為幾何世界,都可以用算術和幾何學來處理。笛卡爾似乎認為自己發現了宇宙的真理。
二 笛卡爾“物質空間”的現代意義
笛卡爾之后、愛因斯坦之前,最有價值、影響最大的當屬牛頓的“絕對空間”觀點。
牛頓的物理學受到笛卡爾物理學的深刻影響。盡管笛卡爾本人沒有完成建立物理因果性的思想體系,以解釋物理世界的經驗內容,但是他的思想還是深深地影響了牛頓。這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機械論的總綱領,二是具體物理原理和問題,“特別是,慣性定律、碰撞問題的公式表示和動量守恒原理、圓周運動的解析法,是牛頓立志建立力學體系時,從笛卡爾那里繼承過來的三項主要成果”[3]126。
但是,與笛卡爾主張“實在空間”(或“有形體實體的空間”,或者直接說“物質空間”)相反,牛頓主張“空虛空間”或“絕對空間”。牛頓說:“絕對的空間,就其本性而言,是與外界任何事物無關而永遠是相同的和不動的”[4]8-9。絕對空間是空無一物的,它像一個無限大的箱子,它是均勻的、各向同性的。不難看出,牛頓繼承的是原子論的“虛空”觀點。
有意思的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時空觀點更多地受到笛卡爾的積極影響,而對牛頓的時空觀提出了批評。
愛因斯坦首先肯定了牛頓的“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實在性。在牛頓時空觀中,“不依賴于主觀認識的‘物理實在’是由空時(為一方)以及與空時作相對運動的永遠存在的質點(為另一方)所構成(至少在原則上是這樣)”[5]114。這說明牛頓的時空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時空。但是,隨后他就對牛頓時空觀的不足或缺陷提出了三點批評:第一,牛頓的時空觀是“關于空間和時間的獨立存在的觀念”,它把空間、時間與物質分割,認為空間和時間同物質一樣都是獨立的實在[5]550;第二,在牛頓那里,空間和時間是彼此分割、沒有聯系的;第三,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同物質的機械運動密切相關,是描述物體的機械運動的一種抽象的產物,“這種理論綱領本質上是原子論的和機械論的”[5]292-293。
比較而言,愛因斯坦則肯定了笛卡爾的空間觀點。他說:
笛卡兒曾大體上按照下述方式進行論證:空間與廣延性是同一的,而廣延性是與物體相聯系的;因此,沒有物體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亦即一無所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以后我們將會看到,廣義相對論繞了一個大彎仍舊證實了笛卡兒的概念。[6]65
在上文省略的部分,愛因斯坦批評笛卡爾把“廣延”局限于物體的觀點。愛因斯坦認為,場也是有廣延的。在笛卡爾的時代,“場”的概念還沒有提出。
一無所有的空間,亦即沒有場的空間,是不存在的。空時是不能獨立存在的,只能作為場的結構性質而存在。因此,笛卡兒認為一無所有的空間并不存在的見解與真理相去并不遠。如果僅僅從有形物體來理解物理實在,那么上述觀念看來的確是荒謬的。將場視為物理實在的表象的這種觀念,再把廣義相對性原理結合在一起,才能說明笛卡兒觀念的真義所在:“沒有場”的空間是不存在的。[6]76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以太”即“引力場”更接近笛卡爾的“有形實體的空間”或“物質空間”的思想。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以太”中, 物質和能量的分布決定空間的“彎曲”程度和分布。在廣義相對論中,電磁場是作為物質的一部分考慮的, 而引力場和空間是不可分割的, 引力是幾何空間的屬性[7]。而笛卡爾的“有形實體的空間”就是廣延,就是幾何空間。笛卡爾根據“物質空間”所提出的“宇宙模型”,可以說明太陽系的歷史演化和光線通過太陽附近時會發生彎曲, 這是接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
總之,笛卡爾的空間觀點雖然產生于牛頓之前,卻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空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注釋:
①笛卡爾對“時間”不大重視,很少論及,而且持一種輕蔑的態度。他把時間看成是一種主觀的東西,說:“我們可以在一個共同的尺度下來理解所有事物的綿延,我們就把它們的綿延與引起年和天的最大的、最規則的運動的綿延加以比較,而把它叫作時間。因此,我們如此命名的這種東西,不是額外添加在一般綿延上的東西,而只是一種思想方式。”(DESCARTES R. of the Priclples of Human Knowledge lvii.,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ohn Veitch.MeditationsandSelectionsfromthePrinciplesofPhilosophy:Descartes1596-1650.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64.)在笛卡爾看來,“時間”是我們比較“綿延”的產物,并不實際存在,只是我們的思想方式。
②應當說,笛卡爾知道數學的界限,后來的康德和黑格爾都繼承了這一思想。康德只在現象界強調數學的重要性,而在道德和宗教領域不再強調數學。黑格爾認為,數學只在低級事物中有其重要性,而在精神領域數學并不重要。
③莊子在《天下篇》中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講的是同樣的道理:有限與無限的統一。
④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徐開來譯,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頁)中說:“地點(空間)也是這樣,一種是一切物體都處于其中的共有地點(空間),另一種是每個物體最初直接所處的特有地點(空間)。”
參考文獻:
[1]DESCARTES R. of the Pri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C]//translated by John Veitch.MeditationsandSelectionsfromthePrinciplesofPhilosophy:Descartes1596-1650[M].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1964.
[2]E.A.伯特.近代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M].徐向東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4]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M].鄭太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5]許良英,范岱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6]愛因斯坦.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M].楊潤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7]殷業.牛頓絕對時空觀和愛因斯坦相對時空觀的統一[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