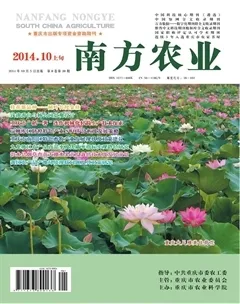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現狀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摘 要 隨著工農業的集約化發展,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造成農產品普遍污染,污染物通過食物鏈傳遞危害人體健康,同時也威脅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現存的產地環境標準覆蓋指標少,科學性及實用性不強,統一性差是造成農產品產地環境污染的原因之一。農業投入品管理技術落后,相關環境法規體系不完善、銜接性差導致產地環境污染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因此,加強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的科學研究,改革我國現行的標準的制定、審核及實施方式;建立農用化學投入品的科學施用與管理技術體系亦迫在眉睫;應完善現有的農產品產地安全相關的法規與政策,完善行政管理網絡,加強相關不同管理部門的溝通,從而在技術與管理兩方面確保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產地環境污染;農產品污染;環境質量標準;評價方法;法律法規;對策
中圖分類號:F3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90X(2014)28-068-05
知網出版網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86.S.20141113.1043.005.html 網絡出版時間:2014/11/13 10:40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然選擇。良好的產地環境是農產品安全生產的前提和基礎,產地環境的優劣直接影響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然而,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集約化的快速發展,工業污染日益嚴重,農藥、化肥等農業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導致農業產地環境污染愈演愈烈。本文從我國農產品污染的特征、農業產地環境現狀、國內產地環境質量標準及評價方法、存在的問題以及相應對策等方面,對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現狀進行初步分析。
1我國農產品污染的主要特征
我國不同類別農產品的污染特征不同[1],可歸納如下。
(1)農藥和重金屬是蔬菜、茶葉及糧食作物的主要污染物。其中,葉菜類易受農藥污染 (表1),如白菜、小白菜、萵筍葉、甘藍、芹菜、茼蒿等農藥檢出率普遍高;甘藍、小白菜、萵筍葉、芹菜等超標比例最大。蔬菜中超標的農藥品種主要為菊酯類、有機磷類和氨基甲酸酯類農藥,如氰戊菊酯、聯苯菊酯、氯氟氰菊酯、三唑磷、水胺硫磷、對硫磷、苯醚甲環唑、克百威、敵敵畏、毒死蜱、氟蟲腈、樂果等。鎘、鉛、汞、砷等是蔬菜中的主要重金屬污染物。茶葉中的主要污染物為鉛。受農藥污染的主要糧食品種是水稻,農藥品種主要為敵敵畏、氧化樂果、甲胺磷等有機磷農藥,此外水稻鎘污染嚴重(以重慶所產水稻為例,表2)。
(2)水果污染物主要為農藥和激素,品種類似于蔬菜。
(3)水產品污染物以漁藥及水環境中各類有害物質為主,檢出與超標的重金屬主要有汞、鎘、鉛等,檢出的違禁藥有氯霉素、紅霉素、硝基酚鈉等(表3)。
2我國農業產地環境質量現狀
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包括土壤、水、大氣的質量,是關系農產品安全的重要環境因素。農產品的污染特征在某種程度上標示著產地環境的污染程度,目前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日益惡化。
2.1土壤污染加劇
由于大氣污染顆粒的沉降及人類活動,如大量使有機肥料(近年來飼料添加劑中含有高量砷、銅等)和磷肥(磷礦石中含鎘等),使農田重金屬污染日益嚴重。有關部門于上世紀末對我國30萬hm2基本農田保護區土壤有害重金屬進行抽樣調查,結果表明,約有12.1%農田重金屬超標。重慶市農業土壤普遍受到重金屬污染且表現為加劇之勢,如城口、石柱農田土壤中的鎘含量均大于2.00 mg/kg,砷含量高達63.99 mg/kg,生產出來的大米重金屬含量普遍較高(見表3)。另據報道,作為全國重工業基地,沈陽市西部的張士灌區,鎘污染已有30多年的歷史,鎘含量高達2.96 mg/kg,該污灌區生產的稻米90%以上鎘含量超過國家衛生食品標準,已不適稻米生產。
除重金屬污染[2]外,土壤中有機物污染也日益嚴重,如農藥、多環芳烴、增塑劑、多氯聯苯等[3-5]化學農業投入品(如農藥、化肥)的不科學使用是我國農田污染的原因之一。我國農藥產量居世界前列,但利用率僅達到發達國家的60%~70%。研究結果表明,施用的農藥對農作物起保護作用的數量僅占使用量的10%~30%,剩余的70%~90%小部分進入大氣與水體,多數殘留于土壤,殘留農藥仍可通過微生物、植物根系及土壤動物的活動而釋放和遷移,從而污染土壤[6]。上世紀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國內土壤中多環芳烴(PAHs)污染已從μg/kg上升到mg/kg,檢出率也從小于20%上升到80%。農田土壤中的增塑劑鄰苯二甲酸酯類(PAEs)[7-8]、直鏈烷基苯磺酸鈉(LAS)污染[9-10]也較嚴重,致使土壤嚴重退化。另外,由于過量施用化肥,導致土壤酸化、硝酸鹽污染及土壤次生鹽漬化嚴重;我國每年農膜殘留量高達45萬t。農業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不僅導致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土壤環境質量每況愈下。
2.2灌溉水污染嚴重
灌溉水包括可用于灌溉的地表水、地下水和經過處理能達到使用標準的污水。然而,灌溉水源污染已成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據不完全調查,蘇、浙、滬的16個縣內井水硝態氮和亞硝態氮的超標率已分別達38.2%和57.9%。太湖流域80%河道遭受污染,60%河湖水質不符合飲用水標準[6],太湖流域地表水中氟化物含量高,地表水、灌溉水及地下水CODMn嚴重超標嚴重[11]。為充分利用水資源,城市污水的農業利用量不斷增加,但污水中的許多污染物在灌溉農作前尚未得到有效去除,致使土壤及農作物受到污染。此外,隨著我國養殖業的壯大,養殖戶在生產中濫用化學藥物,水體中化學藥物殘留量日益增加,危害水產品質量的同時,使人類的經濟收入及健康受到威脅。如,我國出口日本的鰻魚就曾因體內檢出禁用藥物超標而損失嚴重。
2.3大氣環境日益惡化
近年來,我國大氣污染呈現出煙煤污染與機動車污染共存的復合污染,顆粒物為主要污染物;光化學煙霧頻繁、二氧化氮濃度居高不下,酸沉降轉變為硫酸性與硝酸型的復合污染[12-13],大氣污染加劇導致農田土壤繼續酸化。城市大氣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等有害物質通過大氣已成為農田和農產品的污染源。大氣中有害氣體和物質與農作物接觸后,可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并改變其品質。據估計,大氣重金屬污染對影響城郊蔬菜重金屬污染的幾率高達10%,我國茶葉鉛超標也可能與大氣污染有關。
3我國產地環境質量的評價標準與評 價方法
3.1土壤環境標準
我國于1995年頒布了《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95),規定了8種重金屬(鎘、汞、砷、銅、鉛、鋅、鉻、鎳)和2種難降解農藥(六六六和滴滴涕)的限量值。隨著近年來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及無公害食品的發展,國內頒布了一系列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如:《農產品安全質量無公害蔬菜產地環境要求》(GB/T184071.1-2001)、《農產品安全質量無公害水果產地環境要求》(GB/T184072.-2001);農業部則頒布了具體無公害食品的系列行業標準,如《無公害食品蘋果產地環境條件》(NY5013-2001)等,這些標準均是依據《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95)制定。實踐已表明,這些標準與農產品安全生產的要求存在差距。
3.2農業灌溉水質量標準與地表水質量標準
我國現有的農業灌溉水質量標準(GB5084-92)于1992年批準發布,其中灌溉水質中主要污染物指標共17種,包括:汞、鎘、砷、六價鉻、鉛、銅、鋅等重金屬;氯化物、硫化物、氟化物和氰化物等無機鹽;石油類、揮發酚;苯和三氯乙醚等有機物;硼、硒等微量元素。2002年發布的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適合農業用水的Ⅴ類水質指標與農灌水水質指標基本一致。
3.3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我國有關環境空氣質量相關標準與要求,包括保護農作物大氣環境質量標準、環境空氣質量標準與綠色食品產地空氣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我國保護農作物的大氣污染物最高允許濃度標準是綜合考慮作物對二氧化硫和氟化物的耐受能力,以二氧化硫和氟化物對農作物生產力經濟性狀和葉片傷害而制定的。適用于農村地區各項污染物的濃度限值,包括二氧化硫總懸浮顆粒物(TSP)、PM10、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鉛、苯并[a]芘、氟化物等10個指標。綠色食品產地空氣污染物限量要求主要包括TS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物四個指標。
3.4產地環境評價方法
目前,根據不同對象,環境質量現狀評價方法不同。綠色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評價,通常采用單向污染指數法和綜合污染指數法等兩步評價法[14],一般以單項指數評價為主,以綜合指數評價為輔,而且應根據污染因子的毒理學特征和農作物吸收、富集能力分為兩類加以控制。在評價過程中,盡管某種環境污染物超標會造成危害,而平均值可能并不超標。因此,為了突出濃度最大污染物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解決平均值法存在的問題,水質土壤采用分指數平均值和最大值相結合的內梅羅指數法。空氣質量評價既采用空氣平均值法,又采用適當兼顧最大值的空氣質量指數法。
4存在的問題
4.1標準
自2000年以來,僅農業部頒布的產地環境類標準已超出30個,這些標準在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問題[15]。
(1)標準的制定倉促、不科學。制定者未意識到標準的技術法規屬性,制定標準的科學依據嚴重不足。多數產地環境標準是在資料查找及科學研究不充分情況下制定的,頒布前亦未能充分征求相關科研單位及生產單位的意見,加上時間倉促、經費少,一些低級錯誤出現在標準中。如《農產品安全質量蔬菜產地環境要求》(GB/T18407.1-2001)(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頒布),直接引用了國家環保部規定的過期氮氧化物指標及其標準值(《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但是,國家環保部于2000年發布文件《關于發布〈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修改單的通知》中取消了NOx指標,并把NO2標準值做了修改。即GB/T18407.1-2001是在未充分查找資料的情況下制定的。
(2)標準間的統一性差。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構成了我國標準體系,由于不同標準歸口不同的管理部門,標準值依據不統一,致使頒布出的標準相互間出現矛盾。如《農田灌溉水質標準》(GB5084-1992)規定灌溉水中鎘濃度限值為0.005 mg/L,而《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1985)則規定飲用水中鎘濃度限值為0.01 mg/L,即可直接飲用的水卻不能用于農田灌溉,這顯然不科學。此外,標準間統一性差。很多標準的適用范圍、主要內容基本相同,但個別指標卻又存在差異,導致標準的執行混亂不堪。如,目前適用蔬菜生產的產地環境標準至少有三大類:(1)《農產品安全質量蔬菜產地環境要求》(GB/T18407.1-2001),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頒布;(2)《無公害食品蔬菜產地環境條件》(NY5010-2002),由農業部頒布;(3)《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評價標準》,由國家環保總局頒布。正是由于這三類標準見的統一性較差,致使標準的執行者迷惘疑惑。
(3)標準的科學性及實用性不強。中國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關于重金屬的規定均為全量形式,但大量科學研究表明,土壤中只有有效態的污染元素才會對作物、人體和生態環境產生影響[16]。隨著現代化農業的發展,普遍采用塑料大棚或地膜生產農產品。已有調查結果表明,長三角及東莞地區頻頻農業土壤及農產品中增塑劑含量高[8, 17],但現有土壤質量標準對增塑劑類化合物未有任何的規定。現存的空氣質量標準與農用水質標準均存在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控制指標少的問題。如,現有的空氣質量標準缺乏農藥、二惡英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規定。還有,一些影響人體健康的稀土元素與持久性污染物已引起了全球學者的關注[3, 18],而且在制定土壤、水、大氣的質量標準時列入了限值范圍,但在中國尚未有此考慮。
4.2 法規體系問題
我國至今尚未構建完整的農產品產地安全法規體系[19]。由于現有的相關法規都有自己的立法宗旨和保護對象,關聯農產品產地保護的規定各有側重,造成產地保護對象凌亂不堪,也導致了產地保護司法的功能性偏差。尤其是產地環境,不僅包括土壤,也涉及地表水、灌溉水、大氣環境,但現有的法規體系不能全方位覆蓋上述領域。此外,法律法規、政策與規劃間缺乏相應的銜接;環境保護、農業、國土資源等部門管理職責間缺乏溝通,致使管理效率低下。此外,農業投入品是否科學管理、科學使用直接關系到產地環境的安全與否。然而,我國現行的《農產品產地安全管理方法》存在致命缺陷:產地安全管理的法律依據與執法主體也不明確,對農業投入品的行政管理部門的自身法律責任定位不明確,行政管理手段單一化,處罰手段過于依賴經濟處罰。
5對策建議
科學制定環境標準,改變我國現有的標準管理模式。標準的制定基于長期基礎研究的積累。如:(1)要改變目前《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中元素總量評定的缺陷,必須全面準確地調查全國土壤環境元素有效態背景值,研究不同區域不同類別土壤中重金屬的有效態;全面調查及深入研究土壤中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AHs、PCBs、PAEs等)。(2)要積極借鑒或引進國外先進標準。近些年,歐美發達國家頻頻提出某項安全限量標準設定技術壁壘,致使中國農產品在國際上形象不佳。與國外標準相比,我國在標準制定方面科學性明顯不足。因此,我們需要積極借鑒或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標準,健全中國農產品產地環境標準體系。(3)要改變現行的標準制定、審定及實施模式。不受所謂的制修訂計劃的限制,應需要及時組織制定和修訂標準;廣泛吸收和聽取研究者的意見與建議,保證標準的先進性、科學性與實用性;把強制性標準作為法律法規強制性執行,把非強制性標準作為行業協會的自律性標準實行。
建立農用化學品安全施用與管理的技術體系。我國人口龐大,耕地資源不足,決定了未來還必須依靠農用化學投入品(如化肥、農藥等)的實現農產品總量的增長,同時確保環境和農產品質量的安全。因此,一方面要調整農用化學投入品的生產結構,研發生產環境相容性好的農用化學投入品;加強農用化學投入品的綜合管理,如對農藥、化肥等生產、經營和使用的監督管理,指導生產者科學儲存及使用農藥、化肥等。另一方面要加強關于農業投入品使用對農業環境與農產品污染影響的研究,建立符合環境生態與農產品安全性要求的科學農業投入品使用技術及咨詢系統,建立健全農業投入品的使用對環境影響的監督與評價系統。
在法律法規方面:(1)完善現有農產品產地環境安全相關的法規與政策,構建完整的農產品產地環境的法規與政策體系,并注意法律法規間的協調。(2)明確責任主體。政府各部門企業個人應承擔的責任,應在相關法規中界定清晰。對于找不到污染主體的情況,應由政府主導及第三方參與下,根據法律規定確定治理主體。(3)完善行政管理網絡,解決部門間在體制和管理機制方面的協調問題。如由環保部牽頭界定產地環境質量的好壞與修復技術,農業部組織轉接根據土壤質量調整農作物結構,并進行統一監督管理。相關的基礎性調查、數據的共享、監測體系的建立要充分體現部門間的交流與合作。
參考文獻
[1]林玉鎖.土壤環境安全及其污染防治對策[J].環境保護,2007,(1A):35-38.
[2]韓春梅,王春山,鞏宗強,等.土壤中重金屬形態分析及其環境學意義[J].生態學雜志,2005.24(12):1499-1502.
[3]Jones KC,P DeVoogt.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state of the science[J].Environmental Pollution,1999,100(1):209-221.
[4]安瓊,董元華,王輝,等.長江三角洲典型地區農田土壤中多氯聯苯殘留狀況[J].環境科學,2006,27(3):528-532.
[5]馬萬里,齊虹,孫德智,哈爾濱市土壤中PCBs的污染現狀研究[J].環境保護科學,2008,34(2):67-69.
[6]楊肖娥,余劍東,倪吾鐘,等.農業環境質量與農產品安全[J].中國農業科技導報,2002,4(4):3-9.
[7]高庚申.環境介質中鄰苯二甲酸酯類環境激素的調查與評價[D].貴陽:貴州師范大學,2008.
[8]于立紅,于立河,王鵬.地膜中鄰苯二甲酸酯類化合物及重金屬對土壤-大豆的污染[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12,30(1):43-47.
[9]潘根興,韓永鏡.LAS對土壤環境理化性狀和生物活性的影響[J].環境科學,2001,22(1):57-61.
[10]潘根興,韓永鏡,諸清河.太湖地區土壤環境中LAS的分布和降解特點[J].應用生態學報,2002,13(2):171-174.
[11]沃飛,陳效民,吳華山,等.太湖地區農田水環境中氮和磷時空變異的研究[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7,15(6):30-34.
[12]郝吉明,程真,王書肖.我國大氣環境污染現狀及防治措施研究[J].環境保護,2012,9(1):17-20.
[13]平措.我國城市大氣污染現狀及綜合防治對策[J].環境科學與管理,2006,31(1):18-21.
[14]林玉鎖.農產品產地環境安全與污染控制[J].科技與經濟,2004,17(4):40-44.
[15]高懷友,劉鳳枝,趙玉杰.中國農產品產地環境標準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生態環境,2004,13(4):691-693.
[16]McLaughlin MJ,D Parker,J Clarke. Metals and micronutrients–food safety issues[J].Field crops research,1999,60(1):143-163.
[17]蔡全英,莫測輝,李云輝,等.廣州、深圳地區蔬菜生產基地土壤中鄰苯二甲酸酯(PAEs)研究[J].生態學報,2005,25(2):283-288.
[18]陳祖義,朱旭東.稀土元素的骨蓄積性、毒性及其對人群健康的潛在危害[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08,24(1):88-91.
[19]王學軍,龍文靜.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安全法規和政策的現狀與展望[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4,33(4):617-622.
(責任編輯:丁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