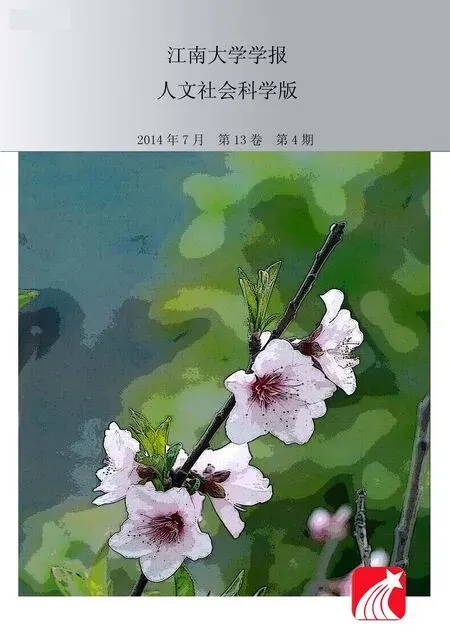明清時期社會治安的條令和鄉規民約
陳學文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7)
明清時期社會秩序、治安治理除了政府發布條令外,民間亦相應實施自治自律,以保證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他們采取集眾議決、歃血為盟,訂立鄉規民約(含族規族約),以規范或約束居民日常行動。這種鄉規民約帶有自律性,以填補政府條令和治理機制的空缺。這些鄉規民約的文本多分散在文集、族譜和日用類書中,整理、開發、利用雖是頗費精力而卻有意義的。
一、鄉規民約的制訂
鄉規民約亦稱地方契約,由村社或族眾經“置酒歃血預盟”的隆重儀式而制訂,慎重其事還須推出約正、族長、里老來監督執行。如廣東“鄉約之設,正仿古人閭師黨正之義。俾其宣化于鄉,以佐官司政刑之不逮。……鄉約者,所以約一鄉之人而歸于善也。……公舉一年高有德,孝悌力行之士,以為一都之約正。並擇一二老誠、端議正直之輩,以為之副。而后同鄉共井,仿呂氏鄉約之儀,始于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終于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之意。”[1]鄉規民約既具有自律性,又受道德倫理的制約,而背后還有官府的支持,如嚴重違約者將受到政府條令、法律的制裁。鄉規民約對于完善、健全村社的自治管理曾起到過良好的作用。各地鄉規民約略有不同,從實際出發,群策群力,制訂了切合地方需求的若干鄉規民約,概由民眾自我推行。
據明代日用類書記載,鄉規民約對地方農業生產作了約定,力保農作順利進行:
鄉約
“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民以食為天,食足則信孚。此農事至重,實王政之首務也。切照本鄉居民稠密,別無經營,惟資耕種,以充歲計。是以既殫東作,庶有以望西成,茲當禾苗盛長之時,不許縱放牛馬踐傷,鵝鴨啄食,各家務宜牢固關閘。爰自某月日會眾議約,以后倘有無籍著,不依鄉約,照例懲罰,如有抗拒不遵,定行呈首官府,眾共攻之,以一科十,縱律無正條,其情可惡,必敬必戒,故諭。”①余象斗纂:《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卷十七《民用門》。明萬歷已亥(二十七年)孟秋書林余文臺 ,43卷,上下二欄層刻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蓬左文庫亦有收藏,缺序。1993年我在東京大學、名古屋大學講學時之暇,曾至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查閱過此書,見該書蓬左藏本有“潭邑書林余文臺雙峰堂刊”,蓋有尾陽內庫印,寬永末年(1624——1643)買本。今收錄在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3—卷5,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1999)刊印。日本仁井田陞參校過這二種藏本,現是采用仁井田陞校勘本。
鄉約很強調民本思想,農事實為王政之首務,必須保證農事按季節播種收成,防止人為破壞,豐衣足食,民孚邦寧。鄉約是集眾商議而制訂,訂立之后,要求村民遵約,如違,損一罰十,還呈官府懲辦。
還有地方契約樣本,側重于地方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治理。
地方契約
“立禁約地方謀等,為嚴申大禁,以一風俗事。竊見鄉設禁條,原非私舉,事有明征,法無輕貸,豈強者依勢橫行,弱者緘口畏縮,或殉情以容隱,或貪和(私)以偏獲,卒至禁令敗壞,風俗益頹,人畜交相為害,不暇悉數。某等目擊斯禍,痛懲厥奸,為此置酒會立條,以儆后患。如有患(犯)者,與眾共罰,若有抗拒不服,會同呈官理論,但不許避嫌徇私,受錢賣放,又不得欺善畏惡,挾仇排陷,有一于此,天日鑒之,神雷擊之。凡我同盟,至公罔私,庶鄉鄰不至受害,而風俗自此淳厚矣。謹以各項禁條開具于后,故不虛立。”②醉云閣楊居理道卿父訂《新刻陸鯤庭先生纂輯云錦新聯》卷六。按:該書又稱《云錦書箋》,又名《新鍥陸林二先生纂輯士民便用云錦書箋》,金壇介生周鐘書于醉云閣。下又署仁和陸培鯤庭甫匯編,明州林時對殿飏甫音輯,潭陽楊居理道卿甫校梓。我于1993年在日本內閣文庫查對過此書,上有眉批。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書上蓋有淺草文庫、薕葭堂藏書、日本政府圖書三顆印章。
這份“地方契約”十分珍貴,在一般文獻中均不易見。反映出明代民間采用“置酒會立條”隆重儀禮訂立鄉約,以正風俗,限制強者欺凌弱者,維護社會平等,也反對官府徇私舞弊,“欺善畏惡”,促使社會秩序正常。
諸多鄉規民約立足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管理,特別是對保護生態環境等訂立了許多禁約,對我們研究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等都是很有價值。下面將從禁止賭博、禁止偷盜搶劫、防止斗毆三方面加以引述。
二、嚴禁賭博
賭博為古往今來社會一大弊病,而犯賭者一旦陷入就不可自拔,因為賭博始自娛樂,繼自貪財,愈陷愈深,且賭博又常與偷盜結合,是社會不安定因素。明政府嚴禁賭博,對設賭場亦予以處罰。“凡賭博財物者,皆杖八十,攤場錢物入官,其開張賭坊之人,同罪。”(《明會典》卷—七零《刑部十二》)民間對賭博深惡痛絕,亦訂有禁約。
禁賭博約
“為禁約賭博事,切惟業農務本者,固無博戲之為游手好閑者,乃有賭博之病,傷風敗俗,蕩產傾家,皆基于此。奈本鄉生齒日眾,禮儀之教不明,遊逸之風愈熾,中間有等無籍之輩,生理不務,惟圖招群結黨,專為賭博之事。或投錢鋪牌,以競輸贏;或擲色局戲,以爭勝負,終日忘饗,徹夜失寐,仰事父母之無賴,俯育妻子之無依,盜心從此而漸生,奸謀由是而輒起。小則穿穴逾墻,無所不至;大則鳴火持刀,靡所不為。若不禁革,深為未便。為此,會議禁革,今后務要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守義存仁,各遵本業。如有長惡不遵者,定行懲治,輕則會眾加禁,重則送官發落,為此俱陳,的不虛示。”③京南龍陽子精輯,潭陽余文臺梓行,《鼎鏝崇文閣匯纂四民捷用分類萬用正宗》卷五《體式門》,萬歷三十七年刊本。日本陽明文庫藏本,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10-11,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刊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蓬左文庫亦藏,但書名為《類聚三臺萬用正宗》(《士民捷用分類學府全編》)。按:又有明佚名《釋義經書士民便用通考雜學》卷二,亦有載此服書式,但有幾字不同。
民間宗族亦有禁賭族約,如江蘇海安崔氏《虎墩崔氏族譜·族戒》·《戒賭博》:“賭博之為害不小,傾家產,壞心術,喪行止,甚則為盜為非,以致割恩傷愛。子弟一或犯此,未有不摧殘破敗者。……凡我族人,務各守分,毋貪他人財產,自貽伊戚。一有不遵守約束者,許眾呈之族長,痛治其罪,仍將攤場財物入祠公用。父兄故縱者并罪之。”④《虎墩崔氏族譜·族戒》,萬歷刻本,轉錄李文治·江太新著《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93頁。
此族戒不僅對犯賭博者“痛治其罪”,還將財物充公入祠,更要將賭者父兄亦治之以罪,使全社會全族人痛恨之。
天啟邊氏《經堂家訓》(天啟甲子二月二日,十世同著)有禁賭錢的家規:
“禁賭錢:
凡人初賭時,只云解悶,又云小賭,有何大害。不知小者大之基,賭錢初則失錢,錢盡則失物,物盡則破產;及至破產,上不能事父母,下不能畜(蓄)妻子,名為匪類,甚而賣子質妻,身居下品,此時悔之晚矣,能無懼矣。”(錄自同上書《李江氏著》,322頁)
明代村社賭博之風盛行,江南尤盛。如蘇州“夜聚曉散,在在成伙”。⑤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浙江海寧,“賭博之事,當初止有市井叢人之處,間有不良落此陷中。今(萬歷三十八年)鄉村曠野,無處無之。”[2]
三、防止偷盜
明政府對偷盜行為多次發布禁令:
“竊盜
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但得財者,以一主為重,倂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
盜園陵樹木
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杖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杖八十。……
強盜
凡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為從各減一等,並于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3]
還有《盜馬牛畜產》、《盜田野谷麥》等條令,相比之下,以對強盜罪最重。
鄉規民約對偷盜多偏重禁止小偷小摸行為,有《禁六畜作踐禾苗》、《禁田園山澤約》、《禁盜雞犬約》、《禁盜田園瓜果菜蔬約》、《禁偷盜筍竹約》、《墳山禁約》等。這些禁約多從保護農作物豐收,不受外來的人為破壞,維護生態平衡,使田園“青苗蔽野,綠蔭連山”,達到“收天地自然之利”。茲錄一節以見一斑:
禁六畜作踐禾苗約
“嘗聞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國)咸寧;民以食為天,天順則人民均富,理固然也。切照本境僻處遐陬,民居稠密,不務工藝(以)營生,罕作經商而覓利,惟藉播谷以給贍家之衣食,種植以供上國之稅糧,日用巨細所需分毫悉賴于此。吾儕方春之時,而竭力于耕播也,可謂勞矣。至于當夏之際,而心勤于耕耨,厥惟艱哉!誠以耕播耘耨之勤勞,預望倉廩豐實之饒裕,使八口之家無啼餓哭寒之苦,一鄉之內有含哺鼓腹之樂。嗟夫!俗有淳漓,民有純駁,知稼穡之艱難者固多,徇一己之私欲者亦有,或縱牛羊踐踏,或放鵝鴨蹂食,若不設禁,誠為害夫!既往者不可追,而未來者尤可救,早晚禾苗之吐秀,乃感天意垂榮,牛羊鵝豕之踐戕(害),實由人心之不謹,是則憂之,良可惜哉!爰會鄉眾僉謀嚴禁之約束(示),仰週知悉。約以厶月厶日為始,各家人等務令(宜)遵守,畜養牲口俱要謹慎嚴固關欄,毋得故意縱放踐食。巡視遇見,登時戮死,不必賠償,亦無爭競。倘有無籍之徒,恃強之輩,出惡(首)言(妄爭),即投申明亭,上從公斷,治罪依鄉例,庶使人知所警(懼)。物遂(其)生,殆見(田)苗而秀,芃芃然于東阡之內,由秀而實,栗栗然北(西)陌之中。惟愿其五谷豐登,共享太平之盛世,四民樂業,同于至治之雍熙,謹示!”①云錦 廣寒子 編次,藝林楊欽齋刊行《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匯錦萬書淵海》卷九《民用門·四民便用》,萬歷庚戌(三十八年)刊行,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本。今收入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6-7,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刊行。按:引文中()為筆者所加,以供備考。
此鄉約寫得很好,有理有情,勸人為善,珍視他人勞動,祝愿人人能享受“五谷豐登”、“太平盛世”的歡樂。對違法者實施處罰,重者“投申明亭,上從公斷,治罪依鄉例”。
在族約中也有《禁盜田園》的公布:“各家田地園圃山場,申約嚴禁偷盜,食踐者,痛責三十板,家人犯者,痛責四十板。”並罰以銀兩。②《宜興筱里任氏家譜》卷二之五,《宗法》,轉錄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55頁。
民間亦有禁盜伐林木的族規族約,如福建“東陽后堤榕樹并海岑榕樹數十株,乃先世培護風水,不許人等剪伐及縱放牛羊踐踏,違者議罰。”③嘉慶福建莆田縣《浮山東陽陳氏族譜》·《家規》。轉錄李文治·江太新著《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318頁
廣東廖氏《家規》嚴禁偷竊:
“入室偷盜財物,罟(網)利魚塘,偷竊豬牛田禾,贓數逾貫者,由主事稟官究治;贓數不及一貫或超過一貫,但已退賠者,不告官府,族內罰停胙三年;偷竊園內瓜果,圈內雞狗,曬晾衣物,池塘魚蝦等,罰胙一年”。④南海《廖維則堂家譜》卷一《家規》,轉錄李文治·江太新著《中國宗法家族和族田義莊》,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144頁
有人認為多盜賊也有與政府缺乏嚴密的防范措施有關,如廣東城鄉日夜均有盜賊出沒,這與官司缺乏有力防范有關,如明代當時地方官項喬就極力主張加強防守措施。他說:“照得近來強竊盜賊,不惟鄉間充斥,城內亦多有之,雖盜賊之不才而貪財以犯義,亦守備之不設而謾藏以誨之之故也。”⑤《項喬集》下,卷十,政類下,《為嚴舊規以防守地方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704頁
尤其是地方基層組織的里甲為保證地方安全,須每夜巡查,並向官府保證,以制裁偷盜。“禁兵某,今于與執結為巡盜事,遵依每夜巡邏地方等處,係各清寧,並無盜賊,中間不敢扶控。如虛,甘罪,所結是實。”⑥萬歷二十四年刻《萬事萃寶》卷十九《矜式門》
四、防止斗毆
明政府有對斗毆處罰條令。“凡斗毆(相爭為斗,相打為毆)以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十;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笞三十,成傷者,笞四十”。但對斗毆致死者,則處以“絞刑”。“斗毆及故殺人:凡斗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全刃,並絞。”[4]
罵詈:“凡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5]
對于罵詈、斗毆的處理是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刑罰,但殺人致死者就處于絞刑。
五、路引·保狀
明代對流動人口實施統制,凡離鄉百里外出經商探親訪友,必須辦理路引作為個人身份的憑證,相當于今之通行證。由離鄉外出者向里甲申請,再由里甲向上級機關呈報,由縣一級政府登記在冊,核準后簽發路引作為憑證,讓沿途關卡查驗放行,這種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仍不失其歷史借鑒的意義。
明政府規定:“凡遠出,先須告引①余文臺《類聚三臺萬用正宗》卷二十一《客商門·客商規鑒論》,萬歷二十七年刊本。“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路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渡關津論。”[6]明人徐琴堂釋曰:“秦關燕壁,路阻且長,倘非棄儒生未有不苦于盤詰者。今某貿易江湖,非區區守故園而老者,與以執照,庶身有照驗關,無留難矣。”②徐筆洞先生精纂《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又名《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萬歷四十二年刻,存仁堂梓·卷九《民用門》,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今收入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之八,汲古書院印,平成十一年。
對無路引《私越冒度關津》:“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渡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外出境者絞,守把之人,知而故縱者同罪。失去盤詰者,各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若有文引,冒名度關津者,杖八十。家人相冒著,罪坐家長。守把之人,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其將馬驘私度關津者,杖六十,越度,杖七十。”[7]
持路引者還須按規定到指定的關津查驗放行,“守把”者如失職、持引者冒名度關津者,亦都要處以刑罰。沿途關津查驗路引亦有職責規定:“凡關津往來船只,守把之人,不即盤驗放行,無故阻當者,一日笞二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官宦勢要之人,乘船經過關津不服盤驗者,杖一百。若撐駕渡船稍水,如遇風浪險惡,不許擺渡,違者笞四十;若不顧風浪,故行開船,至中流停船勒要船錢者,杖八十。因而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8]路引還須按嚴格程序核準辦理,巡檢司不能越權辦理路引,杜絕徇私枉法。“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及軍詐為民、民詐為軍,若冒名告給引,及以所給引轉為他人者,并杖八十。若于經過官司停止去處,例給路引,及官宦勢要之人,囑托軍民衙門,擅給批帖,影射出入者,各杖一百,當該官吏聽從及知情給與者,并同罪。若不從及不知者,不坐。若巡檢司越分給引者,罪亦如之。其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與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及有所規避者,各從重論。”[6]由此可見,對辦理路引是列為政府重要公務,把流動人口的管理提高到法律程序上去執行。
路引樣張查閱諸文獻均未見錄,只有保存在日用類書籍中“民用門”、“體式門”中的“活套”,大同小異可見其具體內容。如《五車拔錦》中就有“路引”的活套:
“出外給引狀式
某縣某里某圖某人為告給文引事,緣某前往某等處探親經商,誠恐前途阻滯,理合告給文引,庶免關津留難,為此給引是實。”③錦城徐三友校正,閩建云齋鄭世魁梓行《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卷二十四《體式門》,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萬歷二十五年刻本。今收錄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一、二中,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印行。又日本蓬左文庫藏撫金華亭徐會瀛匯輯,書林茂齋詹圣謨梓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萬歷二十八年刻,卷二十五《體式門·外出給引狀式》條同載。該書又名《新鍥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有五云豪士天樂生言(序)。另一《給引狀》:“某縣某都某里某人,為告給文引事,身因往某處買賣,猶恐沿途經過關津把隘去處,恐有阻隔,理合告給文引,照身庶免留難,為此給引。上告同里長某人老人某人。”④徐筆洞先生精纂《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存仁堂萬歷四十二年梓,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卷九《民用門·給引狀》。今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之八。
明萬歷時呂坤對路引的使用以及防止意外,有著明晰的思考和周全舉措,為此,他特地設計了一份路引的具體內容,以人驗證,以持引人和路引所列諸項內容相符者才可放行。他所設計的路引項目如次:“若州縣為遠行,照得本州縣衛所某百戶某人,年若干歲,身長幾尺,無須微須,方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棠色,有無麻疤。今由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如在衙門,即以奸盜押回原籍查究。此引回日繳還原發衙門。須至丁引者。右給付某處某人,準此。州押印,縣押印。”⑤呂坤《實政錄》卷四《遠行丁引》
從呂坤所記的情形來看,路引項目具有以年齡相貌特征來查對持引人的內容,還要登記持引者家屬姓名,以便核對身份和查究家屬情況。這是較完備的路引。但是至今仍未發現路引的樣張。
路引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是一個有效措施。對申請、呈報、審核、發放都有一整套完備的程序,防止出漏洞。對冒名使用,不按指定關津檢查放行,發放路引、關津查驗路引放行,亦都有嚴格程序,可見明代政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已很重視。路引持有者還須向鄉村居住地的里長、老人稟報,實亦是一種監督機制。
鄉村里甲對地方治安和管理也盡職盡責,除了對路引監督外,還負責取保等事。在日用類書中亦見到保狀和地方執結,輯錄于次:
保狀
“縣坊某隅某總居民某,今當本縣老爺處,承保到在官(押)犯人某等外出,聽候,不敢違誤,所保狀是實。”
地方執結
“某都某圖里老總甲某等,今于與執結,為地方遵依結到守,本里地方并無生面之人在于地方頓歇,如違事發甘罪,所結狀是實。”①余文臺《類聚三臺萬用正宗》卷十七《民用門·呈狀類》,萬歷二十七年刻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陞文庫本,今收入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三至卷五, 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刊印。
為保證某里人充任公職的證明:
“某都某人等,今當本縣老爺處,承認識字農民某人幾名,不系父子相繼,兄弟出入娼淫,子弟出入隸學書手,亦無公私過犯,今蒙審聞,執法是實。”②余象斗纂:《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卷十七《民用門》。
地方基層組織如里甲以及耆老對地方治安、社會秩序的維護都須盡職盡責,如須對鄉民或童生的人品行為,時須出具證明,如余文臺《三臺萬用正宗》卷十七《民用門》:
“領狀:
某都某圖某人等,今當本縣老爺處實領到某事云云,中間並無冒領,所供是實。
舖行領狀:
縣坊某行某人,今當老爺處承領到蒙硃票計過某件,計價銀若干正,中間不敢冒領,所領狀是實。”“某里某圖某,為歲考事,遵依結得,本童俱系良民,自幼在家肄業,習讀經書,身家並無刑喪過犯,又非曾經黜退人數,今家取結,中間不敢扶同妄控,所結是實。計開:一名童生某,系某圖某籍習某經,一三代曾祖某祖某父某,保結生員某。”③《萬書萃寶》),萬歷二十四年刊本,卷十九《矜式門》·《童生結狀》。轉錄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要錄》頁473-474。
童子執結:
“某都某圖某為歲考童子事,本生自幼在家習讀經書,身家並無刑喪過犯,又非曾經出退人數,今蒙取錄,所結是實。”④徐筆洞先生精纂《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卷九《民用門》,萬歷四十二年刻。
農民執結:
“某都某里長某等,呈為舉報農民事,蒙案著落各該都選報識字農民,今審得本都內有某能通書算,亦無私過犯人才頗堪選用,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認狀:
“某都某等,今當本縣老爺前承認識字農民幾名,中間並無父子相繼,兄弟出入娼媱,子弟隸卒等項,亦無公私過犯,執結是實。與童子其要三代祖與父里老長保之名。”⑤徐筆洞先生精纂《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卷九《民用門·呈結諸式》,萬歷四十二年 存仁堂梓。
領農民狀
某都某人等,今當本縣老爺處承認識字農民某人幾名,審得並無公私過犯,今蒙審問,執結是實。”⑥余文臺《鼎鋟崇文閣匯纂四民捷用分類萬用正宗》卷五《體式門》,日本《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10-11,汲古書院,平成十一年刊行。
保狀、地方執結等文書,對研究明代地方社會管理是一難得史料。
結 語
明清時期社會治安由政府發布若干條令和民間集眾盟議制訂鄉規民約(含族約)以維護社會治安和百姓安居樂業。政府、民間、宗族三方協調,互相配合,共同管理,這一舉措,雖因時空嬗演,但仍有一定的歷史借鑒意義。
鄉規民約多帶自治自律性,但多從規勸、教育和道德倫理的自覺約束出發,啟發民眾自覺遵守,輔以地方耆老、宗族年高德劭者的督促,形成一股無形的約束力,協同政府管理好社會治安。
宗族制在數千年歷史中有其正負兩面社會功能,不能一概全面否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時尚能發揮其正面功能,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指出“宗族者社會國家之基本,無宗族即無社會無國家。”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歷來很重視家庭教育,從小培養子孫承繼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忠孝信義等,從正面培養國民良好素質,這對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有著深遠意義。如明代就有《訓蒙八規》:
“凡為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喜(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敬兄長,處朋友,毋得怠慢,自任己意。”①崇禎元年刻本《萬寶全書》卷三十三《訓童門》。轉引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要錄》,臺灣政治大學叢書之6 ,2001年 382頁。
清康熙時李毓秀非常重視家教,特編纂了《弟子規》一書,注重童訓:“入則孝,出則弟(悌),謹,信,泛愛眾,親仁,余力教。”凡32條。從細微末則以教育兒童養成良好的行為規范,培奍他們孝悌謹信愛眾親仁的寬厚心態和優秀品行。
浙江永嘉項氏為東南望族,他們制定的家訓就很注重社會公德,如《項氏家訓》:
項氏家訓: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項喬集》卷八)
教訓子孫:
“從幼教訓:人家子孫從幼便當教以孝弟(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名義。”
各安生理:
“果能各安生理,則不相凌奪,不相假借,從自有生民之樂矣。”(《項喬集》頁515)
中國日用類書是我國文化寶庫之一,它貼近民間,記載了社會經濟文化習俗多方面珍貴資料,而這些資料在正史等文獻中往往闕載。但很多日用類書流散于域外,日本學界早已注意及此,并進行了整理研究,近匯編成十四卷的《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我國學界對此仍處于方興未艾階段,為深入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必須充分重視中國日用類書的開發和利用。
[參 考 文 獻]
[1] 鄭之僑.《農桑易知錄》卷三《農桑善后事宜》十一《選鄉約》[M]//李龍潛,等點校.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129.
[2] 許敦俅.敬所筆記[M]//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318-323.
[3] 申時行,等.明會典:一六八卷《刑部十·律例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 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九《刑部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9.
[5] 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八《刑部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89.
[6] 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七《刑部九》·《詐冒給路引》條[M].北京:中華書局,1989.
[7] 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七《刑部九》·《私越冒度關津》條[M].北京:中華書局,1989.
[8] 申時行.明會典:卷一六七《刑部九》·《關津留難》條[M].北京:中華書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