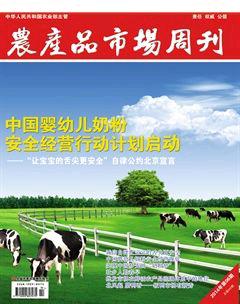農技員吉立斌:守住心里的這片田
李錦華
海南三亞,國內著名的海島旅游城市,有人喜歡這里的明媚陽光,有人喜歡沙灘旁的椰風海景,但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吉立斌來說,只有這里的茂密山林和富饒田地讓他情有獨鐘。
吉立斌在1995年中專畢業時,放棄了最后一撥國家分配工作的機會,回到故里、回歸農田。這選擇源于他對家鄉的惦念、對種植專業的熱愛。從一個三亞市吉陽鎮的黎族少年到農學專業畢業生,從學成歸鄉、投身種養,到成為村級技術員、鎮級農技員,不論身邊的朋友在海島旅游經濟浪潮中翻騰出多少美麗的浪花,他始終守著心里的這片田,用種養技術耕耘鄉親們的致富路,用汗水澆灌農業夢想。一路堅持,直到今天。
一輛摩托一雙腳,串連全鎮19個村
“從鎮辦公室出發,先到新村、安羅、博后村,再到中廖、大茅、羅蓬村,接著是紅花、落筆、南丁等其他村,最后再回到辦公室。”自2009年應聘為三亞市吉陽鎮的編外農技員起,在完成了鎮里的基本工作后,吉立斌一有時間便按照這個路線騎著摩托跑遍全鎮17個村的田地。農民對他的熟悉正是源于這年復一年的“田間巡邏”,每天相伴40多公里的摩托車逐漸成為他的招牌。
1月16日,記者來到他的辦公室,跟隨這位“大忙人”一道經歷了農技員普通的一天。吉立斌通常早上7點來到單位,拿上要填的表格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儀,跨上摩托,便開始了一天的“巡邏”。鄉親們誰家地里的作物有異常,都會招呼他去看看。記者好奇,如此跑圈,一天能否跑完,吉立斌解釋道:“經過這幾年的培訓和推廣,現在大家都有經驗了,不像前幾年,問得確實比較多。”
吉陽全鎮共有25284.7畝耕地,主要由33名安監員負責各自責任田里上市瓜菜的隨機抽樣與質量檢測,吉立斌除了對安監員們每天上交的檢測數據進行匯總,上報市農業局,還需要整理全鎮農戶種植情況表、常用農藥使用記錄表于每周五上報市里,以及負責每周從農貿市場或從常年蔬菜基地隨機采集5到8個品種,150個樣品進行檢測,并記錄攤主姓名、攤位號等信息,嚴禁不合格的產品銷售。去冬今春,吉陽全鎮累計抽檢樣品48129樣,涉及全鎮種植戶2382戶、8447畝瓜菜面積。
事實上,在2012年他還有自己的責任田需要抽樣、檢測,即每天采集35個以上樣品進行檢測,并及時做好信息記錄,后來因為實在太忙,才于2013年將這部分工作交由其他同事負責。記者每次感嘆他的工作量太大時,他都擺擺手說:“我們吉陽每個安監員都很辛苦,他們跟我一樣整天泡在田頭,只是我比較幸運被你們知道了而已。”
上午的采訪結束后,吉立斌堅持要去看看海燕臺風后國家補貼的化肥發放是否到位。接著,他又去了華之林園藝種植合作社指導建立生產記錄,確認其做好檔案管理,以便實施質量追溯制度。合作社的馮經理告訴記者:“吉立斌工作太認真了,比市里要求還要嚴格,一些涉及原則的事情,他甚至有點不講情面。但是,指導我們技術、發放政府補助和物資的時候卻一點也不含糊。”記者采訪馮經理的時候,吉立斌悄悄地站在遠處。
返回的路上,他特意要我們在南丁中村的一家農資店停留。“聽說這里新開了一家農資店賣農藥,這是需要申請經營許可證的,我不放心,來確認一下。”到了現場,看到店主用廣告紙將化肥這一項內容遮擋,他認真叮囑:“這個牌子最好還是換一下吧,沒有賣我就放心了,但是從后面看還是能看到化肥的字樣。”
下午6點多,吉立斌仍在打電話。采訪了一整天,他的手機不停地響,平時每天會有接近100個通話記錄,每月的話費需要400元左右。剛掛了電話,吉立斌不好意思地向記者解釋:“明天市農技中心要來檢查上市蔬菜的抽樣安檢工作,我跟他們溝通一下,本來應該是我帶他們去,這樣會方便很多。”記者的到來耽誤了吉立斌一些工作,他心里十分著急。“其他同事找不到路嗎?”記者問道,“主要是我對每個村的情況都比較熟悉,哪個村哪塊地要收菜了,哪里要施肥了,我心里都有賬,其他人需要打電話聯系確定行程。而且我有一條自己規劃的路線,可以比較有效率地跑遍19個村,省時間。”靦腆的他這時露出一絲笑意,這個路線是他這些年頻繁跑村積累的得意之作。
冬季這3個月是反季節蔬菜成熟的旺季,也是農技員最忙的時候,吉立斌在最近一段時間幾乎每周五天都要按照這個路線跑一遍。
技術過硬,能種也會養
初次見面時,吉立斌極其靦腆、語速緩慢,尤其是記者問到他的工作成績時,甚至會臉紅,并偶爾語塞。但是當他與農民在一起,聊到薊馬、斑淺蠅、青枯病這些專業名詞時,就變得放松、自然,還有些幽默。
農學專業畢業的吉立斌,在學生時代就燃起了鉆研種植技術的熱情。上學的時候,吉立斌被同學們戲稱為校長的“家里人”,因為好學、踏實,他每周五晚上都會被校長邀請去家里吃飯。直到今天,他在專業上有什么問題,仍然會請教老校長,有次校長親自把相關書籍送到了他手中,這讓吉立斌感動壞了。
所有的感動與支持都化作他鉆研農技知識、為農民服務的動力。“全鎮的農民遇到種植技術問題都會找吉立斌,因為在技術員里這塊兒他最懂。”吉陽鎮農業服務中心的譚主任告訴記者。
“你不要太貪心啦,這么粗的枝條上最多結三顆芒果就可以了,現在結太多,水肥跟不上,就會掉果了,不用擔心。”吉立斌在芒果園仔細看完后,幫董恩章分析掉果的原因。“肯定擔心啦,海燕臺風過后,剛長起來,好不容易掛了果,又掉了一地。芒果一年只能收一次,這滿地掉的都是錢哦。叫你來看過,我才能放心。”董恩章拉著吉立斌的手說。“沒事,沒事。”吉立斌笑呵呵地安慰他,“不過啊,你也不要松懈,水肥一定要跟上,還有啊,你這剪枝還是不行,今年再剪的時候叫我過來給你修修。”吉立斌的耐心與負責一點也不輸給他的專業技術。
除了芒果園,董恩章還于2011年末成立了三亞迅發山地雞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今一年可出欄2萬只,每只價格在60至70元之間。三亞市酒店消費量較大,經濟效益很不錯。“要說起養山雞的想法,這最初還是模仿吉立斌做起來的。”2009年之前,董恩章在吉立斌那里學習養殖山地雞的技術,雞苗也是吉立斌帶著他從五指山購買的。他的規模越做越大,但遇到不懂的問題,吉立斌仍然全心全意幫他解決。
“山雞好斗,有段時間‘啄癖鬧得很厲害,我實在不知道如何馴化山雞的好斗性,就請教吉老師。”吉立斌在一旁聽到了董恩章與記者的談話,有點不好意思:“你不要老師長、老師短嘛,大家都是一樣的,相互學習啦。上次看到你圈的地盤有點小,密度太高容易打架,其實飼料配比不合理、缺乏維生素等原因也會引發‘啄癖,包括一些疫苗應激反應都可能是原因。”吉立斌一談到種養技術就會變得很主動。“他就是這樣,只要是他懂的,都特別愿意分享,從來不會藏著掖著不跟我們講,我一般有問題都喜歡找他,一個電話就來了。”董恩章的言談間流露出對吉立斌的信任和依賴。
緊追不舍,為了鄉親們的收益
有時候,吉立斌的專業能力也會受到現實的挑戰。
田獨村的陳老伯已經種了十幾年苦瓜,2013年的苦瓜特別奇怪,葉子發皺,而且總也不長新枝,吉立斌也被難住了。采訪中,他告訴記者心里惦記那片苦瓜,“不知道現在長得怎么樣了,想去看看”。
中午沒有休息,吉立斌便來到陳老伯的苦瓜地,看到有些好轉,他才稍稍放心。“您覺得吉立斌的專業能力怎么樣?”記者問陳老伯,“很好啊,平時一般的問題他都能解決,這次的狀況有點怪,他已經及時幫我們聯系市里專家來看了,之后他也經常來看看。”對于自己也無能為力的情況,吉立斌會迅速向上級部門尋找支持,盡快為老鄉解決難題。“他一般來得快,走得也快,既不抽煙,也不吃飯,連口水都不喝,直接去田里,解決完問題就走了,就怕給我們添麻煩。”陳老伯擔心記者對吉立斌有誤解,極力解釋。
吉立斌遇到問題緊追不舍的勁頭在很多年前已經顯現一二。畢業后的第三年,他種了30多畝辣椒,也帶動了一些其他農戶加入種辣椒的隊伍。因為自己懂技術,收成還不錯,但那年辣椒的收購價卻掉得離譜。種之前1元1斤的辣椒,收獲時變成了1毛1斤,這次讓他虧到了連老鼠藥都買不起的程度。
看到自己與鄉親們辛辛苦苦干一年,卻賠了工夫還搭錢,吉立斌實在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為了打開心結,他決定跟著收辣椒的貨車跑一趟。起先他擔心是中間商壓價太狠,來到長沙批發市場一看,這里才3毛1斤。收購商也滿腹怨言:“昨天還5毛1斤呢,我們算上油錢,跟你一樣,白干!”看到這一幕,吉立斌的心結才打開。
市場價格的波動讓他明白,農民不能只種一樣,一定要發展立體式的種養組合模式。1997年,為了提高經濟效益,三亞市發動農民種植芒果。當時任村農技員的吉立斌,依靠自己的專業優勢,從自家親戚開始,反復向農民介紹芒果的經濟效益。如今,全村大部分農戶都種有芒果,較好地改善了收入狀況。直到現在,吉立斌還在鼓勵鄉親們種完芒果樹,要在樹下散養山雞、幼豬,糞便回收入沼氣池,沼液再還田作肥。
職責沒有范圍,農民所需就是責任所在
“沒有吉立斌,就像斷了我的一只手臂。有的人是出崗不出情,但他人到情到,在用心給吉陽農民做服務。”譚主任告訴記者,吉立斌承擔了很多職責之外的工作。一通又一通的求助電話,正是老百姓對吉立斌的認可。
采訪的第二天,記者跟隨吉立斌來到南丁村的常年蔬菜基地。老魯遠遠地看見他便揮手招呼,這個來自河南駐馬店的大哥已經在三亞種了5年蔬菜,他告訴記者:“我們原來就是瞎種,在阿斌的指導下,我的收入提高了30%。更重要的是,他幫我申請了河道整治,現在雨季也可以種菜了,常年蔬菜補貼也拿到了。”原來,老魯的菜地靠近河道,一到雨季就遭水漫,去年海燕臺風引發的水災將田頭的板房都沖垮了。吉立斌看到他們的情況,便通過鎮里向市水務局、農業局申請了河道整治工程。“明年就好了,我也全年都能種了!”正午的驕陽下,老魯笑地瞇起了眼。
吉立斌的電話又響了。“農戶在催玫瑰苗,我們去趟玫瑰谷吧?”性格溫和、始終保持微笑的吉立斌此時眉頭緊鎖、步履匆忙。三亞市為鼓勵農戶種植玫瑰,出臺政策向農戶提供70%的購苗補助,但是如今農民的地已經整平2個月,玫瑰苗卻仍不見蹤影。原來圣蘭德公司一直等不到市林業局的正式文件,無法開展與農戶簽訂協議、發放種苗等工作。“這得盡快向上級反映,地荒著農民著急。”跟經理溝通完解決辦法,吉立斌著急忙慌地走出圣蘭德公司。
正像吉陽鎮副鎮長林尤回所說,“我們鎮的農技員即是農產品質量安監員,又是檢測員,還是農業生產指導員”。吉立斌的工作內容林林總總,很難界定清楚。中廖村的麥永生對吉立斌充滿感激。海燕臺風給他的合作社造成不小損失,但是不知道國家有災后化肥補貼的他由于沒有申請,并沒有領取化肥的資格。吉立斌了解情況后,第一時間做出調整,將化肥送到他的田頭。麥永生當初修建田頭結構板房時,遭到市執法局叫停,也是吉立斌為他協調,向上級單位說明并非蓋樓,才得以順利建成。
由于工作踏實、反應及時,農民對吉立斌的需要漸漸超越了專業的界限、職責的范圍。只要是農民所需,他都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做人做事,自然真實就是最美
在車上,記者打趣吉立斌:“你這么忙,你妻子肯定不高興吧?”他說:“這幾年對家里的照顧確實少了點。兒子小時候跟我親,現在似乎跟他媽媽更親了。”
采訪接近尾聲,在記者的再三要求下吉立斌答應帶我們去跟他的妻子聊聊。來到吉陽市場,走進農副區,在地上的一推青菜中我們看到了坐在小凳上閉目休息的黎月娟。看到記者,她連忙整了整頭發。
“累了吧?早上幾點出來的?”記者問她。“5點,不累,他比我累。”一直捂嘴笑的她不好意思地指指旁邊的吉立斌。“你整天守在這里,家務誰做呢?”她依舊不好意思地捂著嘴,在吉立斌的鼓勵下,她說:“都做,他做飯比較好吃。”記者又問:“他這么忙,一個月才掙1500元,你支持他做農技員嗎?”這次她主動點點頭說:“支持。他愿意做就做。”蹲在旁邊的吉立斌拍拍妻子的肩膀,含糊不清地說著:“感謝好老婆!”說完,倆人同時臉紅了。
記者發現,吉立斌鬢角不易察覺的白發與妻子的白發相呼應,顯示著這家人的共同特點:同樣的靦腆,同樣的清瘦體形,同樣的寬容理解。黎月娟告訴記者,吉立斌每天早上5點都會送自己出攤,吉立斌告訴記者,為了彌補對家庭的虧欠,他會主動做些家務。這個靦腆、溫和的黎族男子在采訪中多次流露出細心體貼的一面,難怪結婚十二年,夫妻二人從未吵過架。
“種之前,要培訓,生長期,要服務,收獲時,要檢測。”吉立斌把專業知識奉獻給農田,把耐心交付給農民,把時間花在了工作,把真情留給家鄉,當然還有家人。記者始終不明白是什么讓他這么心甘情愿地忙碌。高收入?他沒有;權力地位?他也沒有。可能就是幫到農戶時的成就感,也可能就是在作物被種下、發芽、成熟、收獲的每個階段,他所感受到的喜悅!
這就是三亞市吉陽鎮的最美農技員——吉立斌,再忙再累只為守住心中的這片田!記者問他什么是最美?他說,自然、真實就是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