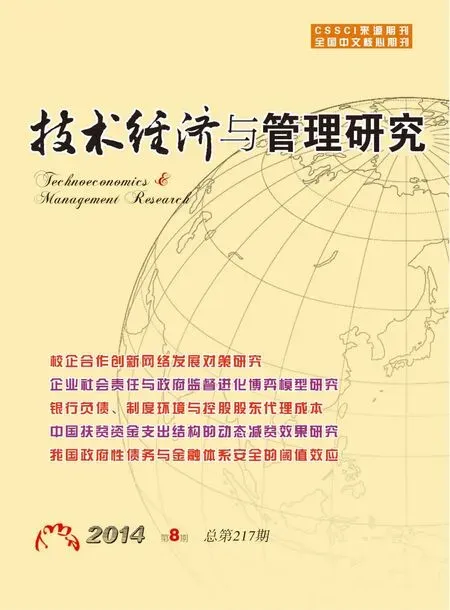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發展對策研究
沙德春,王文亮
(河南農業大學信息與管理科學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一、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理論與實踐發展現狀
隨著創新對人類生產生活影響的深入與全面,關于創新活動的認識逐漸深化,對創新環境與創新網絡的關注也日益突出。早期的創新理論以熊彼特的創新概念為代表,形成了線性技術創新理論模式。這種模式突出企業家的個人以及企業自身的作用,認為整個創新過程都是在企業內部完成。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線性創新模式受到人們的質疑,越來越多的學者將關注視野從單個企業轉向企業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7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Nelson and Winter從共同演化的視角論述了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關系,從而引發了學術界基于系統觀點對創新活動本質及創新過程機制的廣泛討論。80年代末,Freeman and Lundvall等學者開創了以國家創新系統為代表的第三代技術創新理論,產學研結合的思想和原理逐漸在科技管理實踐中得到推廣和應用[1]。90年代中期,歐洲創新環境研究小組(GREMI)指出企業與其所處環境結成的網絡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這種網絡既包括同一產業或相關鏈條上的企業之間正式的產業和經濟網絡,又包括企業與當地大學、研究機構、行會等中介服務組織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組織機構基于合作而結成的各種關系網絡[2]。新世紀初期,美國學者Chesbrough提出了“開放式創新”概念,認為企業應實施開放式創新模式,與大學等外部知識源進行廣泛合作[3]。三螺旋理論重要創始人Henry Etzkowitz認為,校企合作構成現代大學的“第三使命(The Third Mission)”[4]。國內,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促發下,形成了大量有關校企合作動因、合作模式、治理機制、合作效果評價等方面的研究。
實踐中,在政府推動協調下,我國校企合作取得了初步成就,呈現合作形式不斷創新、合作趨向更加市場化、合作路徑更加多樣化的發展特征,并形成了聯合開展科技攻關、合作創辦科技園區、共同建立研發平臺、構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等主要合作模式[5]。然而,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多種原因,我國校企合作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產學研合作的層次不高、產學研合作的深度不夠、產學研合作的資金不足、產學研合作的動力不夠、產學研脫節現象仍然存在。高校與企業在創新的價值目標上存在一定差異,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成果數量可觀,但成果商業化產業化的程度依然較弱。根據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我國每年的科研成果數量規模龐大,達到省部級以上的就有3萬多項,但是成果轉化率卻只有25%左右,而真正能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40%,遠沒有達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目標。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卻高達60%以上,如日本、美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已達到80%,英、法、德等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率達到50%以上[6]。
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科技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更加明顯,突破單個創新主體,實現多主體、多層次網絡化創新的要求日益加強。對于打破對外技術依賴、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我國現階段來說,構建多元節點參與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尤為重要。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由基本創新主體、輔助主體及外部環境構成的開放式系統,即以大學和企業為基本創新主體,以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等為輔助主體,各主體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以資源共享或優勢互補為前提,在技術創新的全過程或某些環節共同投入、共同參與、共享成果、共擔風險,通過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實現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咨詢服務等創新活動的組織形態。作為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實現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路徑,如何進行合理引導以實現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持久健康的發展是一項緊迫而又深具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文章的分析主要從發展理念、發展目標、發展形態、發展路徑等方面,對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的發展策略進行初步探討。
二、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發展的相關對策
1.深化“協同創新”網絡發展理念
隨著技術創新復雜性的增強、技術更替速度的加快以及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當代創新模式呈現出非線性、多角色、網絡化、開放性的特征,并逐步演變為以多元主體協同互動為基礎的協同創新模式。協同創新已經成為創新型國家和地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全新組織模式。實踐中,以協同方式建構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推動知識、技術與產業結合,實現科技與經濟“兩張皮”高度融合的政策模式最先產生自國外,尤其以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研究園的創建發展最為典型。斯坦福研究園將大學人才、知識、技術、企業資金等生產要素集聚在有限的地理空間中,形成了校企合作創新的有利氛圍,創造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局部優勢環境,成為高新技術創新的源泉、培育高新技術企業的孵化器、轉化高新技術成果的加速器以及風險資本的集中地[7]。經過20多年的發展便創造了享譽世界的“硅谷奇跡”。斯坦福研究園以促進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構建的方式為高新技術產業成長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發展模式。這種由美國興起的以高科技園區為空間載體,以構建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為路徑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模式很快超越了國界,向世界各地擴散。
對于我國來說,以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模式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興起相對較晚,同時也是一個政策學習與追趕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面對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沖擊,我國政界和學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1983年11月至1984年3月,國務院先后兩次召開“世界新的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討論會,部分參會學者受到硅谷等國外科學城的啟示,提出“充分開發中關村地區智力資源,發展高新技術密集區”的建議。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為加快新興產業的發展,要在全國選擇若干智力資源密集的地區,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興產業開發區”,從而為我國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的構建與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也為高新區、大學科技園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4月,原國務院經貿辦、原國家教育委員會、中國科學院開始組織實施“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校企合作,促進了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新世紀初期,《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將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打造成“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緊密聯系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2011年4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進一步指出,“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項目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這些論述一方面對我國校企合作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為合作創新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協同創新”成為現階段引導我國校企合作創新的重要思想理念。
“協同創新”是把協同的思想引入創新過程,各創新要素在發揮各自作用,提升自身效率的基礎上,通過機制性互動產生效率的質的變化,帶來價值增加和價值創造[8]。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中心研究員Peter Gloor最早給出定義,即“由自我激勵的人員所組成的網絡小組形成集體愿景,借助網絡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狀況,合作實現共同的目標”[9]。產學研協同創新是指企業、大學、科研院所(研究機構)三個基本主體投入各自的優勢資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務中介機構、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協同支持下,共同進行技術開發的協同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活動是在產、學、研、政、介、金協同下完成的,其核心是產學研三方合作進行技術開發,政府通過法規、政策進行引導和鼓勵,科技服務中介機構提供相關信息服務,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共同完成技術開發和技術創新活動。協同創新通過跨組織的思想、知識、專門技術和機會的共享,能夠保持個體組織持續創新,增補組織創新力量,從而使個體組織彌合已有創新水平和所需創新水平之間的差距[10]。與傳統創新模式相比,協同創新更具整體性、動態性特征[11]。
以高校、企業為關鍵主體,包括政府、金融、中介等其他機構在內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國家創新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提高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路徑,同時也是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載體,因而應積極、自覺地將協同創新思想理念作為網絡發展的精神指引。另外,由于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由基本創新主體、輔助主體及外部環境構成的開放系統,是包括核心創新網絡、輔助創新網絡和外部環境網絡的復雜網絡,網絡的多層次性、多主體性內在要求以協同創新的思想作為發展理念。為促進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構建發展過程中進一步深化協同創新思想理念,需要將協同思想具化為特定的網絡行動,并形成具有一定穩定性的協同發展機制,包括動力協同機制、路徑協同機制、知識管理協同機制等多個方面[12]。同時需要在網絡合作目標、創新資源、創新行動等各層次上實現協同發展。目標層面上,應實現任務分配協調、運營目標協同與戰略協同;資源層面上,包括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與信息資源的協調;行動層面上,包括研發協調、交易協調與成果分配協調[13]。
2.將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的核心網絡
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國家創新系統的一部分,與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其它網絡,如高校合作創新網絡、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風險投資網絡等有所不同的是,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突出的是以高校、企業為關鍵主體,同時包含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等多元主體基于創新活動所形成的復雜網絡。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在理論淵源與政策實踐上,都與國家創新系統有著密切關系。而且,基于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的獨特性,應當確立其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發展與政策實踐中的特殊位置。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末由弗里曼等人較早提出,其是指“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門中的機構網絡,這些部門的活動與交互作用激發、引入、改進和擴散新技術”[14]。朗德沃爾從更具微觀特征和更有理論導向的視角提出對國家創新系統的理解,通過將互動學習、用戶—生產商互動和創新置于分析中心,力求發展一種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新研究范式。尼爾森等人更加關注案例的實證研究而非理論建構。英國卡迪夫大學的菲利普·庫克教授將創新系統理論擴展到區域層次,提出了區域創新系統概念[15]。國內學術界自20世紀90年代末也逐漸開始對國家創新系統給予關注。新世紀初期,國家創新系統理論逐漸走進我國政策實踐領域,成為最高決策層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理論指引。隨著建設“創新型國家”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與實踐在我國發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加快建設國家創新系統,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系統。培育、增強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系統是實現創新型國家發展目標的關鍵路徑。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因其結構特征的獨特性,從而形成與國家創新系統的特殊關系以及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特殊位置。
首先,校企合作創新網絡與國家創新系統構成“面”和“體”的關系。國家創新系統包含多個創新網絡,如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高校合作創新網絡、校企合作創新網絡、風險投資網絡、中介服務網絡等,各個創新網絡立體化、復雜性的交織聯結構成了國家創新系統。因而,一定意義上,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個國家創新活動、創新關系的“綜合體”,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則是這個“綜合體”的“截面”。校企合作創新網絡與其它創新網絡既有交織,又有區別。校企合作創新網絡中的主要節點—企業和高校,分別是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高校合作創新網絡的關鍵節點,校企合作創新網絡中的其他節點,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等,又分別構成輔助性創新網絡的主體要素。各網絡節點具有一定獨立性,同時又相互嵌入、彼此交織,共同構成完整的國家創新系統。
其次,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一種高度異質性的創新網絡。國家創新系統由企業—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高校—高校合作創新網絡、高校—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風險投資網絡、中介服務網絡等多個分支創新網絡相互交織、彼此嵌構而成。各分支網絡中,如企業合作創新網絡、高校合作創新網絡、金融投資網絡主要由同類主體構成,網絡節點具有一定的同質性。相比較而言,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以高校和企業為關鍵節點,同時包含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其他行動主體的創新網絡,體現出網絡節點類別上的跨主體性和網絡構成的層級性,是一種具有高度異質性的創新網絡。這種異質性不僅為行動主體之間價值目標、行動取向的協調提出更高要求,也為網絡規模的擴展、網絡知識吸收擴散渠道以及網絡整體創新能力的增強提供了更廣泛的空間,從而成為國家創新系統中既具有高度異質性又深具創新活力的創新網絡。
最后,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具有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核心網絡的潛質。校企合作創新網絡中的主要節點—企業和高校,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關鍵主體要素。國家創新系統主體要素包括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政府、金融機構、服務中介機構等,各主體圍繞“創新”活動形成的多元交互關系構成了國家創新系統。由于資源稟賦、社會功能的差異,不同主體要素在創新系統中的功能地位有所不同。其中,企業擔當產品技術創新、工藝流程創新的主要職責,高校、科研機構承載了知識創新與創造的主要功能,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提供知識技術創新服務功能,因而在國家創新系統建設實踐中,更多的強調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系統,以高校科研機構為主體的知識創新系統,以政府、金融機構、中介機構為主體的創新服務系統。由于國家創新系統是以培育、增強國家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任務的發展系統,因而以高校(包括科研機構)、企業為關鍵主體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在國家創新系統中占據特殊位置,理應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的核心網絡。
可見,一方面,由于網絡節點的高度異質性形成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巨大的創新潛能;另一方面,基于關鍵網絡主體的獨特性以及與其它創新網絡相互嵌入、彼此交疊的復雜關系,確定了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在推動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構建發展過程中,應明確網絡發展目標,配置優勢資源,努力將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中的核心創新網絡。
3.推動“創新網絡”向“創新生態網絡”轉變
我國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建設已取得一定成就,但網絡主體間合作關系具有偶然性、短期性與不可持續性,往往隨著合作項目的結束走向了網絡生命周期的終結,缺乏有力的長效機制和發展動力。這些問題影響了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的生命力與延展能力。新世紀以來,創新理論中“創新生態”思想為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的構建形成一定的啟示和借鑒。
隨著創新環境的急劇變化,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的日益加劇,傳統的創新發展理論與創新管理思想遭遇越來越多的困境與挑戰。一定意義上,我們已經步入了“創新生態系統”時代。2004年12月,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創新美國一一在充滿挑戰和變革的世界中繁榮昌盛》的研究報告指出,新世紀以來,創新主體、創新模式以及創新環境都出現了一些巨大變化,一度被認為彼此對立的關系現在正日益演變成互補的,甚至是共生的關系。基于創新活動發生的新變化,報告認為,創新不是一個線性或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影響創新的各要素之間存在多方的互動關系[16],從而明確提出“創新生態系統”概念。創新本身性質的變化和創新者之間關系的變化,需要新的構想、新的方法,企業、政府、教育家和工人之間需要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形成一個21世紀的創新生態系統[17]。
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生態系統,創新生態系統是由諸多參與創新的主體構成的。2008年,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產學研究伙伴關系分會發布的《創新生態中的大學與私人部門研究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創新生態系統包括學術界、產業界、基金會、科學和經濟組織和各級政府的一系列的行動者。作為創新系統重要主體的企業之間,企業與大學之間展開的多種形式的合作猶如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態鏈,任何一個鏈條都關系著整個系統的運行和績效。當創新系統遇到強烈的外部干擾偏離平衡臨界點而失去或削弱自組織功能時,需要有平衡力量的出現,以使創新系統重新回到平衡狀態,從而化解創新系統的風險。“創新生態系統”更加突出了創新系統的動態演化性,突顯了創新系統的自組織生長性。“創新生態系統”是系統中科技創新“序參量”主導的演化系統,是不斷演化和自我超越的系統,是創新全要素資源,包括政產學研用結合、“科技+X”(產業、金融等)的協調系統。“創新生態系統”概念的提出體現了創新研究范式的轉變,由關注系統中要素的構成向關注要素之間、系統與環境間的動態過程轉變,從關注創新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轉到關注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18]。“創新生態系統”對于國家、地區以及企業保持創新活力和動力乃至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在《維護國家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報告中指出,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得益于一個精心編制的創新生態系統。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創新。然而,中國的創新生態過多地依賴政府構建的“人工生態”,而不是依托市場自發形成的“自然生態”,創新系統有一定脆弱性,需要進一步的改革發展提高創新的質量和內涵。
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是國家創新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因而在發生“創新系統”向“創新生態系統”范式轉變時,迫切要求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在理論范式和發展形態上做出相應轉換。與創新生態系統相適應,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在理論內涵、運行機制、發展形態等方面應充分體現出“生態”特征,培育創新網絡自組織、自適應、自調節能力,形成相應的反饋機制與調節機制,提升創新網絡自我繁殖空間,延展網絡生命周期,實現漲落有序,動態開放的“生態型”創新網絡發展形態。校企合作創新生態網絡由知識生產者、技術生產者、知識技術使用者、分解者通過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形成網絡種群。網絡種群中各個結點形成復雜的相互關系,企業是主體,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技術產出單位是依托,技術開發機構是孵化器,通過區域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最終形成可供企業生產的成熟的工業化生產技術。在技術生態系統中的市場、信息、服務、保障等服務性經營機構的支持幫助下,向國內外市場輻射,實現技術開發成果的轉移和擴散,不斷地推出衍生技術產品,并以此吸引或聯合一大批強有力的企業群,參與引導區域內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營造良好的制度支持軟環境、提供持續的營養供給、注重外部激勵作用、形成相互依存的網絡系統是構建創新生態網絡的重要路徑。生態型合作創新網絡既包括“網絡內生態”,又包括“網絡外生態”。“網絡內生態”主要是指創新網絡內部各網絡節點之間形成的自組織、自適應、自調節機制能力狀況以及各子網絡之間漲落變化、動態平衡關系。“網絡外生態”是指校企合作創新網絡與其它創新網絡以及網絡環境之間互動、適應、調節、漲落關系。校企合作創新網絡向創新生態網絡的轉變,需要構建一系列的支持機制,包括信任機制、利益分配機制、激勵機制與反饋協調機制等。
4.踐行“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網絡發展路徑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知識型員工的加速流動,開放式創新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創新范式在區域發展、企業成長等實踐領域中得到盛行。作為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重要發源地之一的美國硅谷,很早就認識到,僅依靠公司進行國外生產以及保持與供應商的合作是遠遠不夠的,為保持長久發展的動力,應該建立起基于全球的創新網絡。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新加坡裕廊工業園以及中關村、上海張江等高新技術園區都呈現出打破地理邊界限制,施行開放式創新發展范式的趨勢。此外,在開放式創新范式影響下,企業創新活動的邊界也日趨模糊,“開放式創新”逐漸成為更多企業的選擇。OECD對12個國家59家企業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有51%的企業將5%的研發預算用于支持外部研發,有31%的企業外部研發比例超過10%。開放式的創新投入與創新成果共享模式對創新主體行為方式的影響日益突出。
“開放式創新”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最初由哈佛商學院技術管理中心主任亨利·切斯布洛教授(Henry Chesbrough)于本世紀初期提出。切斯布洛教授通過多年研究發現,世界上許多深具創新能力的大公司卻未能從自身的創新活動中大受益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些大公司過于重視對創新活動的控制,缺乏與公司外部的創新互動,導致大量創新成果長期“沉睡”在公司檔案庫內。基于這些認識,切斯布洛教授在《開放式創新:從技術中獲利的新策略》一書中提出并論述的“開放式創新”的概念,認為企業在創新過程中應該改變原有的機械的思維方式,而將外部的和內部的技術有機地結合成一個系統,這個系統一方面使得企業能夠通過技術許可,從外部獲得企業需要的技術成果;另一方面激活在封閉的創新環境下可能被拋棄的某些企業技術,從而獲益。開放式創新包括創新環境的開放性、創新主體的開放性、創新資源的開放性、創意開發的開放性。開放式創新是針對傳統的封閉式創新而言的,封閉式創新范式下,通常會導致一些不利的后果,如:無力承擔高額研發投入的企業將處于競爭劣勢;企業無視外部創新成果實行“閉門造車”;無法有效應付快速變化與新興的市場等。開放式創新有助于弱化封閉式創新的上述弊端,并能有效克服“創新者困境”。此外,在開放式創新系統下,能有效避免知識創新重復,節約創新成本;能縮短知識創新周期,并分散創新風險。
作為由高校、企業等多元創新活動主體形成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自身就是開放式創新范式發展的產物,它們的本質是要超越創新主體邊界,推動創新行為相互嵌入,促進創新思維高度融合,實現創新資源的優勢互補。在開放式創新知識網絡中,不同的網絡成員往往擁有不同屬性的知識,顧客更傾向于擁有市場知識,競爭者擁有互補的技術知識,而高校院所擁有適用于技術突破的科學技術知識,不同伙伴成員知識的“局部性”、“碎片化”與“過程性”形成了它們各自知識的“異質性”。然而,由于創新主體成長的慣性與價值目標的差異等原因,開放式創新的發展范式在我國校企合作創新實踐中尚存很大的發展空間,企業、高校等沒有真正超越走出傳統角色的藩籬,創新主體之間缺乏實質性的互動機制,創新網絡內部以及創新網絡與外部環境之間沒有形成長久有效的互動協調機制。在交流、開放、互動、合作的時代背景下,開放式創新發展路徑對于區域發展、單一主體創新以及多元主體的合作創新的意義更加突出。
為適應創新管理新的發展范式,推動校企合作創新網絡拓展與績效提升,需將開放式創新發展路徑貫穿核心創新網絡、輔助創新網絡層與外部環境網絡之中,促進各層次網絡內部主體之間、網絡與網絡之間、網絡與外部環境之間高效、便捷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換。
[1] 何郁冰.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理論模式 [J].科學學研究,2012(2).
[2] 蓋文啟著.創新網絡—區城經濟發展新思維 [J].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Chesbrough 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gfor technology [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Cambridge,MA,2003.
[4] Etzkowita H. 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inac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5] 夏靜,吳江龍.大力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 [N].光明日報,2012-03-11(004).
[6] 甄紅線,賈俊艷.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 [J].金融教學與研究,2013(2):35-41.
[7] 陳益升著.高科技產業創新的空間—科學工業園區研究 [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8] 饒燕婷.“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內涵、要求與政策構想 [J].高教探索,2012(4):29-32.
[9] 張力.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戰略意義和政策走向 [J].教育研究,2011(7):18-21.
[10] Ketchen,D.,Ire land,R.,Snow,C.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collarativeinnovation and wealth creation [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 rnal,2007(1):371-385.
[11] 陳勁,陽銀娟.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與內涵 [J].科學學研究,2012(2):161-164.
[12] 王進富,張穎穎,蘇世彬,劉江南.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16):1-5.
[13] 邱棟,吳秋明.產學研協同創新機理分析及其啟示 [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152-156.
[14] 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Japan [M].London: Pinter Publishers,1987.
[15] Cooke P.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ompetitive regulation in the newEurope" [J].Geoforum,1992,23(3):365-382.
[16] 優化整個社會建設創新經濟——《創新美國——在充滿挑戰和變革的世界中繁榮昌盛》述評 [J].中國軟科學,2005(5):156-158.
[17] 賀團濤,曾德明,張運生.高科技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述評[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8(10):83-87.
[18] 曾國屏,茍尤釗,劉磊.從“創新系統”到“創新生態系統”[J].科學學研究,2013(1):4-12.
[19] John Hagel,John Seely Brown. The Only Sustainable Edge. Why BusinessStrategy depends on Productive Friction and Dynamic Specializ-ation [M].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5.
[20] West,J Gallagher,S. Challenges of open innovation: the paradox of firminvestment in open-source software [J].RDManagement,2006(3).
[21] Wang Wenliang,Liu Yan. The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nStructure Model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A].Proceedings of Shanghai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2010:193-197.
[22] PCAST. University Private Sector Research Partnerships in the InnovationEcosystem [R].Nov,2008.
[23] Bowonder,B.,Racherla,J.K.,Mastakar,N.V.,Krishnan,S. RD spendingpa atterns of global firms [J].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 (5):51-59.
[24] Christensen,C. The innovator's dilemma [M].Boston: Harvard BusinessSchool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