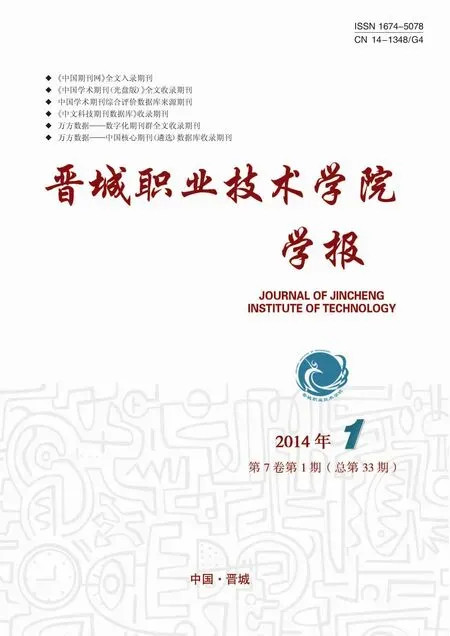戰(zhàn)國封君問題探析
馬云龍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鄭州 450001)
眾多史料證明,春秋末期尤其是戰(zhàn)國時期,卿大夫、貴戚、功臣、名將乃至他國降將,因為宗族關系或有功于國受到諸侯王的賞識,進而被封賞,且封賞至尊至貴者多冠以“君”的封號。自春秋末期起,稱“君”現象開始出現,至戰(zhàn)國時期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戰(zhàn)國時期,群雄并起,為爭奪霸權贏得他國臣服,各國之間結盟對立、對立結盟開始了它們200多年激烈地兼并戰(zhàn)爭。先是大國吞并小國,代之而起的是幾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之間的較量。隨著禮崩樂壞局面的加劇及自身實力的增強,各路諸侯紛紛稱雄稱王。但不可否認的是,各諸侯國的強大與封君制度的延續(xù)和逐漸強化的趨勢有著密切的關系。依托這些封君,各諸侯王加緊對外征服與擴張,同時借助他們來鞏固自身的統(tǒng)治。總之,縱觀戰(zhàn)國時期,封君之風不但未有削弱之勢,反有日盛之形。下文將對封君受封的封號形式、受封原因加以敘述,并且在對各國封君考證基礎上嘗試求證各國的封君數量,以求對封君制度研究有所裨益。
一、封君封號的形式
關于戰(zhàn)國封君名號的形式問題,劉澤華,劉景泉在《戰(zhàn)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一文的戰(zhàn)國封君概況中已做過較為詳實的敘述。此節(jié)為達到行文流暢,順應上下文的承接關系,每一種名號試再各用別例加以對應,使其論據更加詳實完備。
(一)以封地作為封號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1]《索隱》云:“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
(二)以“謚”作為封號
“(趙襄子)封伯魯之子周為代成君”[2]1794并且授予其代地。“代”為地名,由此推之,則“成”可能為其謚。田嬰,孟嘗君之父。“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嬰卒,謚為靖郭君。”[3]《正義》中注有孟嘗君亦為謚號。又楚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4]一句,《正義》為其注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君有也;又非趙境,并合號謚,而孟嘗是謚。”[4]此論在史家研究中尚有爭議,但無論爭論如何激烈,觀點如何相左,戰(zhàn)國時期有些封君封號以謚號命名,則是不虛。
(三)以雅號作為封號
《史記·趙世家》載:秦攻打趙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2]1823《正義》注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2]1823長安君當是雅號。
(四)以發(fā)跡地或原籍作為封號
齊國封君中的鐘離春其原籍即為無鹽,故齊宣王封賞其功時,將封其為無鹽君。受封于燕國昌國之地的樂毅父子皆稱昌國君亦是此理,由此得之。
二、封君獲得封號的原因
學界專家普遍認為,封君封號的獲得之緣由以“因功得封”與“因親受封”兩種觀點為主。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除以上兩種因素之外,亦需考慮其他影響因素,才能使其原委更加完善妥當,現陳述于下。
(一)因功得封
“主父(武靈王)及王游沙丘”,然而公子章趁機叛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因平叛有功,封“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2]1823《趙國史稿》中也有記述李兌因平亂有功、輔佐趙國朝綱而在趙惠文王時被封為奉陽君的內容。又《史記·趙世家》云:“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于,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于下,賜號馬服君。”[2]1823由此得證,趙奢是因功得封無疑。邯鄲之圍后,燕攻趙,廉頗為將,大破燕軍。“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5]故廉頗亦因軍功而受封。再者,上文亦有提到“秦惠王八年,封樗里子右更……”后數立戰(zhàn)功,“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1]《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6]由此得證,嚴君亦是因功得封。
(二)因宗室得封,即親親得封
各國封君中獲得封號較早者即為趙襄子時期的代成君,其為趙國分封的第一位封君。“(趙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7]趙襄子封伯魯之子主要是由于趙襄子對其失意嫡兄伯魯的同情,故將其子周封于代地,以作彌補。[8]平原君亦因親親得封,“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而以國人無動,乃以君為親戚也。”[9]“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10]又有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10]《集解》注曰:“《戰(zhàn)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由以上三例推之廬陵君(趙孝成王母弟)、春平君(趙故太子)皆因其為趙室宗親而得封。之于秦國在秦昭王少時,宣太后大權獨攬,封其二弟為華陽君、三弟為涇陽君、四弟為高陵君,此三君與穰侯(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一起號稱秦國“四貴”,再有魏國信陵君(魏安厘王之弟)皆因親親得封。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舊有分封原則即“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11]的繼承。
(三)因歸降或獻土得封
戰(zhàn)國紛爭不斷,且消耗或傷亡巨大。為減少傷亡,各國多封敵國降將為君,此不失為兩全之計。既能收敵國之將,又能保存實力減少傷亡,甚至還能收到震懾他國之效。《史記·趙世家》載“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封地”,[2]1823《集解》徐廣曰:“故秦降將也。”又有燕國樂毅受齊田單反間計之困,畏燕惠王之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關津,號曰望諸君。”[3]直接原因就是“尊寵樂毅以警動燕齊。”[10]另外,又有獻土得封;趙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太守馮亭將韓國的上黨郡“再拜入趙”,[2]1823《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zhàn)死于長平。”[12]
(四)因逃亡得封
田忌與成侯鄒忌不善,恐誅,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于齊。”田忌謀士杜赫使計勸楚宣王令田忌留楚,并“封之于江南”。[13]
(五)因色、寵得封
江乙說于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不然,無以至此。”又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于王,竊為君危之。”可見安陵君壇為楚宣王寵臣。后來為了穩(wěn)定個人地位,以色相侍奉楚宣王的壇,不惜用宣王死后以身殉葬的誓言來打動宣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13]趙國的建信君也因受趙悼襄王寵幸而受封。[13]另外,《戰(zhàn)國策·趙策四》“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向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14]楊子彥在《戰(zhàn)國策正宗》中注曰:“春平侯,趙國寵臣,當是因寵得封。”[13]但因寵得封最著名的當為龍陽君,此點在《戰(zhàn)國策·魏策四》的《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一篇中有詳細記載,此不贅述。
三、“君”號下各國封君之數量
關于戰(zhàn)國時期封君數量問題,前人做過一些研究,如楊寬《戰(zhàn)國史》中所附《戰(zhàn)國封君表》對各國封君做了較為詳實的考證。筆者依據此表將封君的定義標準進行了再統(tǒng)一,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封君定義標準及趙國封君數量
關于趙國封君,各家對封君數量的考訂觀點不一。楊寬在其《戰(zhàn)國史》中記述趙國封君有27位;何浩認為趙國封君有26位;白國紅認為趙國封君有21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家定義封君的標準不同。白國紅分析,封君與封地根本不同,有封地的不一定有封號。如:齊國的田文在趙國擁有封地武城,卻并沒有被賜予封君封號。反之,有封號的也不一定有封地,如建信君就是有封君之號而實無封地。楊寬將田文、黃歇、魏無忌、秦之長安君(分別被趙賜予武城、靈丘、鄗、饒為食邑)也都歸為趙國封君。他們的定位標準是先得出何為封君的結論,再討論具體人物是否為封君。這一點筆者認為不妥,因為有的受封者僅僅是被賜予食邑,并不為受封者所有;另一方面,有些受封者縱然獲得食邑也只能食其租稅,并無政治、軍事等特權;再者,若受封者也無封號,那么將其劃入封君之列也未免有些牽強。在這里,根據受封者的實際情況,有封地的稱號未必是“君”,而稱“君”者未必一定有封地。所以,筆者去除這類有封地而無“君”號之稱的受封者,總結趙國封君共有22位,但封君有失考者或無載者(如張孟談、平陵君、襄安君、晉君等),實際受封者的數目肯定是要多于此數。
(二)楚國封君數量
關于楚國封君,其一,《戰(zhàn)國策·楚策四》有提到蔡圣侯。楊子彥考之,認為歷史上無蔡圣侯,當為高蔡國(在楚國西南)的國君。故不列。其二,蘇秦亦為封君。《戰(zhàn)國策·齊策三》下《楚王死》一篇中載有:“又使人謂楚王曰:‘……今人惡蘇秦于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愿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于楚也’”。[15]由此推之,蘇秦當是楚國封君無疑。其三,《戰(zhàn)國策·楚策一》中《威王問于莫敖子華篇》有云:“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16]楊子彥注曰: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楚昭王司馬沈尹戌之子,字子高,封于葉,所以稱葉公子高。既然葉為封地,則其可能也是受封者之一。因其為孤證,存疑,故不列。其四,對于郎陵君的身份學界有過一些爭議。何琳儀認為郎陵君當為春申君;李學勤根據江蘇無錫前洲公社出土的三件楚國郎陵君有銘銅器認為:“墓主是郎陵君王子申,封地必在無錫附近,只能在春申君黃歇被李園刺殺以后,即公元前237年之后。他可能是楚幽王之子,也可能是其弟。”經何浩所證,當從李學勤之意見。故楚封君數量為30。
(三)秦國封君數量
秦國封君人數僅次于楚國封君,有20余人。其中尚有存疑者:其一,孫國志所列的被封于平陽的秦公子白。《儀禮·喪服》有云:“君,謂有地者也。”[17]但前文已經提到封君與賜地完全是兩回事,并且有眾多事實證明有封地的不一定是封君。雖《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卒,“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6]但并未有史料明言其為平陽君。再者,秦武公(前697—前678年)時正處于春秋早期,新式的地主階級封君制度尚處于萌芽階段,即使到了春秋末期也未興盛,傳統(tǒng)的宗法分封制仍是慣制。公子白被封于平陽當是分封制的表現,即諸侯分封卿大夫(大宗分封小宗)的表現。將封地作為他們的食邑,有封地之實,而無封地之號,故不列公子白為平陽君。由此推之,《戰(zhàn)國策·韓策三》所載之南鄭、梗陽、平原列于此也屬牽強,當存疑不計;其二,白起有封號而無封地。白起之封為武安君乃因其軍功,漸次被封。按,秦功拔武安在昭王四十八年,且為王齕伐取,白起為武安君時,秦未攻取武安之地,秦不可能封白起于未得之地,故武安之封與封地無涉,當為封號而已。其三,秦國封君中較特殊者有羋戎、公子煇二人。較其他封君不同的是,二人不僅各有封地二處且有兩個封號,且均有史明載,遂計封君數為4。故統(tǒng)計秦封君總數為23位。
(四)齊國封君數量
齊國封君中較為特殊者,首先,當為無鹽君鐘離春。其為一女子而受封,不僅擁有封號而且擁有封邑。然其封號封邑并非因色得封,緣于鐘離春恰恰是一丑女子,四十歲不得出嫁,自請見于齊宣王,陳述齊國危難四點,為宣王采納,立為王后。于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進直言,選兵馬,實府庫,齊國大安。如此功勞,在戰(zhàn)國紛爭的年代里,男權主義極強的環(huán)境下,泛泛之輩實難為之,更何況一女子。這正是無鹽君鐘離春的特別之處,非龍陽君等受封者所能比之。其次,即靖郭君與孟嘗君的封號是因地得封還是因謚得封的問題。司馬遷在《史記·孟嘗君列傳》中云靖郭、孟嘗曰謚;鮑彪為《戰(zhàn)國策·齊策一》做注亦言“靖郭君,田嬰謚”,[18]《正義》言孟嘗亦為謚;然錢林書在《戰(zhàn)國時期齊國的封君及封邑》中根據司馬貞《索隱》、梁玉繩《史記志疑》、陳直《史記新證》持靖郭、嘗為地名的觀點,二者當是因地得封。三家所證皆能自圓其說。然因史料不全,爭議尚存,不可輕下定論。暫陳于此,留待考證。再次,是蘇秦亦在齊國受封,《戰(zhàn)國縱橫家書》十七有載蘇秦為武安君而相秦,當時齊閔王末年(公元前284年)。當時有人游說主持伐齊的秦國御史起賈,提到此時齊國如投靠魏國,是“武安君之棄禍存身之訣也”[19]此與蘇秦在趙國受封在時間上較為契合,當亦是齊國封君無疑。最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云:“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20]此句注曰:“蓋(ge),齊國地名,是陳戴的食邑。”陳戴雖有蓋地,但史料未明其封號,劃為封君與否,當待論之,故不列。則齊國之封君所能明證者除陳戴外,可考者當有6位封君。
(五)魏國封君數量
關于魏國封君,其一,雖將魏襄王時的公子勁列入封君,然其封號、封地因史料不全,并不盡知。《史記·秦本紀》載:“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6]《索隱》注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由此看出,魏公子勁在此受封之前其實早就有自己的封地,此“諸侯”并非指宗法分封制五等爵制下的諸侯,僅是其地位與諸侯的地位相當,則公子勁為魏之封君無疑;其二,成侯當有封地。《戰(zhàn)國策·魏策四》載魏安厘王時,安陵君對信陵君的大使說:“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大府之憲”,[21]由此得之。則魏有17位封君。
(六)韓國、燕國封君數量
韓國封君大多考證詳實,共計7位封君。關于燕國封君,其一,昌國君有兩人:一為樂毅,一位樂間,二人為父子關系,封號、封地為承襲關系。燕惠王時,樂毅為燕將于公元前284年攻破齊國70多座城池,因功封為昌國君;后因齊反間計燕惠王使騎劫代樂毅為將,樂毅奔趙。惠王后來極悔,又以樂毅之子樂間承其封號,為昌國君。封君之世襲在燕國極其少見,而樂間之世襲樂毅為昌國君,確實又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出現的。其二,蘇秦亦為楚國封君。《史記·張儀列傳》有載“……蘇秦,封武安君,相燕。”[22]燕昭王于公元前295年派蘇秦出使齊國,以武安君封之,并受之以相國之尊位,可謂備受恩寵與器重。后來蘇秦獻書燕王云:“以求卿與封,王為臣有之兩,臣舉天下使臣之封而不慚。”由此得之。其三,襄安君之“襄安”作為一個名詞最早出現在《戰(zhàn)國策》一書中:“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風,事必達成。臣又愿足下有地效于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14]“襄安君”是燕國王族,燕昭王時封君,為燕昭王之弟,昭王曾派他到齊國活動。此“襄安”系作為人名出現。是否以封地為名,燕國的封地又如何會在楚地,這些問題均無從查考,故雖云“襄安”,實在與襄安這一地名聯系不上。概計燕國封君為6位。
四、結語
封君制度自創(chuàng)立之始,就成為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封君封號的形式主要有封地、“謚”號、雅號、原籍四種;封君獲得名號的原因主要以“因功得封”及“親親受封”為主。通過分析封君封號表現形式及獲得名號的原因,可以感受其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正如大多數史家所總結的:一因功受封;二因親親受封。[23]此法頗具概括性,不無道理。但有些封君畢竟既非因地受封,也非親親受封,或因獻土得封,亦或因色受封,故不應當簡單劃于前兩點之下。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此兩種受封形式中所占比重最大,是戰(zhàn)國時期最主要的受封形式。正如蘇秦所言“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11]也如《管子》中提及的“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名者,割壤而封。”[24]另外,關于戰(zhàn)國時期各國封君數量的考證表明:楚國封君最眾,其次為秦國、趙國,封君最少者為燕國、齊國。從中也不難得出楚、秦、趙三國封君制度較為發(fā)達成熟而燕、齊二國則較為緩慢滯后。
[1][漢]司馬遷.樗里子甘茂列傳(《史記》卷七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59:2308.
[2][漢]司馬遷.趙世家(《史記》卷四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漢]司馬遷.孟嘗君列傳(《史記》卷七十四)[M].北京:是中華書局,1959:2352.
[4][漢]司馬遷.春申君列傳(《史記卷》七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95:2394.
[5][漢]司馬遷.廉頗藺相如列傳(《史記》卷八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95:2448.
[6][漢]司馬遷.秦本紀(《史記》卷五)[M].北京:中華書局:1995:220.
[7][漢]司馬遷.六國年表(《史記》卷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1995:694.
[8]沈長云,等.趙國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2000:576.
[9][漢]司馬遷.平原君虞卿列傳(《史記》卷七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1995:2369.
[10][漢]司馬遷.魏豹彭越列傳(《史記》卷九十)[M].北京:中華書局,1995:2589.
[11][漢]司馬遷.蘇秦列傳(《史記》卷六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1995:2245.
[12]許嘉璐.二十四史全譯(漢書)[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1617.
[13]楊子彥.戰(zhàn)國策正宗[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14][西漢]劉向.趙策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67.
[15][西漢]劉向.齊策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70.
[16][西漢]劉向.楚策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15.
[17]李學勤.十三經注疏(標點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61.
[18][西漢]劉向.齊策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05.
[19]謂起賈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69.
[20]楊伯峻.孟子譯注(全二策)卷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8:159.
[21][西漢]劉向.魏策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15.
[22][漢]司馬遷.張儀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95:2292.
[23]劉澤華,劉景泉.戰(zhàn)國時期的食邑與封君述考[J].北京師院學報,1982(3).
[24]謝浩范,等.管子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