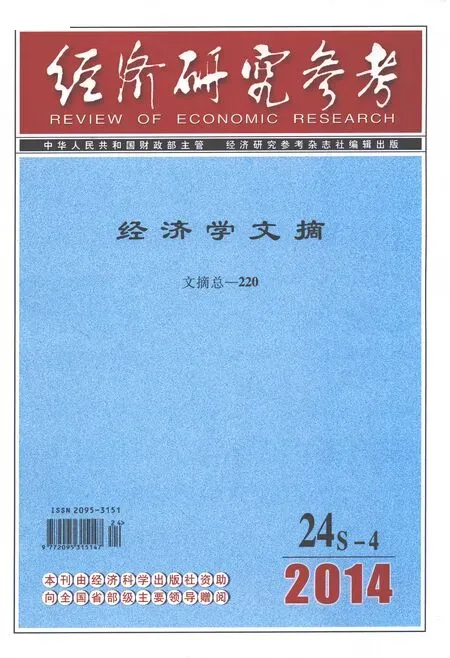省直管縣改革與地方公共教育供給
呂凱波
1.教育支出遵循漸進主義決策模式。以往年度教育支出比重高的縣(市),本年度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也會高。當沒有控制年份固定效應時,無論是差分GMM的估計結果還是兩步系統GMM估計結果都表明上一年教育支出比重對本年影響為正,而兩年前教育支出比重的影響為負,這可能是遺漏年份固定效應造成的。在加入年份虛擬變量之后,一年前和兩年期的教育支出比重對本年教育支出比重的影響都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地方政府在安排教育支出時遵循了漸進主義的決策模式,呈現了增量預算的特點。當然,這也是執行《教育法》相關規定的反映,“各級人民政府的教育經費支出,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在財政預算中單獨列項。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保證教師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
2.省直管縣式財政分權改革降低了地方公共教育供給。在沒有控制時間變量時省直管縣改革與地方公共教育的估計十分顯著,而在加入年份虛擬變量后,省直管縣虛擬變量與公共教育的關系不再顯著。財政分權度則不論在差分GMM估計還是系統GMM估計,也不論是否考慮年份固定效應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可以說縣域經濟增長導向下的省直管縣式分權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公共教育的供給,本文的研究假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這不僅與靜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一致,也與王聞等(2011)和劉佳等(2012)的結論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認為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在縣域經濟增長和通過地方性公共品的提供來改善民生的選擇中大都選擇了前者,在扭曲性的官員考核機制下造成了地方財政資金的錯配,教育等公共服務支出雖然有《教育法》為保障,但仍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3.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學生人口比重與教育支出比重正相關而工業化進程與教育支出比重負相關。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教育支出的正相關性可能是地方政府踐諾教育支出“追4”的體現,雖然大部分縣市與4%的目標值仍有一段距離,但隨著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縣域經濟的發展,這一距離在不斷縮小。學生人口比重與教育支出比重的正相關也符合預期,財政支出的安排往往同人口統計結果密切相關,支出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體的支出偏好,如同老年人口比重越高社會保障支出比重越高一樣,學生人口比重高的縣市,學生群體在預算安排中的“話語權”較大,相應教育支出比重會有所提高。工業化進程與教育支出比重的關系雖然與經典的瓦格納法則、馬斯格雷夫假定相違背,卻體現出了省直管縣式財政分權的基本特征,縣級政府為了發展縣域經濟把大量財政資金用于建設性支出,以此推進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結構的轉變。尤其是取消了農業稅之后,工業和第三產業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稅源,因而在縣級地區出現了以犧牲教育為代價的工業化進程。
(成林摘自《地方財政研究》2014年第3期《省直管縣改革、財政分權與地方公共教育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