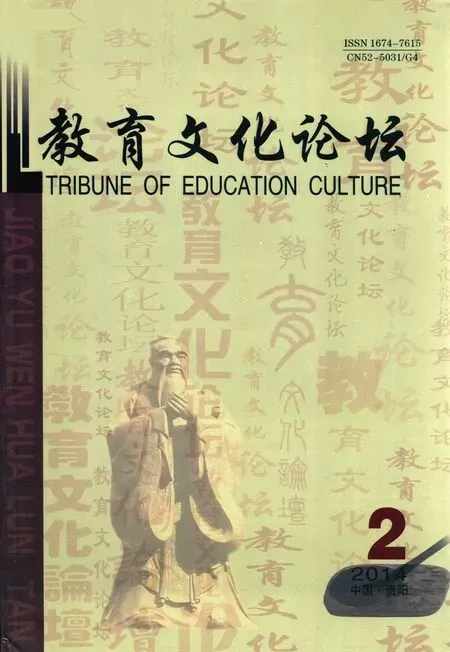龍圖騰:基于多元一體語境的中華民族認同
馬 昀 徐則平
(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大學人民武裝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中華民族不分地域和族群,歷來都以“龍的傳人”自稱。在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5000多年中,東方文明里唯一一個無可取代的特殊符號便是龍圖騰,倘若抹去龍圖騰符號,東方文明可謂不甚完整。論其地位和影響力,從宏觀到微觀——從中華傳統文化到民族心理再到每一個中華民族個體的內心深處,龍圖騰符號無所不在,可見一斑。現實中的龍并不存在,而龍圖騰符號本身只是上古先人的觀念意識物質化。摩爾根在其著作《古代社會》中表明,圖騰是氏族社會的“徽志”,它就好比是一個商標或品牌,通過它來分曉自身族群與他者,使族群內部達成互相認同的狀態。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更深層的指出,圖騰所被賦予的神性和主宰力量,即是源于對氏族社會本身的維系。可見,圖騰對于民族國家的構建具有非凡的凝聚力。中華民族使用蛇、鹿、兔、牛、鷹、虎等九種動物的多元部分,拼湊匯合一體,形成獨一無二的龍的形象,其多元一體的深刻意蘊,是上古先人留給我們打造民族認同,構建民族國家不可多得的契機。[1]
一、龍圖騰符號的多元與一體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龍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在此,我們把龍圖騰符號分為龍的造型、龍的本質、龍圖騰所蘊涵的文化三個層次進行剖析。
從造型上來說,早期中國的原龍是以動物為想象藍本的,形象接近蛇、鱷魚等動物,在原始社會中還有近10余種形象接近其他動物的龍的原型,氏族社會時期的龍的形象是現實中存在的單一的某種生物。[1]而到了文明社會初期,人類把蜥蜴類和鱷類等爬行動物統稱為龍,并創造出雜糅多種動物造型的龍的造型,也是對龍圖騰符號的一種創新解讀。
從本質上來說,龍是一種神靈動物,同時亦是古代氏族社會的圖騰。龍是“九似之獸”,在中國的圖騰中象征著神靈,是有神性的,而這種特殊的圖騰本質上是中華民族的標志,從一個側面表征著中華文明。
從龍圖騰符號所蘊涵的文化來看,龍還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中華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中國古代有很多關于龍的神話傳說,把它們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龍。龍是一種綜合了牛頭、羊須、鹿角、馬鬃、蛇身、蜃腹、魚鱗、鷹爪、虎掌一體多元的圖騰符號,這反映出中華民族形成的復雜性和文化的包容力。}多元的動物造型、豐富的文化內涵,幻化于“龍”這一體,深刻闡釋了多元與一體的融合。
多元的動物造型意味著多元的文化,正是由于多元的文化交融、匯總于華夏之地,造就了龍圖騰符號的“多元”特征。而論其本質屬性,歸根結底,當屬“一體”。龍圖騰是一個整體符號,它不僅體現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成長史,更體現出歷經五千多年而經久不衰的民族哲學思想和民族文化精髓。當然,不可否認我們敬畏龍圖騰符號所包含的每一種動物圖騰的形象,但它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表征出中華民族的身份,不能勾連起子子孫孫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龍圖騰符號的多元孕育于一體之中,倘若割裂開一體,便不能傳遞出龍文化的精髓,自然也就不再具有圖騰符號所共有的號召作用、凝聚作用、和認同作用。鑒于此,民族理論學界應格外關注龍圖騰符號的“一體”屬性所傳遞出的對于構建中華民族認同的不竭動力。
二、崇拜龍圖騰的中華民族研究
自從中華大地上出現龍圖騰符號后,中華民族祖祖輩輩就一直崇拜“龍”,幾千年來始終如一。因此,龍圖騰文化伴隨著五千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人類文明史中為數不多沒有中斷的圖騰文化之一。龍圖騰崇拜的演化,可以籠統分為蒙昧野蠻時代的龍圖騰崇拜和文明時代的龍圖騰崇拜,具體的說,進入文明社會后的龍圖騰崇拜,隨著朝代的更迭,大致以夏朝、秦漢、宋朝、清朝等為重要的發展節點。
原始社會的龍圖騰崇拜主要發祥于距今8000-6000年前的紅山文化。1935年在內蒙古赤峰的紅山遺址中出土的玉器龍被考古學界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龍圖騰器物。這則玉器龍豬首龍身,出土時處在棺槨中尸體的胸前,在表現出墓主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的同時也說明了龍圖騰的崇拜在當時就已盛行。眾所周知,幾乎所有的脊椎動物的脊椎胚胎演化都是從彎月形態開始的,無論是較為低等的水生脊椎動物的早期脊椎胚胎還是人類的早期脊椎胚胎。這則世界上最早的龍圖騰器物也是呈現出幾乎首尾相連的彎月形態,而當時的醫學遠不足以探知動物的脊椎胚胎演化過程,所以,這則神秘的玉器龍飽含著中華民族對生命孕育天然的領悟力和對生命創造天然的敬畏感。[3]
龍圖騰符號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中大多是以兇神形象出現的,其在夏朝僅出現在祭祀專用的青銅禮器上,當時的龍圖騰符號常伴隨著螺旋紋樣,且使用頻率遠不及后世,說明龍圖騰符號在當時尚處在發育期。進入周朝后,龍圖騰符號和鳳圖騰符號在使用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使用范圍局限在祭祀禮器上沒有擴大趨勢,而且鳳圖騰的出現頻率一度超過了龍圖騰,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個別地方的龍圖騰符號被移植進了鳳冠,呈現鳳冠龍頭狀。這大大弱化龍圖騰符號作為兇神的猙獰和威嚴,平添了一絲柔婉感和藝術感。到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的社會狀態使得嚴謹的宗教秩序和祭祀禮儀出現了松動的跡象,龍圖騰符號的使用范圍隨之出現了漫延趨勢,從之前作為兇神出現在祭祀用品,發展到使用在林林總總的青銅器具上,鏡臺、酒樽、門環等等。
百家爭鳴的社會狀態發展到秦漢時,儒學和道教已經被廣為接納,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情結之中,這使得龍圖騰符號也隨之廣為盛行,發展空前成熟。其具體表現為不同于先前的符號變體化、多體化,龍圖騰符號大多呈現出統一的造型,有了公式化、固定化的趨向。秦始皇劃時代的開辟出皇帝乃是真龍天子的先河,隨后在中華民族的民族觀念里龍圖騰符號多包含的寓意不僅僅是兇神和瑞獸,更是神靈下到凡間化身成一國之君。
宋代是龍圖騰符號演進中又一座里程碑。此時,龍圖騰符號已從秦漢之際的統一刻板、簡單粗略,越來越呈現出栩栩如生,繁復逼真的特征。例如,在細節處理上,龍圖騰符號開始以有龍鱗的形象居多;在呈現方式上,龍圖騰符號開始成對出現在廊柱、成組出現在畫卷中;在使用意義上,龍圖騰符號開始剝離圖騰的精神內涵,僅僅以裝飾物品的形式大范圍頻繁出現。此時民間興起了“九似三停”的畫龍技藝,可以說,龍圖騰符號已然從宗教象征進入世俗生活,從祭祀神壇走向民間日常。這套民間畫龍技藝的廣泛認同,為元明清時期畫龍風尚確立了標準,同時又推波助瀾增強了龍圖騰符號的審美旨趣,推動了其在純美術領域的深化發展。
明清時代,龍圖騰符號成為皇權的象征和標志,地位達到空前的制高點。而實際上,物盛極則衰,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即便以真龍天子為詔諭,封建首領集團終究逃脫不了從盛極一時走向衰敗沒落的命運。明清之際龍圖騰崇拜作為皇家崇拜,其老態龍鐘氣象已經顯露端倪了,}時間進入20世紀,龍圖騰符號作為皇室符號的表征意義也進入了歷史博物館。現代社會的龍圖騰符號作為傳統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寓意著祥和的好兆頭,出現在民生百態之中。中華民族作為“龍的傳人”,龍圖騰符號表達為每一位中華后人對祖國深沉的認同身份。世界各地的華人以“龍的傳人”為圖騰的火把,無論置身何處總會把中華民族同宗同源的圖騰認同之火熊熊燃燒于內心,龍圖騰也就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生動寫照。
三、以龍圖騰符號為契機,鞏固中華民族認同
中國民族學界巨擘費孝通先生曾于上個世紀80年代針對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進行了深入探究。他指出,通常我們在提及“長期生活于中國大陸的五十六個民族”、“香港、澳門、臺灣同胞”、“海外華人”這幾大群體時,運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介于此,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中的民族認同體系應當包括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微觀上主要針對的是五十六個下位民族之間的認同問題,以族群屬性作為劃分標準,中觀上主要針對的是香港、澳門、臺灣華人與本土華人之間的認同問題,以社會制度作為劃分標準,而宏觀上主要針對的是海外華人群體與本土華人群體間的認同關系問題,以國界、國籍作為劃分標準。既然同屬中華民族,同為“龍的傳人”,那么我們理所當然應以龍圖騰符號為契機,以鞏固中華民族認同為己任。
(一)鞏固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
狹義的中華民族是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所有下位民族的統稱,[5]而民族認同關系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認同語境中的焦點。從微觀上講,民族認同包括個體對本民族的認同心理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兩個層次。對于本民族的認同心理是下位民族認同,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是上位民族認同,兩者之間并不矛盾。[6]龍圖騰符號作為飽含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歷史積淀的文化精髓,無論對于漢族還是對于少數民族同胞來說,都具有強大的感召作用、凝聚作用和認同作用。而其所蘊涵的九種動物于一體的特征,又恰如今日的中華民族包含著五十六個下位民族于一體。因此,龍圖騰符號理應成為維系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認同心理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的橋梁,成為鞏固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文化認同的基石。
(二)鞏固本土華人與港、澳、臺華人之間的文化認同
本土華人與港、澳、臺華人之間的認同關系問題,實質上,是基于多元一體語境的中華民族認同問題。隨著上個世紀末中國陸續收回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當地華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沖突問題已然不復存在。然而,鑒于臺灣地區的特殊性,仍有部分華人,尤其是出生在和平和繁榮發展一代的年輕人,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上,始終存在疑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認同語境下分析認同問題,具有其獨特的優勢,[6]完全可以運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認同,尤其是龍圖騰符號的認同,來研究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同胞之間的認同關系。
中觀層面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中的“一體”,注重的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統一。雖然由于歷史原因具有特殊性,還無法實現國家和社會制度的完全統一,[6]但必須承認,香港、澳門的華人都已納入中國國籍,腳下的土地也屬于中國領土范圍。中觀層面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中的“多元”,注重的是社會制度的多元化選擇。事實上,多元的社會制度與中華民族認同并行于不同的時空領域,可以相互協調、相互兼顧。一體與多元,分屬思想認同層面和社會制度層面。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應用于大陸與港、澳、臺同胞之間的認同關系研究中,是統籌兼顧中華民族認同與社會制度差異的必然選擇。[6]而龍圖騰文化,作為得到大陸與港、澳、臺同胞普遍信仰、共同崇拜的文化符號,理應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兩岸三地一盤棋中最有力度的一顆棋子,為鞏固大陸與港、澳、臺同胞之間的文化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鋪路,為構建民族國家奠基。
(三)鞏固本土華人與海外華人之間的文化認同
中國與海外華人同為“龍的傳人”,兩方之間的認同關系問題,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認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值得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將海外華人單純的理解為海外漢族。五十六個民族中,苗族、滿族、黎族、京族、維吾爾族等眾多下位民族都有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成員,這些跨境民族的同胞都屬于海外華人。作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這些海外華人群體的認同心理相比港、澳、臺華人群體更加具雙層性:一方面產生了目前居住國的認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認祖歸宗的中華民族認同心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心理主要源于血緣和文化的傳承,而對居住國的認同心理,則主要源于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和社會交際網絡,兩種認同心理可以并行不悖。[6]民族認同心理是聯絡本土華人與海外華人之間的心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尤其是龍圖騰符號的心理認同和文化認同,完全能夠適用于海外華人研究,并為處理中國與海外華人的認同關系提供一種思路。
宏觀層面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語境中的“一體”,側重于民族認同情感的角度。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很多出生在當地的華裔對中華文化,特別是龍圖騰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并以具有中華民族的血統為榮。民族認同情感是將海外華人維系在一起的基本要素,也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一體”。[6]本國華人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認同關系,必須得到審慎地處理,尤其是在中國國際影響不斷擴大的今天,應該用全局性的眼光看待海外華人的積極作用。[6]多元一體語境下的中華民族認同,特別是得到所有華人心心念念向往和崇拜的龍圖騰文化,無疑適用于中國與海外華人的認同關系研究,在此框架下,更加便于海外華人恰當地處理其中華民族認同情感與所在國家認同情感之間的關系。
[1]曹薿丹.淺談龍圖騰的含義與民族性[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2(10):62-65.
[2]段寶林.中華龍圖騰淺說[J].文化學刊,2012(5):102-112.
[3]李玉山.走向世界的中國龍文化[J].學理論,2008(2):131-137.
[4]李玉山.中華龍文化的演化內涵和意義[N].今日信息報,2008-05-26.
[5]周文.佤族心理認同的代際差異研究[D].云南大學,2012.
[6]郭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三個層次[J].東方論壇,2011(5):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