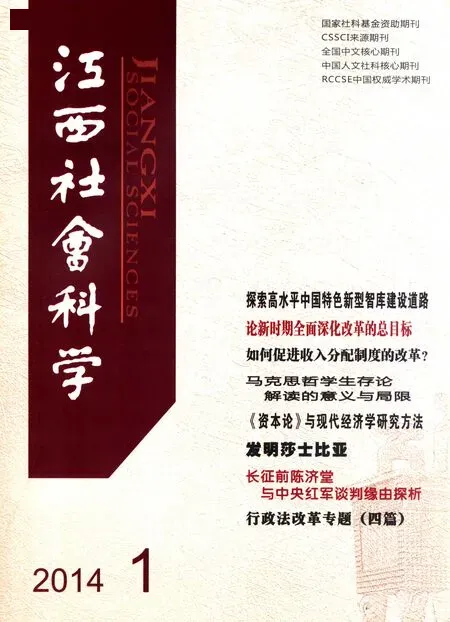道德的個體價值
■陳偉宏 黃巖
當代道德問題的主要原因在道德信仰危機,即人們不是不清楚“我應該遵循什么樣的道德”,而是開始質疑“我為什么需要有道德”這一根本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注重正面積極的應然教育,如:人“應該”講道德,為了成就道德“應該”無條件地舍己、奉獻,甚至自我犧牲。但問題是,個體為什么需要有道德?換言之,道德行為是否具有個體價值?如果沒有,個體又怎能自覺自愿地循“道”而為呢?從道德“求善”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似乎是多余的。但個體總是要食人間煙火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時為了自己的某種需要和為了這種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P286)。因此,深入研究“道德”行為的個體價值,對于激發主體的道德自覺性,增進主體的道德幸福感,便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道德是個體在社會中賴以生存的必要前提
人的生存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生活,人“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2](P6)。馬克思反復指出,那種把單個的、孤立的個體當作歷史出發點的觀念,是屬于“缺乏想象力的虛構”、是“美學上的假象”。[2](P5)人類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兇猛動物的威脅而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社會性,在于人們之間結成了一定的社會關系,變弱小的個體力量為強大的群體力量。
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群何以會形成克己利人之類的美德?對此,哲學家們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解讀。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是兇惡的動物,每個人活動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自我保全,并按照“趨利避害”的原則行事,“如果兩個人想取得同一東西而又不能同時享用時,彼此就會成為仇敵”[3](P93)。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綿延不斷的戰爭中,無論什么時候,誰都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來保全自己。基于安全和自保的需要,人們通過理性的指導,制訂了相互交往必須遵循的道德法則。所有達成和平的手段,如“和平、正義、感恩、謙謹、公道、仁慈以及其他自然法……它們都是美德,而其反面的惡行則是惡”[3](P120)。只有遵循這些美德行事,人類才能擺脫“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3](P95)的黑暗生活。
洛克則認為自然狀態是處于和平、自由、平等的狀態。但由于每個人對未來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判斷,而且在追求私利過程中常常感情用事,這樣就容易陷入戰爭狀態。“凡用語言或行動表示對另一個人的生命有沉著的確定的企圖,而不是出自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就使自己與他對其宣告這種意圖的人處于戰爭狀態。”[4](P12)為了在自然狀態和戰爭狀態之中找到一種平衡,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人們就有必要讓渡出自己的部分自由,接受共同的道德準則。那些被尊為有美德的行為,皆因其對社會的保存是絕對必需的,而那些不利于共同體聯結的原則,則被認為是不好的和惡劣的。
霍布斯和洛克的抽象人性論有著明顯的不足,他們提出的自我利益優先于社會或他人利益的原則也值得我們反思,但以他們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思想無疑是深刻的。人類道德的產生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上帝的啟示,更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超人境界,而是來源于我們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正如J.P.蒂洛所言:“道德的產生是由于人類的需要,由于認識到以合作的和有意義的方式共同生活的重要性。”[5](P30)
馬克思克服了以往抽象人性論的缺陷,將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對人的考察。“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1](P31)在原始社會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人們為了獲取食物、抵御惡劣的自然環境,就必須以原始平等的方式來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并將勇敢、頑強、勤勞、協作等視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對于每一個個體而言,只有遵循這些道德規范,得到集體的庇護,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否則,就意味著死亡的來臨。恩格斯曾以易洛魁人“血族復仇的義務”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同氏族人必須互相援助、保護,特別是在受到外族人傷害時,要幫助報仇。個人依靠氏族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這一點;凡傷害個人,便是傷害了整個氏族。”當然,在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的原始社會時期,“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6](P101),個體也僅僅是無條件地服從氏族整體的共同利益,并將其作為自身的行為準則。
隨著勞動分工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個人與群體的直接同一也遭到了破壞。原始純樸道德遭遇到空前的沖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出現了,“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也出現了。[7](P113)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利益的沖突與對抗,使得社會關系的和諧秩序經常遭到破壞,進而危及社會整體和個體的存在。為什么貪欲、情欲和物欲等冷酷的社會環境并沒有摧毀一切,是什么力量引導著人類不斷前行?究其原因,就在于人類總是有一些共同需要(比如維護生命的存在),人際關系越是惡劣,就越彰顯這種共同需要,道德發生的動力也就越大。正如蒂洛所言:“一切人都有許多共同的需要、愿望、目標和目的。例如一般地說人們在自己的生活中似乎都需要友誼、愛情、幸福、自由、和平、創造性和安定,這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也是為了別人。為了滿足這些需要,人們必須確立和遵循這樣的道德原則,這些原則鼓勵他們相互合作,使他們不必擔心被殺死、被殘害、被偷竊、被欺騙或欺詐,被嚴格管制或監禁。”[5](P30)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蓬勃興起和發展,生產越來越社會化,人際關系也越來越復雜化,人們對互助、友愛、同情之類美德的需求也愈來愈強烈。核武器、生化武器以及盲目生產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如果不能有效加以控制,隨時可能造成整個人類的毀滅;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人與人的交往方式被“人與機器”的交往方式所取代,導致了人際關系的冷漠,催生了“單向度的人”、“孤獨的人”的產生;激烈的社會競爭、快節奏的生活方式,極大地加重了現代人的心理壓力,心理疾病人群隨之增加……1988年1月,全世界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集會,尋找能使“人把自己的命運引向太陽而不是引向深淵”的答案。大會結束發表的宣言呼吁:“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智慧的核心就是“仁”,就是“知人”、“愛人”、“泛愛眾”、“愛類”、“愛物”的倫理智慧。事實上,“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換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1](P515)。社會分工越是復雜,情況越是如此:老師幫我們教育孩子、農民幫我們種植糧食、警察維護著我們的人身安全……誠然,助人者在遇到危險時,也不一定會有人去幫他,但一個人人自保的社會,只能是人人自危的社會,因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在最需要別人的時候能得到幫助。選擇謹守道德底線的人多一些,社會的正能量就會上升一些,我們在困難時遭逢的生存危機才會少一些。
二、道德是個體在交換中獲取利益的根本保障
康德是典型的道德義務論者,在他看來,只有不計任何利害得失,單純為義務而義務的行為才是道德的。受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觀點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學界也存在著類似的看法,即認為講道德就是要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個人利益,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利益和好處。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堅決批判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認為不存在所謂的“道德法則”:“康德只談‘善良意志’,哪怕這個善良意志毫無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這個善良意志的實現以及它與個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間的協調都推到彼岸世界。”[1](P211-21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道德只能從社會實踐的經濟利益關系中才能得到說明。正是人類利益和利益關系的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才造成了道德在人類生活世界的普遍性和現實性。羅爾斯在談到社會何以需要正義時也提到:“由于這些人對由他們協力產生的較大利益怎樣分配并不是無動于衷的 (因為為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每個人都更喜歡較大的份額而非較小的份額),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利益的沖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則來指導在各種不同的決定利益分配的社會安排之間進行選擇,達到一種有關恰當的分配份額的契約。”[8](P2)這些所需要的原則就是道德的原則,借助于道德觀念、道德準則等形式,道德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
“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里的“人”不僅指“類”的人,更指“個體”的人。對個體來說,離開“我”的利益來談道德,在非常態的特殊場合下,可以,但在常態化條件下,不可以。離開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只能是深谷幽蘭,雖令人贊嘆敬畏,卻難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馬克思認為,在現代市場社會中,“表現為全部行為的動因的共同利益,雖然被雙方承認為事實,但是這種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動因,它可以說只是在自身反映的特殊利益背后,在同另一個人的個別利益相對立的個別利益背后得到實現的”[9](P196)。他還鮮明地指出:“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1](P34)鄧小平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時也提出,只講犧牲精神,不談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看到了道德“應當”與“正當”之間的不同,不講物質利益,“對一部分人可以,對大部分人不可以,對少數人可以,對大多數人不可以,一段時間可以,長時間不可以”[10](P136)。
事實上,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非常重視利益調節在道德中的重要地位。理論上,我國既有“人非利不生”的觀點,也有“德福一致”之說,在西方更是有悠久的功利主義傳統。就行為者個體而言,強調道德的功利性確實凸顯了強烈的世俗塵世性,但從實際生活來看,人們遵守道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能給個體生活帶來利益與好處。諾齊克反復強調,“互利的協調”是道德倫理的“第一功能”。之所以強調“互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社會的動物,個人的習慣和行為只有有益于社會和他人,才能得到社會和他人的贊許,并從社會和他人那里得到相應的利益。反之,他就會成為社會和他人譴責的對象,他的生活也將無所依托。主張“兼愛”的墨子對此認識非常深刻,他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美國早期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本杰明·富蘭克林是一個崇尚美德的人,他認為自己在財富、聲望和名譽上的成功正是源于對美德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以自身的經歷諄諄告誡年輕人:“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并善于利用這些錢,那么,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11](P33-34)
有人也許會說,“講道德”未必能得到相應的利益回報,甚至有時還會遭到人家的挖苦、嘲諷。“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但它是非本質的、個別的現象。任何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其行為必然會有高尚與卑鄙之分,但總體而言,人心總是向善的,社會輿論最終是公正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另外的經濟事實已經出現,由此原來的事實就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4](P204)換言之,一旦人們普遍地不能忍受某種道德,其原因可能就在于這種道德不能再給人帶來利益,這種道德就已經過時,人們遲早會拋棄它并另外尋找新的道德原則與根據。
強調道德實踐與利益獲得的密切聯系,并非純粹實用主義的觀點。它所關注的焦點是:社會應構建起賞罰分明的利益分配機制,行善就應該而且也能夠得福。只有在宏觀上創造“吃虧是福”的合乎人性的社會道德環境,讓每一個成員確信自己的個人利益就在他捍衛、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之中,人們才能在感受德行美好的同時享受到德行帶來的實際利益,進而自愿自覺地履行道德義務,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自在自為的主人。
三、道德是個體在生活中實現自我的重要途徑
人的需要是一個從低層次向高層次不斷發展的過程,“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P32)。這里所說的需要,不但指物質層面的需要,也包含精神層面的需要。“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12](P591)而且隨著個體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需要的意愿就愈加強烈。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內在需求是一個開放的、梯狀的多層次追求系統:1.生理需求;2.安全需求;3.歸屬和愛的需求;4.尊重的需求;5.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們對需要層次追求的不同,導致人的價值行為和生命存在境界的差異性,“已得到足夠的基本滿足繼而尋求愛和尊重 (而不是僅僅尋找食物和安全)的人們,傾向于發展諸如忠誠、友愛,以及公民意識等品質,并成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師、公仆等等”[13](P164)。在他看來,道德需要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安全需要基礎上的高層次的、發展性的精神需要,是人存在價值的圓滿實現,是一種人性存在的終極本體性意義。
道德需要之所以代表了人性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道德是專屬于人的范疇,是現實的“我”對人生的反思,它體現了個體擁有自我決定的意識的絕對權利。古人云:“水火有氣而草木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也就是強調道德是人之為人的重要標志。“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不僅生存生活在這個世上,還要去尋求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去實現與超越個體的價值。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馬克思寫道:“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14](P7)這里所說的“天性”,實質上就是指人的道德存在。正是道德的存在賦予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使個體由“小我”走向“大我”,由“世俗”走向“高尚”,由“平凡”走向“偉大”。
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做一個好人、一個為社會和他人所認可的人的道德需要。對于這種需要,中國傳統儒家稱之為“成圣成賢之心”,哲學家康德稱之為“對道德法則的敬重之心”,心理學家馬斯洛稱之為“超越性需要”。對主體而言,道德需要起初總是客觀的、外在的,是個體獲利的手段或工具。隨著主體道德認知能力的提高,他們對人類幸福與自身完美之間對立統一關系的認識也會逐步加深。“自尊自愛并尊愛別人,每一個人才能彼此互相寬容、互相支持,并互相給予力量。”[15](P176)一旦社會道德準則為個人所理解、認同、接受,社會道德就會滲入人的本質和內在心靈,成為人自我規定的一種內在要求,成為人生所努力追求的目的。道德自我實現者,為了某些不夾雜私利、某種與個人無關的事業,常常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利益,有時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為,在他們那里,“自私和不自私、內在和外在之間的分歧”[15](P242)已經得到解決,在為他人奉獻的過程中,他們能切實感受到自己的人格價值,對這些人而言,道德就不再是一種約束,而是一種精神享受,在他們履行一定的道德義務后,他們就能感受到內在道德良心的肯定,從而激起一種榮譽感、滿足感和幸福感。
對于道德與幸福生活之間的關系,美國學者彼得·辛格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如果不關心他人他事,只是刻意地自得其樂,那是不可能獲得幸福的。以這種方式獲得的快樂看起來會是空洞的,很快就會失去吸引力。”因為“要在生活中發現持久的意義……我們必須超越對自己利益有長遠計劃的審慎的唯我論者。唯我論者也許會暫時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但當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全部實現了,我們是否就只是坐下來并且是快樂的?我們真能以這種方式獲得快樂么?”[16](P333)而道德的存在則為我們設立了可以持久關注的目標,讓我們不會因短暫利益的實現而陷入空虛、迷茫的泥沼。道德精神引導個體超越自身意識王國的狹隘界限,追求更加遠大的目標,在實現這些目標的同時,個體幸福感、滿足感會油然而生。在馬斯洛看來,這種超越性需要的滿足是我們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愉悅和最大幸福,“禪思這些價值,與他們渾然化為一體,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極樂”[15](P57)。
道德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應該是辯證統一的。如果忽視道德的目的性價值,只談工具性價值,就將人的存在降低到動物的存在。反之,則會出現“人只為道德而活”的異化現象。“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在于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隨著物質根源的消失,這個對立自然而然也就自然消失。”[1](P275)在現階段,受物質生產發展階段和個人修養程度的制約,真正能夠實現潛在精神生命的個體只能是少數。但這種精神生命,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通過外界的培育以及自己的努力而獲得的。千百年來,人類的道德正是在一個個具體道德榜樣的感召下,在道德主體的自我反省中而不斷進步的。探尋道德行為的個體價值,并非要證明講道德永遠符合每一個主體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使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應該擁有道德,但堅守道德原則,能讓我們心情舒暢,擁有穩固的自尊和幸福的生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英)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4](英)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5](美)J.P.蒂洛.倫理學——理論與實踐[M].孟慶時,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鄧小平文選(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自我實現的人[M].許金聲,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美)亞伯拉罕·馬斯洛.馬斯洛談自我超越[M].石磊,編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
[16](美)彼得·辛格.實踐倫理學[M].劉莘,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