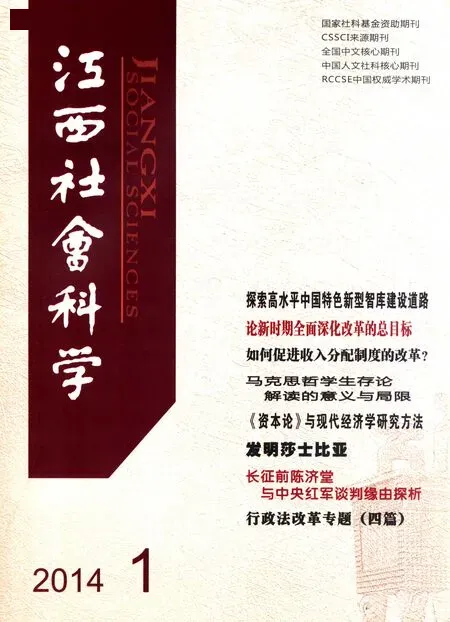論網絡同人小說的反經典性
■李盛濤
在網絡小說中,同人小說已自成一種小說類別。所謂網絡同人小說,是指借用既有的小說、影視劇、漫畫等文本作為戲擬對象而進行改寫與創作的網絡小說。這其中,出現了一批以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為戲仿對象的網絡同人小說。這些網絡同人小說具有鮮明的反經典性,并體現出可貴的文學生態性。
一、文學反經典的合理性
文學的反經典行為有著鮮明的當代文化印記。從文化形態上看,中國當代是由前現代文化、現代文化和后現代文化混雜的時代。西方學者將現代社會視為一個“裂變”的時代:“當代可以被看成是‘裂變’(Umbruch)的時代,即從體系到結構的裂變。當代的一切問題都在裂變的光輝中被提出,并且由此被恰當地解釋和解決。”[1](P8)當然,這種斷裂并不是社會有機體的斷裂,而是一種共識的斷裂。于是,解構、戲仿、反經典等現象都是當今“裂變”時代的文學衍生物。正如琳達·哈琴所說:“戲仿是后現代主義一個完美的表現形式。”[2](P14)而詹明信認為:“后現代主義目前最顯著的特點或者手法之一便是盜襲。”[3](P399-400)可見,文學的“反經典”手法已成為當代社會文化最鮮明的文學性名片之一。
其實,文學的“反經典”并非后現代主義時代的文學所獨有,而是一切時代之文學的一個基本屬性。因為反經典性的文學沖動具有一種文學的先鋒精神:“先鋒派的人是現存體系的反對者。他是現有東西的一個批評者,是現在的批評者——而不是它的辯護士。”[4](P496)因此,文學的反經典性使任何一部經典作品都無法逃脫被模仿的命運。這是一種常見的文學現象。從這點來看,文學的反經典行為使經典作品具有一種文學的衍生力量,催生了經典文本周圍空間里的文學生長,并使得經典文學不斷被關注。因此,文學反經典行為恰恰是對經典的另一種形式的尊崇與確認。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學時代都允許這種反經典性的文學作品的出現。反經典性的文學需要一個較為寬松的文學環境。在當代,網絡文化語境的出現為文學的反經典行為提供了一個具有意識形態豁免權的文學場,更能容忍和接納文學上的越軌行為。因而,惡搞、戲仿、拼貼等反經典性的藝術形式在網絡文學場中倍受青睞。
總之,文學的反經典行為作為文學的一種基本屬性,在當代的文化瀆神時代被激活,并在網絡環境中得到發展,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
二、網絡同人小說故事層面的反經典性
網絡同人小說在小說故事層面的反經典性主要體現在故事情節、人物關系、主題的設置方面與原作的差異。
首先,網絡同人小說大膽突破了原作的故事框架,任意撮合故事和設置情節。其一是將具有當代性的社會與生活事件移植到主人公身上,這在穿越類型的網絡同人小說中尤為常見。穿越主人公帶著穿越前世界的記憶,在穿越后將當代的思想、行為等生存智慧與技巧帶入古代,上演了一幕幕匪夷所思的舉動,以成就其輝煌業績,甚至改變整個歷史,如《重生紅樓夢》(擔花郎)、《賈寶玉新傳》(新空空道人)、《夢回水泊梁山》(李逍遙)等作品。其中要么是具有史詩性的重大事件,要么穿插一些現代性的生活小事件。當代記憶和事件被植入歷史語境,不僅使主人公具有了歷史的優越感和超越性,而且動搖了傳統小說情節設置的基于現實經驗的情感邏輯,使原本不可能、不可信之事變得可能、可信起來,從而使情節極具有傳奇性。
網絡同人小說在情節方面反經典性的第二種情況是在重大情節的設置上與原作相左,使故事別開生面。如在《紅樓夢》中,“黛玉之死”是重要的核心情節之一,它決定了整個故事的精神走向和人物的悲劇命運。而網絡同人小說若要以黛玉為主人公進行創作的話,須直面“黛玉之死”這一情節。對此,君幻鳳的《黛玉傳奇》將此事輕易化解:黛玉在吃了元神絳珠之后得以肉體生還。在李逍遙的《夢回水泊梁山》中,小說從“不可能”的情節處開篇行文。國際通緝犯姚成功穿越到了武大郎身上,而且他早知潘金蓮是蕩婦,將會和西門慶合謀害死自己。這一心結讓穿越后的姚成功非常痛苦。然而,原作中“金蓮謀夫”一節同樣被作者輕易化解。在另一處,原作中的“智取生辰綱”被改為光明正大的武力奪取。這種對原作經典故事情節的逆轉極大地改變了原作的故事走向與人物的結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閱讀效果。
在情節方面,反經典性的第三種情況是任意虛構故事情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張德坤的《大話紅樓夢》,作品寫異世少年石柳穿越成了賈寶玉,來到了內憂外患的清朝前中葉。作者將真實的歷史時空進行錯位嫁接,作品中的清朝前中葉北有蒙古肆意擴張,南有劉備犯亂。這種內憂外患的虛擬歷史空間為賈寶玉的建功立業創造了一個宏大的外部環境。于是,賈寶玉結交了《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許多英雄,并在眾英雄的輔佐下干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事件。這里,不同經典小說人物被作者寫進同一文本,各路英雄都得到夸張性地塑造。盡管這類網絡同人小說看似與經典作品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實際上這類小說的故事已經脫離原作而自成一體,而這些貌似原作的人物已完全契合進新構成的故事空間里。
這種情節的設置也導致了網絡同人小說對原作人物關系(尤其是男女關系)的任意設置。特別是在穿越類的網絡同人小說中,由于穿越主人公帶著當代的記憶穿越到古代,他們在穿越后缺乏強烈的自我身份認同,特別是家族倫理關系加諸自身的約束。如在新空空道人的《賈寶玉新傳》中,王燃先后與王熙鳳、秦可卿發生肉體關系。原作中“王熙鳳”和“秦可卿”相對于“賈寶玉”而言的道德符號意義已完全消失,她們只是穿越主人公在現代獵艷心理驅動下的一個個被征服的女性而已。這種設置使主人公在古代“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外衣下暴露出了當代人在文明宰制下的狂野的本能欲望及其在想象性解禁下的歡樂圖景。在這種人物關系中,“穿越”文學形式的存在使橫亙在當代和歷史之間的堅硬屏障破裂了,從而讓不同歷史時空的人物進行親密接觸,使文本具有極強的傳奇性,并形成了錯綜復雜的互文關系。
網絡同人小說情節構造的隨意性體現了一種隱含的意識形態意義。網絡寫手對經典情節的解構、對不可能情節的設置以及將可能性情節與不可能性情節進行的糅合都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文學性的戲仿與折射。當代“斷裂”的社會中,全球化與本土化、時尚與復古、多元與霸權、解構與建構等矛盾異常突出。因而,當代社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故事性、傳奇性與戲劇性,即一種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解構”特征。正如德曼對于解構的理解:“解構是一種洞穿隱喻和概念的誤人假設和效果的‘否定式眼光’。解構約莫相當于一種認識論上的反證姿態,它反證出一切統攝性原則充當真理與完整性的虛偽性。”[5](P52)在德曼看來,解構具有積極的建構意義。由于“解構”性使當代社會文化語境充滿了活力,而網絡同人小說的情節的恣意設置正是當代“斷裂性”(“解構性”)社會的文學性表達。正如弗雷德里克所說:“情節的可能性可以作為社會有機體活力的某種證據。”[6](P8)這里,情節設置的靈活與社會有機體的活力達成了一種默契,體現著一種深刻的意識形態意義。
除了在情節和人物方面的反經典性之外,網絡同人小說在主題方面的反經典性主要體現在與原作立意的逆向思維上。與原作相比,網絡同人小說的主題滑向了意義價值的另一極,神性與人性、悲劇與喜劇等主題因素在網絡同人小說中完全遭到逆轉。例如,在關于《西游記》題材的網絡同人小說中,經典《西游記》中“神性”主題遭到逆轉,由經典作品的一個關于“神”的故事轉變為一個具有現代性文化內涵的“人”的故事。在今何在的《悟空傳》中,西天佛祖從經典文本中的普度眾生、終極性的精神符號變為玩弄陰謀、戲謔眾生的威權的代表。顯然,這是個披著神話外衣的關于人的現代性故事。而在明白人的《唐僧傳》中,作者讓師徒四人取經成功后又重新東游,結果師徒四人都發生了深刻的世俗化改變。如果說《唐僧傳》還有明確主旨的話,那么林長治的《沙僧日記》則是沒有主旨意向的語言碎片。小說采用日記文本的形式展現了一片散亂、荒誕而幽默的生活碎片,文本的意義也就在插科打諢式的場景中消散殆盡。
由于主題的改變,主人公的審美特性也發生了變化。在林長治的《沙僧日記》中,師徒四人變成了齷齪的猥瑣人物;而在明白人的《唐僧傳》中,師徒四人都成了世俗生活的追求者,甚至是世俗的殉道者。此外,《賈寶玉新傳》中的賈寶玉、《重生紅樓夢》中的賈環、《夢回水泊梁山》中的武大郎等形象都體現了一個圣化的成長歷程。網絡同人小說中對人物的圣化的塑造,體現了網絡寫手的文學救贖意識。首先,網絡寫手通過文學想象和故事的編造而改變了經典作品中的人物命運,使作者成為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命運的掌控者;其次,這種文學救贖意識也可能是網絡作者的現實生存感受的一種文學式的宣泄與轉移。在現實的生存困境中,當青年人的人生理想和事業規劃遇挫時,他們很可能退而在虛幻的文學世界中求得補償。當然,現實中的無奈和文學想象中的成就使這類網絡同人小說在精神取向上是悖論式的:灑脫與拘謹、廣闊與促狹、溫暖與寒意等共同構成了小說現實文化隱喻的一體兩面。
總之,網絡同人小說對經典小說的戲仿,既是對傳統小說創作空間的探討,也是對傳統歷史時空的文化形態和生存方式進行的一種文學式的反思與改造。從而,這一文學的反經典行為在小說創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互文性:網絡同人小說語言層面的反經典性
網絡同人小說在敘述層面的反經典性使其具有鮮明的互文性特征。在有關互文理論中,熱拉爾·熱奈特把由別的文本派生的文本叫作“承文本”。網絡同人小說就是典型的互文意義上的承文本。同人小說與經典小說的互文性可以說是網絡同人小說在敘述話語層面的重要特征。互文性改變了文學創作觀念中文本與現實的關系,它強調文學并非是現實的反映和再現,而是語言自身的產物。“互文性用讀者—文本的關系取代了飽受質疑的作者—文本的關系,把文本意義的位置放在話語自身的歷史里。實際上再也不能認為文學作品具有原創性了;假如有的話,對讀者來說可能毫無意義。文學作品只是以前話語的組成部分,一切文本都是從這種話語獲得意義。”[2](P169)因而,從互文性理論看,一個文本的產生是由其他文本派生而來的,是話語自身活動的一個產物。在網絡同人小說中,互文性的表現是多層次的,既有小說精神層面的,也有文本話語與修辭層面的。
首先,網絡同人小說在文化精神層面的互文性表現為當代文化精神與傳統文化精神的間性關系。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生成于傳統的文化語境之中,因而傳統文化精神通過作品的敘事模式體現出來;而網絡同人小說生成于當代的文化語境中,當代文化因素勢必通過網絡同人小說的敘事模式表現出來。因而,網絡同人小說與傳統經典小說的互文性關系,實際就是當代文化精神與傳統文化精神的互文關系。盡管文化的出現有先后之別,但傳統的文化并未隨著新文化思潮的出現而消失,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都差異性地并存于當代社會語境之中。例如,從經典《西游記》到今何在的《悟空傳》,在主題上存在一個從“神性”到“人性”的轉變。從表面上看,“神性”似乎是被今何在否定的東西,其實并非如此。從現實角度看,在道德失范、精神滑坡、意識形態整合功能相對弱化的今天,“神性”所包含的理想主義、終極主義價值以及整體性的文化訴求并未過時。盡管“人性”被今何在極力頌揚,但他又在“人性”之中注入某種“神性”因素。如作品寫道:“‘我為什么要做神仙?因為我想,那樣至少自己的命,不用握在他人之手。’孫悟空聲音高了起來。”這里,“神”與“人”只是概念符號的差異,而其內涵已近乎等同。
再次,敘述語言中大量的當代文本的嵌入形成了網絡同人小說在話語層面的互文性。這種互文性的運用,極大地破壞了小說故事所虛設的時空界限,盡可能地向外開放以容納其他文本,形成了鮮明的文本間性特色。新空空道人的《賈寶玉新傳》最具有代表性,如:
長崎城中大街上到處可聞老百姓們沿街游行以及開批斗會時發出的呼喝聲:“打倒武士,均分財產;打倒武士,減除賦役”……孩子們歡樂的歌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也到處可聞。
作品中,當代小說、影視劇經典臺詞、歌曲等藝術形式被作者信手拈來,進行天衣無縫式地銜接和運用。盡管這種互文性敘述在主觀上并沒有刻意傳達某種深奧而晦澀的東西,在客觀上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間性效果:對當代生活而言,網絡同人小說以文本的形式介入當下生活,在這個文化健忘的時代喚醒了人們的閱讀記憶以及這個記憶背后的某些深厚的東西;而對于小說文本而言,當代人以及古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都以碎片化的形式介入文本,成為文本話語生命的一部分。歷史與當下、文本與生存、話語與生命等因素在這種互文性的關系中得以保存和呈現。可以說,互文性使網絡同人小說成為一個非常復雜的文本形式。
網絡同人小說敘述話語層面的互文性使文本極具后現代主義小說的特征。互文性手法所形成的混雜的文本形式往往被后現代主義小說稱之為“拼貼”或“拼湊”。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認為:“拼湊與戲仿相似,也是一種奇特面具的模仿,一種死的語言中的言語;但它是這種模仿的一種中性的實踐,沒有戲仿那種別有他意的動機,取消了諷刺的沖力,沒有什么笑料,也沒有任何說服力使人相信隨著你不時借用的反常語言仍然有健康的語言常態。”[6](P171)由此看來,網絡同人小說中的互文性手法更類似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意義上的“拼湊”,體現了語言運用的無目的性和文化價值取向的模糊性。網絡寫手所做的只是一種混雜式的呈現,一種語言能指的雜糅,而非目標確定的語言所指。
這種“拼湊”的話語形式極具陶東風所說的“大話文學”所具有的“話語大拼盤”特性:“大話文學繼承了狂歡文化的精神,打破時間、地點、文化等級的限制,把古語和今語、雅語與俗語、宏大話語和瑣碎話語隨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組成話語大拼盤。”[7](P58)陶東風認為,大話文學是當代大話文藝的一個文學性表現,而大話藝術則是中國當代經典祛魅思潮的一個文化表征。其實,文化的“祛魅”并不意味著一種消失,一種取代,而更多是一種并存的文化狀態。承文本的出現并沒有動搖經典文學的地位。經典文學的地位是通過用一整套的文化體制和國家意識形態教育而得以確立的。這種地位一旦確立便很難撼動。而網絡反經典小說的存在只不過是在經典文學的周邊獲取了一份生存空間,與經典文學共時態性地存在于文學場之中。
四、網絡同人小說反經典的文學生態性
從表面上看,網絡同人小說的反經典性手法體現了一種“斷裂”式的文化立場,但它潛在的重要的文學生態意義往往被忽略。網絡同人小說反經典性的文學生態性主要體現在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審美規范和促進了文學的“群落”式發展兩個方面。
首先,網絡同人小說的反經典性體現在對小說傳統審美規范的質疑與打破上。小說的理論和審美規范是在文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被確立的,具有普世主義價值。但任何理論和審美規范都不是完美的,都有著時代的局限性。因而,反經典手法其實是利用解構手法撕破了小說既有審美規范的看似完美的外衣,以發現其不完善之處。Robert F.Berkhofer,Jr.說:“解構揭示了在表面看來具有統一性的事物表現中被壓制的東西,它還破壞了在表現和指涉之間、文本與現實之間建立中介的努力,因為在它看來現實也不過是社會性地建構出來的東西。”[8](P21)因而,反經典性的解構暗含著打破已有的文學話語體系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虛假契約,“解構的深層目標是揭露所有表現的真實無誤的本質:基于社會的話語建構”[8](P20)。因此,站在文化的創新性角度以及文化平等的立場來看,網絡同人小說的反經典性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意義。
其次,網絡同人小說的反經典性促進了當代文學的“群落式”發展。在生態學的整體性思維之下,文學的經典樣式和非經典樣式共同構成了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兩者屬于不同的文學場。經典文學更多屬于體制文學場,而網絡同人小說更多屬于網絡文學場。盡管兩個文學場有交叉性,但不同點更多。經典文學的地位是由體制文學場決定的,是由一系列意識形態操控機制和教育體系促成的,一旦形成,其霸權地位很難被撼動。而網絡反經典小說更多屬于網絡文學場,是由文學網站的商業化運營機制、網民的自由創作和閱讀等因素構成的,較少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兩者很難置對方于死地,更無法取代對方。因而,經典文學與非經典文學共同構成了當代文學的生存圖景。
其實,非經典作品的存在印證了經典文學的一種近乎被人忽視的文學功能。在傳統意義上,經典承載更多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功能和教育功能,同時它所體現的審美規范和精湛的文學技巧往往被后世所繼承和借鑒。但是,反經典手法的運用發掘了經典文本的另一種文學功能:文本的衍生作用。也就是說,任何經典文本都有著衍生其他文本的潛在功能或會被其他文本所引用。可以說,作為“承文本”網絡同人小說就是文學反經典行為的創造性結果。因而,反經典性的網絡小說與傳統經典小說并存于當代文學場之中,并形成了一個“群落式”的文學圖景,體現著當代文學在傳統經典文學之外的生存圖景和發展態勢。
總之,網絡同人小說以其反經典性的手法在與經典小說的“似又非似”的互文性關系中確立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并在解構性的面具下深藏著文化與文學方面的建構意義,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意義。如果說經典文學是一株株參天大樹的話,各種反經典文學則是形形色色的樹林與灌木叢,它們共存于當代文學場之中,共同構成了當代文學的生態性文學圖景。
[1](德)羅姆巴赫.作為生活結構的世界——結構存在論的問題與解答[M].王俊,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2](加)琳達·哈琴.后現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M].李楊,李鋒,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4](法)尤奈斯庫.論先鋒派[A].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上卷)[C].李化,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M].寧一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M].王逢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7]陶東風.文學活動的去精英化[A].文化與詩學(第六輯)[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Robert F.Berkhofer,Jr.超越偉大故事:作為文本和話語的歷史[M].邢立,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