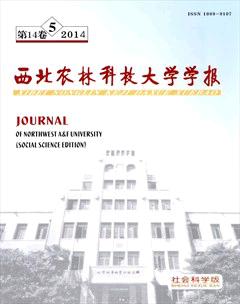社會資本與西部農村地區收入不平等分析
摘要: 21世紀以來,社會資本在反貧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會擴大還是縮小收入不平等,仍無共識。運用分位數回歸發現:家庭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對我國西部農村地區不平等的影響截然相反。前者對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擴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區社會資本特別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會顯著降低農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農民自發組織、發展正規專業的社團組織等社會性力量,對緩解貧困、縮小收入差距、維護社會穩定等有重大現實意義。
關鍵詞:家庭社會資本;社區社會資本;收入不平等;農村地區;分位數回歸
中圖分類號:C91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5-0115-08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不平等一路攀升。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全國基尼系數達到了0.412,超過了國際警戒線;2012年則達到了0.474。另據西南財經大學的調查數據,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更是高達0.61。不論哪套數據更加客觀更加準確,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非常大了。多數人對中國農村的印象是普遍貧窮。但實際上,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遠超乎我們的想象。西南財經大學的數據還揭示,農村家庭內部的收入差距要高于城鎮內部,基尼系數為0.60,基本接近總體不平等程度,并且這種不平等在西部農村地區更加突出。貧窮與不平等現象并存,亟待我們加以分析和理解。
如何縮小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就是減少貧困人口,降低貧困發生率。但中國農村的貧困率不容樂觀,在西部地區則更加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我們勾勒了2000、2005和2010年等三年的全國及西部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的統計表(見表1)。
2000~2010年,中國反貧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貧困線不斷上調的同時,貧困發生率在不斷地下降。其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貧困率從2000年的20.6%下降到2010年的6.1%,下降了70.4%。但同時,西部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卻從60.8%上升到了65.1%。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2010年從全國隨機挑選3個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就有2個來自西部地區。另一方面,中國的貧困線水平很低,一旦提高貧困線,貧困的對象將急劇上升,比如2011年國家將貧困線調整到2 300元,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就增至1.28億。可以預計,其中有70%左右的貧困人口是來自西部農村地區。
21世紀以來,社會資本在反貧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極高的厚望,但也招致了一些非議。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是缺乏實證檢驗,還有則是對社會資本的多層次性及其差異的關注較少。在簡要梳理兩種類型的社會資本發展脈絡后,本文將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從家庭和社區兩個層面來測量社會資本,聯合考察它們對西部農村地區收入不平等,以及對低收入貧困家庭所帶來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
對農村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等角度[2]。但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發現,這些研究通常假定經濟活動是自利和獨立的,而忽略了經濟行動是嵌入在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的。這反映到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則表現為忽略了不同群體和社會行動者社會背景以及其他社會性因素導致的收入差異。這里最突出,也是被廣泛運用的就是個人及家庭的社會資本稟賦,它被認為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資源稟賦之外,另一種影響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資本形式。社會資本同其他資本最大的區別在于,它蘊藏于人際關系網絡之中,可能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但卻是經濟績效的“粘合劑”。總體來看,和經濟績效相關聯的社會資本有兩個主要形態:第一,基于人際網絡的個體、家庭層次的社會資本。第二,基于規范、互惠、社會凝聚力與信任等較為宏觀的社區層次的社會資本。前者以林南、伯特和邊燕杰等人為代表;后者的代表人物則包括科爾曼、帕特南以及福山等人。本文試圖同時考察這兩種社會資本對農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一)家庭社會資本與農村收入不平等
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的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也最具經濟效應。在這個大的領域里面,也有多個理論流派,包括網絡結構觀、網絡規模觀、網絡關系觀和網絡資源觀等,本文采取了綜合分析的視角。已有研究發現,社會網絡資本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就業機會[3]。而且,社會資本對弱勢群體的地位獲得尤為有效[4]。在關于農村地區的研究中,Grootaert最早發現社會資本對于減少家庭貧困有重要作用,是“窮人的資本”[5],他運用了本文所涉及的分位數回歸方法,發現,社會資本在最低收入組的農戶家庭中(10%分位點)的回報率是最高收入家庭(90%分位點)的兩倍。張爽等人根據中國調查資料也發現,社會網絡可以減少貧困[6]。社會資本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獲得非農工作的機會,幫助他們擁有更多的民間借貸渠道,從而更可能創辦自營工商業[7]。
關系型社會資本對于脫貧致富的價值也遭到了很多批評。他們認為,社會網絡資本確實可以傳遞信息、增強信任,有助于互惠合作。但是人們的交往具有同質性,富人的網絡在有意無意間會排斥窮人。所以,窮人的網絡資源實際上是更加匱乏的。這種“馬太效應”,不僅不利于緩解貧困,反而會加深貧富分化。有學者就發現一些社會關系會加劇“最貧窮的人”被排斥的狀態。而且貧困者之間的緊密團結,也意味著對外群體成員的排斥,這種封閉性會導致他們更加貧困[8]。國內研究中,趙劍冶等人也發現中國式“關系”有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9]。
本文認為這些觀點上的對立,只是一種表面的矛盾。關于家庭社會資本會擴大收入不平等的論斷基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規律。這是顯而易見、毋庸置疑的。貧困家庭的社會網絡資源質量必然低于富裕家庭,它必然會給富人帶來更多的經濟回報。但當談及社會資本對不平等的影響時,我們更加關注,社會資本對窮人和富人的回報率是否存在相對差異,而非絕對差異。舉例來說,富人和窮人的年收入分別為5萬和1萬,從絕對收入來說,富人比窮人多了4萬,從相對量來說,是其5倍。但如果我們假設社會資本可以使富人的收入提高1萬,窮人收入提高0.5萬。從絕對量上來說,富人比窮人多了4.5萬,兩者的收入差距擴大了。但從相對量上說,富人收入只有窮人的4倍了,不平等程度其實在下降。原因在于,社會資本的相對回報率對窮人更有利,在我們這個例子中,社會資本可使富人收入增長20%,但可以使得窮人增長50%。很多時候,相對回報率比絕對回報更加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例子只是一種設想,家庭社會資本的分布是極度不均衡的,窮人的社會資本質量可能極度劣于富人。換句話說,即貧困家庭的社會資本是不是差到了相對回報率都低于其他家庭的程度?倘若如此,則家庭社會資本擴大了不平等;如果回報率大致相同,則與不平等關系不大;如果底層家庭的回報率更高,反而降低了不平等。實際上,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出現。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超越了社會網絡資本本身的作用機制了,而是涉及到在整體制度背景下,可以使得家庭收入提高的那些資源(這里指家庭社會資本)本身分配是否比較均衡的問題了。這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定量研究來判別到底哪種狀態更加符合中國西部農村地區的實際狀態。
(二)社區社會資本與農村收入不平等
社區社會資本同樣有多個形態,概括而言有三個視角,即社會聚合、公共參與和社會信任[10]。這些理論視角普遍認為,社區內部的凝聚度、社區成員公共活動參與情況,特別是參與正規專業社團的活動,以及居民間的互信程度,對當地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在農村社區,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傳播農業信息、培育農業技術人才,增強村民的凝聚力、實現生產合作。因而,社區社會資本較高的農村地區,社區成員可以享有更高的社會福利水平。
不同于家庭社會資本的地方在于,社區社會資本外生于個體行動者,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不太受交往同質性的影響,它的分布比其他資本更加平均。只要是某個社區的成員,都有平等的資格享受該社會資本帶來的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說,社區社會資本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還不會加劇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此外,由于窮人對社區社會資本的依賴度更高,社區社會資本對窮人的相對回報率可能要高于富人,因此,社區社會資本更可能成為降低農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二、數據來源、變量測量與研究策略
(一)數據來源
2010年初,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組織了一項關于“農村社會和諧與平等發展”抽樣調查。該調查旨在反映西部地區,尤其是陜西省農村社會的貧富分化狀況,且重點以家庭社會網絡分布以及社區公共參與、社區內部凝聚狀況等角度對貧富分化進行解釋。根據PPS抽樣,該調查包含了陜西省10個地級市下轄的80個鄉鎮。再按照簡單隨機原則,從每個鄉鎮中選取1個行政村。最后結合村級花名冊與地圖法抽樣,在每個村中,等距離抽取了40個家庭戶。總設計樣本3 200個,最終有效樣本2 890個。
(二)變量測量
1.被解釋變量:收入的測量。本文以家庭收入作為分析對象。2009年陜西農村家庭總收入的平均值為2.88萬元,標準差為5.78萬。根據樣本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52,介于幾個權威統計數據之間,具有可信度。在本文分析中,收入以對數形式和自然形式共同出現。
2.解釋變量:家庭社會資本的測量。本次調查中,我們專門設計了“家庭社會支持網絡”,了解被訪者家庭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難時,如缺錢、缺少生活及生產工具、生病等等,可以求助的親戚朋友數量,以及這些人的職業類型。我們計算了表示家庭社會資本的三個主要維度:(1)支持網絡的規模:可以求助的親朋總數;(2)網絡差異性:這些幫助者的職業類型總和;(3)網絡資源含量:按照職業聲望得分,計算被訪者家庭可以觸及的最高職業等級,即網絡達高性。隨后,根據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家庭社會資本公因子,并標準化為均值0,方差1的數據形式。
3.解釋變量: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該類社會資本一般包括兩種類型,自發組織的互惠互利型和正規專業的外部社團介入型,類似于帕特南的內聚與外聯型社會資本。為突出焦點,我們在測量時,并未詳細加以區分。本文對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從主觀歸屬認同和客觀參與兩方面進行考察:(1)主觀心理認同方面,考察了農村居民對村、鎮兩級共同體的關心程度。測量按照五分法進行,“很關心”村委會的事情,賦值5,“從不關心”則為1。對于鄉鎮事情的關心程度同樣如此測量。它們代表了社區的聚合狀況。(2)客觀參與方面,本文通過考察村民實際參加諸如行業協會、合作經濟組織、科技組織、老人會、文化體育組織、民辦組織等組織的總數量來考察。經過重新計算的“社區聚合狀況”和“公共參與狀況”實際上還是個體層面的數據。因此,我們需要再依據同一個社區中所有被訪問家庭在這些方面的情況,來聚合生成相對應的社區層次的指標,同樣運用因子分析,提取出社區社會資本的公因子。
4.解釋變量:其他資源稟賦的測量。影響收入不平等的傳統變量同樣需要控制到分析中,否則,社會資本的效用可能是虛假的。本文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考慮了其他家庭資源稟賦,包括家庭平均耕地擁有量、家庭勞動力數量和家庭成員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5.控制變量:區域。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同樣會影響到收入分化,在陜西省有三大典型區域:(1)陜北地區依靠煤炭資源,人均收入最高,但不平等程度也相對較高;(2)關中地區,自然條件較好,依托省會西安,擁有更多的非農工作機會和農產品深加工的市場環境;(3)陜南地區,以山區為主,交通相對閉塞、自然災害相對更加頻繁,農村總體收入水平低。
關于以上8個變量的統計分布信息可見表2的描述性分析。
(三)分析策略:分位數回歸
目前多數定量研究,包括對不平等的研究,主要是運用OLS回歸或者它的擴展形式(如多層次模型等),能夠描述自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均值的影響情況,但這些方法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統計信息,即被解釋變量(收入)分布的離散程度。而且OLS回歸根據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計方法,還容易受到極大極小值的影響,穩健性相對不足。反映到本研究中,則是我們無法考察社會資本對收入較低和收入較高的農村家庭的差異性影響。分位數回歸基于不同分位點,按照最小化絕對離差的方法,不僅可以吸納更多的收入分布信息,而且估計結果也更加穩健。本文將根據該方法,估計社會資本對不同收入分位點的農村家庭的影響。
分位數回歸的模型表達式為:
此式為最小化誤差的加權和,其中正的誤差項作為θ的權重,負的誤差項作為(1-θ)的權重。第θ分位數(0<θ<1)的參數估計結果為Quantθ^(Y*|X)=X′βθ^。本文重點選取常用的0.25、0.5、0.75等三個分位點進行對比分析。這三個分位點分別代表了收入較低、中等和較富裕的農村家庭。為了細致刻畫社會資本在不同分位點的影響及其趨勢,本文分析了0.05到0.95之間每隔0.05個分位點共計19個分位數回歸情況。
社會資本在不同條件分位數上的收入效應所蘊含的收入不平等可以通過圖1來進一步說明。在控
圖1社會資本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
制其他影響變量的情況下,如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區域等因素,社會資本在高收入分位點和低收入分位點上的偏回歸系數分別為b1和b2。社會資本存量較高時,平均收入也會較高,即圖1中橫向虛線所表示的位置關系。在社會資本存量既定時,高分位點和低分位點之間的跨度,即離散程度,表達的即為組內不平等程度。
圖1還反映出社會資本存量較高,但組內不平等程度較低的一類情形,此時要求低分位點回歸系數b2要大于b1。反過來,當我們觀測到社會資本在低分位點的回歸系數較大時,則表明社會資本越高,收入不平等狀況越低。反之,若低分位回歸系數較小,則表明社會資本越高,收入不平等狀況越嚴重。
三、實證分析結果
(一)社會資本在不同收入家庭的分布狀況
首先關注的是,兩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在不同收入組中的分布是否均衡,及均衡的程度。將收入等分為10組,考察不同組中家庭和社區社會資本的平均值。從表3可以看出,兩類社會資本存量都存在著隨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趨勢。但是,家庭社會資本和家庭物質財富的重疊度要更高,社區社會資本相對更加分散。社會資本與收入組別的相關系數也表明,前者更加集中,后者相對分散。這些都很符合前文的理論敘述,即社會網絡資源存在明顯的同質性交往原則,而社區社會資本則相對分布平均。
表4給出了OLS回歸和分位數回歸的四組結果。其中OLS結果陳列在最左邊,分位數回歸包含3個結果,分別對應0.25、0.50和0.75等3個條件收入分位點。最右邊一列,計算出0.25分位點和0.75分位點估計系數值差異的顯著性檢驗結果。
OLS回歸表明,家庭社會資本和社區社會資本都非常顯著地影響了農村家庭收入水平。其中,家庭社會資本每增加一個標準單位,家庭收入將提高27.5%(計算公式:[exp(0.243)-1],下同);社區社會資本每增加一個標準單位,則提高22.1%。因而,可以判斷它們也會成為影響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控制變量的統計信息也基本符合預期。家庭勞動力數量和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水平正向顯著地影響了農村家庭收入水平,這符合一般理論預期。但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時,家庭耕地擁有量越大,家庭收入反而越低。這可能是由于家庭耕地越多,則有更多的勞動力會從事農業生產,從而降低了非農收入水平。這從側面反映出,農業產出與第二第三產業產出之間存在著“剪刀差”。農業生產者整體回報率低于非農生產者。關中和陜南地區的人均收入要顯著低于資源密集的陜北地區,這符合實際狀況。
(三)分位數回歸結果與啟示
1. 家庭社會資本擴大了農村收入不平等。重點解讀分位數回歸的結果。分位數回歸的前3列分別為0.25、0.50和0.75分位的回歸結果。家庭社會資本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250、0.241和0.254,而且都非常顯著。它們分別意味著規模的變動對于收入水平的各個分位數的邊際影響。可以看到,隨著分位數的上升,即家庭收入水平從很低到很高,家庭社會資本的變動對于收入水平的影響先高、后低,再高。當家庭收入處于較低和較高水平時,家庭社會資本的影響都比較大,當家庭收入處于中間水平時,影響相對較小。但系數差異性檢驗表明,三者之間沒有顯著區別。可以認為:家庭社會資本對于較為貧窮、收入中等和較為富裕的家庭的影響大致相同。
但家庭社會資本對特別貧窮的家庭帶來了更加不利的影響,見表5的結果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列出更多的分位點信息,但可參考圖1的結果。。家庭社會資本在0.05和0.10處的回報率分別為0.159和0.178,且顯著。我們依然將其同0.75分位點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對于非常貧窮的農村家庭來說,家庭社會資本帶來的回報率也要顯著低于其他家庭。從絕對量來看,社會資本每增加一個標準單位,可以使相對富裕的家庭收入提高8 000元,但只能使得特困家庭(5%分位點)提高978元,使貧困的家庭(10%分位點)提高1 397元。因而,家庭社會資本對非常貧窮,尤其是極度貧窮的農村家庭非常不利。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窮幫窮,越幫越窮”[4]。
2. 社區社會資本可以緩解農村收入不平等。
在0.25、0.50和0.75等三個分位點上,社區社會資本都有利于收入提高,三個系數分別為:0.212、0.197和0.078,前兩項在0.00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后一項在0.0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可以看到,隨著分位數的上升,即家庭收入水平從較低到較高,社區社會資本對于收入水平的影響在不斷減弱。并且,差異性檢驗表明,低收入分位點的系數要顯著大于高分位點。這表明,社區社會資本對陜西農村地區的低收入家庭的邊際回報率要高于富裕家庭。表4還表明,這種影響在最低的0.05和0.10分位點上也非常強烈。因而社區社會資本可能對較貧困家庭更有意義。從表4的絕對收入差異來看,社區社會資本對不同分位點的絕對收入提高的作用大致相同。我們知道,同樣的收入增加值,對貧困家庭的福利增加效應更大,也可以更好地改善他們的生活機遇。因而結合本部分的計量結果,可以認為社區社會資本可以有效緩解西部農村地區的收入不平等。
3. 借助圖形理解社會資本與農村收入不平等。前面的分析側重于個別重要的分位點。分位數回歸的巨大優勢在于,可以刻畫各個分位點上的回歸信息以及相互關系趨勢。我們分析了0.05到0.95共計19個分位數回歸,并擬合出兩種社會資本的回報率變化圖。結合圖2,可以清晰地看出,家庭社會資本的回報率總體呈現隨著分位點提高而提高的趨勢,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布最低端的0.05、0.10和0.15分位點上,回報率特別低。其他分位點則在0.25附近變動,差異不大。這進一步證實,家庭社會資本可能會擴大不平等,對特別貧困的農村家庭尤其不利。社區社會資本的情況剛好相反,隨著分位點上升,回報率急劇下降,這種情形與圖1假設一致。而且,19個回歸點比較緊密地圍繞在擬合曲線附近。這說明,社區社會資本特別有利于低收入家庭,有利于緩解農村不平等。
圖2各分位點社會資本回報率的擬合關系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陜西省農村社會發展數據,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檢驗了兩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對西部農村地區內部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兩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對收入不平等有截然相反的影響。由于同質性原則,家庭社會資本分布相當不均衡,導致特別貧困的家庭,社會資本質量很差,互助互惠功效有限。因此,家庭社會資本對農村特別貧困家庭的相對回報率也顯著低于其他家庭,進而表現出隨著家庭社會資本的提高,農村內部的不平等也在擴大的現象。社區社會資本的分布相對平均,公共物品性質明顯,具有較強的正向外部性特征,特別有利于低收入家庭,是可以顯著降低西部農村地區不平等的有利因素。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通過計量分析發現,農村社會組織不僅可以降低貧困發生率,而且相對于富裕家庭,它可以為低收入農村家庭帶來更多的福利,緩解農村地區的收入不平等。但當下的現實狀況是,農村居民的自我組織程度不高,缺乏公共參與的熱情和能力,同外部社會也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11]。本文揭示了培育引導村民自發組織、發展正規的社團組織等社會性力量是破解農村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徑,也是農村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因素。自組織源于農村發展的內生偏好,屬于內聚型社會資本范疇。這種社會資本的形成源于組織內部成員多次重復博弈而建立起的信任、合作共享機制[12]。它可以滿足農村社區的內部團結、整體歸屬,有利于農村社會的凝聚力增強。而正規專業的社團組織,如NGO,屬于外部力量介入型的外聯型社會資本范疇,可以為農村社區帶來新的農業知識,有利于科技創新與現代文化積累。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13.
[2]唐為,陸云航.社會資本影響農民收入水平嗎[J].經濟學家,2011(9):7785.
[3]張順,程誠.市場化改革與社會網絡資本的收入效應[J].社會學研究,2012(1):130151.
[4]趙延東.再就業中的社會資本:效用與局限[J].社會學研究,2002(4):4354.
[5]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1999(6):180.
[6]張爽,陸銘,章元.社會資本的作用隨市場化進程是減弱還是增強[J].經濟學,2007(2):539560.
[7]馬光榮,楊恩艷.社會網絡、非正規金融與創業[J].經濟研究,2011(3):8394.
[8]周文,李曉紅.社會資本對反貧困的影響研究[J].教學與研究,2012(1):6371.
[9]趙劍治,陸銘.關系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及其地區差異[J].經濟學季刊,2009(1):363390.
[10] 帕特南.獨自打保齡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148.
[11]柳錦銘,陳通.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的新農村治理對策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14.
[12]蘇楠,文龍姣,楊學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研究:基于楊凌現代農業示范園區的實證調查[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