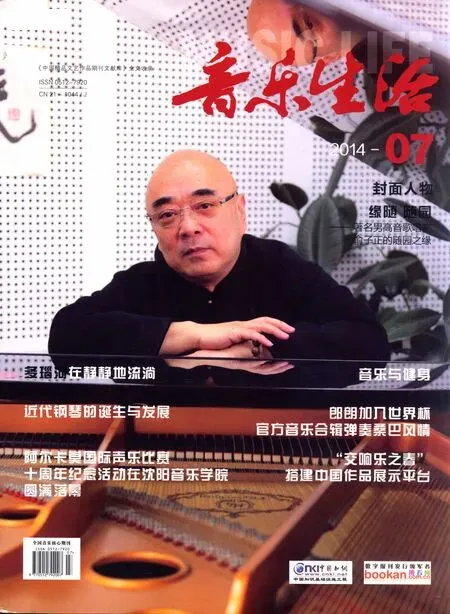關于音樂創作的三個話題(續)
文/范哲明
關于音樂創作的三個話題(續)
文/范哲明
話題二:“精神與物質”——音樂創作思維層面上的話題
大凡藝術創作都是由精神到物質的過程,音樂創作也是如此。精神來自作曲家的生活體驗,物質出自作曲家的技術訓練。
一個技法純熟但審美意識模糊的作曲家是難以寫出令人震撼的作品的;反之,一個樂思如泉但創作手段粗陋的“音樂人”也不可能成為作曲家,充其量只能說是所謂的“票友”或“玩家”。而那些偉大的作曲家無不是以其代表作品中所體現出的那種超脫的審美追求與超群的創作技藝之完美結合來踐行自己的藝術觀,從而贏得了人們的尊崇與敬意。

圖 5
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馮·謝林[圖片5]對藝術及其本質的認識或許對現代中國審美文化如何走出困境有所啟示,他認為“藝術是自由和必然結合的最高形態,在藝術中從事自由創造的人是人的本真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追求的不應是藝術生活化,而應是生活藝術化;不應是精神生活物質化,而應是物質生活精神化。”(張園《謝林帶我們重回“藝術”》)
北大教授張世英先生在他的《人生的四種境界》中,將人的生活境界分為四個層次,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審美境界”。
“欲求境界”乃“食色性也”的境界,現實中以“欲求境界”占人生主導地位的人,就是一個境界低下的人,即所謂“低級趣味”的人。“求知境界”使人了解到自己可以是命運的主人,若要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滿足,就必須獲取知識,懂得客觀規律。處在“道德境界”的人一定會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對他人負責。而“審美境界”之所以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則是因為處在這一境界的人對于己與他、人與物的認識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應該是使自己不斷提升至審美境界的實踐活動。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以美國后現代女藝術家米埃勒·尤科莉絲于1978—1980年創作的行為藝術作品《接觸衛生系統》(Touch Sanitation)為例來釋義
審美境界,這個作品是以藝術家本人站在清潔管理站的入口處和8500多名清潔工一一握手道謝,說:“謝謝你們讓紐約保持了活力”(Thank you for keeping New York City alive)這樣一種行為藝術形式來實現的[圖片6]。一些參與到作品之中的清潔工人說:“一輩子沒有見過這種事,如果這是藝術的話,我們喜愛這種藝術”。“有人說,尤科莉絲的行為不過是一種道德行為,不算藝術,算不上‘審美境界’。其實不然。尤科莉絲行為的特點正在于,她不僅僅是出于道德上的‘應該’而行事,而是超越了‘應該’,自然而然地從事這一活動,她把這一活動當作一種特別的‘藝術作品’獻給清潔工。在她的精神境界中,這一活動是席勒所說的‘游戲沖動’—— 一種‘自由的活動’、‘審美的活動’。她的行為,像許多西方后現代藝術家一樣,撇開了視覺美,而體現了一種崇高的人生境界之美。”(張世英《人生的四種境界》)
作曲家的音樂創作由始至終都應該處在這樣一種“審美境界”的層面上,因此對于作曲家來說,審美感的養成尤為重要。謝林對于審美感的重要性頗有見地:“他指出,人必須有審美感,否則人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無權充滿人的精神去談論歷史。”(張園《謝林帶我們重回“藝術”》)


圖 6
話題三:“復制與創新”——音樂創作技術層面上的話題
藝術創作的本質在于技術與創新,而藝術作品技術構成之前提就是復制。從藝術創作的發展與傳承角度來看,復制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對于當今中國的藝術家們,創新只是復制中的“變異個體”,因為“中國藝術今天的情況是,只能微觀創新,多數在整體上是宏觀復制。復制是中國文化及藝術的最大特色之一。”(鄒文《當代藝術:宏觀復制、微觀創新》)
在技術層面上,創新往往蘊蓄在復制的過程中。因此,藝術家們意欲創作出與前人不同的作品,就必須在不斷地復制前人的技術手段之同時,萌發自已新的創意。
也就是說,“一位音樂家如欲達到他本身才能應有的高度,必須學習像手藝人那樣工作”(柴科夫斯基,《1890年5月18日致羅曼諾夫的信》)。
作曲家的創作追求不在于標新立異空前絕后,而更多地在于使自己的語言、風格以及表述方式易于與前人的和他人的語言、風格以及表述方式清楚地區分開來,以便使自己的時代坐標和文化方位清晰地表露出來。當然,一些激進的作曲家認為難以超越前輩大師們的藝術成就而另辟蹊徑,他們中的一些人也確實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創作理念與技術方法,不過這樣一些創新更多地應被看作是“翻新”,從本質上看還是復制。時至今日,世界上以復制為主要手段的作曲家仍占多數,他們的歷史作用和文化價值不容輕視。
“有人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作曲家如果不在相當程度上重復一些偉大音樂藝術大師早先已經表現的內容,就難以提出什么真正的新東西。不,情況不是如此,音樂材料,也就是說,旋律、和聲、節奏,是絕對汲取不盡的。再過一百萬年,如果我們所理解的音樂仍舊存在,那么,我們的音階里同樣的七個基音,它們的那些節奏活躍的旋律組合、和聲組合,仍將是新樂思的源泉。”(柴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訪談錄》,1892年11月12日《彼得堡生活》刊載)
復制與創新有如一塊硬幣的兩面。從文化意義上講,藝術創作中的復制與創新并不等同于落后與進步、保守與開放,因此也不應將復制與創新對立起來,“創新是對傳統文化革命性的優化,創新也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到底也具有復制性。”(鄒文,《當代藝術:宏觀復制、微觀創新》)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藝術復制有其積極意義。‘復制’不僅有利于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也利于推動社會進步。藝術作為一種精神文明成果必須經過‘復制’而社會化,有利于精良藝術的共享”;“中國文化之所以歷千年而基本不變、不斷,乃是因為這種文化本身對創新的適度約束。反之,若中國文化非常鼓勵創新,就會造成歷朝歷代的創造都異常頻繁,千變萬化,最終很多經典的東西會在歷史發展中途丟失,各種各樣的文化難以完整留傳至今。保持文化的不變、不斷、不衰,必要以節制創新為前提。”(鄒文,《當代藝術:宏觀復制、微觀創新》)
將兩首相距889年的詞作一比較,可看到中國文化中復制與創新間的微妙關系。兩首同一詞牌的作品格式上基本一致,字數完全相同(95字)。但是毛澤東卻根據自己的表達需要,在不破壞整體格式的前提下,調整了個別句子的節律(見劃線的句子),將11個字構成的句子由原來的4+7改為6+5。
【水調歌頭】 蘇軾(1076年)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毛澤東(1965年)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但復制又有其不可忽視的消極面。中國文化,無疑因封建社會造成了自身相當的惰性和保守性。在近現代的后果就是,國民創新精神被嚴重耽誤和影響,創新量銳減,創新的周期拉長,社會更多地重視簡單的復制,缺少各個方面的探險精神。自主知識產權擁有極少……我們向世界提供的大型原創的發明成果相當有限,很難例舉出一兩件全世界人都在享用的來自20世紀中國人的發明創造。”(鄒文,《當代藝術:宏觀復制、微觀創新》)
“創新”于21世紀的中國確實是個關鍵詞,盡管在許多領域中“創新”還只是響亮的政治口號中的一個術語。更多的中國精英們已經認識到,創新迫在眉睫,創新時不我待,特別是文化創新,更是關鍵之關鍵。但對于文化創新的理解,精英、大眾與政府三方從來就沒有形成過共識,當然也就難以形成合力。所以,對于藝術創新,質疑多于贊同,嚴苛多于寬容,冷漠多于熱心。說到底,多數習慣了藝術復制環境的中國“文化人”對于藝術創新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心存疑慮。因此,藝術創新能否被大眾認可,似乎成為判定藝術創新之社會價值的唯一依據,一些學者們不得不處心積慮地為兩者之間的糾結辯解:
“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形態的藝術,還要不要遵循藝術服務于大眾的原則?或者從另一個方面說,探索性或前衛性的藝術可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嗎?我想回答應是肯定的。讀讀有關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藝術的文獻,我們便可以了解西方這些前衛藝術家不少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他們要把藝術從象牙塔圈子里解放出來,要讓藝術從博物館走進大眾。他們的做法也許比較激進而不可取,但是他們擁有的這一理想值得我們關注。”
“有人認為,只有多數人看得懂的藝術才可能是為大眾服務的,反之則是脫離大眾的。這種看法不夠全面。藝術要服務于大眾,當然要讓群眾看懂、看明白,而且看懂和看明白的人越多越好。不過,藝術品被群眾看懂、看明白有不同的情況,有的作品可能一看便明白,有的則要有一個過程;有的藝術形式為群眾喜聞樂見,有的則可能要通過引導才可能為群眾所理解、接受。例如源自西方的抽象主義藝術,不少中國觀眾甚至一些藝術家都曾經因不解其意而斥之為荒誕、怪異而將其拒之于門外,但經過一些解釋,經過反復展示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它不僅是一種可以欣賞的藝術形式,而且可以承載積極的思想內容。”(邵大箴,《藝術屬于人民》)
畫家鐵心的《晚宴》系列看似過于抽象[圖片7],實則非常具體,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對于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碰撞及混亂的形象刻畫令人過目不忘。鐵心以寫實主義與抽象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向人們傳達了他對當今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的危機之深深憂悒,作品的藝術構思與技術體現并不晦澀難懂:
“19世紀,愛迪生發明了這些白熾燈泡,引起了工業社會的一大變革:它們使夜晚亮如白晝。這就大大延長了人類改造世界的時間,加快了工業文明的進程。雖然,白熾燈泡在城市里已逐漸被日光燈、節能燈等新型燈具所替代,但是,它們仍牢牢占據著中國農村這塊廣大的陣地。這些燈泡脆弱的本質難以遮掩光芒和承受光芒的重量,一經沖撞,立刻成為文明世界里的‘碎片’。鐵心是這些‘碎片’的表現者。他極力地表現著這種尖銳的結構、恐慌的解體、混亂的秩序……提前為“白熾燈泡”時代唱響一曲挽歌。”(牧風,《存在,一次合理的解釋》)
當下中國音樂創作在觀念與技術上的創新遠遠落后于美術創作。由于音樂作品的生產機制遠比美術作品復雜,新音樂的境遇也就更為艱難,那些意欲以新觀念、新技法、新內容、新形式來創作音樂作品的作曲家們,或偃旗息鼓望洋興嘆,或遠赴歐美另謀發展。所以,以復制為主要手段的音樂作品遠比以創新為主要目的的音樂作品更容易獲取“生產資料”。

圖 7
結 語
有關本文話題一開始時的“3W”提問,似乎每一個從事音樂創作的人都認為自己能夠作出明確回答。但審視一下一個階段以來的音樂作品,就可以看出許多創作者并沒有透徹地思考過這三個問題,即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高端”作曲家,從其新近創作的作品中透露出來的那種矯揉造作和言不由衷,可見他們也未必徹底地領悟了藝術創作的真諦。
中國的藝術尤其是音樂若想在當今世界的藝苑中奇葩頻現,包括作曲家在內的藝術家們就必須認真地審視自己的創作觀念與審美取向,明確自身的社會責任與創作的文化意義。我們的藝術創作若要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宗旨,就必須真實地反映“蓬勃的生命在現實社會環境中所承受的焦慮、不安、無奈等等。社會的巨變,各種領域內部的矛盾沖突以及全社會的矛盾交織,社會分配和社會成員相互之間社會關系的改變,政治體制由此帶來的社會治理結構的轉型,人們生存空間的改變導致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的變化,無不造成人們的種種內心沖突”(天乙,《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是怎樣實現的——鐵心油畫作品評述》)。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落實“五個建設”總體發展布局的工作要求,而這個“五位一體”的奮斗目標都是要以創新為前提來實現的。如何以高質量、高品位、高效應的藝術創作來推動文化建設更上一層樓,不應只是藝術家們要思考的問題,但作為藝術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境況與自己的責任:“進入21世紀,中國文化創新缺失的危機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傳統文化強化創新機能,藝術應該先行,應該通過藝術的頻繁、活躍、生動的創新,來營建社會追求創新的氣氛,制造文化的進步動力。”(鄒文,《當代藝術:宏觀復制、微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