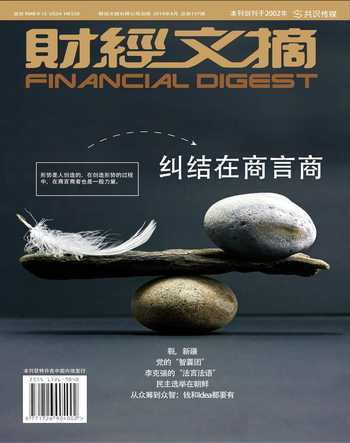霧都孤兒,走向何方?
袁家珣


一般來說,對于一件事,不管你做了什么選擇都好過讓結果來選擇你,然而霧霾就是這么一件無奈的事,你罵這國家只搞經濟建設,不顧藍天白云青山綠水,不顧人們的生命安危,但到底也得拼死拼活地蹭口熱粥。30年來大工業化的成果落進得利者的腰包,但大部分人還沒來得及嘗到一點甜頭,卻得一起分享著空氣里這份惡心。小資布爾喬亞們開始意識到健康,鍛煉身體,吃東西講究有機,無奈外界之毒無孔不入,就像那則網絡笑話:一個老外來到北京,每天堅持繞著二環跑步,2年之后,得了肺癌死了。
中國人到底關不關心霧霾,近年來是肯定的。
北漂青年早上先刷一下手機PM2.5指數,可以不出門的待在家里,門窗緊閉......媒體上關于霧霾的報道并不鮮見,2013年人民網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人們關注的并不是“嫦娥奔月”和航空母艦,而是食品安全、物價上漲、空氣污染等民生問題。而霧霾上升到民生問題的范疇,其實還有勞美國大使館把那微波爐大的偵測器帶進來,還有那些微博“大V”們的殷勤轉發“又爆表了”“毒空氣肆虐”。
霧霾在全國各地“爆發”,并非最近才開始的,之前也有不少“空氣污染”的議題,只不過“霧霾” 一詞還未普及,有些人仍以為那只是霧,或只是簡單的“大城市空氣不好”而已。有北京網友指出,最早播報PM2.5的時候人們還不太當回事,過了大半年之后,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霧霾會讓肺變黑,那些當年調侃戴口罩的外國運動員“怕死”“居心叵測”的愛國青年也不得不加入口罩哥們兒之列。
的確政府也開始關注了,畢竟霧霾不像家里垃圾,往別的地方一扔,就可以假裝看不見。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民眾信息來源多了,用“藍天指數”哄哄民眾終究不是長遠之計。最初也有些發言者說PM2.5不重要啦PM10才關鍵,后來也不得不羞答答地承認PM2.5的毒能量。但是,經濟保八的包袱放不下,要大量減少排放或停止生產不可能。中國一開始還可以把重工業移到不那么醒目的地方,讓各地自己去解決,反正門面干凈就好,但顯然這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只是設了一個定時炸彈。
才沒多久,那些令人懷念的鄉村已經很難找到一方凈土,適宜生存之地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如今霧都之人們也無去處了,可悲的是,往往直到自身生存條件受到危害時,大家才慌忙地開始想辦法。
不可承受之重?
中國人到底關不關心霧霾,首先我們是否認識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PM2.5里面有什么,工業廢氣、建筑工地揚塵、汽車尾氣等占了多少比例,什么才是治療之方,專(磚)家們各說各話,民眾一知半解,而許多城市連測試器都沒有,在信息極度不透明的情況下,關心起來特別費力。
另一方面,還有更多的人先填飽肚子才能考慮那東西是不是地溝油,空氣好不好;如果空氣質量改善也會拍手叫好,但帶來的效益遠不及物質上面的改善。不要說考慮戴什么樣的口罩了。
即使關心霧霾,并不代表會做出行動,比視而不見更可怕的,是習以為常。所謂改變不了大環境,就改變小環境,改變不了小環境,就去適應環境。是的,“咱沒那個權力,也解決不了”,當今大多數人顯然還是在尋找適應環境的方法,比如戴口罩騙騙自己,或干脆搬家移民,但是當環境正吞噬著生命時,豈容許人們去適應?顯然這已是無路之路。
改善小環境,就得多出一些麻煩,你會為了減排而坐地鐵,或是改開電動車嗎?你會上訴附近的污染企業,還是收了一筆錢就搬走?而對于那些更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或是對于那些直接制造污染源的企業,能做的就更多了。“反正不差我這一份”是要人命的毒藥。
環境污染是個惡性循環。美國學者威爾遜曾提出破窗效應這一概念: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不去修補,不久就有更多的窗戶被人打破,在公眾麻木不仁的氣氛下最終導致整體敗壞。前不久有媒體人預測:10年內一定會有極端的環境災難事件出現,想必非無稽之談。跟許多問題一樣,這需要從規律、制度上找原因,而普通民眾也有一定的角色,當然這除了需要渠道和平臺外,也跟公民意識脫不了關系。
盡管作為一個個體,要承擔起推動環境改善這個擔子,似乎是不可承受之重。不可否認,環保更多的還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在“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上,政府缺乏治理方案和監督體系,國內環保部門靠掛在各級地方政府部門下,以至于對本級政府的制衡作用受到限制。產業升級以及能源消耗量的控制,難度之大不是一般。更重要的是,社會缺乏一個獨立于其他勢力又能夠達到制衡作用的群體。至今也有一些環保組織站出來了,雖然與國外比起來能發揮的影響力較小,但總比兩手一攤等死好。長期被裹在“官本位”的蛹里,突破雖不易卻有必要。
制度與人性的關系是巧妙的,所謂的道德正義有時候是權力和價值觀的產物,“文革”時的告密文化就是一例,只要權力在控制、管理著生命,公民性在權力之手越強的體制里就越卑微。在霧霾籠罩的中國,“公民”更該拋頭露面了,并不是要學習雷鋒精神,而是以公共利益為根基,從而使得社會各種層面的權利都能受到關照。
并且,環保意識其實就是舉手之勞,從最小的地方開始,就像日本人回收寶特瓶會先把外面那層皮剝下來,皮和瓶蓋分別處理,就像臺灣人在外面吃飯還會自備筷子。再說,當社會愈來愈多公共知識分子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勢必能起到規范力量,不然,人人都不想扛的擔子自然會忽喇喇似大廈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