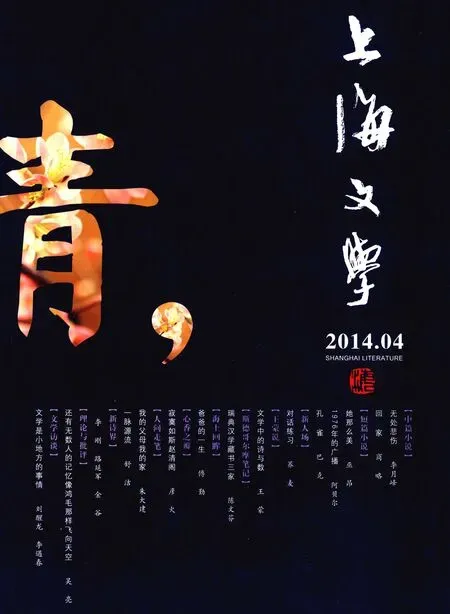還有無數人的記憶像鴻毛那樣飛向天空
吳亮
葉兆言在長篇小說《很久以來》的“后記”中流露的明顯不適、抵觸與懷疑絕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即對他所不滿的知識分子精英們之中國歷史解釋和人性解釋——這里我們難免會想起艾略特講過的一段話,他說“一個可能成為偉大藝術家的人,仍然可能具有壞影響”,緊接著艾略特以彌爾頓為例,聲稱后者對十八世紀壞詩的影響超過了任何人——現在,這個彌爾頓的幽靈則是以一個影子群體的復數形式出現在中國的;而在文學里,自詡掌握了歷史真相和政治正確的知識分子精英們,即便他們手里可能的確持有真理鑰匙或者他們可能同彌爾頓一樣偉大,就像一百年前艾略特形容的那樣,今天照樣正在影響一大幫“蹩腳詩人”。
《很久以來》第二章“北京,2008年的大雪”,作者作為“敘述人”第一次在文本內部“分身”,從剛剛開始的情節中間切入,說明性地折回到產生寫作這部作品的念頭之前,耿耿于懷地插敘了“故事中的作家”身不由己在北京經歷兩次質量低劣的國際性文學交流——2006年主辦方是德國一家著名讀書俱樂部,“一向不喜歡在大庭廣眾朗讀,不喜歡不斷被重復提問,不喜歡拋頭露面”的“南京作家”遭遇了兩個雖愚蠢卻認真的問題讓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前一個問題“你在中國寫作自由不自由?”來自對中國未必不了解的德國童話作家,后一個問題“你動不動就描寫秦淮河邊的妓女有意思嗎,難道不庸俗嗎?”來自對南京未必了解的中國美麗姑娘。2008年則又是被動性與東歐詩人們的交流,其中某位捷克詩人尖銳地指責“哈維爾既不是一個好作家,同時又是個政治動物”,而另一位“鏗鏘有力的糟糕普通話很像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湖南詩人繼續鼓吹詩歌應該占據金字塔頂尖的陳詞濫調,盡管這位詩人早已成為發了財的有名書商,魚翅熊掌兼得之后,不無得意地用“詩人可以人格分裂”與文學史上詩人經商屢屢得手的個案為這種人格分裂進行標榜性自我解嘲。
這四個問題各自將引向的所謂正確結論,或可能被意識到隱匿在問題背后的結論陷阱,統統是一目了然的,同時也是“壞”的,即只有“蹩腳詩人”才會醉心于這樣黑白分明的真理與假裝隱藏著的秘密;換句話說,自阿多諾聲稱“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之后,誰再鸚鵡學舌重復阿多諾這句話,“即便不是壞的”,起碼也是十足愚蠢的——文學的邏輯就是如此。
故事是在南京,從“1941年3月30日”拉開帷幕的。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時間,現在則是一個被虛構的時間,欣慰和春蘭在這一重疊時間里相遇了。小說家必須受制于真實歷史,不得不表現出小心翼翼的態度;同時小說家必須動用他的自由想象權,兩個女孩兒的初次見面安排在這一天看似情節巧合,宿命隱喻卻也昭然若揭。依據資料檔案,故事敘事人笨拙地提示這個歷史真實日子的不同尋常之處——汪偽政府設定的“還都紀念日”恰逢一周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故事的主人公欣慰,這天是她的十二歲生日,而她之所以牢牢記住了這一天,只是由于欣慰遇到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春蘭。這種看似無意的碰巧和對比,暗示了整部小說的“輕與重”將被刻意顛倒,現在讓我們暫且先放下這一有待深入的話題。
《很久以來》前四章,有三章背景放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淪陷的南京以及上海,凡涉及亂世當年之地名景觀、顯赫人物、政府設置、宗教機構、樓價暴跌暴漲乃至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在南京街頭出現的著三種顏色警服的警察之奇觀描述,小說家考據可謂細心謹慎,然而這并非小說家熱衷于此。盡管《很久以來》多處提及汪精衛、陳公博與周佛海,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將周佛海扯進故事,不但成為欣慰父親竺德霖留日其間的老相識、此后的頂頭上司兩者還過從甚密。小說家慣用的伎倆通常是,在細微末節處處留意,在緊要關頭逸筆草草——故事敘述人回避對中日戰爭發表個人觀點不是無緣無故的,有時候,故事敘事人也會虛與委蛇,在他認為有必要的地方不痛不癢地套用國家教科書觀點,不僅因為小說家本人不愿意在此冒險,更關鍵的是:為他所關注的被大歷史遺忘的諸小人物,既非抵抗者或出賣者,亦非橫尸沙場的無名英雄或大屠殺蒙難者;而是那些繼續生活在淪陷之都,渺小卑微、平庸瑣屑、無力自保的被本國武裝力量因抵抗失敗而放棄的“城市非戰斗人員以及他們的家眷們”。
可是溯流而上,小說進程直至終局,我們恍然發現,欣慰這個形象并不是從上述“歷史小人物們”或“一場戰爭浩劫中幸存下來的家眷們”中遴選出來,類似別林斯基式的“這一個”。尾隨著《很久以來》緩緩推進,時間將不可抗拒地慢慢走進另一場浩劫,欣慰的故事則令人驚奇地朝相反的方向走。葉兆言在“后記”里泄露,“欣慰”這個文學形象起源于“1971年盛夏某一天”,年方十四的少年作者在飯桌旁聽到了父母的談話,他們“萬分震動極度恐慌”,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熟悉的女人“真的會被槍斃”,她叫李香芝,一個真實地存在于歷史檔案中的女人。我們不能斷定李香芝就是“竺欣慰”的原型——至于《很久以來》第九章“2011,南京,上海”,“故事中的作家”已將“李香芝”與“欣慰”并置于同一個“虛構/真實空間”,則不過是小說家擅用的雙重障眼法,即不僅存心混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同時這一露骨的用意又反過來加強了故事的虛構性,而只有被確認的虛構性所具有的說服力,才能達至小說家所需要的真實性。無論“虛構的欣慰”是否是“真實的李香芝”借尸還魂,這種引人入勝的對小說人物的“原型”與“本事”之追究偏好,現在尚不是我們將要重點討論“真實”這個概念的動力。
《很久以來》的真實由兩部分組成,一半是“出處的真實”,一半是“重新想象的真實”。那么,什么叫“出處的真實”?什么又叫“重新想象的真實”?司湯達曾經十分粗鄙地聲稱,“要以‘事實取代‘好看的情節”,甚至建議“文學應該停止模仿,直接去敘述和轉述”,因為“已經過去、已經消失了的豐富性,不可能被重建了”。作為小說家的司湯達在說這個話時肯定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一,它是這樣發生的;二,它在事實上是如何發生的;三,歷史不可能讓我們直接接近那個客觀事實;四,意識形態和寫作策略會決定小說家的選擇,他的關注對象以及如何描述。按照這個順序,《很久以來》的起源與形成就可以這樣平行地建立以來:一,1971年盛夏,少年作者從父母那兒聽到了李香芝被槍斃的消息,“聽到這件事”構成了第一個確鑿事實(它是這樣發生的);二,多年以后,作者通過傳聞與檔案資料了解了李香芝事件的部分內情,開始追溯“那件事”(它在事實上是如何發生的);3,因“歷史不可能讓我們直接接近那個客觀事實”,作者訴諸想象,萌生了虛構一部小說的念頭;4,2008年之后,作者不滿于“蹩腳詩人”和“知識分子精英”對類似歷史題材的流行詮釋,最后決定以他的“意識形態和寫作策略”對這一必須“重新想象”的題材進行“選擇”。
被不同的人陳述的事實不僅各不相同,且殘缺不全,即便陳述人信誓旦旦保證其陳述完全真實確鑿,亦未必一定可信。但與法庭證人證言的司法解釋不同,小說是一個公然鼓勵放肆虛構的語言領域。為了營造返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歷史場景的擬真氛圍,也為了滿足作者從檔案中尋找隱秘樂趣的偏好,《很久以來》前幾章諸多篇幅描寫來自“有出處的真實”,亦即“舊聞史料”、“大事記”、“卷宗”或“機要密錄”,或許這些頗費作者一番心思的歷史考古學知識恰恰構成另一些不愿合作的讀者最感乏味的段落——虛構文學的傳統魅力在于,它與我們對歷史和科學的理解不同,它不要求它所揚言的真實性需要我們過于認真地對待,虛構本身就具有不被認真對待的性質,我們甚至能夠預見它得到的反應還包括否定性:不合作、質疑與誤讀。
不過誰又會質疑作為虛構作品的《很久以來》之史料引用不當、鋪張、錯訛乃至濫用呢?第三章“上海,南京,1941年12月8日”,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為題,幾乎用了全部篇幅,不厭其詳地敘述了欣慰之父“竺德霖”的身世,只在這一章最后輕描淡寫地敘述少年欣慰和春蘭在上海一家旅館白色搪瓷浴缸中一起洗澡,那個夜晚飛機在空中盤旋,防空警報呼嘯,日軍已進入公共租界,欣慰趴在窗臺與正在樓下站崗的日本兵目光相對,春蘭嚇了一跳,欣慰卻毫無懼色……作為愿意與《很久以來》的想象力合作的讀者或許以為這部小說不過是“亂世佳人”的中國版,只是真正的亂世和劫難還在后頭。由于我們已經事先獲悉無辜的竺欣慰將蒙難于三十年之后一場國內浩劫的暴力機器絞殺,那么請在此輕描淡寫的幾行字面前稍作停留,“欣慰仍然沒有絲毫懼色”,如霍蘭德所言:“她永遠不會再回到這個場景了。”
這個揮之不去的情境,就是前面所指的“重新想象的真實”。與其說故事講述者傾心投入給《很久以來》的“新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不如說故事講述者對想象力的發揮非常節制,相對于民國歷史資料引用所派生出來的“衍生想象”之風生水起、活色生香,《很久以來》那些男男女女的行動想象、欲望想象和情節想象,絕大部分都是俗套的、灰色的、匱乏的——尤其當他們集體進入到第五章之后。英國詩人布萊克偶爾也說粗話,當然不是在平常罵人的時候,“這破爛的記憶啊!”有一次布萊克這樣形容不堪回首的某些往事,不知道他是悲憤還是反諷。“肉聯廠的冬天”,第五章用這樣一個粗俗的小標題究竟別有深意,還是信手拈來?灰色想象必有灰色的外在現實土壤,灰色生活和灰色人群必留“破爛的記憶”,及至灰色人群漸漸被推向紅色生活,覆水難收,所有人不能幸免,所有人的記憶變成腥紅的海洋,春蘭夢見欣慰身穿紅色羊毛外套“血淋淋艷麗”不再“黑白”。灰色時期主題是飲食男女,情節粗鄙語言露骨,細節是饑餓、虱子、豬油、狐臭、真刀真槍;紅色時期的沉重幕布拉開,地點依然“肉聯廠”,景觀壯觀、粗野而原始,“一個被圈起來的大棚,幾個大缸,滿地鴨子,活的和死的,十幾個女人一手拿刀,一手一只接一只撈身邊的活鴨子,拎起來就是一刀,那些鴨子無處可躲,挨了一刀有的立刻斃命,有的躺在地上掙扎,最觸目驚心的,是一只挨過刀的鴨子,頸子斷了,居然耷拉著腦袋向欣慰走來,這情景讓春蘭不寒而栗。接下來是去看殺豬,殺豬已經完全機械化了……”此流水線屠殺場景不僅屬于葉兆言的“肉聯廠”,也屬于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墻》。愛德蒙格·弗洛伊德說:“無論整個人類還是個人,過去的一切都不會遺忘,它將以變形的方式反復出現在我們的心中。”華茲華斯有一句詩,“這一事件給我無盡的悲傷”,然后他自己意味深長地反諷道:“我帶著陳腐的道德進行反思”!
《很久以來》沒有通常人們理解的那種“對文革的反思”,很遺憾,這個似乎刻意安排在《第七章》“欣慰之死”中的“奧威爾一頁”立即被翻了過去,故事講述者顯然不愿意在此停留。《很久以來》不以思考尖銳見長,反以重申婦孺皆知的街談巷議和長輩的陳腐教誨引人矚目。無論隱身故事之內的講述者,還是跑到故事之外現身說法的作者本人,都反復為一種“活著就好”的求生哲學辯護,同時為文革浩劫中罄竹難書的鴻毛之死感到“無盡的悲哀”,不值得啊!“很多事千萬不能太當真”、“天大的事過去了也就過去了”、“死了也就死了,基本上是白死”這一類句型的“毋庸置疑之常識”在《很久以來》中不絕于耳,可能就是有感于唯大梟雄死了才會被后世熱衷“會當臨絕頂”的墨客騷人樹碑立傳并贊頌為“重于泰山”,鴻毛固然永遠是鴻毛,但鴻毛再輕也固然是生命。
時過境遷,回溯腥風血雨的文革歷史現場,回憶起一個一個渺小生命被翦除被扼殺,發出這樣的事后感慨難道僅僅是出于無奈與自我撫慰嗎?渺小者的想象替代不了偉大者的想象,渺小者善良的個人愿望也改變不了偉大者無情的歷史判斷。作者說“文革的最大特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樣的例子當然有;不過這個概括性描述反過來可能更成立,即文革的另一個致命特點恰恰是“無事生非小題大做”,直到釀成“人命關天”乃至“驚天動地”的大禍,政治肉聯廠的屠宰流水線一旦開動,無論天下大事還是區區小事,絕不是當年任何人想過去就能過去的——但是這個幾乎沒有爭議的描述,并不能改變、也沒有改變今天渺小者與偉大者各自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地位,渺小者們的命運依然被相信歷史決定論的偉大者們繼續決定著。只要渺小與偉大在正義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輕與重在美學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權力者與無權者的現實狀況沒有絲毫改變,我們就拒絕簡單地將《很久以來》的此類議論看作是一種婦孺之見,而寧愿看作是一種“含混表達”,如果還不是“反諷”的話。赫勒指出,“含混從未被認為是一種力量,而在卡夫卡那兒偏偏如此。”含混的力量!如果“含混”在卡夫卡那兒表現為自甘失敗,意味著“一切障礙粉碎了我”,那么在葉兆言這里“含混”則表現為承認陳腐,意味著“想不開也就想開了”。
“想不開也就想開了”就這樣不可抗拒地成了欣慰與春蘭下半生唯一可以選擇的人生哲學,肉聯廠的暴力美學替代了六朝古都的頹廢美學,后來者居上,殺氣騰騰的閭逵替代了眉清目秀的花花公子卞明德,替代了英俊黝黑的抗大干部羅福庠,粗鄙戰勝了文雅,本能壓倒了愛情——愛情即盲目,人類社會男男女女反復無常,品味猶存的欣慰偶然選擇了卞明德,仰慕成熟的春蘭偶然選擇了羅福庠;好景不長,婚姻即計算,肉聯廠生存鐵律不可抗拒,最終粗鄙野蠻的閭逵先后成為這兩個女人的丈夫——這難道又是《很久以來》為我們勾畫的關于在極端年代發生于蕓蕓眾生間的男歡女愛曲線圖?沿著一條挫敗、隱忍、墜落、凋零的下滑路線,“想不開也就想開了”是否就是“不接受也要接受”的宿命訓示?由此看來《很久以來》幾乎是絕望的,盡管它不斷絮絮叨叨地用諸如此類的警世通言安撫我們,《警世通言》的道德訓示或許早已陳腐不堪,《警世通言》中的人物卻一直在故事里呼吸,只要我們再次將之打開。《很久以來》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僅僅含混而且陳腐地說破了一個秘密——世界依然是陳腐的,新鮮的理論說辭改變不了陳腐的世界,而描寫人類渺小悲劇的虛構小說,用龐德的話比喻,不過是“從一個陳腐形式到下一個陳腐形式之間呼出的一口氣”。
這樣就解釋了為什么《很久以來》敘事風格接近詠嘆,像是“一聲長長的嘆息”。第一章,通過故事敘事人,隱藏于背后的作者撇開南京淪陷汪偽附逆之重,“輕描”欣慰跟著朱琇心師傅學昆曲,順手錄下《桃花扇》里的一段〈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顯然插入了一種不合時宜的感傷主義小說的哀婉氣息,“商女不知亡國恨”不再被認為是諷喻弱小無力之平民百姓的失節……直至整部小說塵埃落定,后記中,作者似乎還有話要說,內容既非控訴極權政治亦非建議全民懺悔——這些論調不再會被認為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秘密——就僅僅重復了幾句“做官永遠是好買賣”、“平民百姓才真正永無出頭之日”,莫非是一種本土化的在蒙田意義上的消極經驗主義?作者干脆含沙射影地抄下了元朝張養浩《潼關懷古》后半段:“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兩個“陳腐形式之間”的兩次呼吸,陳年老話總有道理。太陽底下無新事,蒙田在五百年前就敏銳地指出“人類認識的不一致性”,受不可靠的不同文化模式影響,普通人容易相信他們最早接觸的論點、偏見和迷信,他們愿意相信循環論,因為他們總以為自己看到的類似現象今古無異;至于博學之士,他們的知識帶來的自信與高傲,往往妨礙了他們進一步深刻地理解事物的復雜性,導致這些出類拔萃之輩不愿聽取別人的意見。毫無疑問,此后的積極經驗主義者培根希望將正確知識影響知識分子精英,然現今所謂的政治哲學反思,儼然是某種曲高和寡的知識分子自詡之特權;而蒙田所謂的消極經驗主義或狹隘經驗主義,卻永遠在那兒提醒一種“平民百姓”的頑強存在,小說家不只是有責任“觀念性地”指出“怎樣的思考是對的”或“怎樣的結論才是合乎理性的”,還要退回到“文學地呈現”出“其他人不是這樣思考的”和“凡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很久以來》回到了蒙田的傳統,它誠實地呈現了人的命運、情感和經驗的局部性,呈現某一種復數的思考之停滯,回顧往事,對生命流逝的無盡感傷、對無謂犧牲的悲涼痛心、對歷史循環論的消極認可,“無話可說”是它最終的沉重嘆息。
顯而易見,《很久以來》對議論并不感興趣,因此凡在情節進程中遇到不得不議論兩句的地方,敘事人敷衍式的見解從來不會比故事的當事人更深刻——敘事人既不愿拔高故事人物的思想狀況,也無意拔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將“欣慰之死”或曰“一個渺小人物死于非命”的悲劇瑣屑化,就像諾克林所辯護的,將浩劫祭壇上的無辜犧牲“貶抑到平常與家常的領域”,擯棄浮夸的慘烈、悲憤與慟哭之場面描寫,反而著墨一些瑣屑、無聊、心寒乃至不堪的細節——小芋所表現的大義滅親極端冷漠并不意外,閭逵在欣慰的最后時刻還在猥瑣地幻想、窺探他妻子是否曾經對他不忠,卻像是來自另一個方向的赤裸裸冰水,粗暴地撕開了本來就沒有過溫情的性愛面紗,“一切固有的和有差別的東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沖垮這個秩序的不是無情的資產階級工業大革命,而是激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先知般的預言居然在字面上被一連串低卑的瑣屑情欲顛倒性地涂改了。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徹底的、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說得何等好啊!有時候我們真要懷疑,似乎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人類的某些兇悍的歷史行為,無法理解人在某種特殊處境中選擇的反常行為。渺小者,無權者,或此刻所謂的卑賤者,他們有時候三位一體,有時候則不是。他們什么時候“輕”,什么時候“重”?作者“后記”提醒我們,文革中“逞一時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沒有快活幾天”,是啊,法國大革命吉特倫派、羅伯斯庇爾派也沒一直快活下去。但是不管時間長短,革命作為“人民的盛大節日”,歷史的小人物們畢竟“快活過幾天了”,渺小者成了歷史車輪,無權者成了領導階級,卑賤者成了最聰明者——等到“天下大亂”重新回到“天下大治”,有的人“扛過一時,熬過最艱難的幾天”就豁然開朗,“苦難變成永遠的資本”;有的人“苦難一世,苦難永遠是苦難”,換句話說,一旦秩序恢復,無數篡位與錯位的渺小者立即被打回原形,一切渺小者、無權者與卑賤者將重新歸位,迅速脫魅!
《很久以來》講述的,就是一個很久以來一直頑固地沒有改變過的人類歷史真相與真理,迄今還沒有過時,至少在作者看來是如此,或許作者佯裝相信如此——所有的高談闊論和貌似嚴肅的提問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們的作家根本不愿意談論或回答此類問題——真實的狀況是:平民百姓,祖祖輩輩,或蕓蕓眾生,亦即所謂的渺小者群體,他們是人類中最大多數,他們遍布世界每個角落,他們就在我們身邊,他們中就有我們自己;他們和我們都是身居其中的作家的寫作背景和寫作對象,作家對他們滿懷同情,又膽戰心驚地懷疑這種同情;作家愿意為他們爭取某種據說他們應有的天賦人權,又非常悲觀地懷疑這種人權是不是存在;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拒絕自以為有資格“怒其不爭”,甚至不愿意為他們難以置信的乖戾行為辯護,不愿意為他們不知好歹的受苦受難哭泣。
稍微討論一下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吧,烏托邦,反烏托邦,還有烏合之眾,反叛的大眾,大革命,群眾與法西斯,一神教,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無權者的權力、通往奴役之路等等這些概念——也許《很久以來》的作者并非平時沒有涉獵這些其實一點都不深奧的詞,只是他不愿意在一部虛構作品中深究這些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和精神分析議題。但是我們終究要涉及,哪怕是浮光掠影地涉及,因為我們已經為《很久以來》做了文學辯護,我們重申了一部小說是一個自足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疆土和邊界,小說主要功能是呈現真實,而不是表達正確;我們指出了《很久以來》的風格是詠嘆調式的,它隱藏著的美學主題是“輕與重”,而不是“是與非”,更不是“善與惡”。現在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完全按照小說的疆土與邊界劃定的路線,亦步亦趨地進行我們的思想旅行。抬起頭,在這個“自足的世界”之上,是我們唯一可以共同仰望的自由天空,我們不能想象只有呈現的小說才能告訴我們全部真實,尤其是——當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幅員遼闊的東方國度所發生的故事,這故事不過是千千萬萬類似故事的其中之一,而這個故事又與具有類似經驗和遭遇的犧牲者、幸存者、遺忘者、曾經的施害者或受害者、仍然懵懵懂懂地活著的無數渺小者繼續發生血肉聯系的時候,這樣的討論也許并不應當刻意回避。
在《很久以來》這出詠嘆式悲劇的核心部分,作為全景社會的極權主義運動始終是一種籠罩其全體成員的迷狂氛圍,它本身就具有時代全景式劇場的性質。時光倒流,它的劇目浮出我們記憶,它的主題是階級斗爭,它的遠景是烏托邦,它的燈光是紅色,它的角色人物包羅萬有,它發生在正當性不容懷疑的國家內部,這一國家似乎已失控秩序似乎已不存在但是它的暴力專政還存在,甚至更突顯其無所不在——最高領袖與平民百姓全體卷入連續不斷的最高指示和不分晝夜的群眾聚會,學習、教育、改造、洗腦、監督、舉報、斗爭、揭發、隔離、監禁、告密、公審、表決、判決直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處決他們的異類和同類。渺小的平民百姓被一種難以想象的激情所蠱惑,他們義憤填膺山呼海嘯,他們的內心隱藏著恐懼;他們被迫選擇敵人繼而配合發現敵人甚至為了自保不惜出賣親友,他們害怕被揭發所以選擇了主動坦白與揭發,他們害怕被人民陣營驅逐所以忍辱負重接受了莫須有的罪名;天地旋轉日月無光,他們全體無法逃脫,誰不屈服誰就不能生還,在永無休止無所不在的階級矛盾和敵我矛盾的鼓動下,幾乎所有的權力者和無權者、高貴者和卑賤者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或施害者——這樣的描述難道就一定準確嗎?也許我們的小說家未必會認同,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就讓我們做出一次妥協,就像蒙田的消極經驗主義告訴我們的解決方式,各自相信自己的經驗和堅持自己的偏見,至于那個“整體”或“總體籠罩”先請它見鬼去,我們依然返回到《很久以來》的規定情境與規定人物中,讓我們把最后的焦點匯集到故事里的三個女人身上,一個“欣慰”,一個“春蘭”,另一個是欣慰的女兒“小芋”,看看我們還能說些什么?
《很久以來》的作者事后形容“欣慰和春蘭有點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和薛寶釵”,但是忘記補充一句,《紅樓夢》夾在兩個女人之間的賈寶玉位置不幸被薛蟠式的閭逵所占據,這又何其悲涼——如同作者后記中特別提到他讀到林昭《祭靈耦文》,后者竟然為“柯慶施那個老男人”寫下“讓他們靈魂而今如何兩情繾綣以膠投漆”的肉麻字句,令我們的小說家立即“天昏地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涼”。欣慰被男友李軍揭發是“悲涼”的,欣慰要求春蘭揭發自己是“悲涼”的,小芋被女公安通知竺欣慰已遭處決表情平靜是“悲涼”的,故事結尾春蘭告訴小芋她的母親獲得平反昭雪,小芋依然表情平靜是不是還可以用“悲涼”來描述,來定義?如果現實的林昭內心情感秘密之不可理喻,對我們的小說家簡直是一個無底深淵,是因為此前即已預設了前者的殉道者形象;那么虛構的小芋令人齒冷淡漠無情的背后又是怎樣黑暗沉默的深淵,小說家又作如是想?
欣慰不是殉道者。故事講述者沒有具體告訴我們她有什么政治信念,或懷疑某種政治信念,她的入黨不妨理解為當年的風潮——在故事講述者看來,重要的不是政治的欣慰,她根本就不政治,不過是一個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渺小人物,纏繞于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工作變動與男女糾葛,她就像我們最常見的那種容易發生傳統故事的女人,命薄心高遇人不淑,不知為何,這樣的女人總會給自己和身邊的人招惹麻煩,正是一場難以躲避的全景式政治浩劫,使欣慰的性格麻煩變為政治麻煩,最終招來殺身之禍。欣慰的“糾纏模式”終止于極權政治的斷裂性震蕩,以那種被現代政治分析歸納為“受害者與施害者的巧妙配合”的命名去解釋欣慰的處境與結局,并不是不能考慮的。我們驚奇欣慰在她最后日子其間言行舉止的匪夷所思,她的遺物沒有一個字留給女兒讓我們迷惑不解,她的遺書聲稱自己是一個理想的革命者讓我們難以想象,她似乎突然變了一個人,她好像只有幻想自己是個殉道者,這樣才能接受引頸就戮的蒙難者命運,她居然像是模仿布哈林一樣在臨刑前呼喊領袖萬歲,視死如歸,所有這一切瘋狂想象,所有發生在她眼前我們卻無法看見的幻相,都是欣慰,不,是《很久以來》作者為我們留下的謎題——這個謎題當然首先是屬于文學的,但又絕不是文學本身可以自動揭示的。我們再強調一遍:《很久以來》消極的詠嘆調風格,以及將“輕與重”位置顛倒,雖然暗含了“反崇高”的潛意識,但未必出于刻意。我們不認為弗萊徹所謂“崇高風格具有摧毀奴性快感的功能”是絕對正確的,這也是我們為什么一開始就指出“崇高的彌爾頓可能會對蹩腳詩人產生壞影響”的原因——不過弗萊徹的另一句意義平常的話卻十分適合《很久以來》,“災難是一種逐漸的磨損,它慢慢地磨損人生,終于某一天猝然停頓”。
現在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很久以來》骨子里是沉重的,壓在故事人物身上的不是暴行與罪惡,而是一種仿佛永遠不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左右、一種被難以逃脫的蠻橫外力所無情裹挾的靈肉苦難——欣慰曾經是輕盈的,還有輕盈的春蘭,輕盈的甚至輕佻的卞家六少,輕盈的所有其他《很久以來》中的渺小人物,對于這大多數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渺小人物,通向烏有之鄉的道路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是通向祭壇的道路……但是,我們突然從中發現了一個人,“小芋”,她的出生是個意外,她身體瘦弱,她幾乎在沒有愛的環境里長大,她成為母親的累贅被親戚寄養,她被忽略,她是一個多余的孩子,她沉默寡言她的心理活動小說家似乎一無所知付之厥如——無獨有偶,第六章以“小芋的寂寞”為題,作者卻以大量篇幅啰啰嗦嗦述敘欣慰與春蘭私房話以及各自的男歡女愛,不僅于此,連閭逵強暴春蘭都發生在已經熟睡了的幼年小芋身旁,而“小芋”究竟怎么“寂寞”統統留給了我們的想象——德·曼有一句話好像專為《很久以來》說的:“作者就是那個‘說得多,卻‘知道得少的人!”
不能直接觀察到小芋的心事,可以看見小芋的行動,《很久以來》展示了小芋一些值得分析的“標志性細節”,她封閉內心,以沉默為自保,以謊言為抵押,她預支安全和不為人注意的私人自由,她對外界保持警惕,她的選擇和行動總是那么出人意外,連我們的小說家都難以想象:多年之后再遇到小芋的時候,她已經同幾個不一樣膚色的數位外國男人生了四個混血兒,聽說之前她為了出國不惜代價,小說家的伯母對此“不可理解”,這又是蒙田為之辯護的個人經驗主義判斷總是會對另一種個人經驗主義選擇感到奇怪的生動例子——我們缺乏反對小芋這樣選擇的理由,只要這個選擇完全取決于她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強制。小芋的父親母親皆為她與生俱來的“污點”,她的父親母親都不明不白地死無葬身之地,當周圍的人都遺忘她、忽略她、踐踏她之后,我們想不出她還有什么理由繼續留在這塊沉重的土地,她本來就是一個渺小的人,可能骨子里也是一個輕盈的人——讓我們為她想象,如果這種想象不完全是畫蛇添足,她的混血兒孩子不再追問他們母親的父輩,不再糾纏他們母親的歷史、血緣、語言與傳統,那么我們將慶幸小芋的遺忘或已經深入骨髓的不能遺忘的遺忘,一切歷史都將進入虛無,無論是宏大的歷史還是渺小的歷史,終究都要接受最后的審判,終究要來到上帝的面前。既然小說家在《很久以來》最后告訴我們小芋現在是個基督徒,那么我們就不妨想象此刻的小芋已經擺脫了不自由的大地、黑暗、苦難、屈辱、恐懼與悔恨,無數渺小的記憶與靈魂像輕盈的鴻毛那樣飛向天空。唯在這個“輕與重”位置再次顛倒之時,我們才能在相反的意義上引用彌爾頓的撒旦于《失樂園》的如此呼號:
別了,希望;
別了,和希望一起的恐懼;
別了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