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還鄉的回歸之旅
書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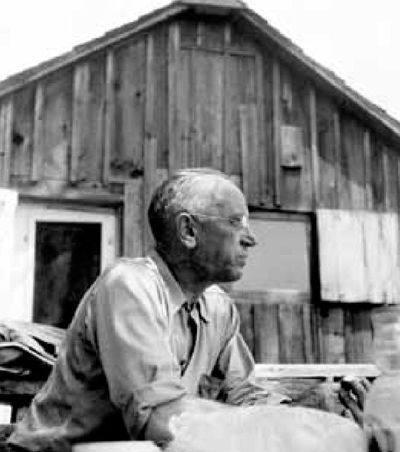

2013年初秋,國內書壇上出現了一束“重放的鮮花”——《美國自然文學經典譯叢》,它的譯者就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夫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外語系英語教授程虹。一直未有露面的程虹近一年來愈加受到民眾的關心,與其說是因為她有了總理夫人的新身份,不如說是因為她以教師的本來身份為大家奉獻了一套高水平的文學譯作。身為英美文學教授、曾經師從中國社科院文研所趙一凡先生并拿下文學博士的程虹,翻譯過許多外國的著名文學作品,如今她的譯著也成為國人熱買的書籍。《美國自然文學經典譯叢》包括程虹早年翻譯的《醒來的森林》《遙遠的房屋》《心靈的慰藉》三本舊作,以及新譯著《低吟的荒野》。這幾本書都是美國文學史上大名鼎鼎的自然文學家的成名之作,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經典珍品。這四部作品以優美的文學語言揭示了大自然的美麗、神秘和氣象萬千,展現了人回歸自然后所獲得的心靈自由與內在寧靜,反思了人與自然、人類精神與自然這些古老但被現代人漸漸忘卻的問題。面對這些作品,閱讀它們無疑是一次心曠神怡的審美經歷,一次開闊視野的求知探險,也是一次精神還鄉的回歸之旅。
本期我們就將沿著公眾聚焦的視線,把鏡頭對準程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并引入國內的美國自然文學寶庫,并由此伸展開去,帶領讀者進一步領略世界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
新大陸·新自然·新家園
美國自然文學是源于17世紀,興盛于19世紀,形成于當代的一種別具美國本土特色的文學流派。從形式上來看,它屬于非小說的散文文學,主要以散文、日記等形式出現。從內容上來看,它主要思索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簡言之,美國自然文學最典型的表達方式是以第一人稱為主,以寫實的方式來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進荒野中的那種身心的體驗。那是美洲大陸的移民們對于上帝賜予的這片沃土最深切的感情——掙脫了舊大陸(歐洲)的精神枷鎖,告別了舊大陸那已然人工化的、腐朽的自然,投身到一個新的世界,人們不僅煥發出了創造新家園的勃勃生機,同時也在北美的荒野中汲取著新的精神力量,孕育著美洲文化的新生兒,這個新生兒在未來將如雄鷹一樣擁有它自己獨立的天空。
美國自然文學總的創作思想與文體風格常常帶有比較鮮明的區別于一般文學的特色。如把文學描述的焦點由人轉向荒野;由生態視野而形成的位置感(sense of place)——“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完全并且創造性地與荒野共存的文明”;不是單純地寫景論景,而是借此抒發體驗自然的心靈感受,力求表現心性與自然的融合。再如19世紀的梭羅提倡用一種與土地相似的“褐色的語言”,寧肯自己的文章帶有幾分稚嫩,也不要那種雕琢的古板;20世紀的艾比則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自然而新鮮的,寧肯要表面的“鮮活”,也不要深沉的“死性”。
正如程虹所講,在美國自然文學中,每當我們想起一位作者,在我們眼前展現的也是一片片獨特的風景:美國自然文學的先驅梭羅,使人們自然而然地聯想起瓦爾登湖;繆爾使我們想起美國西部優美的群山峻嶺;艾比使我們想起猶他州孤寂而壯美的沙漠;貝斯頓使我們想起新英格蘭地區科恩角的海灘;威廉斯使我們想起了像人類一樣有生有息的鹽湖;迪拉德則使我們想起了那條奔流不息、每分鐘都是嶄新的汀克溪。在美國自然文學中,幾乎每位作家都有其與眾不同的寫作背景,他們已與腳下的那片土地融為一體,把自然的風景與心靈的風景融為一體,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永恒。
人與自然:由分離到共處
美國的自然文學作家不論是19世紀的愛默生、梭羅,還是20世紀的繆爾、卡森,大多崇尚像自然一樣有一顆質樸的赤子之心,為的是在紛繁的物質世界之外追求一種精神世界的提升,在工業化的喧囂中尋覓人的本真屬性。當然,由于各個創作時代的審美理想有別,各個歷史階段作家作品所體現的生態整體觀不同,當我們回顧美國自然文學發展歷程時,也好像是一邊欣賞參天大樹,一邊梳理和辨認著大樹的分枝和葉脈。
在早期殖民開拓時代(17世紀—18世紀),當時的自然文學從人類中心論出發,在人的主觀心靈與自然環境的審美結合中,突出“人”對“自然”的觀察。主要代表作品是約翰 ·史密斯的《新英格蘭記》、威廉·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開發史》、亞歷山大·威爾遜的《美洲鳥類學》等。
到了工業革命時代(19世紀—20世紀初),自然文學的立腳點雖然還未脫離人類中心論,但在人的主觀心靈與自然環境的審美結合中,已逐漸強調“人”對“自然”的精神體驗,自然不再只是一個僅供觀賞記敘的純粹的客體,它正在逐漸成為能給人帶來愉悅的精神反饋的寄托對象。 這也是具有獨立意識的美國文學擺脫歐洲思想文化束縛、走向崛起和興盛的時期,涌現了一批對后世影響頗深的先驅、向導和典型人物。比如托馬斯·科爾及其《論美國風景》的散文、愛默生及其《論自然》、梭羅及其《瓦爾登湖》、惠特曼及其《草葉集》等。
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通常被稱為后工業時代的來臨期。由于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有些已經走到了異端,工業化浪潮不僅使人類異化,而且使大自然滿目瘡痍。這個時期的自然文學已經開始從謳歌自然轉為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對人類給地球家園造成的破壞發出生態預警。反人類中心論開始盛行,作家的寫作,在人的主觀心靈與自然環境的審美結合中,開始由衷地表達自然對人的精神慰藉。此時“自然”和“人”已經有了位置的對換,由以“人”為主體去體驗自然,轉換為以“自然”為主體來撫慰人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約翰·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約翰·繆爾的《我們的國家公園》和《夏日走過山間》、瑪麗·奧斯汀的《少雨的土地》等等。
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信息化、數字化時代,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生態保護共性問題、東方古老的天人合一傳統,為西方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理念、新基因。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被看做是美國自然文學生態意識獨立自主的標志,也是世界文學生態學新紀元的開始。20世紀80年代,當代的自然文學終于以“生態文學”的樣貌和命名,從一般文學中脫穎而出、成就了自身的地位。近幾十年的生態文學也從海外傳播到中華大地,帶動了中國生態文學的萌芽與崛起。后期的生態文學繼續從反人類中心論出發,在人的主觀心靈與自然環境的審美結合中,終于超越了物我兩分的二元對立,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只有如此,人類才能最終找回那孩提一樣自然純樸的初心,在流浪了幾百年之后返歸自己的精神家園。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包括: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又譯《沙郡歲月》)、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亨利·貝斯頓的《遙遠的房屋》、特麗·威廉斯的《心靈的慰藉》、盧岑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等。
新的概念——“環境想象”
從19世紀的美國生態文學家及思想家梭羅、詩人惠特曼到20世紀的利奧波德、卡森等,他們是一群從自然荒野走向現代科技理性時代的先知,他們對生態想象和未來所做出的努力,都對后代起到了預警和啟示錄的意義,他們以各自不同專業和藝術眼光,穿透了當時科技理性或現代工業給人們帶來的迷茫,又用警示般的語言告訴人們,人們現在的生活受到人類中心價值或人類欲望的影響,已經陷入到無法自拔和自救的地步。從那個時期開始,歐美社會反思人類生態歷史的人越來越多。也是這樣一條生態思想路線,深深地影響了20世紀歐美生態政治的選擇和近十幾年“環境想象”思潮的蓬勃興起。
21世紀初,以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家、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布伊爾和英國生態文學家、利物浦大學教授貝特為代表的英美生態文學最前沿的人物提出了一種新的意識和觀念——“環境想象”。這個前沿的、先鋒的思想為我們昭示了從文學藝術創造的想象空間入手,去重開啟新生態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前兆,它將重構或更新人類社會生態精神文化,催生想象環境和夢想未來的契機。這是西方思想界尋求改變及超越自身文明、文化的一次新選擇。“環境想象”促使我們反思:現代社會創造、發明的科技在什么地方走錯了道路、選錯了方向?隨著社會進步發展起來的文化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早期的人類,用勞動和創造出來的文化回應著地理環境對生命的挑戰,也同時用創造性想象的環境意識或觀念來進行文學藝術的活動。人們更多的不是從自然中掠奪和索取,而是用藝術或宗教的方式去適應自然環境的生活,這時自然與人的和諧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地。那時大自然由人類來替它們代言,人是大地上的花朵,綻放了自然最深層的美麗。
人類的歷史,遠比我們所知的要久遠綿長,人類曾有與山水萬物共舞、與日月星辰同眠、與宇宙頻率諧振的黃金時代,對于精神的修煉提升遠勝過對于物質和權勢的追逐占有。遠古時期對自然能源及能量的使用有著迥異于現代的模式,但卻可能蘊含著更為先進的原理;遠古創造的輝煌文明,曾讓人類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那個時代可以產生無數金字塔這樣的奇跡,但它的生產力并不聚焦于滿足和刺激人類世俗的物欲,而是引導人們敬畏宇宙的秩序、皈依自然的和諧、尋求靈魂的安寧。人們用更多的時間去進行精神生態創造生活的開拓,從事巫術、宗教、舞蹈、狩獵、歡慶、狂歡等社會生活,那是人類早期的烏托邦生活的理想,也是人類環境的想象中創造出來的和諧與共的自然生態生活。
從遠古時期人類就用環境的想象去創造人類的精神文明,才有了后來不同民族的神話和傳說。不論是古代希伯來人的《圣經》還是上古時期的華夏傳說《山海經》,不論是蘇美爾泥板上最早的文字,還是荷馬史詩恢宏的篇章……恰是在這些璀璨的遺產中,我們發現了當時自然環境變遷的歷史和自然災難的演變遺存,它們不同程度地折射在人類早期的神話傳說中,想象的環境已經在人類早期意識的萌動中,表達了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同時也極為生動、懇切地展現了原始的生態預警。人類只有從想象的環境角度去體驗早期人類社會創造文明、文化時所面臨的困境,才能更深地理解當代人類社會突破科技理性的重圍、找尋涅槃之路的艱難。當我們只剩下生態文學想象的環境時,不正是地球生態環境已經到了最難以控制或保護的時候了嗎?我們必須從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轉移,肩負起應該承擔的自然責任、生態道德倫理,在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中尋找到解決當代社會危機的道路。
英美第一代生態文學家、生態思想家先后用想象的環境穿透了科技理性主義迷霧,對這個人人皆愛的科學技術所成就的人類歷史發展結果進行了深刻思考。同樣,一些西方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早就注意到東方文化中所滲透的“天人合一”思想,如愛默生、梭羅都曾經閱讀過中國和印度的典籍,海德格爾也曾研究過中國的老莊哲學以及日本文化中所蘊含的道法自然的思想;當代新儒學的很多學者則用儒家思想來研究生態與人類的關系……
環境想象既是對生態環境危機意識的警醒,也是對我們置身其中環境生態理想的一種重估和超越。比如那些預警的生態小說、生態詩以及生態文學批評,并不是對傳統歷史意義上神話傳說的恢復,而是站在今天生態危機的現實上,進行歷史的批判和反思,從科技理性之外去尋找一條路徑,突破當代社會對技術的盲目輕信和不加批判地完全接受。有了人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生態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在不同領域里對人類生態環境的想象,并領導大眾為我們的未來付諸行動,我們整個世界才可能發生巨大的變化,才可能向生態和綠色政治邁出真正的一步。
(本文部分內容節選自徐珂《美國自然文學的審美理想》和王諾《歐美生態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