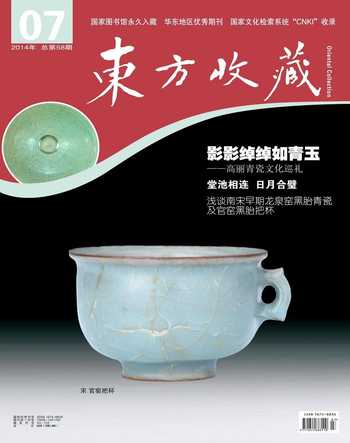品讀高臺羅紋硯
獨羊居主人 廖文偉
硯臺之所以能一躍而為文房四寶之中的魁首,是得益于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一道圣旨。
一讀羅紋硯,追根溯源
環肥燕瘦,綽約綾羅多旖旎
趙匡胤登基伊始,便下旨“勒石三戒”,其中“保全柴氏子孫”和“不殺士大夫”兩條,無異于詔示天下:戰爭硝煙已散盡,文化藝術須大倡!于是乎,文人士大夫為重文輕武時代的來臨而歡呼雀躍,他們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文化藝術得著繁榮昌盛的大好時機。制硯藝人一統天下的制硯行當,文人士子再不肯袖手旁觀作局外人了,不少人親自操刀,投己所好,創新硯式,將審美情趣和心儀情懷,盡情抒發到磨墨寫字的石頭上,制造出許多名垂青史的佳硯。硯林中的佼佼者──文人硯,便是在這種環境中名聲鵲起的。文人制硯,癡情儲硯,一時間蔚為時風。
高臺硯式應運而生,它高可二寸許,團團六面,擁有足夠空間布設書畫式圖飾,為中華民族硯文化錦上添花。
流傳至今最負盛名的高臺硯,要數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蘭亭硯”了,二面刻畫,四面書字。據說那是北宋大書畫家米芾親手制作的,乾隆年《西清硯譜》有其著錄,說“是硯石質既美,周刻布景,行筆具極古穆,所鐫縮本稧序,亦圓勁有骨,疑即芾所自制,且經宣和、紹興兩朝鑒賞,真文房瑰寶也。”康熙皇帝尤愛此硯,將它“貯熱河避暑山莊,幾暇臨池,曾供御用”。安徽博物院亦藏有宋代“蘭亭硯”,同為高臺硯式,為館藏珍玩。臺灣有個“珍翫雅集”沙龍,曾展示一方高臺“蘭亭硯”, 明代之物,周刻布景,藏家極為寶重。
老夫亦有幸藏著一方“周刻布景”高臺硯,明代之物,長24厘米、寬14.8厘米、高7.5厘米,重達6公斤,為庭園嬰戲羅紋硯(以下簡稱羅紋硯)。是硯由釆自歙州婺源龍尾山的歙石琢制,高大厚重,堪稱硯林小巨人。
羅紋硯跋涉數百度春秋來到今天,免不得飽經滄桑、屢遭磨難。更有悠悠歲月日日舔舐,汗手摩挲,塵埃蒙拂,為硯覆裹上一層“黑漆古”狀包漿。
宋人趙希鵠著《洞天清錄》,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當指藍色譜系中淡淡的青灰之色。而宋人高似孫在《硯箋》中卻說,“細羅紋,如羅谷。色青,緊密堅重,瑩無瑕璺,硯之奇也”,直言其奇妙。所云“硯之奇也”,指的則是淡淡青灰色中的奇妙絲羅。宋人陳繼舜有詩唱歙硯,說是“潤含蒼璧隱青羅”,便一并贊頌藍色譜系中之淡淡青灰色及淡淡青灰色中羅紋之美妙。羅紋即硯品也,在“金星、金暈、羅紋、眉紋、玉帶、魚子等”之列。而僅是羅紋,又分粗羅紋、細羅紋、水波羅紋、角浪羅紋、刷絲羅紋、金星羅紋諸多品類,豐富多彩。
羅紋硯硯堂上,那淺淺淡淡隱約可辨之青灰色,正是古籍中論歙專著所云藍色譜系中的稍稍偏藍者,且純凈無點雜。這淺淺淡淡青灰中,布牽著纖纖細細、起伏錯落的紫黑青絲(圖1),宛若縷縷綾羅隨著輕柔春風飄飄蕩蕩,恰似粼粼水波在夏日的陽光下閃閃爍爍,便是《硯箋》中推崇的細羅紋了。米芾云“細羅無星為上”,宋人還以為“細羅紋最溫潤”、“紋青黑不露之暗細羅為上”,羅紋硯上正是無星暗細羅。其旖旎多姿,其縹緲虛無,但凡凝神細看,不由得會憶起南唐馮延巳《謁金門》詞中那名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意趣分外清純。
端歙兩石孰優孰劣?古人云:“端石如艷婦,千嬌百媚;歙石如寒士,聰俊清癯”,謂端石歙石皆品貌兼優也。中國制硯佳石達130余種,唐宋以來朝野推端石甲天下者甚眾,據說唐太宗甚愛王羲之書法,竟特意選擇一方端硯,將褚遂良臨摹的《蘭亭序》精銘其上,賞賜給功臣魏征。朝野舉歙石天下冠者亦甚眾,《靈壁志略》載李唐后主李煜有方歙石三十六峰硯,視之為南唐寶硯,江南國破以后輾轉流離于世,宋時終為書法大家米芾獲得。后米芾相中友人蘇仲恭之弟一處晉唐人古宅基地,蘇堅要三十六峰硯相易,其身價之高,不言自喻。足見端歙二石,環肥燕瘦,實為硯石大家族中的和氏雙璧。
二讀羅紋硯,文人雅趣
士子情懷,滿園春色關不住
老夫之羅紋硯不單“紋青黑不露之無星暗細羅”,其紋飾則為明代中期典型的庭園嬰戲圖紋,美景稚童,耐得窗前品讀。
琢硯藝人匠心縝密,將硯面設計成庭園樓亭的前門。從松陰蕉林入得園來,便見左右建有高大的覆鐘式門亭,黑瓦青磚飛檐,一派大家門第的威嚴肅穆。過園門,踏上茵茵如毯的寬闊草坪,便是硯堂了。硯池則設計成一彎曲水,曲水上飛架雕欄小橋,過橋有松陰小道,直通硯額之臨水樓亭。樓亭雕欄前,有三名童子在玩耍,其一抬腿正要跨上雕欄,想必是要觀看曲水中的游魚,身旁兩童似乎分外焦急,忙著勸他不可冒失。草坪前、曲水旁,一株巨柳拔地而起,祥云駐足,柳絲飄綠。覆鐘式門亭后面,右有遮天蔽日的滴翠蒼松,左有倚伴奇石的嫩葉芭蕉。佇立庭園樓亭前,也許看不到“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這滿園春色(圖2)不也是“關不住”的?
羅紋硯四個側面皆為庭園組成部分。左側(圖3)雕琢有遒勁蒼松,綠陰十丈,五名童子正在樹前燃燒松枝野草取樂。亦或是濕草難燃吧,一童抓起一把青草扇風,另一童子則用松枝翻撥火堆助燃。另有三童,其一或是經不住煙火熏嗆,拂袖背臉;其他二童卻在撿拾柴草。硯的右側場景稍有不同(圖4),一童靜坐土崗若有所思,一童斜倚松干與其打趣。其余三童一邊嘻嘻哈哈,一邊撿拾枯枝敗葉。左右兩側畫面皆出現一門亭,童子們顯然是在草坪樓亭的一左一右玩耍,但見翠竹搖風,芭蕉隔岸,間有地皮小草。硯額(圖5)一側有四童,蕉竹叢前,稍長者正數說微嗔的童子,蒼松下之稍長者,則正指點另一童啰嗦些什么。畫面有小片云,有地皮草,有松蕉竹。硯尾(圖6)一側亦有三童撿拾枯枝敗葉,稍長者正在數說稍幼者,后者顯然不太服氣,歪頭側腦,敢怒而不敢言。畫面有闊葉矮樹,有扶搖健竹。園中二十童子,天真無邪,盡情享受暮春的和煦。
硯背(圖7)則深陷2厘米有余,藝人將其設計為庭園中的一口方塘,亦可見飛檐門亭,表示仍在庭園之中。岸邊一株垂絲綠柳,幾葉帶露芭蕉,滿池盈盈春水。粼粼波光之中,蓮葉田田,一雙游鴨相伴相依。
團團一硯,儼然便是富貴人家幽雅庭園的一軸春光水墨圖畫。人在春光里,詩在圖畫中,“蒼松翠柳掩樓閣,暖池雙鴨戲蓮荷,祥云靄靄不肯去,停看小童玩煙火”,比尋常所見嬰戲圖之放風箏、踢皮球、燃鞭炮、敲鑼打鼓等等的童稚之戲,給人平添許多想象空間。
三讀羅紋硯,時風為環
環環成鏈,幾百春秋誠可信
一定的歷史時期,不同載體的工藝手段和藝術特點是相通的,其時代風格必然會反映到那個時期相關門類的藝術品個體上來。比如明代青花瓷器紋飾的時代特點,那個時期的竹刻技巧,羅紋硯上都有所反映。
先說庭園嬰戲圖。迄今所知,童子耍戲的紋飾圖案最早出現在唐代的長沙窯器物上,宋元時期延續,明代大盛,清代有所發展。從一兩個孩童到十幾個到二三十個,直至“百子圖”。但即使是明代,各個歷史時期嬰戲圖的時代風格亦大相徑庭。羅紋硯嬰戲圖為二十子,紋飾風格從成化前的粗獷豪放過渡到了細膩柔美,線描工整,服飾清晰。且童子身形體態比例適當,臉龐圓正,五官趨簡,發髻靠后,著右衽長袍,單衣。藝人著意于簡筆寫意,必要處兼工,因而筆意飄逸,生動傳神。這正是明成化年到萬歷年之間,青花瓷上嬰戲圖童子造型的基本時代特征。嘉靖以后,嬰戲圖童子便開始變形,后腦突出,前額變大,造型夸張,從工寫兼備漸變為完全的寫意。
后說蓮池雙鴨圖。蓮池雙鴨紋飾元代開始盛行,明代青花瓷常見釆用。羅紋硯硯背的蓮池雙鴨,甚至很像明洪武年間青花瓷上的水藻游禽,說鴨亦可,稱鵝亦未嘗不可。蓮池之波紋成規整的鱗狀波濤,這種鱗波紋出現在明代“空白期”,直到萬歷年間仍盛行。
再說小景紋飾。羅紋硯上之小景紋飾,尤與明代中期青花瓷器上的紋飾大同小異。硯面的柳絲,明顯是斷續雨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隨風飄忽。柳絲左上角的游云為小片云(圖8),同明代前期的大片云和后期的括號云有明顯的區別。蒼松拔地,遒勁古盎,但松針作圓渾小球狀,正統年后才向橢圓漸次演化。芭蕉葉面闊大,中梗留白,成矮樹叢狀。小草成片草狀,稀稀落落,連著小塊地皮,陶瓷學家們稱其為地皮小草,形象至極。
再說雕琢技法。從工藝技法角度品讀不難發現,羅紋硯的雕琢工藝,既承襲漢代磚雕壓地隱起和減地平雕的淺浮雕一類工藝技巧,又借鑒了明代中期竹刻工藝手法。
明代中期,竹刻雖說出現金陵、嘉定兩個主要藝術流派,前者大都學養極高,工于金石書畫,其代表人物朱鶴、朱纓、朱稚征祖孫三代,以淺浮雕、高浮雕和圓雕名垂竹雕史;后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有濮仲謙,亦面亦線的陰紋淺刻,是其拿手技法之一。這兩派竹刻之技法,與漢磚雕工藝手法亦是一脈相承的。
完全有理由說,羅紋硯綜合借鑒漢磚雕工藝的壓地隱起、減地平雕以及竹刻工藝淺刻等諸多技法,壓地僅僅一二毫米,圖案紋樣僅僅凸起些許,乃為陽紋類中極為淺薄的浮雕。薄薄隱起的人物庭園輪廓上,又錯落有致地精雕二三層次,然后陰刻人物庭園細部。這種淺浮雕工藝用刀如運筆,線條柔逶秀逸,造型明快清新。于是人物顧盼有神,草木搖曳生姿,樓亭進退有序,既拉開了景深,又突出了質感,表現出很好的繪畫效果。
自然,判定羅紋硯之為明代物,證據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唯溫瑩幽潤的“黑漆古”可以擔綱。“黑漆古”是幾百年歲月之手的杰作,不經滄桑歲月的洗禮,青灰色的歙石上,如何能出現這種濃稠如漆而熒潤生輝的包漿?倘若缺失“黑漆古”包漿作為真實可信的第一環,其他各環便都難逃造贗之嫌,用其斷代,是不足以為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