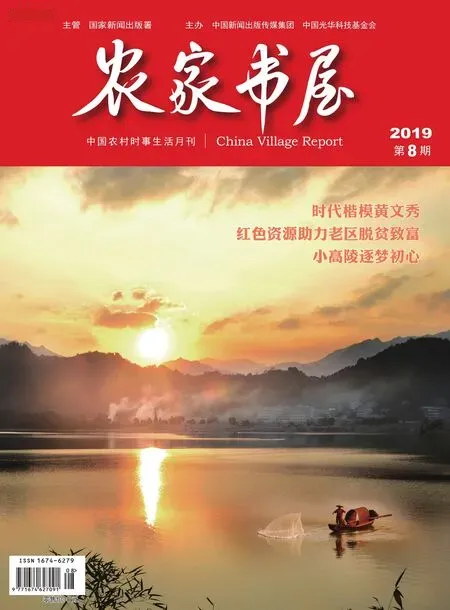李漁:在鄉居與城居之間徬徨
沉鐘
人生是一場奔波,馬不停蹄,風塵仆仆,于是,對家居的憶念和眷戀也尤為真切。萬千奔波的勞苦,其實只在于一個安寧而穩固的家——不僅僅是作為最終歸宿的寄托,也往往著眼于短暫駐足的風景。
李漁的一生,幾乎一直都在為安頓自己的“家”而籌畫、而忙碌、而困惑。從出生地如皋到故鄉蘭溪夏李村,再到金華、杭州、南京乃至北京,最終回到杭州,其間,經歷了“小城——鄉村——中等城市——鄉村——大城市”之間的多次輾轉往復。古往今來,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比李漁先生在家居建設上投入更多精力的文人墨客了。
唯其如此,也當仁不讓地成就了他作為有清一代無人可與比肩的造園大家的地位。
李漁對“家”的選擇,起初完全處于被動的狀態。在他出生時,“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而立之年,科場失利,遭遇時變,境況急轉直下。據他后來回憶:“甲申乙酉之變,予雖避兵山中,然亦有時入郭,甚至幸者,才徏家而家焚,甫出城而城陷。其出生于死,皆在斯須倏忽之間”(《閑情偶寄·飲饌部》)。改朝換代之際,兵火連天,李漁在金華城里的家被毀,死里逃生,無處存身,只得回到蘭溪夏李村的故居。此時家道破落,財產銷盡,要修建幾間可容一家人的茅屋都無能為力。他在《擬構伊山別業未遂》詩中寫道:
擬向先人墟暮邊,構間茅屋住蒼煙。
門開綠水橋通野,灶近清流竹引泉。
糊口尚愁無宿粒,買山那得有余錢。
此身不作王摩詰,身后還須葬輞川。
幸而一批親朋好友伸出援手,幫他了卻一樁心愿。此后,他便絕意仕進,今生甘為“識字農”,一度把心思都花在了這“伊川別業”的布置和修飾上,種花蒔草,引水灌園,經過一番精心打理,居然將幾間草房及周邊環境弄出了一派詩情畫意。這一段鄉居生活,成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回憶。他在《閑情偶寄.頤養部》中記述:
予絕意浮名,不干寸祿,山居避亂,反以無事為榮。夏不謁客,亦無客至(兵燹過后,自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匪止頭巾不設,并衫履而廢之(呵呵,完全不必顧忌斯文掃地!)。或裸處亂荷之中,妻孥覓之不得(此公實乃現代版“天浴”的第一著作權人。);或偃臥長松之下,猿鶴過而不知(是人類退化為動物,抑是動物進化為人?)。洗硯石于飛泉,試茗奴以積雪。欲食瓜而瓜生戶外,思啖果而果落樹頭(簡直有點孫猴子的味道!)。可謂極人世之奇聞,擅有生之至樂者矣。后此則徏居城市,酬應日紛,雖無利欲薰人,亦覺浮名致累。計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僅有三年。今欲續之,求為閏余而不可得矣(笠翁一生閱歷,堪稱“曾經滄海難為水”,自認為得享仙福者“僅三年”。我等庸常之輩,細忖起來,一生中又能真正享有幾年清福?)。
但李漁終究還是放棄了這種無心無事、閑云野鶴式的生活,將他精心營造的“伊川別業”連同所置的周邊百畝山林全部轉賣,攜了這點資本,遂由寧靜的鄉居轉向喧嘩的城居,謀求另一種人的活法。
李漁注定不是一個湮沒無聞的鄉曲之士。他處在一個劫后余生的時代,黎民百姓需要撫平戰爭留下的心理創傷,個人亦急需在廢墟上重建家業并重振家聲,而清初相對松弛的文網也為他提供了發揮才情的獨特空間,那個時代更需要借他的杰出天賦去開辟一塊無人問津的新文化領域。他這一去,著述賣文、出版圖書,度曲演戲、組建戲班,策劃生活、設計造園,又是小說家、劇作家,又是戲班班主兼導演,更是身懷絕技的造園藝術大師,一時鋒頭凌厲,八面風光,名滿宇內,賓朋天下。與此同時,他把家安在了杭州,安在了南京,甚至安到了北京。
李漁的城居,最有名的當數南京的“芥子園”,既是住宅,又是書局,還是戲院。“芥子”,極細微之物也,佛家曰“芥子納須彌”,意謂一粒小小的芥子能夠容納廣大、莊嚴的須彌山。李漁為南京的芥子園手書對聯:“因有卓錐地,遂營兜率天。”這芥子園“過目之物盡是畫圖”,傾注的豈止是泛泛的匠心,更是主人巧奪天工的創意和靈感。也許是揮灑之余意猶未盡,李漁又把芥子園的“分店”開到了京城。可惜,如今這南北兩京的芥子園都已付諸塵埃,無有覓處。
直到67歲那年(康熙十六年),李漁才從南京搬回杭州,最終定居并老死于云居山東麓的“層園”。
營造“層園”這個最后的家園,可謂李漁平生最后一搏,搞得心力交瘁,貧病交加,一次還失足滾下樓梯摔傷了筋骨,差點送掉老命。因資金鏈斷裂,工程無以為續,不得不給京城友人寫公開信求援,信中說:
我本是浙江人,雖然家于金陵,并非土著。狐死必首丘,此念蓄之已久,況且故鄉還有祖宗的墳墓在。自從乙卯年兩個兒子回浙江就讀,便決定搬回杭城。幸蒙主政官員幫助,使我得遂買山建宅之愿。自夏至冬,不到一年,卜居擇基之后,便投入土建;土木工程尚未完成,又遇婚娶之事;婚娶方畢,即著手搬家事宜。從金陵到杭州,有上千里之遙,四十口之家,非一舟一車可載;何況在金陵住了二十年,負債滿身,在則可緩,去則不得不償。所以臨行所費金錢,十百倍于搬家之數。除去賣掉金陵別業(即芥子園),還有生平著述之版權、衣物乃至妻女的首飾等等,凡是值點錢的,無不變賣,還清債務,才得挈家啟程。可憐彼一時也,只顧醫瘡,使盡難剜之肉,以致此一時也聽其露肘,并無可捉之襟……
可見李漁最后一次對家的選擇仍然相當被動,力不從心,勉為其難。也是幸得朋友資助,才使他得以圓滿最后的歸宿。
如果說李漁一生對家居有過主動的選擇,唯有“芥子園”差可擬之。但自從他搬離南京后,芥子園繼續作為書局的存在,已不得不改換門庭,花落別家。
李漁在小說《聞過樓》中有一段夫子自道,古語云:“小亂避城,大亂避鄉。”予謂無論治亂,總是居鄉的好;無論大亂小亂,總是避鄉的好。……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過十年宰相,所以極諳居鄉之樂。如今被戎馬盜賊趕入市中,為城狐社鼠所制,所以又極諳市廛之苦。
晚年的李漁思鄉之心尤切,有一次乘船沿富春江回蘭溪,經過嚴子陵釣臺時寫下一首詞,詞中道:“同執綸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輕!不自量,將身高比,才識敬先生。相去遠:君辭厚祿,我釣虛名。”
總結回顧自己的一生,在鄉居與城居之間,李漁高度肯定了鄉居的價值,而對曾經給他帶來輝煌的城居卻刻意加以貶薄。此種心態,看似與當今一些出自草根而借城市發跡卻口口聲聲念叨著“鄉愁”的成功人士如出一轍。
不過,李漁此處說的的確是真話。為了奢華的城市居住和生活,他的付出太多太多,不止是金錢和物質,更是精神上的透支。城居令他疲累不堪。
賣文為生,售藝養家,靠自己的才能吃飯,沒什么可說的,“我以這才換那財,兩廂情愿無不該”。尤為可貴的是,李漁作為中國第一位文化企業家和中國第一位專業戲劇導演的天賦,讓他可以用自己賺的錢使一家四十余口活得相當滋潤。只可惜李氏戲班的兩個臺柱子——喬王二姬過早離世,從事業巔峰驟然跌入谷底,迫使他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打抽豐”這一當時文人慣常的謀生手段,由此而來,自我感覺中的人格自尊也不得不自貶三分。雖說李漁平常與那些貴人、富人打交道,交朋友,為他們賦詩撰聯,談文說藝,唱曲賣笑,籌畫園林設計和營造,不但能“混跡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公卿之府”,還不時獲得豐厚的饋贈,但這種角色充其量不過是“高級文丐”而已,“人以俳優目之”,其內心的角色沖突無可避免。時人譏其“奔走勢利之門”,其實,所謂“市廛之苦”,笠翁可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那么懷念當初的“居鄉之樂”,良有以也。
平心而論,不論是當今社會還是李漁那個時代,鄉居與城居于人生都是各有利弊。鄉居生活成本低,輕松怡養,悠游自在,益壽延年;城居生存壓力大,環境嘈雜,尤多外在和內心的霧霾。——不過,憚于生計,競爭驅使,城居轉而有助于成就一番事業,也合乎邏輯。
設想李漁當年不走出蘭溪夏李村,何以成就他歷史上的李漁?
據說李漁回到蘭溪故里,已是物是人非,不禁感慨萬千,賦詩道(《二十年不返故鄉重歸志感》):“不到故鄉久,歸來喬木刪。故人多白冢,后輩也蒼顏。俗以貧歸樸,農由荒得閑。喜聽惟澗水,仍是舊潺湲。”
從古到今,失去了的鄉居不可復得,消散了的鄉愁不可追尋。蓋因一切隨時間空間條件轉移,鄉愁所附著的鄉居、鄉居所附著的土地,皆如暗逝的流水吞聲而去,讓人再也無法踏入同一條河。
這也是當今許多年輕人寧愿漂在城市而不肯回到小地方的原因。
至于某些成功人士一邊享受著城市的盛宴,一邊又在渴望鄉野的風味,所表現的除了物欲之貪婪,就只剩了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