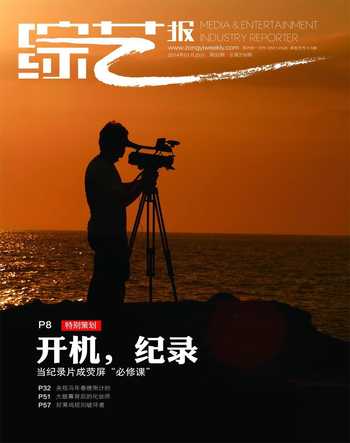張同道:用紀錄“抗擊膚淺”
南瑞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自2009年以來已連續發布4年。4年來,主編張同道見證了中國紀錄片產業的艱難起航及生態改善。記錄2013年紀錄片發展的《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4)》,張同道正帶領團隊創作中。2014年,除了這份研究報告,他的《小人國2》也將問世。
張同道有兩個身份,他是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另一個身份是紀錄片創作人,他長期奮戰在紀錄片拍攝一線,一部《小人國》讓紀錄片圈外的更多人認識了他。
張同道是一個理論工作者,他的研究為紀錄片產業提供盡可能多的理論支援和可參考意見。一手數據資料搜集的工作龐雜細致,花去了張同道和他的團隊數年時間。但成果是值得欣慰的,每年披露的《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為正在崛起的中國紀錄片產業提供了具有價值的數據和理論支持。
創作
張同道談起對紀錄片的研究,比談創作更有熱情,他遺憾2013年缺少《舌尖上的中國》這樣有全國性影響的作品,欣慰行業的整體制作水準大有提高。“整體環境在改善,紀錄片銷售價格在提高,一些新的公司冒出來,2014年將會有大批片子出來。”
他也有擔憂,資金涌進來后,紀錄片圈子已經出現了需要去矯正的問題。比如,有的紀錄片投資很大,把很多錢放在了情景再現和技術上,但真正打動人的情感和命運部分展現不充分,人文含量不夠,本末倒置。“沒有人文含量就沒有拍片的必要,其次才是提高技術水平,不能拍出來黑乎乎、晃悠悠、慢吞吞。”
張同道不提倡媒體自己制作紀錄片,“應該市場化”。中小臺沒有制作精品的能力,如果拿自制的錢去市場上購買,不但可以買到精品,還能讓精品紀錄片賣出應得的價格。
他提醒從業者“永遠不要想紀錄片有一天會像《非誠勿擾》一樣有那么多觀眾,沒有可能性。”
張同道有自己的工作室。這個工作室除了是教學基地外,更是紀錄片試驗田。研究了那么多紀錄片后,他有很多個人想法,想通過自己的方式實現。
三類題材對張同道有特別吸引力,首先是與專業電影史相關的題材,他制作了《電影眼看中國》,選取了1920年至1949年之間的中國經典紀錄片,通過紀錄電影見證歷史的變遷,2013年4月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他對文化碰撞類題材興趣濃厚,后面即將開始的兩個選題,都與此有關;教育一直是張同道紀錄片重點關注的對象,2006年起他就一直拍攝孩子,《小人國》《成長的秘密》以及即將問世的《小人國》第二部,都聚焦于兒童的心理世界。
多年研究紀錄片,張同道攢了一大堆創意,“都拍出來需要十年時間”。決定先拍哪個的原因常常是這個項目當時獲得了比較好的投資。不過,先后順序在他看來并不十分重要,因為紀錄片不是應景的東西,一部好的紀錄片平均壽命要有八年以上。
近年來,張同道拍的片子集中在大片和精品上,以他的標準,大片投資1分鐘2萬-3萬元,精品投資1分鐘1萬-1.5萬元。資金來源渠道多樣,央視紀錄頻道和各個電視臺,以節目運營公司為主的媒體企業,各級政府和銀行、航空公司等大企業,都與他有合作。
張同道的創作團隊長期合作,“紀錄片臨時組團比較困難,成功的團隊都是長期合作。”團隊粘合力關鍵在于文化價值追求,張同道說,沒有這個價值觀,光靠錢,團隊聚不攏。
制作一部紀錄片的流程大致是這樣:先花3—8個月實地調研,找準采訪對象,確定采訪環境,只有大量的一線調研,后期拍攝才會從容;然后進入拍攝,時間幾個月到幾年不等;拍攝完畢后進入后期制作,這一階段主要依靠技術團隊,剪輯、特效、音樂大展身手。作為導演,張同道貫穿整個過程,其他的工作人員則是分段參與。一部片參與人數30—40人是正常情況,最多的時候有可能達到100—200人。
《小人國》拍了8年,積累了600多小時的素材,最后剪成80分鐘。《小人國2》2010年開拍,拍了300多小時,最后將剪成一個多小時的電影。
張同道選擇鏡頭最大的原則是鏡頭能否講好故事,他偏愛能表達人物和環境關系的、有意味的鏡頭。
“人性中迷人的風景”
自從博士畢業偶遇紀錄片之后,張同道人生的關鍵詞一直就是紀錄片。
“從經濟的角度說,不會選擇以紀錄片為業,選擇是因為覺得有意義,有價值。”人的生命由有限的時間組成,紀錄片為他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體驗不同人生的機會,“這是快樂的事情,值得癡迷。”
這份快樂成為走下去的動力。隨著認識的不斷變化,作品的主題隨之變化,張同道試圖在每一部作品中注入新東西。但對人性的揭示和美學的突破在他的作品中一以貫之,在他看來,紀錄片可以挖掘出“人性中迷人的風景”,而這風景在其他藝術形式中看不到。
張同道的本職是教師,生活較其他紀錄片創作者有保障,拍攝紀錄片為的是實現夢想。“僅僅用紀錄片謀生,目前還是有些問題。”改善紀錄片人的處境是紀錄片發展的前提,張同道認為這個要由市場自己完成,如此紀錄片才能變成一個有自我發動能力的行業。
在教師的工作上,張同道還肩負著培養紀錄片人才的重任,培養紀錄片工作者更花費時間和精力,對人才的要求也高,要有文化厚度和研究能力,最關鍵要沉得住氣,“速成很難做出好東西。”
張同道希望紀錄片給世界留下一些思考,“在一個浮躁的時代,如果大家只是傳微信、微博,就慢慢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世界正在變得膚淺,張同道說,而“紀錄片可以抗擊時間、抗擊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