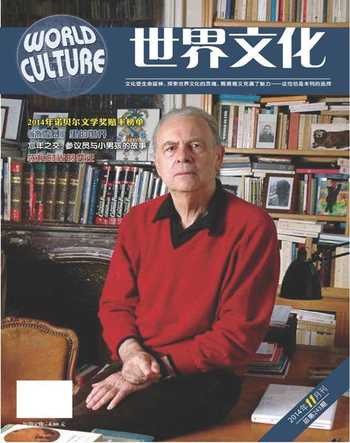格雷《墓園挽歌》中的風景及其作用
趙國柱


在眾多的藝術形式中,詩歌與繪畫經常被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素有姊妹藝術之稱。早在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詩人、文論家賀拉斯就在《詩藝》中提出了“詩如畫”的說法,從而奠定了西方傳統美學的一塊理論基石。進入18世紀后,受歐洲大陸興起的古典主義思潮影響,以亞歷山大·蒲柏和托馬斯·格雷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詩人在英格蘭文壇崛起。他們崇尚理性、自然、古典和道德等原則,創作了許多以風景描寫及其引發的思索為主要內容的風景詩,其中最為知名、堪稱英詩經典的當屬格雷的《墓園挽歌》。
《墓園挽歌》描述了詩人于黃昏時分憑吊一處鄉間墓園的所見所思,字里行間流露出對鄉村農夫生命消逝的感嘆。全詩長128行,分為32節,每節含4行五步抑揚格詩句。細讀整首詩,我們會發現關于風景描寫與哲理思考的詩節基本上呈交替出現的規律。格雷先后三次將自己置入語言構筑的風景中,對景色進行了仔細的觀察與思索。具體來說,第一次是開篇對農夫日常活動的描寫和之后長篇的道德與社會性評論;第二次包括對農夫墓前簡陋碑文的簡短描寫和對死亡之痛及必要安慰的短暫思索;第三次則是詩歌結尾部分對鄉間詩人生與死的描寫和以墓志銘形式出現的對其生平的評價。
詩的前四個詩節描繪了黃昏時分的戶外景色。在光線漸暗的畫面中,有迤邐慢走的牛群和一個回家的耕夫,還有裹著長春藤的塔、榆樹、紫杉和起伏的草皮。格雷平生喜愛自然,曾多次前往白金漢郡的偏僻鄉村及泰晤士河谷游覽,沉醉于榆樹、山毛櫸、教區教堂、蜿蜒小路等構成的田園風光。現在,這些細節都被納入到一幅使人回味的詩意圖畫中。偶爾,詩中還會出現少數被18世紀讀者視為圖畫標志的詞語。比如,詩人會通過指示代詞向讀者暗示風景的存在:“只有,那邊裹著長春藤的塔上,/郁郁不樂的鴟梟向月亮哀告:/有誰在她隱秘的閨房邊閑逛,/把她古老而僻靜的領地煩擾。/那些蒼老的榆樹和紫杉蔭里,/滿是草的地上隆著壘壘荒冢;/埋在各自狹小墓穴里長眠的,/是村中缺文少禮的先祖先宗。”之后的三個詩節圍繞著已故農夫的世間生活展開。這些詩行中雖然包括一些視覺細節,但它們并不直接產生畫面感。依據德國文藝評論家萊辛的觀點,這些視覺細節真正顯示了詩人獨一無二的力量。萊辛認為,只有詩人可以“通過否定方式作畫,將肯定與否定兩種方式完美地結合起來”。在這三個詩節中,格雷把萊辛提及的詩人才能發揮到了極致。現在,農夫們已經死去,詩人和讀者看到的是黃昏時的圖景。但通過一系列否定表達,如“再難把沉睡地下的他們喚醒。/他們再享受不到爐火的熊熊/或辛勤主婦在衣食上的關心;/沒兒女跑來牙牙地歡迎父親/或爬上膝頭去分享巴望的吻”等,格雷重新勾勒了農民們白天的田間生活和夜晚的家庭歡樂。
按照萊辛的標準,這三個詩節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圖畫式的。比如,描繪農夫在清晨被喚醒的細節不是以空間,而是以時間構思的,而且呈不斷強化的趨勢。從清晨“微風的輕呼”“燕子的嘁喳之聲”到“公雞的尖聲報曉”,農夫覺醒的感覺愈來愈強。同樣,在開篇的四個詩節中,我們會讀到“朦朧的景物現在從眼前消隱”,顯示出光線并不穩定,而是不斷在變化。緊接著,黃昏變成了完全的黑暗。此外,有些意象也不全是視覺性的。如晚鐘敲起、耕夫邁著沉重的腳步、鈴聲在催眠、人格化的早晨在吐著清香,這些表現的都是明顯的動作感。可以說,格雷具有只有詩人才能使畫面變得生動的良好的藝術感覺。
開篇的四個詩節雖然優美,但若整個詩歌都是純粹的風景描寫,是不合18世紀的讀者的口味的。英國古典學者托馬斯·特文寧認為,“詩歌不能建立在蒲柏所謂的純粹風景之上,里面沒有人物;風景作為自然的形象,孤獨且不被打擾”。繪畫亦是如此。法國藝術評論家阿布·杜·波斯指出,“最好的畫家深信這一道理。他們很少向我們展示完全荒涼、沒有人物的風景。畫家在風景中置入了人物,通過采取某種動作的人物來感動我們,引起我們的關注。”在這種文藝氛圍的熏陶下,格雷很自然地從純粹的風景描寫轉向了人物和人性關懷。
在從第8節開始的長篇思索中,格雷使用了許多古典主義詩歌中常見的擬人化手法。其中,有的擬人化用法表現出細微的動感,如雄心會加以嘲諷,財勢會露出鄙夷不屑的笑容。盡管如此,造型藝術的暗示仍無處不在,且深具意義。格雷會讓讀者意識到權勢人物埋葬在有著雕花拱頂的教堂之內,他們的墓碑上矗立著雕像和戰利品。“刻有傳略的甕和逼真的胸像”傳達出藝術格言的傳統意義,即雕刻過的石頭,憑借藝術天才的奇跡,能創造出一種充滿活力的真實感覺。這種藝術創造幻象的力量原本是令人頌贊的,但在這里卻只會引起煩亂的思緒,產生諷刺的效果。畢竟,藝術品只是形式上逼真,而不是生命本身,不能在現實中“召喚消逝的鼻息重歸軀殼”。
之后,格雷的思緒重回墓園,開始描述農夫們墓前的石碑。他發現這些墓碑非常簡陋,上面“綴有拙劣詩句和難看的雕刻——/以此吁求過路人賜一聲長嘆”。農夫們沒有顯赫的生平值得抒寫,于是只能由鄉間詩人(即石匠)為其在墓碑上留下姓名、生卒年月及幾句經文作為曾經生活于此的確證。隨后的簡短沉思中,格雷引入了一個擬人格——“無言的遺忘”。它沒有具體的視覺形象,只是作為一種意識上的存在嵌入了圖畫的布局中,顯示了詩人對淳樸的鄉間農夫們生老病死的悲憫之情:“誰肯拋卻這悲喜的人間,/離開這歡快溫暖的白日境域,/也不戀戀難舍地回頭望一眼,/從此被無言的遺忘一口吞去?”
在最后一次風景描寫中,格雷可以說是嚴格遵從了杜·波斯對畫家的忠告。他不再只是使用擬人格的手法,而是引入了真正的人物為墓園景色增添意義。這一部分主要圍繞鄉間詩人的生與死展開描述,其中最重要的視覺細節包括“那邊老山楂樹下的碑刻”和三個活生生的人物。他們分別是詩人、白發莊稼漢和識字的問路人。詩人即主人公“我”,來自喧囂的城市,接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他為已經去世的鄉間詩人撰寫了墓志銘,對其進行了高度評價。白發莊稼漢是農夫的代表,他并不完全理解和欣賞鄉間詩人在世時的生活狀態。問路人是詩人提到的“同道之人”。他將在未來某個時候游覽鄉間,在白發莊稼漢的指引下來到鄉間詩人的墓前,從墓志銘中了解到主人公“我”對鄉間詩人的頌贊。
格雷的朋友、插圖畫家理查德·本特利曾為《墓園挽歌》結尾處的景色作過插圖。不過,本特利并未完全按照詩歌中人物的真實狀態進行描繪。格雷原本是讓莊稼漢告訴問路人鄉間詩人的墓碑所在。而在本特利的插畫中,莊稼漢是以牧羊人的形象出現的。他單腿跪在墓碑前面,用手指著碑上的銘文。問路人被處理成倚著拐杖行路的牧羊人形象,他站在莊稼漢的旁邊,在墓碑上投下了細長的身影。在美國學者讓·H·哈格斯達勒姆看來,本特利的處理手法似乎是受到了法國古典畫家普桑的名作《阿卡迪亞的牧羊人》的影響。作為17和18世紀歐洲哀婉之情的代表作,普桑名畫所表達的阿卡迪亞主題已經進入了英格蘭人的意識之中。格雷本人十分喜愛美術,他后來還被同時期的許多知識分子公認為歐洲知識最淵博的人。基于這一事實,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只是本特利,即使是格雷在創作《墓園挽歌》的七八年間也會時不時地想起《阿卡迪亞的牧羊人》。
普桑一生創作過兩幅以阿卡迪亞為主題的畫,一幅現存于英國德文郡的查茨沃斯莊園,另一幅收藏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中。查茨沃斯莊園的畫屬于典型的巴洛克風格。兩個牧羊人和一個牧羊女出現在畫面的左側,他們身上的衣裳十分凌亂,顯然是剛剛經歷了風流快活。畫面的中心是一個巨大的石棺,上面放著一個骷髏。從他們臉上的駭然表情可以看出,他們的艷情受到了不期而遇的恐怖景象的干擾。年長的牧羊人用手指著石棺上“我也在阿卡迪亞”的銘文。在畫面的右下角,河神阿爾斐俄斯微低著頭,正在憂傷地沉思著。
完成此畫的五六年后,普桑又回歸了阿卡迪亞主題,創作了他更為知名的盧浮宮藏畫。在這幅古典主義風格的畫作中,牧羊人的數量比原來增加了一個。畫面的中央不再是華麗的石棺,而是一座簡樸的長方形墳墓。原來引起緊張和不安的骷髏與河神消失了,安享田園生活的牧羊人不再縱情狂歡。他們衣冠得體,不是被意外的駭人景象阻擋了前行的腳步,而是沉浸在平靜的談論和思索中,臉上流露出的都是對生命易逝的感嘆。年齡最大的牧羊人單腿跪在地上,用手指著碑上的死亡警告——“我也在阿卡迪亞”。 最年輕,看上去也是心思最細膩的牧羊人用食指指向碑文,目光則專注在旁邊可愛的牧羊女身上,似乎在與后者談論著死亡。畫面左邊的牧羊人似乎因同情死者而陷入了憂郁的沉思中,他放松下垂的身體姿態表達了他對命運的順服。
準確地說,這就是格雷《墓園挽歌》所要傳達的充滿哲思的憂郁基調。格雷年輕時就把普桑視作憐憫大師,他認為普桑具有描繪人類樸素情感、引發人們同情的才能。與格雷同時代的英國評論家塞繆爾·約翰遜博士雖然不大欣賞《墓園挽歌》中的詩意詞藻,但仍然對該詩評價很高,贊其“形式完美、內容清新、格調和諧、藝術優雅,充滿著人們可以想見的意象,滿懷著每個人都能產生共鳴的感傷”。約翰遜和18世紀的人都覺得這是古羅馬抒情詩人維吉爾的典型特點,因此把維吉爾、普桑和格雷的名字聯系起來,就不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格雷的《墓園挽歌》與普桑的繪畫不僅有著共同的道德主題,而且都涉及一塊刻有銘文且令人駐足沉思的墓碑。但兩者之間同樣存在著重要的差異。在普桑作畫之前,銘文“我也在阿卡迪亞”中的“我”已經不再指代死亡,而是變成了已死之人。普桑使用這句銘文似乎是為了告訴我們,牧羊人在思索他們自己的死亡,因為他們的一個同類,一個曾經享受過伊甸園般歡樂時光的人,現在卻死了。格雷的主題則要更微妙一些。詩歌的主人公與已死的鄉間詩人不同,他來自城市,屬于更高的智力和社會階層。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兩個詩人并不擁有相似的生活經歷。不過,鄉間詩人碑刻上的銘文似乎又在提醒我們,他也曾是個詩人,也曾“被憂郁女神收下,標識出來”。于是,通過這種深層的精神方面的相似性,兩個詩人就擁有了超越他們生活環境的能力。作為讀者,我們會感受到詩人之間的這種特殊關系,感受到死亡面前人與人的終極平等——驕傲者最終的謙卑和卑賤者最終的驕傲。
除了主題的相似性外,普桑的繪畫還為格雷《墓園挽歌》的圖畫式風格提供了重要的批評注解。詩歌中關于風景描寫及所引發思索的片段都會令人產生圖畫式的聯想,而這種描寫和思索的關系正是源于雕像傳統的一個特點。《墓園挽歌》并不完全是一系列視覺細節構成的風景圖,由風景引發的道德與哲學思索似乎才是格雷的重點所在,最終的目的是將我們引向一尊雕刻上的銘文。這首詩并非傳統的敘事詩,詩歌的推進也不依賴于邏輯嚴密的論證,甚至也不是自由聯想式的情感宣泄。憑借幾個圖畫式的靜止瞬間、均勻穿插其間的人生哲思以及詩歌非個性化的客觀風格,《墓園挽歌》儼然就是一幅經典的古典主義風景畫。而格雷“具有穿透力、優雅精確的措辭”,就像詩歌的主題及風景傳達出的普遍性一樣,似乎也正是普桑名畫《阿卡迪亞的牧羊人》最為貼切的語言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