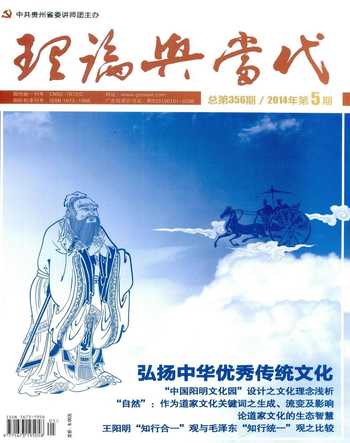有一種貧富差距更需要警惕
2014-04-29 09:39:36
理論與當代 2014年5期
吳忠明在3月19目的《光明日報》上撰文指出:就過大的貧富差距而言,實際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貧富差距是相對擁有底線保障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正處在“休克療法”的社會急劇轉型期,其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但是,蘇聯時期所建立的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民眾,特別是能夠為貧困者的基本生存提供有效的“兜底”,因此,社會并沒有出現劇烈動蕩。第二種類型的貧富差距則是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及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比如,拉美和非洲一些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或基本缺失,社會成員的流動機會也比較少。因而這些國家的社會安全局面有時難以得到保障。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應當承認,近10年來,中國在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歷史欠賬過大、公共服務意識尚未普遍形成等種種原因,從公共投入結構角度來看,同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用于基本民生改善的比重過小。此外,中國如今的社會流動遭遇到一定的瓶頸,有待于突破。這突出地表現在社會成員特別是基礎階層成員向上流動的障礙在增多、阻力在增大,社會成員上行的通道在變窄。同擁有保障底線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相比,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危害要更大,可能加重整個社會浮躁不定的氛圍,減弱社會活力及創造力,不利于社會的安全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