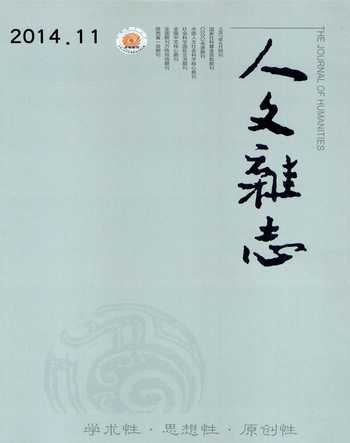論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創新壟斷
張康之 張 桐
內容提要 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進程中形成了世界中心-邊緣結構,而在這種結構中,存在著中心國對技術創新成就的壟斷問題。由于中心國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獨特地位,決定了它總能匯聚起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從而總是處在技術創新的前列。出于在國際競爭中維護國家利益的需要,中心國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而實現創新壟斷。邊緣國加入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后,中心國在創新壟斷的前提下也以技術援助的名義對邊緣國轉讓一些落后技術,并在這種技術轉讓中實現理論特別是價值觀的輸送。然而,邊緣國在此過程中往往是無奈地接受,并無條件地向中心國奉獻自己的智識與技術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邊緣國往往是因為缺乏自信而向中心國奉獻其知識與技術,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心國的承認和肯定。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題被突出,而中心國的創新壟斷已經對人類社會的共生共在造成了威脅。
關鍵詞 中心-邊緣結構 創新壟斷 知識產權 技術轉讓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4)11-0117-09
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國對邊緣國的剝削和邊緣國對中心國的依附可以說存在于它們之間的每一重關系中:在經濟方面,中心國剝削邊緣國的經濟剩余,積極鼓吹所謂正統的經濟理論,邊緣國則將其視作為救國之神明;在政治方面,邊緣國受到中心國所宣揚民主理論的迷惑,深陷于對中心國的政治依附之中;在智識方面,邊緣國知識分子囿于中心國所編織的神話,深陷于智力依附之中。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心國對創新的壟斷(包括硬技術壟斷和軟知識壟斷)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對生產技術的創新壟斷大幅提高了中心國的生產力,也增加了其剝削邊緣國經濟剩余的能力;對軍事技術的創新壟斷使得中心國獨占最先進的軍事技術,用軍事威懾換取一些邊緣國的言聽計從,或用軍事打擊摧毀那些一意孤行的邊緣國;對傳播技術的創新壟斷為對邊緣國的理論宣傳與政治干預提供了有力保障,雖然美國的“竊聽門”事件也讓其他中心國成員暴跳如雷,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似乎將中心國監聽邊緣國的同樣做法拋諸腦后;關乎健康與生命的藥品也被中心國以專利保護的名義而拒絕知識和技術共享。不僅是硬技術,那些軟知識同樣受到了中心國的保護。當然,我們經常看到中心國似乎大度的技術傳播或技術援助,而在其背后,則是披著“技術”外衣的理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擴散。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國擁有創新優勢是因為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誘使全世界的創新人才向它那里匯聚,而邊緣國卻因為人才的流失創新能力大為削弱。顯然,中心國以其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而輕易地將人類智力成果據為己有,從而增強了它在貿易或談判中換取利益、騙取利益、掠取利益的實力。如果說中心國其他方面的壟斷都是對曾經的或現有“資本”的控制,而在創新方面的壟斷,則保證了它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未來的領先地位,并以此將邊緣國置于永遠依附于它的地位上。
一、世界中心-邊緣結構形成中的創新保護
在西方國家,私有觀念似乎是天成的,它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就已經有了對財產和知識的私人占有沖動。因而,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能夠發現一些對知識或智力創新加以保護的跡象。在中世紀,“各王國都為能給自己帶來新方法或新技術的人提供特權……從發明的角度來說,創新就是用壟斷體系在一種技術實踐上創造絕對的權利,從而為王國的統治帶來好處。各王國都利用壟斷特權來吸引和留住其領土上有用并且流動的人才。” [澳]彼得·達沃豪斯:《知識的全球化管理》,邵科、張南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79頁。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制定了第一個專利法,這種做法也逐步在歐洲擴散開來。盡管類似的專利制度通常是被作為奉行重商主義的國家政策的一個部分看待的,但總體看來,此時的創新保護是作為一國內部的一種特權出現的,并不存在于國家外向關系之中。到了18世紀中后期,這一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專利等相關知識產權問題開始出現在國際關系中。因此,有學者將18世紀晚期之后的一個世紀稱為“多國專利時代”。 [瑞典]奧弗·格蘭斯坦德:《創新與知識產權》,載[挪]詹·法格博格等編:《牛津創新手冊》,柳卸林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65頁。如果說此前的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制止本國其他人對創新者權利的侵犯而鼓勵技術創新的話,那么,到了18世紀中期,尤其是在工業革命浪潮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競爭狂潮時,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也就突破了國家的邊界,進入了國家間的關系中。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起點,同時,工業革命也激發出知識生產的熱情。資本主義世界化代表了突破國家邊界的開放維度,而在知識生產中出現的創新壟斷則反映了產權保護的封閉維度。這一點看似矛盾,但在實質上卻是符合資本主義的邏輯的,一方面,資本越過國家的邊界向外擴張;另一方面,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又維系了其獲得超額利潤的優勢。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化的兩個面相。
顯然,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過程中,存在爭奪海外市場、爭奪殖民地等競爭,但也正是這種競爭,驅動了對創新的壟斷追求。當然,這種對創新的壟斷追求起初是存在于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間的。因為,此時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而在創新方面,日后的邊緣國還處在外圍,還未被中心國納入自己的創新壟斷的結構之中。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生成的過程中,正是知識與技術方面的創新,使中心與邊緣間的地位變得越來越明晰。謝爾曼(Brad Sherman)和本特利(Lionel Bently)在《現代知識產權法的演進:英國的歷程(1760~1911)》中認為,大致是從1760年代開始,出現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 [澳]布拉德·謝爾曼、[英]萊昂內爾·本特利:《現代知識產權法的演進:英國的歷程(1760~1911)》,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從歷史上看,正是在1760年,英國出現了一場關于文學財產的爭論。但是,就這場爭論來看,還是發生在英國國內的產權保護要求,然而,重要的是,18世紀中期的文學財產保護要求不僅是擔心英國國內其他人對某項著作權的侵犯,也開始擔心其他國家對英國人著作權的損害。更為重要的是,來自于文學著作權保護的要求也隨著技術革新浪潮的涌動而擴散到專利方面的保護。也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關于本國技術創新可能被他國“竊取”的擔心也開始不斷增強。所以,關于文學財產權的爭論在英國引發了一場更大范圍內的關于智力勞動保護的討論,這其中也包括保護創新技術的專利制度的生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在英國出現的專利制度,才最終確立了英國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中心地位。
英國的專利制度起源較早,1623年的《壟斷法》(Statute of Monopolies)中就有了專利方面的規定,在實踐中,甚至早在16世紀就有了授予專利的做法。但是,授予專利一直是王室授予發明人以特權,而作為一種授予特權的行為,明顯地具有不穩定性的特征,更為重要的是,王室授予這種特權的行為被理解成是對被授予特權的人的一種恩惠。也就是說,王室并沒有義務去授予發明人以專利權。在這一問題上,《壟斷法》具有轉折的意義,根據這項法律,專利授予權從王室轉移到了政府部門。當然,在現實中,這種權力的轉移并不是由《壟斷法》的頒布而一步完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時期。到18世紀中期,隨著以國家為主體的技術保護要求的不斷增長,才使專利保護變得嚴肅起來。“知識產權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授予的特權而明確地被認為是反壟斷規則的例外……國家可以授予特權,但絕不是有義務授予。轉變為‘權利一詞則表明維護知識產權是國家的義務。” [美]蘇珊·K·賽爾:《私權、公法——知識產權的全球化》,董剛、周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頁。從間歇性的和不穩定的恩賜性王室授予到確定的國家義務的轉變,這通常被解讀為國家主動地為本國創新者的利益做謀劃。然而,這種專利保護的實質卻是國家利益的需要。當專利保護只是王室的授予行為時,它是最接近“專利”的本來含義, 專利是“‘專利特許證(letters patent)的簡稱,最早來自于拉丁文‘Litterae Patentes,這在中世紀的歐洲指密封但可公開閱讀的一種皇家信件,是授予持有者的某種權利、特權、頭銜或職位。‘專利一詞源自拉丁文‘patere,意為‘公開”。([瑞典]奧弗·格蘭斯坦德:《創新與知識產權》,載[挪]詹·法格博格等編:《牛津創新手冊》,柳卸林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64頁。)因為,這種專利制度的目標只是為了鼓勵個人的創新行為,刺激國家的技術進步;而當現代國家將其確立為一種法律制度和國家的義務時,“專利”的本來含義被扭曲了,專利保護的目的變成了吸收各國創新人才為本國技術創新做貢獻,同時防止本國先進技術外流到其他國家。這就是創新壟斷。正如格蘭斯坦德(Ove Granstrand)所說的,“事實上,專利壟斷權成為以限制壟斷特權為特征的‘壟斷法令的一個例外。這些皇室授予的特權逐漸退化了,英國議會想要終結這些特權,但又顯然意識到鼓勵技術進步的極端重要性。” [瑞典]奧弗·格蘭斯坦德:《創新與知識產權》,載[挪]詹·法格博格等編:《牛津創新手冊》,柳卸林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第264頁。也就是說,如果英國國會和政府想限制皇室的權力,就應當取消專利制度(就像荷蘭在1869年廢除專利法一樣),然而,面對技術的“極端重要性”,英國卻將授予專利權的權力從王室轉移給政府,這就為基于創新壟斷的國家利益的實現鋪平了道路。
在這一時期,英國政府授予的專利數迅速增長,在18世紀40年代授予了80項專利,50年代則增加到100項,70年代又增長到300項, 參見[英]克利斯·弗里曼、羅克·蘇特:《工業創新經濟學》,華宏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頁。這樣的專利增長通常被正面地解讀為專利制度對技術創新的刺激作用,而另一面則是對技術擴散(包括國內和國際的技術擴散)的限制。以瓦特的蒸汽機為例,1775年,瓦特蒸汽機的專利在原有基礎上又被延長了25年的期限,瓦特因此在更長時間內拒絕開放其發明。有學者就此指出,這種拒絕“阻礙了金屬行業超過一代的發展。如果他的壟斷在1783年就到期的話,英國很早就會擁有鐵路了”。 轉引自惠普爾(Whipple, R.)的觀點,參見[美]蘇珊·K·賽爾:《私權、公法——知識產權的全球化》,董剛、周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頁。在英國國內如此,放眼世界,同樣如此。例如,當時的英國禁止出口蒸汽機及其零件,也禁止相關技術人員出國,如果將有關秘密私自運往國外的話,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回顧歷史,盡管許多學者將英國領先的原因歸功于其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例如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就指出,“工業革命期間出現的那些宏觀性發明起初只能在英國獨特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得到應用,并獲利豐厚,一旦移至其他國家使用時則表現出‘水土不服的癥狀,不能持續獲利。” [英]羅伯特·艾倫:《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毛立坤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3頁。事實上,對技術創新的壟斷才是其他國家“水土不服”的真正原因,因為技術壟斷延遲了技術擴散。想象一下,如果沒有這種壟斷的話,技術創新成果得以擴散的時滯就會很短,新技術也就會很快在全球范圍內遍地開花,各國也會根據本國特點而對新技術進行相應的改良。然而,正是因為創新壟斷的存在,技術在傳播中的時滯被人為地拉長了。結果是,為一些國家成長為超級中心國家贏得了時間。以蒸汽機為例,至19世紀,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輪船代替了帆船而成為英國遠洋運輸的主力軍,“英國的遠洋商船隊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商船隊,其船只數和噸位數同其他國家的商船隊相比均占壓倒性優勢。”② [英]羅伯特·艾倫:《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毛立坤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3、436頁。而相關技術通過各種渠道擴散到其他中心國家(更不用說邊緣國家了)的時間,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延遲,一些國家在親眼見識了從英國漂洋過海的蒸汽機動力船的威力時才開始效仿,一些國家是在購買了英國的相關產品后才開始了自己的模仿和研發之路。當然,也有我們熟知的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等人的例子,在英國嚴控創新技術外流的形勢下,他們憑借記憶將技術秘密帶到美國,從而引發了美國的工業革命。盡管技術壟斷已經造成了技術擴散的延遲,但這時的英國人似乎仍不滿意,因為他們所期望的不是延遲擴散,而是完全不擴散。艾倫在《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中對此所作的評論是:“這樣一來,工業革命的成就便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英國在工業革命初期特有的競爭優勢至此已不復存在,而破壞這種競爭優勢的人恰恰就是英國人自己。”②這說明,艾倫作為一個英國人所表達的是對新技術擴散的深深遺憾,其中所包含的一個愿望就是,如果歷史可以重寫,他們將會更加嚴格地保護這些創新,以維持自己特有的競爭優勢。
19世紀中期,系統化的現代知識產權法逐步確立起來,對創新的保護和壟斷也就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了起來。正如謝爾曼和本特利所指出的,現代法(19世紀中期以后)與前現代法(19世紀中期以前)“之間最重要的一個差異,是將該法律組織起來的方法……在前現代法中,并不存在任何諸如該法律應當如何進行編排之類的明確共識:沒有任何一個思維方法開始占據優勢而成為組織模式。相反,那時存在著許多相互對抗的,并且從我們現代眼光看來彼此格格不入的組織形式。”④ [澳]布拉德·謝爾曼、[英]萊昂內爾·本特利:《現代知識產權法的演進:英國的歷程(1760-1911)》,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頁。由于法律具有了組織的意象,對法律的編排也就反映出了某種組織模式,或者說,法律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組織形式,因而,也就有了空間形態。正是這種空間形態,包含了中心與邊緣的結構。不僅如此,法律自身也以中心與邊緣的形式出現了,那種為了提高確定性、可預測性、可控性的法律編排形式逐漸躍升為中心,成了現代法的主導形態,而那些“相互對抗的”法律形式則被邊緣化了。在中心-邊緣的結構視角中,這種現象是不難理解的,如果法律內部依舊保持某種相互競爭的形態,顯然是無法高效地回應現實的,更不用說去控制現實了。只有當法律也具有了中心-邊緣的構型,甚至當這一中心成為主導性的支配力量,才能更高效地處理現實中的事務。同時,“現代知識產權法傾向于更為抽象(abstract)和具有前瞻性(forward looking)。特別是,前現代法的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法律的運行環境做出被動回應而確定的,而在現代法的立法起草過程中,則不僅考慮到其所調整的對象,而且也關注法律在實現這些任務時自身所采取的形態。”④從被動回應到主動預測并加以控制的演進過程,表明國家越來越有能力以現代知識產權法為工具去保護國家利益了。
二、在創新壟斷中強化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
19世紀70年代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以及世界經濟的蕭條等助長了保護主義的再度興起,現代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就是這時在許多國家建立起來的。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國際公約》的簽署,大英帝國在帝國范圍內建立統一專利法的嘗試,二戰后美國的崛起及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迅猛發展,1967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立,1973年歐洲專利協定的簽訂……都是一些大事件。這些事件表明,知識產權的保護是發生在國家間的,而且參與到這些事件中的各個國家似乎也是平等的。事實上,在這些事件背后卻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原因是,這些事件發生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之中,所保護的是中心國的國家利益,是服務于中心國的知識和技術壟斷的。此前,對知識和技術的壟斷大都發生在同處于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中心國之間,邊緣國在這一方面幾乎處于集體失聲的狀態。但是,在20世紀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以及法律制度向世界的推廣,一個讓邊緣國認同和支持中心國實現知識和技術壟斷的國際體系生成了。比如,以前述的蒸汽機擴散為例,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中心國之間由于競爭而建立起了壟斷,所表現出來的是技術在中心國之間傳播和擴散的遲滯現象。 有研究統計了英國博爾頓瓦特公司在1775到1825年間來自外國的蒸汽機訂單,可以看到,其中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可謂是后來的中心國家,而剛果、印度、巴西等地區雖然也有訂單,但他們在當時仍處于殖民統治之下。(參見Tann, Jennifer, and Michael J. Breckin,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he Watt Engine, 1775~1825,”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31, no.4, 1978, pp.541~564.)然而,隨著邊緣國加入到這個知識和技術壟斷體系中來,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學者們卻很少關注創新壟斷對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強化功能。在《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中,艾倫在努力炫耀英國工業革命的偉大功勛時,是在極力掩飾世界的不平等,試圖否認作為超級中心的英國向其他中心國技術擴散的遲滯現象及其消極影響。根據艾倫的看法,“西歐和北美地區的鐵路建設進度幾乎和英國保持著同步推進的態勢”,“即便是在俄國和印度這類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落后經濟體,截止19世紀晚期也相繼建成了大規模的鐵路運輸網。” [英]羅伯特·艾倫:《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毛立坤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4~275頁。這似乎是在說中心國的創新壟斷并沒有在世界的發展中產生遲滯效應。事實上,正如拉美學者所揭露的,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
1949年,普雷維什在其被稱為“拉美經委會宣言”的《拉美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一文中指出,傳統國際分工格局的確立是建立在一個誘人的卻完全錯誤的假設之上的,“根據這個假設,科技進步的好處,要么通過降低價格,要么通過增加相應的收入,會在全社會(the whole community)以相同的狀況擴散開來”,事實不是這樣的,“如果‘社會(the community)在這里僅僅指的是大的工業國家,那么,科技進步的好處確實會逐步擴散到所有的社會群體和階級。但是,如果將社會一詞進行擴展,將世界經濟的邊緣國家也包括在內,這種概化做法里就隱含著一個嚴重的錯誤。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擴散至邊緣國的部分與那些大工業國的人們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④ R.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7, no.1, 1962.根據中心國的邏輯,技術革新帶來了生產率的大幅增加和價格的相應下降,而在國際貿易中對原材料的需求也顯著提高,以出口原材料為主的國家就能獲得所謂的比較優勢,同時初級生產部門的價格下降相對緩慢,因而,邊緣國在此之中是獲益者。然而,普雷維什的研究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那就是邊緣國的貿易條件存在著走向惡化的趨勢,而不是像中心國所宣稱的那樣會在長時期內獲得好處。根據普雷維什的意見,如果邊緣國被中心國的邏輯所蒙蔽的話,就會止步于初級生產,滿足于通過這些看似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競爭力卻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獲得收益,從而失去技術革新的需求和動力。當普雷維什的“貿易條件惡化論”提出之后,由于在結論上與產生于中心國的經濟學理論完全不同,因而遭受了諸多批評,但普雷維什堅持認為,“中心國保留了其工業技術進步的所有利益,而邊緣國卻將其自身科技進步的部分成果轉移給了中心國。”④確實如此,當邊緣國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后,中心國技術進步所取得的成果被保留在中心國本土,邊緣國難以從中分一杯羹,但是相反地,邊緣國技術進步所取得的有限成果卻要被中心國攫取一大部分,甚至邊緣國會積極主動地向中心國無條件地奉獻知識和技術的成果,這不僅包括技術進步所取得的經濟成果,也包括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智慧成果。當下中國學者極力希望到所謂SCI或SSCI等期刊上發表論文,并希望得到中心國對其成果和智力的承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是心懷自信地向中心國家展示中國與自己的智慧,相反,是不自信地謀求中心國承認。也就是說,中心國無條件向邊緣國輸出的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邊緣國由于缺乏自信,往往需要把知識和技術成果等真實貨色呈現給中心國,以期得到中心國對其能力的肯定。
為了解決對初級產品出口的過分依賴問題,拉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采用“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取得了一定的繁榮,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又陷入了對中心國更深的依附之中。在對這一問題的反思中,“依附論”學者發現,普雷維什及其拉美委員會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之所以會使拉美再度陷入到對中心國的依附之中,恰是因為沒有認真對待邊緣國在技術上依附于中心國的問題。這就是多斯桑托斯(Thetonio Dos Santos)所指出的,“統治國對依附國擁有技術、貿易、資本和社會政治方面的優勢(在不同歷史時期擁有上述范圍內某些方面的優勢),從而使它們得以對依附國強加條件,進行剝削并掠走其國內生產的部分盈余。”②③④ [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毛金里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02~303、315、325~326、315頁。也就是說,雖然中心國與邊緣國的依附關系是由包括貿易、資本、技術、政治等各類因素決定的,但在不同時期,中心國在對邊緣國實施剝削時所依賴的工具是不同的,而邊緣國在這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對中心國的依賴,也有著程度上的不同。根據多斯桑托斯的分析,在殖民時期主要存在著“殖民地商業-出口依附”;自19世紀末開始,則確立起了“金融-工業依附”;到了二戰后,逐漸確立起了“技術-工業依附”。所以,拉美在七八十年代再度出現對中心國的依附主要是一種“技術-工業依附”。多斯桑托斯具體地分析了這種依附關系,“我們就可看到依附性關系給發展帶來的第三種結構性限制,即工業發展決定性地受制于帝國主義中心實施的技術壟斷。我們前面曾提到,不發達國家發展工業所需的機器和原料依賴于進口。但是,這些生產要素并非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自由獲得的。它們都受專利權的保護,而專利權一般都屬于大公司。它們不是把機器和材料當作簡單的商品出售,而是要求為使用那些機器和材料支付特許使用費,或者在多數情況下把這些商品轉變成資本,以它們自己投資的形式引進。”②由于邊緣國在本國工業發展中對新技術表現出很強的渴求,包括專利保護在內的各種技術壟斷行為也就成了中心國在與邊緣國貿易中的談判籌碼,他們對技術收取高于其本身價值的高昂使用費。即便如此,這種即時的收費也僅僅是剝削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心國將技術以資本的形式投入邊緣國,以此獲得長期收益。多斯桑托斯將這些行為與現代地租進行類比,嚴厲地批評道:“對這些服務的估價過高,在許多情況下并不存在服務僅僅是對商標和專利壟斷的結果,與現代的地租形式很相似,換言之,這是一種向真正的生產參與者征收租稅的純法律上的權利,就是說,把一般生產盈余轉移到那些通過壟斷人類知識產權進行投機的無所事事者手中。”③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那些在統治中心被更先進的技術替換下來的機器,就這樣作為資本運往依附國去裝備設在那里的子公司。”④換句話說,一方面,中心國不斷地研發新技術,另一方面卻不忘用淘汰的技術換取短期和長期的利益。這樣一來,無論邊緣國制定了什么樣的趕超計劃,無論通過什么樣的努力去追趕先進國家,也不可能改變其邊緣地位。加爾通曾舉例說:“舊時代的通訊/交通方式與生產方式(經濟方面),破壞方式(軍事方面),以及創新方式(文化方面)一道,都可以——有時以二手貨的形式——賣給這一垂直貿易/援助結構里的邊緣國。中心國的飛機和船舶更快捷,用起來更直接,看起來更可靠,也確實能夠吸引更多的乘客和貨物。當邊緣國追趕上來的時候,中心國已經在通訊衛星領域領先了好多年了。”⑥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8, no.2, 1971, pp.81~117.邊緣國所享受的只是中心國剩下來的殘羹冷炙,而且經常以施舍的樣子出現。中心國向邊緣國轉讓技術,邊緣國通常滿意地接受(其實是不得不接受)這些施舍,從而有了“技術援助”這個優雅的名稱。中心國往往宣稱,通過技術援助向邊緣國提供了無償的或優惠的服務,完全是為了幫助邊緣國發展技術和提高生產力,而在實際上,這些“援助”只不過是施舍給邊緣國的一些殘羹冷炙。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技術“援助”中的一個通行做法就是,中心國委派相關技術與管理人員到邊緣國中傳授經驗,培訓邊緣國的有關人員,或者邀請邊緣國人員到中心國學習先進經驗。這樣也就形成了一種師徒關系。對此,加爾通從中所讀出的是:“如果中心一直提供老師,并定義了什么東西才值得被傳授(從基督教的信條到科學技術的教義),而邊緣一直提供學生,這就形成了一種帶有帝國主義味道的情形。”⑥所以,技術援助不僅是壟斷者所做出的某種施舍,而且是通過施舍的方式向邊緣國輸送中心國的理論與文化。技術壟斷使邊緣國的技術水平永遠滯后于中心國,而技術援助在施舍了已經落后的技術時又同時附加上了理論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以至于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被經營地牢不可破。也許人們以為在接受了中心國的技術后可以進行因地制宜的改造,即實現某種改良和革新,并在此基礎上逐漸超過中心國。其實,這只能是極其幼稚的“小人之心”,因為,多斯桑托斯已經指出了這一點的不可能性,“如果改變一下機器的技術規格使之適合本國的知識,那么本國的工程師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這種技術援助。但是,我們的工程師無疑是接受了跨國公司教科書的系統訓練,形成了一種完全受這些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技術模式影響的知識、志向和行為類型。” [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毛金里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27頁。所以,伴隨技術援助或技術轉移而來的價值觀早已形塑了邊緣國的“知識、志向和行為類型”,早已限定了邊緣國發展的一切可能,在這里,并不存在多少改良和革新的空間。
三、掙扎在世界中心-邊緣解構中的創新壟斷
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看創新壟斷,可以看到對創新的保護走過了這樣的歷程:起初是在一國內部保護創新者的權利;然后進入到國際關系的領域,反映在中心國的競爭之中,則是出于國家利益而對創新加以保護;隨著邊緣國加入到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之后,創新壟斷則成了中心國剝削與遏制邊緣國的工具。在今天,我們滿眼所見的都是中心國的創新壟斷,而邊緣國在這一創新壟斷面前除了等待中心國可憐的施舍之外,別無選擇。邊緣國缺乏創新人才,即使培養出了創新人才,也會輕易地流向中心國。邊緣國為了吸引人才,可能會竭盡所有對那些回流的人才給予特別優厚的待遇。這樣又傷害了那些生長于本土的人才,促使讓他們削尖腦袋到中心國去鍍金,以至于邊緣國陷入了創新人才匱乏的惡性循環之中,不僅吸引回流的人才無法獲得創新的土壤,而且已有的人才儲量也會急速地流失。這就是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邊緣國的劣勢地位,而中心國的創新壟斷又在不斷地強化邊緣國的這種劣勢。20世紀后期以來,全球化運動正在對既有的資本主義世界化格局作出挑戰,表現出了突破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沖動。然而,中心國為了維護資本主義世界化所帶來的世界格局,為了鞏固其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優勢地位,在創新壟斷方面也開始了一輪新的“創新”,以求在既存的創新壟斷中繼續實現自己的利益。
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形成了一份在國際知識產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公約,即1883年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國際公約》(簡稱《巴黎公約》)。《巴黎公約》往往被認為是國際法的典范之作,因為它“沒有為成員國創建實體法,同時,也沒有將新的法律強加于成員國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只是對各成員國間形成的共識的反映,這些共識在各成員國國內法律中就已經被認為是正當合法的”。 Gana, Ruth L., “Has Creativity Died in the Third World: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nv. J. Intl L. & Poly, vol.24, 1995, pp.109~144.考慮到《巴黎公約》第一批的簽署國家(比利時、巴西、薩爾瓦多、法國、危地馬拉、意大利、荷蘭、葡萄牙、塞爾維亞、西班牙和瑞士等11國)和產生的原因(為吸引和保證更多國家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發明博覽會),這一公約是得到中心國或近中心國的國家所認同的,因而具有了某種平等的特征。然而,到1993年,當世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可以把大多數邊緣國納入進來時,則以另一種面目呈現了出來,即成為中心國剝削邊緣國而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手段。達沃豪斯(Peter Drahos)認為,世界貿易組織在1993年通過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標志了知識產權保護新階段的開啟。 Drahos, Peter,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21, no.3, 1997, pp.201~211.在美國的主導下,TRIPs協定為中心國構筑起創新壟斷“新帝國”(達沃豪斯語)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與曾經企圖建立全球專利制度的大英帝國相比,這一“新帝國”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以國際組織與國際協定的名義將中心國與邊緣國同時納入一個看似平等的國際框架之中,而其實質則是“強國將本國的法規模式通過法規新殖民化的過程強加于弱國”。 [澳]彼得·達沃豪斯:《知識的全球化管理》,邵科、張南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224頁。TRIPs協定“通過擴大知識產權所有者對權利的壟斷范圍,使得信息和技術價格大幅增加,并且要求各國在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上發揮更大的作用”。③⑤ [美]蘇珊·K·賽爾:《私權、公法——知識產權的全球化》,董剛、周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13頁。正如我們所強調的,當知識產權保護成為一種國家義務時,那些授予特定個人或公司的知識產權都蘊涵著一種國家壟斷力量,而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存在于中心國的這種壟斷力量不僅表現在某個中心國與某個邊緣國的關系中,也不僅表現為幾個中心國的聯合壟斷,而是借助于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去把更多的中心國和邊緣國網羅到同一個體系中,并為這個體系確立起中心-邊緣結構,分別把中心國與邊緣國安排在不平等的位置上。
TRIPs協定的許多簽署國“在簽訂協議時并未充分地意識到TRIPs的影響。他們在談判前和談判中都受制于發達國家的經濟脅迫。此外,他們同意以簽訂TRIPs換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承諾,即放寬發展中國家農業產品的市場準入和紡織品出口”。③正如賽爾所看到的,亦如簽署類似國際協議的情況一樣,其背后充滿了欺騙、威脅和交換(威逼加利誘)。一般說來,中心國總是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國際協定去隱藏自己的陰謀,這是因為,這些協定從構想、起草、制定、談判、通過和簽署的整個過程,通常都受制于某個中心國或某幾個中心國組成的聯盟,TRIPs就是美國聯合日本和歐洲的產物,所以,在其中注入了為己牟利的內容,并輕而易舉地隱藏了他們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幾乎所有的國際協定的簽署中,中心國都會向邊緣國描繪一幅協定將會帶來的大好藍圖,TRIPs協定就包含著這樣的敘述,“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施行應有助于促進技術革新、技術轉移和技術傳播,有助于生產者和技術知識使用者的互惠,其實現的方式應有助于社會與經濟福利,并有助于權利與義務的平衡。”⑥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C.許多邊緣國正是在這些描述的蒙蔽下在協定上簽了字,以致于“未能充分地意識到TRIPs的影響”。中心國的另一個伎倆就是交換或利誘,事實上,這并非即時的利益交換,而是用對邊緣國的未來利益承諾換取此時邊緣國的妥協,至于誘導了邊緣國簽署相關協定后,那些非正式的口頭承諾是否能兌現,往往是由邊緣國自認倒霉而去加以消化了。當然,也會有一些正式的文字承諾,但也不一定會兌現,因為這些文字與他們所簽署的國際協定一樣,也是任由中心國把持。不僅如此,在協定簽署后發揮作用的漫長時期中,中心國還會充分利用這些協定為自己謀利,當國際協定成為中心國實現利益的障礙時,或者對協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或者要求修訂協定,或者干脆繞開協定等。
美國一直是一個主張貿易自由的國家,而知識產權保護顯然是與自由貿易的理念直接沖突的,但是,為什么美國會在20世紀末強勢推進基于貿易的國際知識產權協定呢?“考慮到直到1982年美國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執行措施一直是相對比較寬松的,所以美國倡導全球性的承諾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讓人頗感意外。”⑤不過,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去看,這一點又應在意料之中。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再度流行起來,然而,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展所反映的只是中心國家要求全世界向自己敞開利益輸送之門,這種所謂的“自由貿易”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從來都不會是自由平等的。因此,中心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知識產權保護雖然在表面上是與自由貿易相沖突的,而在實質上卻是為中心國的利益服務的,在這一點上,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TRIPs協定的開篇中就冠冕堂皇地寫道:“為了減少對國際貿易的扭曲與阻礙,并考慮到促進有效而充分地保護知識產權的必要性,同時保證實施知識產權的舉措和程序本身不構成對合法貿易的阻礙;鑒于此,制定如下新的規則和原則。”⑥可見,中心國并不會理會這種知識產權保護與自由貿易之間的表面矛盾,而是依然打著保護貿易的旗號推進知識產權保護。除了保護貿易的說辭,中心國還重復著知識產權保護會刺激創新等這類陳詞濫調。所以,關于中心國在其國內寬松實施知識產權保護而在國際上強勢推動知識產權保護也就不難理解了,那無非是在維護創新壟斷罷了。這也再一次證明,中心國向邊緣國積極推行的制度或政策(例如民主制度、發展模式)與其國內所實施的制度政策之間并不一致,換言之,中心國在事實上并沒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模樣去塑造這個世界。
從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來看,每一次的技術革新浪潮都伴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重要舉措,創新壟斷是起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而創新壟斷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轉化為剝削邊緣國的手段則始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現在,人類進入全球化的新階段,隨著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方面的新的技術革新浪潮的涌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提出了新的挑戰。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改變了原有的技術傳播途徑,并在某種意義上無視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制約,從而使中心國意識到,這很可能意味著他們所享有的傳統優勢即將失去。雖然邊緣國“廠商逐漸增強的其傳統工業品滲入遠地市場的能力讓發達國家不得不比以前更依賴他們在生產知識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② Reichman, Jerome H., “TRIPS Component of the GATTs Uruguay Round: Competitive Prospect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in an Integrated World Market,” Fordham Intell. Prop. Media & Ent. LJ.1993, p.4.但是,中心國此前牢牢控制著邊緣國的狀況已經開始松動。盡管中心國聯盟內部也存在競爭,而在面對邊緣國時,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依然是一個事實,希望聯合起來從邊緣國那里獲得足夠的利益。所以,在中心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時,他們立刻推動TRIPs的簽署,試圖以此去鞏固中心國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優勢地位。
當然,中心國因擁有技術優勢而要求以貿易的形式向邊緣國轉讓技術,認為這一轉讓技術的方式能夠有效地保護中心國的利益,反之,則會使中心國的利益受到損失。在TRIPs中,就有著相關表述:“不通過進口或經許可的方式而使用外國技術,通常會給技術出口國帶來非法的經濟損失。”②也就是說,在中心國擁有技術優勢的條件下,邊緣國能夠通過貿易的方式獲得什么技術,都需要得到中心國的許可,哪些技術可以轉讓,哪些技術不能轉讓,都由中心國來決定。這顯然是一種霸權邏輯,而且也是維護霸權的做法,更不用說進口技術所要花費的高昂費用在邊緣國這里能否承擔得起了。于此之中,可看到,中心國所考慮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至于全球化條件下的人類共同利益,則被棄置不顧。比如,中心國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在碳排放技術方面又做出嚴格的壟斷,或者要求邊緣國通過貿易的方式購買他們的碳排放技術。這無疑是一種在經濟上扼殺邊緣國的做法,目的就是要維護中心國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的位置不變。另一方面,從歷史上看,中心國的這些要求也不具有合理性。“在蒸汽機技術的早些年里,英國禁止出口蒸汽機及其零件和技術人員。美國卻不顧一切地進口所有這三類……對美國來說,在當時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最好的政策就是不去嚴格執行外國的知識產權。” Merges, Robert P., “Battle of Lateralis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BU Intl LJ, 1990, p.8.而是盜取了英國的先進技術,等到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實現突破時,卻開始積極推進知識產權保護。
總的說來,中心國享有三項對創新的絕對壟斷權:產出、支持與合法化。首先,中心國由于網羅了全世界的創新人才而獲得了較高的創新能力,這就壟斷了創新的產出。19世紀后半葉和20世紀的美國就是通過各種渠道從全世界引進技術與人才而成就了自己非凡的創新力。其次,中心國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硬件條件(例如實驗室),即使邊緣國有了某種創新的靈感,也由于缺乏足夠的物質條件支持而不得不放棄,相反,中心國則具備先進的物質條件以支持創新,這就壟斷了對創新的支持系統。最后,通過覆蓋全球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使中心國享有判斷某項新事物是否屬于創新的話語權,即只有獲得中心國的肯定,某種新事物才能被合法地界定為創新,否則就被視為應當被扼殺的新事物。邊緣國知識分子不遺余力地想獲得中心國的認可就是想要獲得中心國對自己某項創新知識的肯定。實際上,這種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全服務于中心國創新壟斷的要求,也是妨礙全球面對共同問題開展合作的設置。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人類已經成為一個共生共在的共同體,風險和危機不會承認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全人類攜起手來去共同應對。在這種情況下,中心國拒絕合作和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而削弱人類應對風險和危機的能力,顯然是不明智的做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秦開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