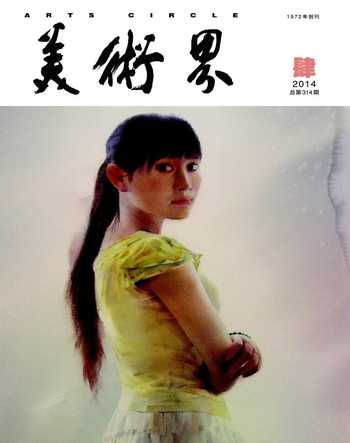唐、宋鞍馬形象之變
馬作為六畜之首,不僅與人類的日常活動息息相關,而且在歷史的演進變革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在中國繪畫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鞍馬同樣以其奔放英俊的外形為文人士大夫所好,涌現出了諸多彪炳史冊的畫馬名家。馬的形象出現在繪畫中由來已久。魏晉時期顧愷之根據曹植文學作品所作《洛神賦圖》,是較早有記載的帶有馬的形象的傳世作品,畫中馬的形象已經具備中國鞍馬畫成熟的樣式。此時鞍馬絕大多數是根據畫面需要,或者作為點綴、襯托人物而出現的,并未獨立成科。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之“敘畫之興廢”篇講:“六法解在下篇但取一技可采,謂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馬、或花鳥,各有所長。①”可見,鞍馬作為一個獨立的畫科出現在唐朝。
鞍馬畫在唐朝獨立成科且迅速走向成熟,出現了一批專攻畫馬的名家,成為鞍馬畫史上的一個巔峰,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明僧宗衍《題韓幹畫馬圖》: “唐朝畫馬誰第一,韓幹妙出曹將軍。”韓幹是唐朝鞍馬題材繪畫中相當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不但專攻畫馬,而且流傳作品最多,影響最大。《宣和畫譜》記載他“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在朝為官,皇室御廄所飼養的良馬眾多,所謂“玄宗好大馬,御廄至四十萬”(《歷代名畫記》),為其提供了近距離細致觀察的寫生對象。宋董卣在《廣川畫跋》中云:“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韓幹重視寫生,以真馬為師。曾詔入供奉唐玄宗,令師陳閎畫馬,帝怪其不同,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也。”杜甫在《丹青引曹將軍霸》中言:“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韓幹藝術成就的取得與其在創作過程中嚴謹細致的態度是無法分開的,其遺世作品很大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客觀真實地唐朝盛期鞍馬形象。傳世作品有《照夜白圖》《牧馬圖》等。
唐朝人物畫豐滿圓潤,以“豐腴”為美,唐朝盛期的鞍馬形象同樣為此。韓幹筆下的馬,已經不再是馳騁沙場的戰馬形象,而是以肥壯為主。其作品《牧馬圖》中一深一淺共兩匹御馬,馬的裝備富貴華麗,其中色深者完全呈現出來,其用線、設色比較簡練:以圓潤的弧形線條為主,胸部、肚子與臀部長而圓的弧線貌似可以連在一起組成一個大大的橢圓,與杜甫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記載的“斡唯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剛好相符;設色大體遵循了“隨類賦彩”的原則:以明暗漸變微妙精細的分染,十分巧妙地突出了鞍馬的體積。圓潤的用線加之于突出的體積感,將馬的分量表達得淋漓盡致,肥碩豐壯的形象躍然紙上。
李公麟是北宋最負盛名的文人畫家之一,時為宋畫第一人,善畫人物,尤工畫馬,《五馬圖》是李公麟鞍馬畫中最具代表性的傳世作品。李公麟的繪畫創作尤為重視觀察寫生,他的人物畫可以區分出人物的身份、地位,甚至于地域、種族都可以一一看出究竟。李公麟最初學畫是從畫馬開始,在朝為官卻仕途不暢,經常在宮廷的馬廄里觀看御馬,“終日不去,幾與俱化”。蘇軾曾稱贊他:“龍眠胸中有千駟,不惟畫肉兼畫骨”。可見,其鞍馬畫同樣重視客觀物體的真實,同樣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真實客觀的北宋中期的鞍馬形象。
李公麟作為北宋畫馬第一人,在繪畫的表現方式上另辟新徑:沿襲并發展了唐朝大畫家吳道子的表現方式“白描”,并將其確立為一種新的畫種。白描畫用墨色線條勾描形象而不施加色彩,在這樣樸素簡練的變現方式中更加突出客體的外在形象特征,忽視了客體的外在豐富的色彩,卻以少勝多、忘形得意,更加注重客體內在的精神狀態,同時,體現著畫家注重淡泊、儒雅的文人氣質。遺世作品《五馬圖》即是采用了白描畫法,畫中忽略了色彩,更加突出了線條的表現力,線條的徐疾、輕重、濃淡、長短,不僅生動準確地體現了馬匹的動態、神態,而且將不同材質的質感體現得淋漓盡致,如蓬松的皮毛、堅挺富有彈性的肌膚。蘇東坡給予李公麟鞍馬畫的評價相當之高,在《馬圖贊并引》中寫道:“龍眠胸中有千駟,不惟畫肉兼畫骨。”此詩在側面也表明李公麟筆下的鞍馬不再全是豐壯肥碩。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韓、李筆下馬的形象變化。這種變化受繪畫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畫家主觀審美意識的不同是繪畫風格形成的直接因素,而主觀審美意識的形成自然也有先天因素的影響,所以此種轉變不能排除偶然因素的影響。但是,一種繪畫風格的轉變又是必然的,外在因素的不同必然會形成不同風格的藝術作品。時代的更替、社會思想的變化,對于繪畫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韓幹是中唐時期的畫家,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令人向往的時代之一,遠離了戰爭的侵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富庶,思想開放,社會安定有序。儒家思想作為治國安邦的一劑良藥,頗受統治者的推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仕人實現人生抱負的準則。積極入世的社會思想之下仕人充滿著壯志豪情,紛紛投身于建功立業的行列。中唐時期,唐朝縱然出現下坡,但是經過短暫的修整之后依然強大,強健豪邁、積極向上的時代風尚依然未變。安定的社會生活,常年遠離戰爭,鞍馬不同于奔馳在戰場上英勇雄壯、健壯有力的形象,更多則成為統治階級游玩的工具。張萱同為唐朝鞍馬畫的出色代表,其作品《虢國夫人游春圖》就是描繪統治階級貴族乘馬外出游玩的情景。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開宗明義:“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 此時的文藝創作是“為君、為民、為事、為物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繪畫都已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韓幹受唐玄宗詔入,曾官至左武衛大將軍,作為供奉統治階級的畫家,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其藝術創作亦不斷為統治階級所掌控。韓幹筆下豐碩肥壯的鞍馬形象,體現著唐朝所崇尚飽滿的美,一方面在映射著盛唐氣象的同時,在安史之亂的中晚唐也有著為統治階級粉飾太平的意味。另一方面,在表現方式上,韓幹以工整細致有力的弧形線條,略加渲染,將馬的形體結構表現的準確生動。同時又將馬的肥碩甚至慵懶體現得淋漓盡致,韓幹筆下嚴謹準確、形象生動的鞍馬畫,無疑是繪畫“唐尚工”最好的詮釋。
縱觀兩宋民族矛盾始終存在,面對日益嚴峻的民族矛盾,統治者漸漸失去了最初的積極政策,開始茍且于一隅安寧之地。時代的戰亂,直接使李公麟“不惟畫肉兼畫骨”健壯的鞍馬形象替代了韓幹“惟畫肉不畫骨”豐碩肥壯的鞍馬形象,此時的駿馬有著奔馳沙場的矯健。當亦儒亦畫的有識之士看到統治者一味的茍且偷安,久而久之就對于仕途失去信心。此外,北宋時期儒學再度繁盛,與漢唐之儒學大有不同,“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在傳統儒學的基礎之上,向著哲學思辨與探討宇宙生成的方向發展。重內省悟性,以解萬物人生。在理學中體現的典型而充分。”②這是吸收了佛教、禪宗之后的新儒學即理學,在北宋中期逐漸形成并占據主導地位。新儒學不同于唐朝注重仕功、治國、平天下的外向型進取的思維方式,而是把建功立業的外在追求內化為內在性情的涵養。內圣外王,強調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對于自身內在素質的修養,完善精神需求。就像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所講:“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仕途的不暢加之于儒學思想的轉向,使其繪畫表現方式發生了變化。繪畫作品《五馬圖》是現存較為可信的李公麟的真跡。李公麟不再僅僅滿足于外在形象的真實刻畫,理學“靜坐”、“節欲”的思想使其忽略了客體張揚的色彩,拓展并形成了新的表現方式——“白描”,對后世影響深遠,被趙孟頫稱其為“白描之祖”。理學“格物致知”的影響下,其筆下的鞍馬不在停留于外在形象的描繪,開始追求內在的真實,作品《五馬圖》中線條如行云流水,雖然忽略了客體的固有色彩,僅以線條描繪對象,卻有著相當強的表現力,皮毛、斑紋、人物的地域特征仍然體現得淋漓盡致。
鞍馬作為中國文人畫家所熱衷表現的一種對象,在中國繪畫史中形象不斷發生著轉變。隨著時代的更迭、社會思想的轉變,首先受其熏陶的無疑是文人士大夫,而畫家多為文人,由此,其對于繪畫的影響自然是必然的、潛在的。
注釋:
①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精讀[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14頁.
②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348頁.
【曹國橋,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