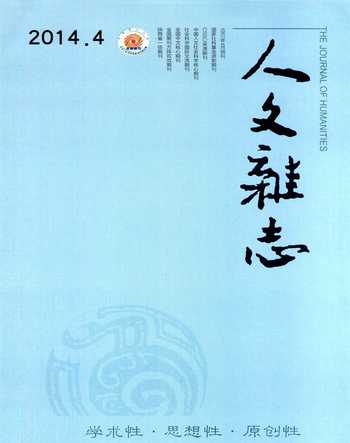欲望策略:俄狄浦斯情結的偏頗
王小妮
內容提要:俄狄浦斯情結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論中最為驚心駭俗的部分。其將弒父娶母的悲劇追溯到嬰兒時期的性欲壓抑和“閹割”威脅,著重從內在主體的心理結構、心理欲求和心理積淀去理解文藝活動這種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復雜的精神活動,成功地揭開了千百年來困惑人類的精神奧秘,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但其“從現在的觀點去解釋過去”,把人類生物化、歷史簡單化和文學審美價值闡釋化,存在許多偏頗。
關鍵詞:俄狄浦斯情結 自然化 生物化 闡釋化
〔中圖分類號〕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4-0123-03
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又稱戀母情結,最早見于1910年弗洛伊德寫的《對愛情心理學的貢獻》。《夢的解析》的第五章《夢的材料與來源》一文,弗氏已經開始用俄狄浦斯情結闡釋文學。這種嘗試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古希臘著名悲劇《俄狄浦斯王》。弗氏認為這部古希臘悲劇表面上是命運和個人意志的悲劇,但實際上表現的是人類童年時代受到父親閹割威脅后的成年復仇,即弒父娶母。《俄狄浦斯王》之所以震撼我們,是因為俄狄浦斯的命運很有可能在我們身上重演,這也就是弗氏在1920年發表的《超越唯樂原則》中提出的“強迫重復原則”。弗氏將俄狄浦斯難以改變的命運看成是人與生俱來的原罪。弗氏認為,人的性欲的第一個對象就是他的母親。從一開始,幼兒對母親的態度就明顯地表現出性欲。弗洛伊德的學生奧托·朗克甚至認為,胎兒位于母腹之中時,就有了性欲的特性。特別是從分娩活動開始就出現了俄狄浦斯的悲劇。[俄]巴赫金、B.H.沃洛希諾夫:《弗洛伊德主義批判》,張杰、樊錦鑫譯,中國文聯出版社,1987年,第47頁。由于父親干涉幼兒與母親的關系,激起了兒子對父親的仇恨,父親就成了兒子的情敵。一般人之所以沒有弒父娶母,是因為暫時忘卻了對父親的敵視。弗氏認為索福克勒斯揭示出,“自孩提時代起,我們一直自以為聰明,一如俄狄浦斯,卻看不到人類與生俱來的欲望加給我們的重負;一旦真相揭開,又閉目不敢正視這童年的故事。”陸揚:《精神分析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頁。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不過達成了童年的愿望,索福克勒斯所挖掘出的,是人類兒童時期內在的受到壓抑自我,普通人群因為緩解稀釋了這種心理癥,成功地將對母親的性沖動逐次收回,從而漸漸忘掉對父親的嫉妒心。通過對達·芬奇創作、莎士比亞《三個匣子的主題思想》、歌德自傳中的童年回憶以及易卜生的《羅斯莫莊》等的考察,弗氏一再論證了自己的判斷。如他梳理了達·芬奇的生平,認為私生子達·芬奇得到母親卡特琳娜的溺愛,因而也刺激了他的性沖動,使他早熟。達·芬奇的畫作實際上有不少表現母子關系之間的這種受到壓抑的隱秘,無論是《蒙娜麗莎》的甜蜜獨特的微笑還是《圣安娜和另外兩個人》中兩位女性的那種迷人的微笑,都是這種童年受到壓抑的性沖動的投射。在弗氏看來,無論藝術家、作家覺察與否,俄狄浦斯情節所含蘊的童年經歷和創傷記憶都對作品具有催生驅動意義,成為闡釋一切藝術、文學作品的一把金鑰匙。
弗氏甫一提出俄狄浦斯情結,就為社會和道德所不容。弗氏認為這種情結是與生俱來的普遍存在,是受到遮掩壓抑的本能沖動,常常在無意識中通過隱約可察的偽飾顯現出來。它充分說明了為什么在不同民族之間都廣泛地留傳著有關母子亂倫、弒父娶母或父殺子的神話傳說,他指出這種情況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哈姆雷特》和《卡拉瑪佐夫兄弟》都是俄狄浦斯情結的表現,不同在于“在《俄狄浦斯王》中,作為基礎的兒童充滿欲望的幻想正在夢中展現出來,并且得到實現。在《哈姆雷特》中,幻想被壓抑著。”[奧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美文選》,張喚民、陳偉奇譯,知識出版社,1987年,第17頁。他認為哈姆雷特之所以再三延宕,完全出于戀母情結。俄狄浦斯情結欲立足作品的深層蘊含,找尋人們心理和心理發展中某種無意識的“原型”和積淀在文學作品中的投射,這種嘗試和努力無疑意義重大。從方法論上,我們不難看出,“兒童情結的整個結構是通過回顧的方法而得到的;它是建立在解釋成人的回憶和解釋可以用來搞清這些回憶的那些折衷構成物的基礎上的。”這種方式,用現在的觀點解釋過去,正如巴赫金所批評的——“從現在的觀點去解釋過去。根本談不上什么客觀地回憶我們過去的內心體驗,”諸如“戀母性本能”、“父親即情敵”、“憎恨父親”、“盼望父親死”等事件是在成年以后的意識中“才獲得有意味的內涵、有價值的色調、在思想觀念上的整個分量”,因而,如果我們“否定觀點、評價和解釋(它們是純屬于現在的)向過去投射,那么就永遠談不上什么俄狄普斯情結,不管引以證實這一情結的客觀事實怎么多。”[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曉河、賈澤林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65-466頁。《弗洛依德主義批判綱要》這種將文學創作簡單的歸于“力比多”,從主觀主義的自我意識出發,將我們的心理圖畫僅僅表現為欲望、情感和表象的沖突,使得俄狄浦斯情結存在許多偏頗。
首先是人的生物化。弗氏簡單地認為人只有處于動物狀態的性,性本能推動了人類的發展,片面地理解了性,又過高地估價了性。弗洛伊德認為性力是人的天賦的本質,也是人類趨向完善的本能,這種本能將人的智力和道德境界達到了現有的最高水平。在《超越唯樂原則》中他談到:“至于在極少數人類個體上表現出的那種趨向于更完善境界的堅持不懈的沖動,可以理解為一種本能壓抑的結果,這種本能壓抑構成了人類文明中所有最寶貴財富的基礎。”[奧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選》,林塵、張喚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第45頁。《超越唯樂原則》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弗氏指出人類在生存的壓力重壓下,性本能升華了,“轉向他種較高尚的社會目標。”[奧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9頁。他將人的性欲分為四個階段:嘴巴階段嬰兒在吸吮活動得到了性的滿足;肛門階段兒童從大小便中獲得了快感;“崇拜男性生殖器階段”(三到六歲)兒童在擺弄自己的生殖器中得到快感,小女孩因缺少陽物而仰慕男孩,并對父親深情專注,想取代母親的位置,形成“埃勒克特拉情結”(又稱“戀父情結”)。而男孩愛的第一個對象就是他的母親,他想獨占母親而仇視父親而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結”; 從“生殖的階段”起,兒童所面臨的任務就是擺脫指向他母親的“力比多”愿望,并利用這些愿望為他的愛情去尋找外來的對象。嬰兒出生后的第一件活動是吸吮母親的乳房,但這是生存本能。小男孩稍大仇視父親,愿意和母親呆在一起,因為他和母親有一種天然的臍帶式的聯系,母性使小孩得到溫飽和溫暖,使小孩有安全感。父親的存在使男孩有與母親分開的威脅,這種關系是一種天然的萌發。男孩長大后,這種潛在的壓抑會待機而發,最終形成類似于俄狄浦斯弒父棄母的報復行為。但人的心理不同于動物本能,在生物性本能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社會性的需求。男孩慢慢長大,道德、文化、習俗等都會對其逐漸完成重塑,使其脫離嬰兒或者幼兒狀態,成為“社會人”。俄狄浦斯情結將人退化到起初的動物狀態,“家庭和全部(無一例外)家庭關系(俄狄浦斯情結)的全盤性化”,[俄]巴赫金、B.H.沃洛希諾夫:《弗洛伊德主義批判》,張杰、樊錦鑫譯,中國文聯出版社,1987年,第51頁。藝術和哲學作品中的每一個字也都簡單地成為赤裸裸的性象征。阿瑞提對弗氏的批評一針見血,他說俄狄浦斯的悲劇“似乎是描繪了人類意識的局限性而不是俄狄浦斯與其母親的亂倫欲望。他的‘罪過實際上是不知道或沒有‘看到。他沒能充分觀察到周圍的許多跡象,其中有些是潛在的跡象。如果他知道了當然就不會這樣做了。”[美]阿瑞提:《創造的秘密》,錢崗南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7頁。德勒茲和瓜塔利的批評更為徹底,他們認為俄狄浦斯情結“武斷地認為欲望只是力比多情欲,被認為存在于父親—母親—兒子的三角結構關系中,從而割裂并掩蓋了欲望在社會語境下被壓抑的本質”,它“通過社會壓制和心理壓抑對欲望進行封鎖,從而掩蓋了欲望的革命性”,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he Althone Press, 1984, p.274.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幫兇。
其次是歷史的自然化。弗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一直被認為是他用驗證俄狄浦斯情結的代表作。他認為無論就人類還是個人而言,弒父都是一種顯著的原始的傾向,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被殺,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父親被殺,有著毋庸置疑的聯系——“男孩與他父親的關系,正如我們所說,是‘含混不清的。除了仇恨,力圖除卻作為情敵的父親,一定程度的柔情,通常也是存在的。心靈中這兩種態度的結合導致對父親的認同;小男孩希望坐到父親的位置上,因為他崇拜他,想要同他一樣,也因為他想要趕走父親。”④[奧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基礎叢書,1959年,第229-300、235頁。轉引自陸揚:《精神分析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45頁。《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弗氏用俄狄浦斯情結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由于仇父情結的壓抑,導致父親認同以超我的形式壓抑了下來,伺機待發,但從來沒有擺脫弒父意念的糾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描寫了19世紀下半葉舊俄外省地主卡拉瑪佐夫一家自農奴制度以后,一家父子、兄弟間因金錢和情欲引起的沖突,直至發生仇殺的悲劇,反映了當時俄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畸形關系,同時也提出了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等種種社會問題。弗氏完全將其歸結為俄狄浦斯情結,將歷史和小說簡單的自然化,顯然經不住推敲,但由此弗氏卻將俄狄普斯情結提煉為文學母題。他說:“很難說是由于巧合,所有時代文學中的三部經典——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都表現了同一題材——弒父。不僅如此,所有三部作品中,弒父的動機,對一個女人的性爭奪都展示得一清二楚。”④《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不難看出,弗氏認為藝術家的創作動機大多緣于他們埋藏在自身的父親壓迫和性欲沖動,而性欲的沖動似乎也成了人類邁向文明的動力。因而他認為《俄狄浦斯王》之所以引起我們靈魂的震顫,并非表現古希臘人對命運的頑強反抗,而是為了實現童年時代的愿望。
俄狄浦斯情結還有一個嚴重的局限就是闡釋缺少審美判斷。弗氏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經常矛盾、沖突和斗爭,無意識是混亂的、毫無理性的,其按照快樂至上的原則活動,雖受到社會道德的壓抑,但常常突破“自我”的閥門,成為人類精神的主要驅動。弗氏對《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瑪佐夫兄弟》的分析,都片面地從無意識的爆發和沖突來闡釋這三部偉大的作品,沒有了任何美學上的意義,只有本能發泄和與生俱來的原罪,一切文學藝術都是無意識的必然爆發和本能滿足。因而偉大的和渺小的,優秀的和拙劣的作品都被放在了一個維度上。他只片面的看作品表現了什么,只注意“性”這一生物本能,忽略作品在其他方面的的審美價值,作家的審美心理往往被簡單地看成性心理,所以西方有許多人批評精神分析缺乏最起碼的藝術價值觀和價值尺度,實際上“不外乎是精心謀劃的闡釋學體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闡釋理論。”[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8頁。馬林諾斯基以特洛布里恩特島為例,研究發現母系社會里母親及其家族有著重要的地位,而父親則處于弱勢處境,因而俄狄浦斯情結只能存在于父系社會,而不能在母系社會生根。埃里克·弗羅姆為等學者也支持馬林諾斯基的這一看法。弗羅姆通過分析《俄狄浦斯·雷克斯》《科羅納斯的俄狄浦斯》《安提戈》等認為,俄狄浦斯式境遇的關鍵沖突是男孩合法地反抗壓迫他的父親,這種沖突發生在父子之間,完全與母親及性無關。后來弗氏本人也承認,在理解偉大作家的創造性方面,精神分析是無能為力的。
作者單位:上海思博職業技術學院、國際商務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