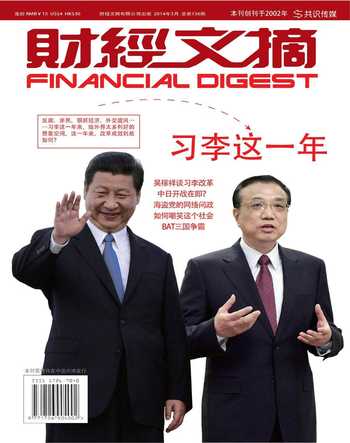唯有善待異端,政治才有可能現代化
人云

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總有一類人,為了捍衛自己的良知和信仰,竟敢于以弱微之力挑戰強權,最終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價。在茨威格的傳世著作中,這類人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異端。
應當說,在前現代社會,異端的結局注定是悲慘的。“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羨慕”,用這兩句話來總結異端者的志氣和命運是恰如其分的。正是這些層出不窮的異端者們,成就了一個不斷進化的人類文明,不管是在道德上,還是在制度上。
以中國歷史為例,每一個王朝都不乏異端,他們在朝則以行勸諫之舉,不配合乃至反抗強權,終落得陷入囹圄乃至人頭落地的下場,在野則著書立說挑戰當世統治權威,紛紛成為文字冤獄的受害者。眾多異端人物中,最悲慘的莫過于那個被誅了十族的明代儒臣方孝孺,他只因拒絕為發動“靖難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最終牽連親友870余人全部遇害。由是觀之,在皇權專制的古代中國,統治集團對待異端的手段是何等殘暴。
無獨有偶,西方文明在演進成現代文明以前,也出現了不少只忠于信念和良心的異端,他們的結局同樣是悲慘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一個在狂熱信仰時代,“蒼蠅撼大象”,憑借一己之力質疑乃至挑戰彼時的“先知”加爾文。可以想象,等待他的,除了有生之年的被監禁和有計劃的迫害之外,乃至在他死后的很多年里,他的著作幾乎不為人所知,因為對他的被審查一直被延續了長達幾個世紀之久。如果你對卡斯特利奧這個名字仍感陌生的話,那西方文明史上的另一個著名異端,后世公認的大智者哲學家蘇格拉底,應該再熟悉不過了吧,我想,他的命運就不必我贅述了吧。
政治異端者在當下中國的境遇
然而,在現代社會,對待異端的態度是判斷一國政體優良與否的基本標志。而且,每一個現代國家的成功轉型,都離不了異端者們的抗爭和努力。具體到政治層面,所謂異端者,指的就是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應當說,有執政者的地方,就會有持不同政見者;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至少有發表政治言論和組黨結社這兩大自由作為自己參與政治的保障,反之,在那些后發的轉型國家,政治領域的異端者,往往就不那么幸運了。
當下中國,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聲,然而,對于要改哪些,如何改,誰來改這些基本議題都未能達成共識。而對于由執政集團主導的這一輪改革,民間意見呈現出分歧態勢,有對新領導信心滿滿,看好改革者,亦有不贊同改革路線,唱衰改革者。而對于民間的不同看法,官方最高領導給出的回應是: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
在“兩條路都不走”這個原則的指示下,官方在行動上也采取了防范乃至限制主張“老路”和“邪路”的政治舉措。當下中國語境下的“老路”,說的無非就是毛氏極權路線,其最極端的主張,即全面否定改革,意欲回到“文革”時代。很長一段時間,“老路”擁躉者們云集在一個非常活躍的網絡平臺——烏有之鄉上,而今,這個平臺已被要求關閉,且沒有重新開放之勢。此一舉措,可以看作是執政者對持“老路”觀點者們的態度。
另一方面,主張走“邪路”,或者說在執政者看來是在走“邪路”的異端者們,同樣沒有因為官方主張全面改革而在政治上的待遇有所好轉,相反,對他們的高壓,相比此前,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新公民運動”的全軍覆沒即為明證,而且,這一次,因涉事者付出的代價是失去自由,而為國際主流輿論界所同情。
有論者分析,執政者走的是“用共富穩住底層、用改革穩住中層、拒絕左右綁架”的“第三條道路”,若確如此論,前述對待“老路”“邪路”的態度和舉措,也就不難理解了。
善待異端是政治現代化的前提
但是,這樣一條名曰排除左右干擾,實則唯我獨尊的全面改革,真的能實施下去嗎?能的話,又可以走多遠呢?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筆者很難表示樂觀。
一則,放眼寰宇,今日之世界,但凡政治運行良好的政體,無一不是包容多元的。在此背景下,一個排他性政府所代表的價值導向,很難稱得上是現代和普世的,它所主導的改革,無論是初衷還是最終目標,都是令人生疑乃至擔憂的。
再則,今天的改革,在政治上可以排斥主張走“老路”和“邪路”的異端,同樣,在將來的某一天,一旦執政者發現了其他可能危及其統治的“路線”,他們還是可能會以不能走“X路”的名義,打壓相應的政治主張和舉措,顯然,這不是民眾所想要的,即便其被冠以改革之名。
西諺有云,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取決于它對待弱者的態度,同樣,我們可以說,一國政府的現代化程度,取決于它對待異端的態度。僅就當下那些政治異端者們的遭遇而言,政治上的中國還不能算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而且,從那些已然轉型成功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善待異端是政治現代化和多元化的一個前提。
最后,我還是想以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一書序言的一句話結束這篇小文,“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尸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斗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