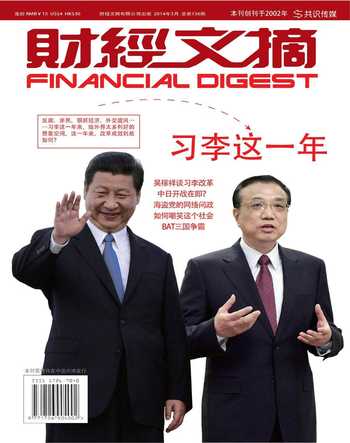中日開戰(zhàn)在即?
張菲菲


“戰(zhàn)爭不可能發(fā)生。”一戰(zhàn)前,諾曼·安吉爾寫了本暢銷書《大幻覺》,在書中,安吉爾認為西方各國的經濟嚴重依賴彼此,沖突無異于自取滅亡。
但修昔底德卻在闡述人類社會為何會走向戰(zhàn)爭時提出了三點原因——利益、榮耀和恐懼——這些在世界歷史中頗有市場,亞洲似乎也處于這樣的微妙階段。修昔底德有關戰(zhàn)爭爆發(fā)的所有因素在中日之間并不或缺。正如麥凱恩所說:“亞洲的緊張局勢具有另一個‘八月槍聲的意味。”(八月槍聲指一戰(zhàn)的爆發(fā))
“修昔底德陷阱”
“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zhàn)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zhàn)爭變得不可避免。”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解釋雅典和斯巴達戰(zhàn)爭為何不可避免時說:“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這也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中日最近似乎正深陷其中。
乍看,似乎確實如此。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日本經濟十年停滯不前,無論是中國對某些問題,如參拜靖國神社的忍耐度,還是日本的心態(tài),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曾經但凡引發(fā)兩國矛盾的問題,雙方政府都盡力保持克制,但2013年12月安倍的參拜卻讓中國幾乎窮盡所有能夠使用的外交手段,不僅有外交抗議、外交文宣戰(zhàn)、國際輿論戰(zhàn)——中國駐日、英、美等國以及駐歐盟的外交使節(jié)分別在所在國(區(qū)域)發(fā)表文章或者談話,外交部長王毅也連續(xù)與德、俄、韓、美、越外交首腦通話,希望在外交上孤立日本。
北京認為安倍的行為代表了日本政壇的集體右化和國策已經轉變。日本則毫無“反省”之意,正如安倍在2014新年致辭中所強調的要“恢復強大日本的戰(zhàn)斗才剛剛開始”,發(fā)誓要“全面恢復日本的地位”。
在中日對話大門關閉,以及毫無妥協的跡象下,在問及“日本和中國是否會開戰(zhàn)”時,日本首相安倍的回答更讓這一問題的答案開始清晰。
安倍說:“目前中日之間經濟相互依賴,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彼此有著重大共同利益,這同當時的英德一樣,但英德間的經濟關系并未阻止1914年大戰(zhàn)的爆發(fā)。”
經濟分道揚鑣,沖突前奏?
曾經有人指出,盡管中日之間有根深蒂固的分歧,但這并不要緊,因為存在“政冷經熱”的情況,但隨著兩國緊張局勢的加劇,中日兩大亞洲經濟體正在分道揚鑣。
2013年,中日貿易額同比下降5.1%,但中國的外貿總額則增長了7.6%。中日之間的投資也受到了重創(chuàng)。在2013年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增長5.3%的背景下,中國對日本的直接投資下降了23.5%。
日本對中國投資下降,有很多原因,如中國不斷上升的工資,但“政治緊張是主要原因”,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非所副主任宋志勇說:“中國政府把島嶼爭端看得非常重要,因此中國企業(yè)在對日投資前要考慮壓力和經營風險。”
中日經濟的變化不禁讓人想起塞繆爾·亨廷頓在他著名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的著名論斷:“高水平的經濟相互依賴可能導致和平,也可以導致戰(zhàn)爭,這取決于對未來貿易的預期。如果各國預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賴不會持續(xù),戰(zhàn)爭就可能出現。”
那么中日雙方預期的高水平相互依賴會繼續(xù)下去嗎?宋志勇說:“中國官員可能會加大利用經濟杠桿來實現地緣政治目標。”
2014年開春,日本向中國大陸團隊游客和自由行游客發(fā)放7.9萬與3萬張簽證,盡管這一數字是2013年同期的10倍,中國的有錢人也未必能緩解東亞緊張的政治局勢。當然,中國赴日游客的增多有助于緩解狀況,但在整個事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中,這并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外交政策》曾撰文《雙面亞洲:亞洲的精神分裂癥》說:“這是一個雙面亞洲,‘經濟亞洲朝氣蓬勃,協調一致,該區(qū)域內成員間的貿易額占其貿易總額的53%,高達19萬億的區(qū)域經濟總量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安全的亞洲,國家主義和民族統一主義傾向明顯的區(qū)域內各國彼此猜忌,小小的島礁和淺灘導致他們之間的領土紛爭逐步升級,并有不惜一戰(zhàn)的姿態(tài)。”
事實上,現在亞洲,經濟和安全已經不再游走于兩條平行線上,它們完完全全處在沖突的境地中。
為何中日之間經濟聯系削弱事關重大?有人說,“當經濟相互分開時,國家就會對對方的成功不感興趣”。但不幸的是,歷史告訴我們接下來可能會發(fā)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