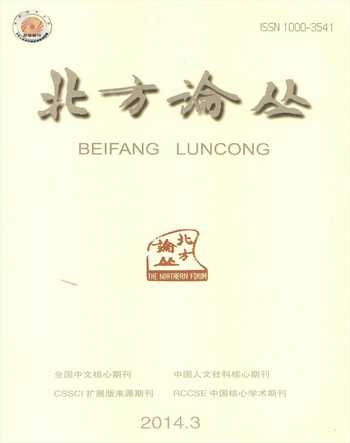溫麗深穩(wěn):歐陽修詩歌風(fēng)格與詩學(xué)沿革
馬驥葵
[摘要]學(xué)者們通常從風(fēng)格論層面詮釋歐詩的“溫麗深穩(wěn)”,其實“溫”、“麗”、“深”、“穩(wěn)”既能展現(xiàn)出歐陽修詩歌的主體審美風(fēng)格,也可指向歐陽修在詩美追求、詩藝方式與詩歌語言方面所做出的詩學(xué)沿革。欲求開創(chuàng)宋詩新風(fēng)的歐陽修沒有墨守成規(guī),卻能夠在革故鼎新中找到詩歌沿革的最佳契合點,開創(chuàng)了宋代文學(xué)的新體制、新格調(diào)。
[關(guān)鍵詞]歐陽修;溫麗深穩(wěn);詩風(fēng);沿革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3-0014-05
一代文宗歐陽修,作為北宋詩文革新的領(lǐng)袖,開創(chuàng)了宋代文學(xué)的新體制、新格調(diào)。他在詩歌理論上多有建樹,對宋代詩壇產(chǎn)生深遠影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獨辟蹊徑、大膽革新、別具特色、卓有成就。
一
李東陽指出:“歐陽永叔深于為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diào)為深。然核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墻藩籬之間耳。”[1](p1386)學(xué)界對于歐詩的詩學(xué)淵源多有論述。陳尚君先生評論歐陽修詩歌:“有直接標(biāo)明學(xué)習(xí)李白、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王建的,也曾受到杜詩、白詩、西昆詩的影響。”[2](p205)此論不謬。歐陽修對于前人與時人的詩作,尤其是唐詩能夠轉(zhuǎn)益多師、兼收并蓄,而在效法唐詩的同時,也能做到革故鼎新、承中有變。
古代學(xué)者對于歐陽修詩作的審美風(fēng)貌多有評述,見仁見智。《蔡百衲詩評》評歐陽修的詩風(fēng):“溫麗深穩(wěn)。”[3](p2518)學(xué)者們通常從風(fēng)格論層面詮釋歐詩的“溫麗深穩(wěn)”,認為其平易疏暢,同時亦有秀麗和精深的一面。筆者認為,以“溫麗深穩(wěn)”概括歐陽修的詩歌風(fēng)格與詩美取向,是很全面而準(zhǔn)確的。“溫”、“麗”、“深”、“穩(wěn)”既能展現(xiàn)出歐陽修詩歌的主體審美風(fēng)格,也可以指向歐陽修在詩美追求、詩藝方式與詩歌語言方面所做出的詩學(xué)沿革。四者共同構(gòu)成了歐陽修在詩歌發(fā)展史,以及中國詩學(xué)史上繼承、融合、開拓、創(chuàng)新的歷史地位,后者也促使歐陽修能夠在北宋詩壇踵武前賢、“新變代雄”。
歐陽修“詩窮而后工”、“意新語工”、“詩尚平淡”等,詩學(xué)理論引領(lǐng)了北宋詩歌革新的理論方向,開拓了詩歌題材的表現(xiàn)范圍,增強了宋詩語言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使宋詩增添了雄深雅健的筆力與雅正脫俗的格調(diào)。在詩歌革新方面,“以文為詩”、“以氣格為詩”、“以議論為詩”等,詩藝方式經(jīng)歐陽修的大力弘揚后一發(fā)而不可收,這也是對傳統(tǒng)詩歌句型規(guī)范的重構(gòu)與表現(xiàn)功能的解放。歐陽修的詩歌革新開啟一種新的詩歌語言形式,開拓了詩歌的表現(xiàn)功能;也使宋代詩人更崇尚詩歌思想之新、義理之妙,開啟宋詩尚意的發(fā)展道路。
歐陽修詩歌開辟出唐詩所不具備的宋詩新風(fēng),但宋詩發(fā)展至歐、梅、蘇為代表的仁宗朝時期,宋調(diào)并沒有完全確立。目前,學(xué)界認為,宋調(diào)的最終確立期應(yīng)屬于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所處的北宋后期。而歐陽修所處的仁宗朝詩歌應(yīng)屬于宋調(diào)的發(fā)軔期。宋仁宗朝詩壇主要取法唐詩開元和元和兩大高峰,并選取韓愈和杜甫作為詩壇的宗主。歐陽修及其領(lǐng)導(dǎo)的詩歌革新運動正是在廣泛繼承取法前人詩學(xué)遺產(chǎn)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符合時代精神的詩學(xué)審美追求,從而在詩學(xué)理論和詩歌創(chuàng)作上有所創(chuàng)建。
“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指出了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面對唐詩趨于定型的詩歌題材、詩歌意象與臻于純熟的詩歌語言、詩藝手法的一種窘境。歐陽修遍考前作不僅僅是為了繼承前人豐碩的詩學(xué)遺產(chǎn),更重要的是為了探尋前人詩學(xué)與創(chuàng)作進程中尚未經(jīng)行之處。劉克莊在《江西詩派序》中評宋初詩壇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guī)規(guī)晚唐格調(diào),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昆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shù),學(xué)者宗焉。”論詩歌成就與創(chuàng)新,梅堯臣其實并不亞于歐陽修。而劉克莊能給予歐陽修如此高的評價,恐怕也正源于歐陽修在詩歌理論與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對前人的廣泛吸收及大膽開辟。
二
具體就“溫麗深穩(wěn)”四個層面深入探究歐詩的特色,會對歐陽修在詩歌史與詩學(xué)史中的承傳與開拓有更深一層理解。
“溫”即溫雅古淡。
“溫”源自于歐陽修對王禹偁、范仲淹、梅堯臣等人平易溫婉、清雅疏暢和古淡精微詩風(fēng)的效仿,以及他們詩美理想的影響。王禹偁作為宋初詩文革新中對歐陽修影響最深的文人,其思想、人格、操守,以及“易道易曉”之文學(xué)主張、清新溫婉之詩風(fēng)都對歐陽修有一定的影響。王禹偁《答張扶書》一文主張:“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4](p358);歐陽修的《與石推官第一書》強調(diào),道應(yīng)“易知而可法”,言應(yīng)“易明而可行”[5](p.991)。王禹偁詩《酬種放征君一百韻》倡導(dǎo):“古澹啜铏羮,文雅鏗木鐸。”[6](卷三)而歐陽修在強調(diào)平易的基礎(chǔ)上,亦推崇自然流暢之風(fēng)格,從而將二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他在《與澠池徐宰第五書》中指出:“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jié)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7](p.2474)這一觀點既適用于歐陽修的散文創(chuàng)作,同時也可視做歐陽修的詩學(xué)審美取向。 梅堯臣作詩以平淡為其審美理想,他在《讀邵不疑學(xué)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中提出:“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8](p.845),在《依韻和晏相公》中又云:“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9](p.368)梅堯臣這一觀點影響了歐陽修。歐陽修在《送楊辟秀才》詩中,也標(biāo)舉自己崇尚平淡之詩美理想:“世好競辛咸,古味殊淡泊”[10](p.22),《讀張李二生文贈石》一詩云:“辭嚴(yán)意正質(zhì)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10](p.24)歐詩所標(biāo)舉之“古淡”、“淡泊”,是外表素樸而內(nèi)涵深刻之平淡。如蘇軾所謂:“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書唐氏六家書后》)葛立方云:“大抵欲造平淡,當(dāng)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11](p483)歐陽修崇尚的平淡實為絢爛至極而歸于平淡,豪華落盡而見真淳。歐陽修亦極其推賞梅詩之平淡素樸、寓意深遠之風(fēng)。他稱贊梅詩為:“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六一詩話》)梅堯臣是歐陽修人生中最親密的知己及詩文革新過程中的同伴和戰(zhàn)友。二人長期保持著詩歌唱和活動,在詩藝上爭奇斗巧,同時也相互仿效學(xué)習(xí)。錢基博指出,歐詩有“清煉似梅堯臣而原出郊島之寒瘦者”[12](p.516)。因此,歐詩古淡清煉之詩風(fēng)是從梅堯臣處效法而來。
“溫”還源自于歐陽修自身性格氣質(zhì)的塑造。在《鶴林玉露》中記載:
楊東山曾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并駕,作四六,便一洗昆體,圓活有理智,作《詩本義》,便能發(fā)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13](p264)。
這段論述一方面指出,歐陽修各種文體均善于向傳統(tǒng)學(xué)習(xí),以至“事事合體”;另一方面,也說明歐陽修“溫純雅正”、“藹然粹然”之人格特點對其文學(xué)風(fēng)格之形成有重要之塑造作用。惟其如此,其各種文體才能不蹈襲前人,從而自立面目。
“麗”即清新婉麗,源自歐詩對于西昆體與晚唐體有所選擇的吸收和借鑒。對于西昆體,歐陽修雖然反對后期西昆派辭采雕刻、內(nèi)容空洞之浮靡文風(fēng),但對西昆體并非一概排斥。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一文云:“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14](p.1045),還曾在《歸田錄》中稱贊西昆領(lǐng)袖:“真一代之文豪也”[15](p1923),“先朝楊劉風(fēng)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16](《與蔡君謨帖五》),劉克莊看到這句話也評價說:“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碑版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17](p22)歐陽修曾對西昆體和晚唐體進行比較:“楊大年與錢、劉數(shù)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以變。而老輩謂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xué)者之弊……蓋其雄文博學(xué),筆力有余,故無施而不可。”(《六一詩話》)可以說,歐陽修給予西昆體很高評價,而能將西昆末流與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體區(qū)別對待,也體現(xiàn)出歐陽修較為達觀的審美取向。西昆體對當(dāng)時流行的詩風(fēng)進行“滌腸換骨”改造,以淵深雅致之詩風(fēng)獨辟蹊徑,以致于“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18]。西昆體做為北宋詩歌革新的先行者,其詩歌史意義不容抹殺。西昆體所熔鑄的典雅雍容、才力縱橫、學(xué)養(yǎng)深厚、無施不可等審美趣味與藝術(shù)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后來宋調(diào)的基本要素。在歐陽修早期詩歌中的確能看到一些帶有西昆風(fēng)味的詩作,對仗整齊、工穩(wěn)妥帖、講究格律、清詞麗句,“工偶儷之文,故試于國學(xué)、南省,皆為天下第一”[19]。歐陽修后期的詩也能看到西昆體影響的痕跡,譚獻在《復(fù)堂日記》中曾評價歐陽修詩歌大體“清折高峻”,“集中西昆不少”。然而,西昆體學(xué)李商隱卻沒有吸收其精髓,只是借助李詩的某些技巧手段,以艷麗示富貴,以縝密求典雅,以故事逞才學(xué);卻忽視了義山詩秾麗中有沉郁,精警中有挺拔。歐陽修在《蘇氏文集序》中,對西昆一派提出批判:“學(xué)者務(wù)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夸尚”[20](p.613),正是反對西昆末流的“移此儷彼,以為浮薄”[21](《與荊南樂秀才書》)。簡而言之,宋初三體之弊都在于委頓卑弱而缺乏氣格。究其根源,西昆體典麗濃艷之風(fēng)不符合當(dāng)時的時代精神與詩學(xué)審美追求,終究會衰亡。歐陽修實質(zhì)上吸收了西昆體工致精麗之長,排除其饾饤雕琢之短;并用古體詩的氣格及以文為詩的方式矯正它,使北宋中期詩歌走上“尚意”、“尚健”之路。明人張綖《刊西昆詩集序》評價稱:“楊、劉諸公倡和《西昆集》,蓋學(xué)義山而過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優(yōu)游坦夷之辭矯而變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嘗不有取于昆體也。”[22]宋仁宗朝詩壇由于崇尚以氣格為詩、以議論為詩亦難免流于粗硬與直露,歐陽修便以溫潤婉麗之風(fēng)對其矯變。由此可知,昆體對于歐詩影響頗深,歐詩又對昆體承中有變。至于活動于太宗朝時期的晚唐體,以九僧、寇準(zhǔn)、林逋、魏野等為代表人物。由于學(xué)界對于“晚唐”、“晚唐詩人”、“晚唐體”的概念界定說法不一。因此,對于宋初晚唐體詩人的界定也有爭論。有學(xué)者認為,學(xué)習(xí)賈島、姚合五律的九僧才是真正的晚唐體,而學(xué)習(xí)杜牧、許渾七律七絕的林逋、寇準(zhǔn)不屬于晚唐體[23](p.95)。筆者對此暫取一個廣義的界定,將其界定為,宋初一些具有隱逸情調(diào)并展現(xiàn)出精雕苦吟之風(fēng)的詩作。筆者認為,晚唐體無論在當(dāng)時詩壇還是對歐陽修本人都沒有西昆體影響深遠,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也曾不屑于晚唐體的境界窘仄,但歐陽修曾稱許林逋及九僧的詩歌創(chuàng)作。由此可知,晚唐體精巧細致的手法與風(fēng)花雪月、清麗婉轉(zhuǎn)之風(fēng)對于歐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深”即精深透辟。這源自于歐陽修吸收韓孟詩派尚意、尚奇之詩學(xué)崇尚,以及學(xué)習(xí)韓愈詩歌“以氣格為詩”與“以才學(xué)為詩”所形成的揚厲暢盡、雄文健筆。歐陽修當(dāng)時即以“意新語工”作為自己的詩學(xué)審美目標(biāo):“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六一詩話》)這一詩學(xué)主張,其實就是追求詩歌內(nèi)容上能表現(xiàn)更多的現(xiàn)實生活的新意,詩歌立意上不受前人束縛;并且要求詩歌語言精確生動、自然流暢。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歐詩學(xué)習(xí)韓愈、李白、杜甫等人,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之手段,從而形成其“深入無淺意”之詩歌特點。歐陽修學(xué)習(xí)韓愈詩歌并非亦步亦趨,亦有取舍和改造。筆者認為,歐詩從韓詩處師法所得的最關(guān)鍵要素,即“以文為詩”與“專主氣格”兩點。這兩點賦予歐詩命意深、格調(diào)高的特質(zhì)。歐陽修目的在于,以贍博的學(xué)問和高明的見識去糾正晚唐五代以來的淺薄和卑俗。歐陽修的以文為詩與韓愈不同,大都是為取得意思連貫暢達的效果,歐詩中議論又常常帶情韻以行,是其散文創(chuàng)作的“六一風(fēng)神”在詩歌中的體現(xiàn)。歐詩能夠出于韓詩而不囿于韓詩之處在于,韓詩注重的是表現(xiàn)才力、宣泄情感,而歐詩則注重流暢平易、挖掘事理。歐詩中不但體現(xiàn)出其獨有的雍容平和、雅致流暢之風(fēng),而且還展露出雄深雅健的筆力和理性思致的光芒。歐陽修在詩歌表現(xiàn)形式上大膽開拓、勇于創(chuàng)新,注重詩歌命意造語上的意新語工、思深理妙,但同時歐詩又崇尚詩歌語言的平易暢達。在語言風(fēng)格方面,韓愈為文崇尚生新出奇,他主張:“惟陳言之務(wù)去,戛戛乎其難哉”(《答李翊書》),而歐陽修則崇尚平易自然之風(fēng),主張:“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24](p.139)歐陽修詩歌中常常滲透著一種平和淡遠、雋永深沉的內(nèi)在意蘊。歐詩形成他特有的紆徐婉轉(zhuǎn)、曉暢明達、透辟新警、深入淺出的風(fēng)格特點。惟其如此,歐詩才能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棄韓詩之奇險拗峭,而以平易疏暢之風(fēng)自立面目。筆者認為,宋詩自西昆體后,詩歌創(chuàng)作更加重視技巧,格律精嚴(yán),崇尚以才學(xué)為詩,注重議論說理,書卷氣便越來越濃。歐陽修在詩歌題材內(nèi)容與詩藝方式上,“求深”是為了矯正宋初詩壇淺俗卑弱之風(fēng)氣,因此,他批判地繼承西昆體 “尚雅”、“尚學(xué)”的審美取向,同時以平易暢達之風(fēng)矯正西昆后進過于崇雅而至晦澀之弊。“深”是歐陽修對于杜甫、韓愈等詩人“以才學(xué)為詩”、“以氣格為詩”的繼承與發(fā)展,也代表著影響有宋一代詩壇的“尚意”、“尚健”的詩學(xué)觀。后者是歐詩連接北宋詩歌新變派與王安石詩歌的關(guān)鍵要素,對于之后王安石詩歌的思深理妙、健拔奇崛之風(fēng)的形成,以及宋調(diào)的確立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穩(wěn)”即工穩(wěn)流暢。這源自于對孟郊、賈島、白居易等人詩歌藝術(shù)及詩學(xué)理念的學(xué)習(xí)和借鑒。歐陽修很推賞孟郊、賈島的詩歌,在其詩文及詩話中亦多次論及。歐陽修還曾效仿孟郊作《刑部看竹效孟郊體》。孟郊、賈島都是以“苦吟”、“推敲”著稱的詩人,對此,歐陽修在文中論述說:“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然二子名稱高于當(dāng)世,其余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tài)見于數(shù)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邪”[25](《試筆·郊島詩窮》)。
歐陽修提倡詩歌的構(gòu)思精嚴(yán),同時亦不反對詩歌的推敲琢磨。孟郊、賈島詩歌創(chuàng)作向來講求格律,工整妥帖。歐陽修從中多有效仿。《六一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倍嘗之,不能道此句也。”歐陽修贊賞郊、島詩歌能夠細微地刻畫現(xiàn)實生活中的情思和感受。歐詩中也能貫徹此原則,感情濃郁真摯,體會真切自然;并且歐詩還學(xué)習(xí)孟郊、賈島詩歌用字穩(wěn)實、對仗工穩(wěn)、組織工致。歐陽修還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構(gòu)思精嚴(yán)、推敲詞語,但不能刻意雕琢,以至于語義晦澀。他在《與樂秀才第一書》一文中指出:“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26](p.1023)只有做到音韻鏗鏘、鍛煉無痕、流暢自然才能稱為“語工”。此外,白居易對于歐詩的影響往往為大家所忽略。其實,歐陽修平易詩風(fēng)、寫實精神及其理性趣味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對“元和體”白居易詩學(xué)理念與詩歌藝術(shù)的效法和開拓。歐陽修平易疏暢的基本詩風(fēng)的形成與元和體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劉寧云:“元和體的入實趣味經(jīng)歐陽修的點化,化平淺直白而為內(nèi)涵獨特的‘平易,也為宋詩審美風(fēng)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27](p.383)歐陽修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去虛浮而切實情,注重詩歌的現(xiàn)實意義與諷諭作用,從而形成了歐詩穩(wěn)實暢達、重意思理之風(fēng)。他在《書梅圣俞稿后》中,稱賞梅堯臣詩歌:“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fēng)物,英華雅正,變態(tài)百出”[14](p.1048),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28](吳充《歐陽公行狀》)。這源自于歐陽修借鑒白居易“為時為事”而做的詩學(xué)審美追求。歐陽修的這一詩學(xué)理念對于宋代講求征實、注重事理的詩學(xué)理論潮流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高舉詩文革新大旗的歐陽修并不僅僅局限于對前人詩歌傳統(tǒng)的吸收與借鑒,也在不斷地探索和開辟有宋一代新風(fēng),在沿襲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于他開拓了元和體的寫實趣味。
三
縱觀北宋詩壇,從真宗朝的王禹偁到楊億,以及與真仁之交的晏殊,再到仁宗朝的歐陽修、梅堯臣,最終于北宋后期的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這幾位詩人為北宋詩歌的革新與流變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在北宋詩歌發(fā)展史上也自然占據(jù)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王禹偁《答張扶書》一文倡導(dǎo)“傳道而明心”的文學(xué)主張[4](p357)。在詩歌革新方面改變白體的淺俗空洞之風(fēng),開拓詩歌題材,開始創(chuàng)作反映現(xiàn)實、憂國憂民之作,詩風(fēng)平易警秀。楊億在詩歌革新中倡導(dǎo):“富于才調(diào),兼及雅麗,包蘊密致,演繹平暢”[29](p435),矯正白體之缺乏藝術(shù)性、淺俗直露,提倡注重音韻、對仗、典故、辭采的富贍典麗的西昆詩風(fēng)。作為西昆體與詩歌新變派之間的過渡人物晏殊雖繼承西昆體的富貴氣象與華麗語言,但較少使用典故,追求語言的自然含蓄。歐陽修、梅堯臣則對晏殊詩歌有所揚棄,矯西昆體之尚學(xué)尚雅為尚意尚健、崇尚思理之詩美取向,以平易暢達代替富麗精工的審美崇尚。蘇軾文中曾引歐陽修語云:“我所謂文,必與道俱”[30](p.1956);梅堯臣倡導(dǎo):“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9](p.336),內(nèi)容上變歌功頌德為諷諭時政,進一步開拓詩歌題材和體裁,增強詩歌表現(xiàn)功能。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則更加注重格律精研、命意構(gòu)思與詩法技巧,更注重翻新出奇、議論說理和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最終促成了宋調(diào)的確立。
歐陽修在中國詩歌史上的意義,前人多有論述。其論點大體上都是據(jù)于歐陽修作為文壇盟主提攜培養(yǎng)出許多后起之秀,并組織聚合了一個有大量詩歌唱和活動的詩人群體,以及他對北宋詩文革新所做出的歷史貢獻兩個方面。關(guān)于歐陽修的詩文革新成就,元人袁桷在《書鮑仲華詩后》中做出一個客觀的評價:
宋太宗、真宗時,學(xué)詩者病晚唐萎苶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飾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思流蕩,奪于援據(jù),學(xué)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巨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厲,摩云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fēng)》之旨,則蔑有余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31]。
北宋詩歌新變派部分吸取西昆體“尚學(xué)”、“尚雅”之詩學(xué)觀及一些優(yōu)秀的詩歌特質(zhì),并用“以氣格為詩”、“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方式予以矯正,使北宋中期詩歌走上“尚意”、“尚健”之路。歐陽修、梅堯臣二人的“意新語工”說,拈出 “意”、“語”二字,即代表著北宋詩壇詩學(xué)追求與審美取向的轉(zhuǎn)變。這種“尚意”、“尚健”的詩學(xué)審美理想展現(xiàn)出一種尚氣格、講理智的宋調(diào)之風(fēng),它顯然有別于盛唐詩歌興象玲瓏、情景交融的審美取向。由此必然引發(fā)宋詩全新的詩歌語言與藝術(shù)范式,引導(dǎo)宋詩逐漸走上“詩言志而平淡”之路。當(dāng)然,北宋詩歌新變派 “尚意”、“尚健”的詩學(xué)追求,對宋詩也產(chǎn)生一些消極影響:為矯正宋初三體,詩歌新變派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盡量避免唐詩充分使用意象及表現(xiàn)情韻的成功經(jīng)驗,亦有些矯枉過正。由于片面追求古體和古淡,過分崇尚“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歐陽修也曾遭致批評;由于片面追求“出新出奇”,過分崇尚“以意為詩”、“以俗為雅”,這也使其陷入“險怪”、“奇峭”及“以丑為美”的怪圈之中。
歐陽修、梅堯臣提出“意新語工”一說,看似是對之前詩歌復(fù)古理論某種程度的自我否定,實則是在“尚理性與尚情韻”、“尚載道與尚筆力”之間的一種平衡。欲求開創(chuàng)宋詩新格調(diào)的歐陽修既沒有墨守成規(guī),也沒有一味求變,而是在革故鼎新的過程中,逐漸找到詩歌沿革的最佳契合點。“意新語工”也可以看做對詩壇“以文為詩”、放筆恣肆創(chuàng)作傾向的一種補充與矯枉,一味地追求散體化和議論化的暢盡揚厲,亦會使詩歌喪失興象玲瓏的意境與含蓄雋永的韻味。因此,歐陽修和梅堯臣強調(diào)“意”應(yīng)含而不露,提出:“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雖然歐、梅二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并未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這一詩學(xué)審美追求,對北宋中后期崇尚韻味與氣韻的詩學(xué)追求有深遠影響。宋仁宗朝詩壇最終在“緣情與言志”、“載道與筆力”、“雅正與通俗”、“承繼與新變”的種種矛盾對立中實現(xiàn)統(tǒng)一,從而使宋仁宗朝詩壇既保留唐音,也實現(xiàn)宋調(diào)的發(fā)軔。
綜上所述,歐陽修在詩史上的意義在于傳承與開拓與宋調(diào)發(fā)軔所作出的貢獻。歐陽修詩歌轉(zhuǎn)益多師、眾體兼?zhèn)洹τ谠妼W(xué)沿革所作出的努力實乃歐陽修于宋詩的最大貢獻。在宋初三朝,王禹偁、楊億等人的詩作已經(jīng)顯露出一些宋詩新風(fēng),在宋仁宗朝儒學(xué)復(fù)興運動、古文運動與政治改革高漲的時代背景下,歐陽修敏銳地洞察到北宋詩壇革新的發(fā)展趨勢,他既對前人的詩學(xué)遺產(chǎn)有所繼承和揚棄,同時也建立了“抑情尚理”、“詩道合一”的詩學(xué)審美追求,確立了宋詩平易暢達的審美風(fēng)格和“意新語工”的藝術(shù)精神,領(lǐng)北宋詩歌革新的發(fā)展方向。歐陽修開創(chuàng)了宋詩新風(fēng),并為這一全新的藝術(shù)范式構(gòu)建了大體的輪廓與框架。
[參考文獻]
[1]李東陽.麓堂詩話[C]//歷代詩話續(xù)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2]陳尚君.歐陽修與北宋詩文革新的成功[C]//研究生論文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3]蔡絳.西清詩話[C]//吳文治宋詩話全編[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4]王禹偁.答張扶書[C]//全宋文:卷一四六[M]成都:巴蜀書社,1993
[5]歐陽修全集:卷六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2001.
[6]王禹偁.小畜集:卷三[C]//四部叢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5.
[7]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8]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歐陽修全集: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1]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C]//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錢基博.中國文學(xué)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3.
[13]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丙編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4]歐陽修全集:卷七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5]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六[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6]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7]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8]田況.儒林公議[C]//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邵博.邵氏聞見錄:卷一五[C]//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0]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1]歐陽修全集:卷四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2]西昆酬唱集:附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3]趙齊平.宋詩臆說[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
[24]歐陽修全集:卷九[M].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25]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三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6]歐陽修全集:卷七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7]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2.
[28]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三[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9]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0]蘇軾文集:卷六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5.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講師,黑龍江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
[責(zé)任編輯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