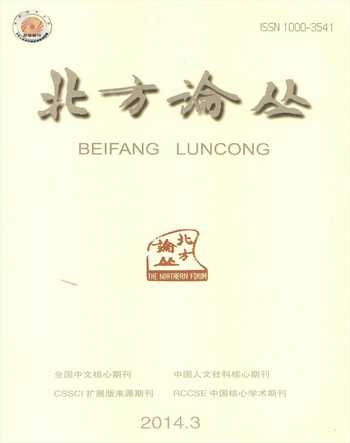曹學佺與萬歷丁酉科舉案關系考論
孫文秀
[摘要]晚明詩壇著名詩人曹學佺因卷入萬歷丁酉科舉案而仕途受挫,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關于曹學佺坐丁酉科舉案被貶謫一事,《萬歷野獲編》等文獻著錄時有牴牾,通過考察曹學佺與丁酉科舉案主要人物之間的關系,考辨丁酉科舉案相關事件及文獻的真偽情實,試圖再現晚明士人生存狀態之一隅。
[關鍵詞]曹學佺;丁酉科舉案;張位;張蔚然
[中圖分類號]K2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3-0079-04
Abstract: Cao Xuequan,a famous poet in late Ming Dynasy,was frustrated at his official career because he was involved in Ding-You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in Wan-Li period. It had been a major influence on his literary creation. There is a contradictory record of that Cao Xuequan was frustrated because of Ding-You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in WAN-LI WILD WAS COMPILED etc.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Cao Xuequan and people associated with Ding-You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to research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vents and literature ,related to Ding-You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and to reveal the severe condi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Cao Xuequan; Ding-You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Zhang wei; Zhang Weiran
曹學佺既是晚明詩壇著名的學者和詩人,也是明末閩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曹氏22歲即捷試春宮,才名揚于京師。但正值春風得意之際,卻因卷入丁酉科舉案被貶謫,成為其一生仕途生涯及文學活動的重要轉折。不過,關于曹氏與萬歷丁酉科舉案的關系究竟如何,后世文獻著錄時有牴牾,但目前學界尚未作厘定辨析。
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京察中,曹學佺坐丁酉科舉案被貶謫,后世載錄較詳細的文獻主要有二:其一,曹學佺之子曹孟善所撰《明殉節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雁澤先府君行述》一文;其二,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五相關記載。現分別摘錄如下,以備辨析:
戊戌,新建張公被逐歸,踉蹌走出通灣,一物不備,門人故吏莫敢往視。宮保公適為倉曹,追送舟次,為庀輿馬、糗糧甚悉。公視曰:“何相報之篤也?”未幾,臺省以銜公不已,遷怒于宮保公,指摘丁酉科分考所取場卷為險怪不經,調南京添注大理寺左寺正[1](《曹學佺集》后附錄)。
丁酉順天(今京津地位)二主考,獨焦漪園竑被議,攻之者惟二、三科臣,皆次揆張新建客也。焦以進《養正圖記》,為新建所痛恨,而郭明龍以宮寮為皇長子講官,亦深嫉之。焦既出闈,即以所撰圖說具疏呈御覽,其時禍本已成矣。監生吳應鴻、生員鄭棻先被斥,而曹蕃、張蔚然等數人則重罰,以待覆試分考,行人何崇業、主事費寫本、費作、曹學佺等調南京,焦亦調外任[2](卷十五,《鄉試借題攻擊》)。
上述引文中的“新建張公”,即指曾擔任內閣首輔大臣的張位。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曹學佺參加京師會試,張位正是當年主考官,二人為座師與門生關系。上述兩段引文,前者有相關細節陳述,后者則側重概述科舉案始末脈絡,但二者無疑都揭示了曹學佺受丁酉科舉案牽連,被貶謫南京的史實。細讀這兩段文字,則會得出兩種相反的結論:根據曹孟善的記錄,曹學佺是張位異黨以丁酉科舉案為借口進行排斥、打擊的,可以說,曹氏是因為和張位走得過近受到牽連,應屬于張位一黨;但根據沈德符的說法,曹學佺和焦竑、何崇業等人一系,是被張位、郭正域等借丁酉科舉案進行的對象,所以,曹氏應屬于焦竑一派。兩種文獻的記載到底哪一種更符合事實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弄清丁酉科舉案的來龍去脈,以及曹學佺在這場科舉案中的實際處境等問題。
萬歷丁酉二十五年(1597年)順天府會試,會試結束發榜第二天,擔任副主考官的焦竑及分考官何崇業等人,便受到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及楊廷蘭等人的彈劾。彈劾的主要理由之一即是:此次錄取的舉子試卷中多險誕語,即曹孟善行述文所提到的“險怪不經”之意。隨后焦竑、何崇業上疏力辯,理據頗為充分,但最后仍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責罰。同時被彈劾的舉子或被永久取消會試資格,或勒令以后重考。萬斯同《明史》卷三八五《焦竑傳》記載了此次科案的一些具體細節:
會二十五年順天鄉試,所司以考官名上,神宗特度次用竑,于是諸不獲者亦弗悅,北榜發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都下遂有浮言,而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即據以入告。咸至詆竑為莽、操、懿、溫,且及其它事。竑疏辨言:“科場故事,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今所摘多正考中允全天敘所取,臣不待辨章。”并下所司,竟黜二人,永停二人會試,余悉停科,俟再試,謫竑福寧州同知,房考何崇業等亦被謫,而置天敘不問,一時物論頗不平 [3](卷三百八五)。
丁酉科舉案從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十月,項應祥、曹大咸等人上疏彈劾開始,到同年十二月禮部作出結論,其間圍繞的主題都是張位黨人與焦竑、房崇業等人之間的政治爭斗。根據前文所引曹孟善和沈德符的記載,曹學佺也是丁酉科會試的分考官之一,但參閱現存和此案有關文獻,我們發現,無論是項應祥等人的彈劾疏文,還是焦竑等人的申辯疏文,以及禮部最后頒發的責罰公告,全部未提及曹學佺名字 關于和丁酉科舉案相關的疏文,可參閱《萬歷邸鈔》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卷十二月所收錄疏文。。另外,在曹孟善的行述文和曹學佺本人的詩文作品中,記載曹學佺被貶謫南京的時間為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春天,此時丁酉科舉案已經結案,在此案中行動最為積極的曹大咸、楊廷蘭等人,亦皆坐張位黨被逐,而張位本人也已被罷相歸田。種種跡象都表明,在這場科舉案中,曹學佺既不屬于焦竑一派,亦非張位黨成員,而是和當時的主考官全天敘處境一樣,被置于“不問”的行列。
那么,既然被置于“不問”的行列,為什么兩年之后又被張位異黨以此案為借口加以排擠呢?曹學佺與張位黨派的關系究竟如何?他與此次科舉案無法脫離干系的關鍵證據又是什么呢?對于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曹學佺與科舉案所牽涉及的主要人物之間的關系,尋求答案。
被牽涉進丁酉科案的主要人物,我們可將其概括劃分為三列:一列為張位黨派,一列為焦竑等被彈劾的考官,第三列則是被張位黨人拿來作為證據的考試舉子們。前兩列人物分別可以以張位和焦竑為代表,因為二者才是此次科舉案中對陣角力的關鍵人物。
首先,考察曹學佺與張位之間的關系。曹、張二人最早相識應始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京師會試。關于當年會試及師生第一次見面具體情形,曹孟善在為曹學佺所做的行述文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
宮保公會詩卷分在歷城。董公時為職方司郎中,公薦之主考新建張公、任邱劉公。二公亟以是卷當冠場,置之座右。而同考諸公謂:“部署房中元,久無此例。”主司方在遲疑,有一房公從旁語曰:“此卷洵有元局,但似科深之人,恐不雅觀。”張公提筆頷之曰:“君言是也。”遂于卷面一字加豎,為第十名。及發榜庭謁,張公遽彈指曰:“誤矣,誤矣,因與房師訂館選當以見畀。”乃未修私覿之禮,遂弗踐其言焉[1](《曹學佺集》后附錄)。
“董公”指董其昌,當年歷城分考場的主考官;“任邱劉公”,則指與張位一同擔任主考的吏部侍郎劉元震。根據上述引文可知,曹學佺在會試時分到歷城考場,其考卷最先得到分考場主考董其昌的賞識,然后將其推薦給主考官張位與劉元震。曹學佺與董其昌的相識,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考察,最早應該開始于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曹學佺抵達京師之時。曹學佺在準備參加會試之前,與當時云集京師的海內名士如蕭云舉、湯顯祖、袁宗道、袁宏道等人,多有交游論學,他的才華也正是在這一階段得到大家的認可,被譽為“歸太仆(有光)后身”,并預言其能金科奪魁[1](《曹學佺集》后附錄)。董其昌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在京師與蕭云舉、湯顯祖、袁宏道等人于京師第二次結社,談禪論學。雖然沒有文獻資料證明曹學佺曾參加過他們的禪社活動,但從二者交游人物有頗多重合的情況推斷,董其昌應該知曉曹學佺其人。董其昌在會試時特地將曹學佺的考卷推薦給張位,似乎也透露出二者之間惺惺相惜的意味。不過張位雖然也對曹學佺頗為賞譽,且流露出將其定為狀元的想法,但在其他考官干涉等因素影響下,最終還是將其降格錄為第十名。
張位初見曹學佺,連呼“誤矣!誤矣!”此種言行,一方面說明曹、張二人在此之前確實并不相識;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曹學佺的才華與風貌確有過人之處。假如才華可以從之前董其昌所推薦的試卷中體察出來,那么初次見面時令張位贊嘆的,則更多可能是緣于其外在的神采風貌了。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對當年乙未科才士進行了品評,其中提及曹學佺云:“閩人曹尊生(曹學佺字,筆者注)戶部,總角登鄉書,再試成進士,以末甲守部,久住燕都,幾如衛叔寶看殺。”此條文獻根據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補修本的沈德符之《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二“乙未諸才士”條所載。中華書局1959年、1979年及2004年刊印的《萬歷野獲編》,雖然也是根據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為底本刊印,但卻未見收錄“乙未諸才士”條內容。被喻為魏晉時最美的男子“衛叔寶”,可見曹學佺之風神秀逸不凡,非一般人可比。此等才華與風貌俱佳的青年才俊,單純從選拔人才方面來講,假如被錄為會試科元,倒也名副其實。但曹學佺最終沒能成為狀元,而且連張位曾承諾過得入館選一事也落空。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曹學佺并沒能真正得到張位或其他閣臣們的舉薦和提攜,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五之“讀卷官取狀元”條,記載的乙未科取狀元及館選等事宜,當年和曹學佺同科狀元朱之蕃,即是由當時的工部右侍郎沈思孝所取。沈思孝與張位等內閣大臣皆為同年,彼此相厚善,因此,朱之藩便順利成為狀元,進入館選,正所謂“從來非相公屬意,則本房分考力薦,未有外寮得與者”[4](卷十五《讀卷官取狀元》)。此事正可以說明,張位并未把曹學佺作為自己派系成員提攜和栽培的意向。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曹學佺授戶部主事,后改任潞河倉曹一職。從其被分配的職務看,時任內閣大學士、加進吏部尚書的張位應該也沒有特別關照。
此外,曹學佺在這一時期成集的《潞河集》及《掛劍篇》,師友唱和往來的題材占了很大比例,卻唯獨未見與張位有關任何信息。這說明踏入仕途之后,曹學佺與張位之間關系仍然是比較疏離的。雖然后來曹學佺也有兩首和張位唱和的詩即《桃花嶺次韻奉呈相公座師二首》,是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游歷江西時所作,此時張位已經被罷相閑居江西5年。但這兩首詩中未述及師生交往狀況,我們很難據此得出二者的關系比居京師期間更為密切的結論來。
以上種種信息提醒我們,曹學佺居京師期間,和張位內閣的關系應該是較為疏離的。但因為二者之間畢竟還存在一層座師與門生的關系,所以,我們可以將其定位為游離在張位內閣邊緣地帶的人物。如果僅僅是因為與張位之間的師生關系,在當時還不太激烈的黨爭中,倒也不至于即被歸入張黨一系。曹學佺被他人視為張位黨,主要原因還在于張位被罷相之后,對其表現出極大的同情,而且還“追送舟次,為庀輿馬、糗糧甚悉”。張位居內閣期間,由于積極爭取和擴大內閣權限,不但與六部同僚關系緊張,最終也引起了神宗皇帝的反感。張位被罷相離京之時,昔日門生同僚皆莫敢往視,曹學佺偏偏就是在這樣的時局下獨自出頭為張位送行,以致令張位深感愧疚,感嘆“何相報之篤也”。曹氏此舉或許僅僅是為了尊師重道曹學佺素來尊師重道,萬歷二十四(1596年)年身在京師的曹學佺聞少時恩師“周明府”卒于南浦,當即疾馳歸閩,又從閩中以素車白馬,不遠千里赴江西金溪,哭吊于恩師墓前。具體詳情可參閱曹學佺《挽周先生明府》《祭周明府先生文》等文獻記載。,但卻最容易引起張位異黨和神宗帝反感,最終被歸入張位黨一系不足為怪。
既然不屬于張位黨派,那么是否即可將其視為焦竑一系呢?翻檢曹、焦二人這一時期作品,并未發現任何交游信息。二人相交是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即雙方被貶謫至南京的那段時間,因文學雅集活動而往來頻繁。另外,在丁酉科舉案件中,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曹學佺對焦竑進行彈劾或辯護的任何文獻記載。由此可以推測,在科舉案發生之時,曹學佺與焦竑的關系狀態應是相對疏離的。
既然曹學佺與張、焦兩大陣營的關系都比較疏離,如果沒有確鑿證據,后來坐張位黨受到貶謫就可能承擔了莫須有的罪名。那么,令其被牽涉進此場科舉案無法脫身的關鍵證據又是什么呢?有必要關注曹學佺與科舉案中牽涉的第三列人物的關系。
根據項應祥和曹大咸的疏文,被提出作為試卷“險怪不經”例證的舉子一共有9位:曹蕃、吳應鴻、張蔚然、鄭棻、汪泗論、丘夢周、趙士麒、鄭宏才、趙名言。9位舉子的資料在后世文獻中記載并不多,有的只是在這場科案中被提到過萬歷丁酉科舉案被彈劾的舉子詳情,可參見《萬歷邸鈔》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卷十月《禮科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各糾發科場大弊》與同年十二月收錄的相關疏文。。考察曹學佺與位舉子之間的關系,發現只有張蔚然一人與曹學佺來往較為密切。張蔚然博涉多聞,精于易理,曾以程朱道學,與當時黃汝亨、沈守正齊名,著有《易義分編》《三百篇聲譜》等經學著作。其論詩也較為通達,著有詩話《西園詩麈》一卷,頗受時人首肯1922年李楁的《杭州府志》卷一百八中有“張蔚然,仁和人,漢陽通判,丁未丙辰。”同書卷一百九又載:“張蔚然,丁未丙辰會試副榜。”這里記載張蔚然為丁未丙辰榜進士,實際上是張蔚然在因丁酉科舉案受到責罰后,又重新參加科舉考試所取得的功名。。
在曹學佺官居京師期間成集的《潞河集》中,有記載與友人雅集之詩《季春望日,集于鮑莊,載游言別,悲喜并焉,爰述長篇以紀其事。在席者:吳允兆、周叔宗、張去華、黎慎之、張孟奇、阮太沖、陳道源、馮女金、吳陽居、張維誠、王種民、張克鳴、邱伯幾也》[5](卷十七),此次參加集會的人員名單中即提到了張蔚然。另,曹學佺同鄉友人董應舉《長溪張侯德政碑記》一文中曾提到:“張公維誠,令長溪三年,士民大歡,條其德政三十一事于石……吾于戊戌歲見侯文字于曹能始之邸,知其有立也。”[6](卷十三)“戊戌歲”,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此時丁酉科舉案剛剛落幕。根據董應舉記載可知,曹學佺與張蔚然在丁酉科舉案發生前后的那段時間,已經有詩文來往,可視二者為文字交。丁酉科舉案之后,兩人也一直保持較密切的聯系,張蔚然在為曹學佺晚年所編纂的《五經困學》作序文,又自稱門人弟子,可見二人后來是亦師亦友的關系。
在現存和丁酉科舉案相關的文獻中,并沒有記載曹學佺和張蔚然有何種關聯。但仔細翻檢曹學佺本人作品可發現,其62歲時所作《靖藩長史長溪郭公墓志銘》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公之縣父母師為武林張維成。維成固不佞萬歷丁酉歲畿闈所取士也,說者以為衣缽相承云。”[7](卷三)這篇墓志銘是曹學佺為福建長溪郭姓友人所作。張蔚然在重新參加科舉取得功名后,曾擔任過三年長溪縣令,所以,曹學佺在文中稱張蔚然是郭姓友人的“縣父母”。根據這則材料,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丁酉科舉案中被彈劾的舉子張蔚然,實際上正是由曹學佺所錄取。這也從一個側面也更加坐實了焦竑被冤枉和打擊的歷史事實。錄取張蔚然一事,便成為曹學佺與丁酉科舉案無法脫離干系的關鍵證據。所以,在丁酉科舉案結案兩年之后,張位異黨才會又以此案為借口,將其貶謫至南京。
通過上述考察可知,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對曹學佺因丁酉科舉案受到貶謫一事的記錄,在一些細節上不夠準確的。曹學佺與當時處在權力中心的張位、焦竑等人保持疏離狀態,可能是緣于其剛直孤傲的學者秉性,又或者僅僅是一種初入官場的生存策略,但最終還是卷入黨爭的漩渦。丁酉科舉案發生的當年,曹學佺由于并非黨爭的中心人物而僥幸逃過一劫,但在案件結束兩年之后又因此事被貶謫,則具有了幾分在劫難逃的意味。晚明變幻莫測的政治黨派爭斗,令置置身其中的人如履薄冰,像丁酉科舉案中焦竑等人是屬于被刻意冤枉的,但像曹學佺則只是無意卷入而又無法逃脫的無辜犧牲品而已。
詩人不幸詩家幸,曹學佺從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被貶謫至南京,冗官南京近十年。在此期間,曹學佺歷覽金陵名勝,廣交游于金陵的文人俊士,同時組建了金陵詩社,宴游雅集,賓朋過從,將主要精力用于結社倡和,著書立文,成為金陵詩壇的核心人物。一時間,金陵文壇“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最終形成了有明一代,聲名遠播的“金陵之極盛”的文壇繁榮局面[8](丁集“李臨淮言恭”條附“金陵社集諸詩人”)。
[參考文獻]
[1]曹學佺.曹學佺集[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3]萬斯同.明史[M].清鈔本.
[4]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5]曹學佺.潞河集[M].清乾隆十九年曹岱華刻本.
[6]董應舉.崇相集.明崇禎刻本.
[7]曹學佺.西峰六二文[M].明崇禎刻本.
[8]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作者系復旦大學博士后)
[責任編輯張曉校]